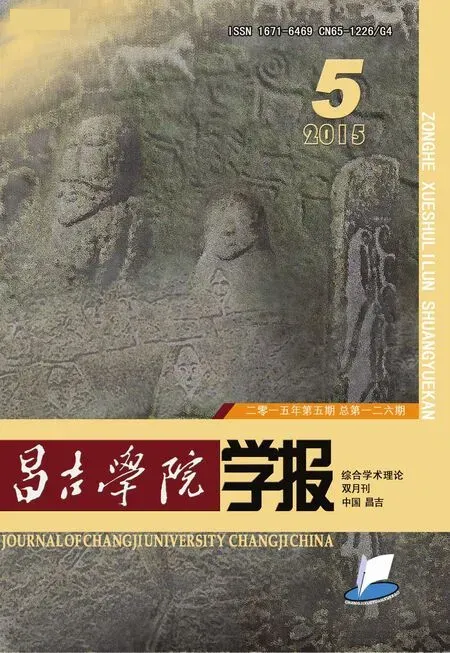地下室的“瘋癲與文明”——對理性之反抗
易儷儷 袁上草
(1.重慶師范大學 重慶 401331;2.四川大學 四川 成都 610011)
在《瘋癲與文明》前言中的第一段,福柯引用了兩個人的話:
帕斯卡說過:“人類必然會瘋癲到這種地步,即不瘋癲也只是另一種形式的瘋癲。”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記》中寫道:“人們不能用禁閉自己的鄰人來確認自己的神智健全。”
福柯這部著作論述了瘋癲與文明的對立置換關系,“瘋狂不是一種自然現象,而是一種文明產物。沒有把這種現象說成瘋狂并加以迫害的各種文化的歷史,就不會有瘋狂的歷史。”[1]同樣,通過分析《地下室手記》的復調特征,我們可以發現地下人所體現出的“瘋癲”及其與文明的對抗。以往對于《地下室手記》的研究分析多集中在其民族特質、地下人的形象分析、理性、生命意志等方面,筆者在對文本的復調特征進行分析時發現其復調特征下的思想對話所體現出來的反抗才是地下人最急切想要表達的聲音。
一、瘋癲表象——“過多的意識就是一種病”
巴赫金認為,復調型小說的實質就在于“小說中有著眾多的各自獨立而不相融合的聲音和意識,他們有機地交錯在一起,彼此平等地相互討論、爭辯,構成眾聲喧嘩的景觀”。[2]復調的這種對話性首先體現在話語的對話上。話語的對話關系有兩層含義,一是指話語在有具體的指稱的情況下時與他人的對話;二是指即使在獨白情況下,話語依然是以聽者在場為假設,以獲得回答為目的的對話性話語。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復調小說中,話語的對話關系將注意力集中在雙方思想的交流之中,它被理解為“他人涵義立場的標志、他人表述的代表”。[3]復調小說中的人物傾向于客體化,語言的藝術功能減弱,人物自我意識和邏輯關系體現為話語,成為不同的人物主體在話語中表達、表述出來的涵義立場。
《地下室手記》中,“地下人”自白部分的開頭便是同他人“隱性辯論”的對話關系,這是在對他人的預料的基礎之上形成的。“你們是否覺得,我現在似乎是在向你們懺悔,在請求你們寬恕呢?……我相信,你們肯定是這樣想的。……然而,我要告訴你們即使你們這樣想,我也無所謂。”[4]小說的文體整個就確定在了他人話語的強烈影響之下,但是主人公對這些他人觀點、他人評價采取漠視態度,因為他必須由自己來掌握終極話語。地下人在獨白中破壞自己的形象,不斷地打破和否定,目的在于擺脫他人意識的控制,即使是將自己比作耗子、惡人,也要成為自己的主人。在這種踐踏自己在他人心中形象的努力中,我們看到了主人公竭力想要證明自己、定義自己而又拒絕給自己下定義的矛盾沖突,他無法接受他人的控制,也無法接受由于長期的文明浸染而形成的自我定義,只好一直以辯論、斗爭和否定來證明自己的存在。這與理性一直追求的肯定與清晰相違背,甚至被認為是一個瘋人的自言自語,然而在這瘋瘋癲癲的話語中,我們一直堅信的理性受到質疑,我們開始思考地下人在表象上看起來的“瘋癲”是否才是更加真實的理性。
盡管地下人一直在否定中界定自己,但有一點是地下人反復強調的:“我是一個有病的人。”這并不是指生理上的疾病,而是指擁有“過多的意識”本身就是一種病。“過度的意識感”是地下人的主要特征之一,保持理性和做一些與理性違背卻是自由意志使他分裂出的兩個部分。這里的意識感不單是指對于世界的思維和探索,也包括關于自我的思考。由于大多數人按照傳統既定的理性方式生活,地下人選擇的反抗在具有理性的人看來就是“有病”。大多數人習慣做合乎理智的事情,但地下人意識到,意志的自由比理性選擇所代表的利益更吸引人。理性和非理性因素在地下人的身上交織,他舉出了“牙疼”的例子來說明這一矛盾的心理,無病呻吟對自己和他人都沒有好處,但他仍然堅持著這樣做,并將其作為一種樂趣。在因為牙疼而呻吟的過程中,最初的渴望憐憫變為了對他人的嘲弄和對自己的侮辱。“對于你們,我現在已經不是我過去想扮演的那樣是個英雄了,我不過是個可惡而又討嫌的人,是個無賴。”[5]這番話與其說是針對他人,不如說是針對他自己。他自由的意志對于自己理性部分的惡意促使他做出有違最大利益的行為,這種行為是故意無恥的,不過也是極度痛苦的。地下人在“故意丑陋”的文體中想要辯論的不僅是其他人,不僅是那些能聽到他無病呻吟的人,也是自己思維的對象,即世界及其制度。“在他的每一種關于它們的思想中,都有聲音、評價、觀點的斗爭。在所有這一切中,他首先感受到的是他人意志,它預先決定了他。”[6]他的思維是受到世界秩序的欺凌的,世界的惰性和盲目性所決定的他人思維影響著他。因此,他必須與之激烈的抨擊、斗爭,跟這個世界辯論,才可以避免被同化,在這種矛盾的斗爭中保持自身的獨立性。
二、狂歡世界——“廉價的幸福”或“崇高的痛苦”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中還根據西方民間的狂歡節活動提出了狂歡化理論,活躍在復調小說中的思想對話與人物情節相結合,通常都會出現狂歡化的場景。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被巴赫金歸為狂歡化路線的延續,即“嚴肅—笑謔”領域的發展。“嚴肅—笑謔”體裁指一種狂歡式的民間創作,是“對一切嚴肅的、正統的觀念事物進行強烈的諷刺”。[7]在“嚴肅—笑謔”領域中又出現了不同的變體,使文學的狂歡化更為多樣、具體,如蘇格拉底對話和梅尼普斯諷刺。蘇格拉底對話是指“真理以及人們關于真理的思考在本質上是對話的。”[8]在這個概念上形成了蘇格拉底對話的兩個基本手法,對照和激發,即將思維對話化,使它外化并變成回答。這也就決定了主人公必須是思想者,而事件本身也必須是探索和考驗真理的純粹的思想事件。人物被置身于一個排除外界干擾類似真空的環境之中,迫使他們進行自我思維的深度挖掘。思想不再只是人物的附屬部分,而是與人物緊密、有機地結合起來。通過這些特點可以斷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正是延續了這一變體。但是關于具體的體裁特點和情節結構安排,則需要追及到另一種變體,即梅尼普斯諷刺(以下簡稱梅體)。梅體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奧林匹斯圣山、冥界和人間。在奧林匹斯圣山充滿著自由的狎昵、丑聞和怪誕,到了冥界則形成了徹底的狂歡化,一切的等級秩序都不存在,死亡廢除了一切加冕,至于人間則加以自然主義的描寫,除了丑聞和狎昵交往,還出現了不對等婚姻、喬裝、騙局等等。
在貧民窟自然主義的描寫之中,總是會出現與之格格不入的形象和特質,形成尖銳的對照,在急遽的過渡和交替中構成各種不對等婚姻,比如具有充分意識的“地下人”,比如圣人與妓女的組合。社會地位低下的人卻是思想最深刻的人,同時他又不可避免地周期性前往妓院以暫時忘卻內心激烈的矛盾斗爭。在妓院和麗莎的談話之中,地下人找到了自尊感,在一個妓女面前自覺到在人格上的崇高感。正如他在第一部分的獨白中幻想的一樣,他變身成為一個圣人,將人間的美好施舍給可憐的妓女。當地點轉移到“地下人”的房子里,身份突然倒置了,“地下人”成為了那個乞求的妓女,麗莎因為她純潔的心成為了圣人。愈是感受到這一點,“地下人”愈加覺得自己受到了羞辱,而這羞辱又照例是他自己給自己強加上去的。“地下人”和妓女的交往是在充斥著丑聞與怪誕的氛圍中產生的,“地下人”受到了同伴的侮辱后為了報仇才追到妓院,但他內心是希望找不到他們,因為他明白這不過會是又一次的受辱。在愿望成真后,他抱著“死里逃生的快樂”選擇了一個姑娘,兩個陌生的人置身于狎昵的交往之中,從日常的規范中逃脫出來。“地下人”本來打算用繪聲繪色的演說去打動以便嘲弄她,顯示出自己道德上的優越感,可是他自己也陷入了圈套之中,他把自己的惡意剝落,顯示了善良、慷慨的一面。在他營造出來的圣人的氛圍里,他和麗莎的不對等婚姻得到凈化,擺脫了人間的丑陋,進入奧林匹斯圣山的自由狎昵之中。
狂歡節上有一項重要的活動——丑角國王的加冕與廢黜——丑角被捧上王位,地位最低下的人充當世間最高權威代表,世界的秩序受到扭曲。在至高權威的轉換下,人們也脫離日常規范,在破壞中進行創造。加冕與廢黜是一個動態的交替過程,在這種注定要死亡的新生中孕育著狂歡的快感。丑角國王的廢黜也并不意味著秩序的恢復,而是再一次的轉換與破壞。在狂歡世界中沒有絕對的權威和肯定,只有在不斷否定之中發展起來的交替與變換。
地下人的第一次加冕與廢黜是在巴黎飯店的聚會上,但是他并沒有得到狂歡國王的權力,他像國王一樣表現,居高臨下,卻仍被視為丑角,加冕尚未得到承認便被廢黜。第二次加冕是在妓院,雖然觀眾只有麗莎一個人,但是他的權力得到承認,有人心甘情愿屈服于他。可是等到他離開妓院回到家里,他的權力就消失了,甚至對于他雇傭的仆人也無計可施。他在等待麗莎的過程中既有一股無名火和想要侮辱她的破壞欲,又升起甜蜜的幻想想要挽救她。在他的矛盾狀態中,麗莎帶來了他的廢黜。在麗莎純潔美好的心靈面前,他的圣人形象破滅了,他不再是那個高高在上的國王,而是重新恢復了地下人的身份,甚至比他以前更為惡劣。在加冕—廢黜中,狂歡形象會在不同程度上模擬著自己并進行諷刺,他在死亡與復活的交替中否定自己,“主人公在他的雙重化身上死去,達到凈化并超越自身”[9]地下人在這連續兩次的加冕與廢黜中不斷地否定自己,讓自己死亡以求復活。在趕走麗莎后,地下人給自己提了一個問題,“什么更好——廉價的幸福好呢,還是崇高的痛苦好?你說,什么更好?”[10]這暗示著地下人永遠不會走出他的地下室,只有在地下室里,他才能持續他“崇高的痛苦”。地下人的未完成性是無出路的,他終究無法與自己融合成為一個統一的、獨白的聲音,因此他也無法完全地否定對方,只能把這種意向推進“內在的無窮性”。
三、地下人的反抗——無出路的未完成性
由于主人公希望打碎強加在自己身上的桎梏,擺脫他人話語對他的定義,他就必須為自己“造反”。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建立一種“新的看待人的完整觀念”[11],即揭示“人身上的人”。這種新的創作形式只能建立在人物具有充分自我意識的情況下,“人身上的人”即是指人物在設定好的、已經終結了的形象之上所具有的表達的自由。這種自由顯示出了人物對于使他表面化的、從背面下的定義之中擺脫的意志,他通過思想意識、自由行為等表現出他的未完成性,關于他自己的終極話語不在作者手中,也不是在敘述者手中,也不是在文本中其他人物的手中,而是在他自己的掌握之中。在反復的自我思想對話中,地下人身上的理性與非理性的對抗也體現出來。只有在這種對話中,地下人才能實現他的反抗。
在和社會主義者的論辯之中,“二二得四”是他們一直在尋求的一座永遠摧毀不了的水晶宮,象征著永恒的理性王國。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認為理性能夠代表人的全部精神和生命,在他的眼里,意志的任性是生命的重點所在,正是這種任性“為我們保存了最珍貴最緊要的東西——我們的人格,我們的個性”[12]。不管何種程度的舒適和幸福都不能夠滿足人們對于自由意志的需求,意志的自由和任性也正是對于自身存在的肯定,“確切地說,他真正保存的東西正是他虛妄的夢,是他那些最愚蠢的想法,一邊向自己證明——好像真的有必要似的——人終究是人而不是鋼琴鍵”[13]。我們也可以將其理解為對于不斷重復著的世界的否定,人們遵循著生活的軌跡不斷經歷著昨天,一切都已完成,剩下的只有重復。“地下人”先是以自己生活的地下室否定了虛構的水晶宮大廈,言之鑿鑿,可是在下一章中又全盤否定,說他連自己的一句話都不信,說這些都是連續四十年貼在門縫上偷聽來的。在外形式上,主人公越過敘述者和作者直接與讀者對話,與讀者討論這些獨白的真實性,擺脫了作者對他的掌控。在內形式上,“地下人”又以不斷地否定和辯論將自己的形象打碎,讀者不再能看到一個完整的客體形象,只能夠聽到一個聲音,這個聲音,通過隱藏自己的形體更加突顯出自我意識,將作者趕出場外,迫使讀者與自己交流、對話。同時,在對話的過程中打破固有的定義,在否定中重塑自身,在內部重生,“把任何使他們表面化和完成化的定義變成一種謊言”[14]。只要他還存在著自我意識,可以自由選擇,他就沒有被完成,就還沒有說出他的“終極話語”。
看似瘋癲與丑陋的自言自語實則是對所謂文明的一種破壞,均衡穩靜不再作為一種標準,這個心靈能夠自覺它的每一個弱點,并決定去揭發它。我們所聽到的“個性之歌”是可悲的和叛逆的,但無論它給人何等不幸,卻仍然是最高的善。地下人的過多的意識是他對于自我和世界的再思考,這種強烈的自我表現在遇到理性所展示出來的安適時,更是用“任性”來對抗“理性”,只因這是生命意志的表白。無論是話語的對話性,還是狂歡化的特質,《地下室手記》所體現出來的復調特征也同樣充滿反抗性。兩次加冕與廢黜帶來的激情使地下人得以復活,但是他的意志會讓他不得不選擇“崇高的痛苦”,使他能夠繼續對抗這個理性的世界。這種對抗是無出路的,但也不會消失,是未完成的,因而地下人能夠在其無出路的未完成性中得以向內無限延伸。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思想與存在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是存在主義是讓我們在自我的選擇中尋找意義,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則“向我們提供了一個世界”[15],他要的不是選擇,他將我們內心狀態的不安、焦躁展露無遺,地下人所反叛的只是代表著主流的理性思考。地下人所表達的只是“反抗”。這種故意的任性是對于世界原有秩序的強烈抗議,也是對于自我的重新思考。《地下室手記》的反抗,是地下人執拗地待在地下室中,是他對自己的故意為難,是他貼在門上的偷聽,也是他對麗莎的侮辱。地下人選擇的非理性不一定是好的,但是面對理性的強大攻勢,他清楚地知道,必須要反抗。
[1](法)福柯.瘋癲與文明[M].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三聯書店.2013:1
[2][3][4][6][7][8][11][14](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M].劉虎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
[5][10][13](俄)陀思妥耶夫斯基.雙重人格 地下室手記[M].臧仲倫譯.北京:譯林出版社,2004.
[9][12]謝·阿·尼科爾斯基.張百春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地下室人”現象[J].俄羅斯文藝,2011,(03).
[15](美)考夫曼.存在主義:從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沙特[M].陳鼓應,孟祥森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