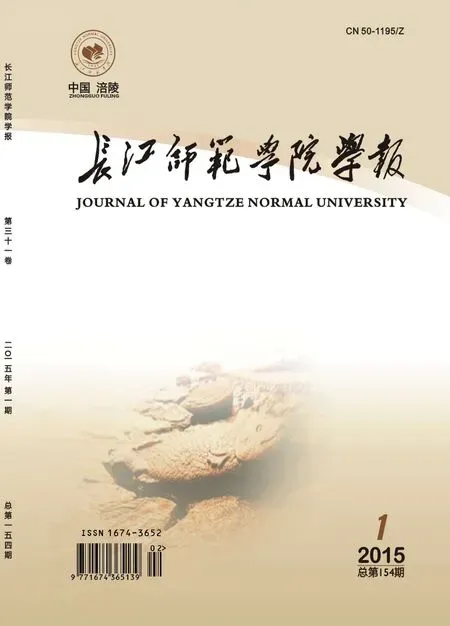現代語境下布依族婚姻儀禮的變遷——一個布依族村寨的實例
現代語境下布依族婚姻儀禮的變遷——一個布依族村寨的實例
龔德全
(貴州民族大學西南儺文化研究院,貴州貴陽550025)
[摘要]布依族婚姻文化作為布依族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之一,其變遷是一個不斷推進的過程,從傳統社會語境到現代語境的轉換,消解了布依族傳統婚姻文化的某些因子,卻楔入了新的民俗事象,并最終導致了傳統婚姻文化意蘊的變遷,這里主要以一個布依族村寨的實例闡明了這一點。新的民俗事象的大量涌現是民眾應對社會文化變遷而進行的不斷調適的結果,是民眾轉移和釋放社會變遷壓力的一種有效途徑。隨著社會文化變遷的進一步加劇,民眾將會不斷地調適自己的行為和觀念,從而創造出更多“新”的文化表達方式。
[關鍵詞]現代語境;布依族;婚姻儀禮;社會變遷;文化調適
[中圖分類號]K892.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3652(2015)01-0033-05
[收稿日期]2014-09-17
[作者簡介]龔德全,男,貴州貴陽人,博士,副研究員,主要從事民俗文化研究。
婚姻禮俗作為一種典型的民俗傳承事象,因其在民眾日常生活和構建社會網絡中的重要作用,備受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等相關學科的關注。作為民族文化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的婚姻文化,它內蘊著一個民族深厚的歷史積淀與文化意蘊。通過梳理該民族婚姻儀禮的傳承與演變,我們可以透析其變遷背后的社會動因及民眾的文化調適行為。陶立璠曾指出:“中國少數民族的婚前儀禮豐富多彩。從擇偶到成婚,有許多獨特的講究。它充分表現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生活習俗的差異。”[1] 284這提示我們對于婚姻儀禮的研究要充分注意不同民族的差異性以及民眾婚姻實踐的區域性特征。這里即沿此思路,通過一個布依族村寨的實例,探討在現代語境下布依族婚姻儀禮變遷的相關問題。
一、傳統社會語境:布依族婚姻的締結
關于傳統社會布依族婚姻文化的研究,學者們已經取得了很多的研究成果。如汛河編著的《布依族風俗志》[2];黃義仁、韋廉舟編撰的《布依族民俗志》[3];王偉等編著的《布依族》[4]等,在這些著作中都有對布依族婚姻禮俗的描述。此外,還有許多學者發表過不少的相關論文,對布依族婚姻文化進行了多維度的探討①此類研究,如:龔佩華、史繼宗,《布依族婚姻試析》,《貴州民族研究》,1981年3期;陸新紀,《布依族婚姻研究中有關問題商榷》,《貴州民族研究》,1981年4期;韋廉舟,《布依族與漢族的嫁娶禮儀》,《南風》,1982年2期;楊昌儒,《淺談布依族“浪哨”習俗》,《黔南民族》,1991年1期;楊昌儒,《論布依族“浪哨”文化的演進》,《貴州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年增刊;陳玉平,《浪哨:從社交、娛樂到自由擇偶》,《貴州世居民族研究》(第2卷),貴州民族出版社,2005年;陳玉平,《論布依族“浪哨”與婚姻的關系》,《貴州世居民族研究》(第3卷),貴州民族出版社,2006年。。
與其他民族婚姻的禮俗相類似,布依族人的婚姻締結在不同歷史時期以及不同地區具有不同的形式與特點。在布依族早期的傳統婚姻制度中,自由擇偶的方式比較普遍。在《大明一統志》中有“男女自婚”的記載,指的就是自由擇偶。它主要是在布依族青年男女平時趕場或節日集會時,通過“浪哨”(布依語稱nanghsaul,主要形式是對唱情歌)等社交活動而結識相愛。當然,“浪哨首先是布依族青年男女的社交、娛樂活動,只有深層次的浪哨才進入戀愛的境界。”[5] 312在布依族社會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浪哨擇偶都是一種具有極強生命力的婚姻締結方式。其實,浪哨擇偶這種富有特色的習俗在南方其他少
數民族中也很常見,只不過“叫法”不同罷了。如壯族的“趕歌墟”、瑤族的“耍歌堂”、侗族的“行歌坐月”、水族的“玩月”等都是和布依族“浪哨”擇偶相類似的民俗活動。雖然浪哨擇偶凸顯出了自主性特征,但在現實生活中,要想完成最后的婚姻締結過程,一般也要經過父母的同意。父母在擇偶決策中擁有很大的權威,如果得不到家庭的肯定與支持,婚姻締結也是難以成功的。因此在許多布依族地區都有“戀愛自由,結婚不自由”的說法。
除“浪哨”擇偶習俗外,由于受到中原漢族婚姻禮制的影響,在布依族傳統社會中,也有憑媒說合的聘娶婚形式。如清乾隆《獨山州志》載:“聘資用牛只,或一二只,或三五只,每牛掛角銀二兩。”[6]苗蠻《黔南識略》亦載:“荔波方村等地,娶必求姑之女,名曰要回,其聘禮或以牛,或以銀。”[7]卷十一這些記載都反映出在當時的布依族社會中對以聘而娶的婚姻禮俗的遵行。這種憑媒說合的聘娶婚,可能事先經由當事人同意,但在更多的情況下是由父母包辦的,即婚姻大事完全是父母作主,而當事人在擇偶決策中的地位卻受到相當的壓制,往往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布依族聘娶婚的程序依地區的不同而有所變化,但一般都有提親、訂親、要八字①要八字,指男家邀請一個小孩將女方的生辰八字帶回男家,男家則請人據此擇定結婚日期,并告知女家;有的布依族地區將“訂親”與“要八字”這兩個儀式合并在一起來舉行。、迎親等環節,與漢族傳統社會中的“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大致相同。不同之處在于,布依族在舉行婚禮后,女方還有不落夫家(也稱“緩落夫家”,delayed transfer marriage)的習俗。這一習俗也出現在苗瑤、壯侗等語族的其他南方少數民族中。
雖然憑媒說合的聘娶婚在廣大布依族地區逐漸地被視為正統,但是布依族古老的“浪哨”擇偶習俗卻從未就此湮滅,相反卻出現了“浪哨”擇偶與憑媒說合兩種婚姻形式并置的情形。但這兩種方式本身就內隱著矛盾與沖突:一方面是當事人自主的決策;另一方面是父母的決策獨斷。因此,在布依族的傳統社會中,就出現了因為不滿于父母包辦婚姻而逃婚的情況。一般為女子單方面逃婚至相愛的男子家里,待生育后才回來認親;也有個別因為逃不出封建枷鎖而被迫殉情的婚姻悲劇發生。但是,這樣的情況并不具有普遍性意義。在現實生活中,更為普遍的情形是將兩種方式加以協調而復合。先是青年男女通過“浪哨”自主擇偶,而后由父母按照聘娶的程序為其操辦婚事,即“經過浪哨—聘娶—舉行婚禮—女子不落夫家—雙方共同生活這樣的成婚成家過程。”[8] 316此種模式因其自身的優點而逐漸地成為布依族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締婚方式。
通過對布依族婚姻儀禮形式與特點的歸納與梳理,我們可看到布依族婚姻儀禮既具有本民族自己的特色,又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融入了其他民族的多種文化因素,但在其多種締婚形式中,“浪哨”與“不落夫家”是布依族婚姻禮俗中最富有特色的標志性習俗,它體現出與漢族婚姻禮俗迥異的特點。但是,上述這些禮俗都是布依族傳統社會中民眾所普遍遵行的婚姻實踐,而在當下實際的田野調查中,其實已經很少能夠見到這些傳統的婚姻禮俗了。婚姻文化本身是一個歷史范疇,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地發生變化,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布依族社會的文化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而造成其婚姻文化的形式與內涵發生了諸多的變異,且此種變異的速度遠遠地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故民眾有關婚姻儀禮的文化實踐也必將對此做出相應的“調適”(adaptation)。關于這一點,在以往的研究中常常被忽視,下面我們將以一個布依族村寨——翁村為實例,借以闡明布依族傳統婚姻儀禮在當代的變遷問題。
二、布依族傳統婚戀模式的變異:滿月酒與婚禮合一
翁村是貴州省長順縣擺塘鄉的一個布依族村寨。從地理環境上說,這里距離縣城較遠,地理位置比較偏僻。加之,這里群山環抱,山高坡陡,使得民眾出行多有不便。這種“邊緣”的地域性特征直接地造成了歷史上翁村人的交往范圍狹窄,因而其婚嫁流動也大多是在近距離范圍內進行。據我們調查,在整個翁村的300多戶人家中,20世紀80年代以前僅有4樁婚姻的通婚半徑延展至長順縣城,其余全部是在本村及其鄰近的幾個寨子。由此可見,在附近村寨內擇偶是傳統翁村人最為流行的婚嫁空間模式;而婚戀模式則為“浪哨”擇偶與憑媒說合并置,且家長與媒人在擇偶決策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20世紀80年代前,翁村的交通、社會和經濟條件尚無明顯的改善,當地民眾傳統的婚嫁習俗也基
本上沒有太大的改變。但最近30多年來,即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以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翁村交通條件的改善以及外出打工人數的增多,翁村布依族傳統的婚嫁空間模式以及婚戀模式則發生了諸多的變異,具體表現為:青年人工作地、居住地的延伸直接地導致了婚姻圈的擴大與擇偶途徑的多元化,突破了以往時代地緣、血緣、姻緣關系的范圍,這反映出“每一次新社會關系的出現,都被民眾自覺地整合到擇偶途徑中。”[9] 116目前,翁村人的婚嫁空間范圍已從原來集中在本村及鄰近村寨,擴展至貴州長順縣城、羅甸縣以及云南省。相應地,其擇偶方式也由“封閉式擇偶”發展為“開放式擇偶”[10] 285。此外,個體在擇偶決策的地位升高,多為男女雙方自主相識、自由戀愛,這就使得傳統媒人角色的作用日漸式微,父母的絕對權威亦受到挑戰。而傳統的“浪哨”擇偶習俗,也因大部分青年已不會唱“浪哨”歌而名存實亡;“不落夫家”的習俗更是早已不復存在;傳統聘娶婚的婚禮程序也大為簡化,有的甚至連婚禮都取消了,待男女雙方生子后,再將滿月酒與婚禮同時舉辦。近5年來,此種形式在翁村大量出現,表明其已成為一種很重要且很普遍的締婚方式。因此,這種文化現象的背后動因及文化意蘊很值得我們深入探究。
2013年10月28-30日,我們在翁村參加了一次滿月酒與婚禮合一的儀式。此次儀式的男主人CZM是翁村布依族男青年,在5年前離開家鄉去長順縣城打工,在此期間結識了縣城的漢族女孩HBY,兩人情投意合,決定完婚,但這門婚事卻遭到女孩家人的強烈反對。無奈之下,兩人一同回到翁村CZM家中,共同生活,但一直沒有舉行婚禮。在居住1年后,兩人生下一對雙胞胎男孩。此時,女方家里才對這門親事認可,于是男方家才將婚禮與“滿月酒”儀式合并在一起舉行。
雖然女方“逃婚”的現象在布依族傳統社會中也曾發生過,但畢竟數量極少,而且與本個案中的社會背景也完全不一樣。前者是為反對父母的包辦婚姻而進行的一種反抗,后者卻并不存在此種情況,而是由于女方父母不同意其嫁到農村,在多次協商無效的情況下,女子才決然地私奔到男家。當然,“私奔僅僅是表示當事者兩人相互的同意,在結婚手續上不能稱為完備。”[11] 104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在此個案中,“合一”儀式的舉行是由于女方父母的強烈反對而造成的,多少帶有“被迫”的意味,但即使是在女方家庭沒有反對的情形下,采用此種模式的也不在少數。據我們對翁村年輕人近5年婚姻狀況的統計,“合一”儀式的舉辦已占到了三分之一左右的比例。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像CZM與HBY的這種不經媒聘、不舉行婚禮、自相結合、待生子后將婚禮與滿月酒同時舉辦的締婚模式已帶有一定的普遍性意義,而且這種因為青年外出打工結識對象而成就的“自主婚”會逐漸地形成為一種“群體效應”,翁村的其他年輕人有可能紛紛效仿而采用此種模式。因此可以預見,隨著翁村封閉狀態進一步被打破,開放程度進一步加強,將會有更多的年輕人采取此種模式,完成婚姻的締結過程。
通過對本個案的進一步解析,我們發現:儀式主體在這樣一個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的婚禮中,主要在于實現三個目的。其一,促成男女雙方家庭重新確認姻親關系。如前所述,由于女方家里不同意此門婚事,HBY才在無奈的情形下來到CZM家。在此情境下,CZM家如果舉行婚禮,HBY家里也不會有人來參加。在翁村,男方家舉行婚禮,如果沒有娘家人參加,男方家將會受到村里其他人的負面評價,從而造成男方家在該社區網絡中地位的下降。所以,男方家也就不再舉行婚禮。同時,這也意味著兩家的姻親關系處于一種“隔斷”的狀態。但是,CZM與HBY有了小孩,這成為一個轉折點。在這種事實婚姻的情況下,女方家出于女兒在男方家未來地位的考慮,也就出席了這場象征意義遠大于實際意義的婚禮,這就在客觀上促成并確認、維系了兩家的姻親關系。其二,儀式主體(CZM與HBY)在公共場域下,通過展演的方式完成了人生角色的轉換,即向整個社區公開地強調了自己的已婚情形與為人父母的狀態。新成員的加入與新生命的誕生,必然會對社區內部原有的社會關系以及社區平衡造成破壞。因此,作為通過儀禮變異形態的“二合一”儀式的功能仍然在于“整合社會狀態的過渡帶來的無序和不穩定”[12] 11。同時,它也消解了處于“閾限”(liminal)階段的當事人的焦慮心理狀態。其三,舉行這樣一場具有象征意義的儀式,也是為了幫助儀式主體構建與延展自己在翁村的社區網絡,尤其是親屬網絡。我們知道,翁村具有鄉土社會的諸多特征,是以姻親、血緣關系為基礎而構建的地方社會網絡。因此,在這樣一種“熟人社會”中,對于一個新組建的家庭來說,構建社區網絡是至為重要的,它將成為新組建家庭日后生存的平臺。同時,它也為其提供了行動的基本框架。
由此可見,雖然“二合一”(滿月酒與婚禮合一)的儀式脫出了布依族傳統的婚禮儀式行為,但是它仍然實現了傳統婚姻儀禮的功能,即構建姻親關系、轉換主體的社會角色、重構社會網絡等。但是,二者所內蘊的文化意蘊卻有著顯著的區別,而且“二合一”儀式行為帶有強烈的功利性與目的性色彩,隱喻了當地村民對傳統儀禮文化意義的“另類”理解。
據我們調查,面對此種與布依族傳統婚禮相背離的儀式,當地人也認為它偏離了布依族傳統的道德規范與價值觀念,侵蝕了建立和維持婚姻關系的民間習慣,但是他們也表示出了寬容與接受的態度。這說明,在社會急劇變遷的情況下,民眾對傳統儀禮模式信仰的減弱與民俗規范的松弛,社區內部已經失去了強有力的民間傳統。
作為一種在翁村布依族社會中大量存在的婚戀模式,滿月酒與婚禮合一的儀式處處體現出“反傳統”的特征:媒人的作用被消解;家庭的權威被挑戰,個體的作用被高揚與放大;婚禮的儀式被“推移”,并與滿月酒儀式進行了組合。這是對布依族傳統締婚模式的一種背離,是對傳統價值觀的一種對抗。在這種背離與對抗中,凸顯的依然是民眾對確認與維護姻親關系、構建社會網絡的文化訴求。民眾在對傳統儀式進行重構與組合的同時,置換了傳統婚禮原有的文化意義。
三、結論——傳統儀禮變遷:文化調適中的另類表達
在現代語境下,民族傳統文化的變遷是一個具有普適性意義的現象。因之,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可將翁村的傳統文化及婚姻儀禮變遷視為中國農村社會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縮影。雖然并不能冀望一個翁村的實例能夠涵蓋布依族婚姻儀禮變遷的所有層面,但它至少能夠凸顯出某些文化信息,而通過這些文化信息,我們還是可以管窺整個布依族社會變遷的某些軌跡。
面對社會外部大背景與社區內部小背景的共同變遷,民眾必然對其觀念和行為做出相應的“文化調適”。這里所論及的借滿月酒補辦婚禮的儀式就是為了適應這種變化而進行調適的結果,是當地民眾轉移和釋放社會變遷壓力的一種有效途徑。此種變異模式“撕裂”了布依族傳統婚戀模式的規則與限制,對傳統儀式進行了重構與組合,并在重構與組合中置換了傳統婚禮儀式原有的文化意義。它在消解了實際意義的同時,卻凸顯了內蘊其中的象征意義,但同樣實現了傳統婚禮的功能。因此,從這個角度上講,此種婚戀模式是作為民眾對傳統模式的一種替代性策略而存在的,它是民眾應對社會文化變遷的一種曲折式回應。在此曲折式回應中,民眾表達了他們的文化期望。
當然,民眾在對傳統婚禮儀式進行“修剪”的同時,還是會保留其基本的框架,借用其外在的形式。換言之,婚姻文化的意蘊在傳統與現代之間雖有一定程度的“躍遷”,但必然會保留一定的繼承關系。唯有如此,才能使民族傳統文化在歷史與現代的關聯中向前推演。在本個案中,“合一”(滿月酒與婚禮合一)的這種變通方式本身就與布依族傳統社會中的某些文化因素有著內在的歷史淵源。另外,據我們觀察,在婚禮儀式中也保留了某些布依族傳統文化的因子,如在娘家客人到來時,男方家用一根纏上紅紙的竹竿擋住他們的去路,不讓其進入男家屋內,必須對歌才能通過;在酒宴結束后還要對唱“親家歌”,這些都是傳統婚禮儀式中的環節,這集中地體現了布依族傳統文化的特點。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民眾是以傳統儀式為依托,并在傳統文化框架內展演出變異的婚姻文化形式與內涵。這種變異的儀式同樣地發揮了凝聚的功能,強化了社區網絡,尤其是親屬網絡,但它也真切地展示著社會的變遷。
毫無疑問,翁村人乃至整個布依族社會的民眾在未來的生活中將會一直面對傳統與現代的矛盾,社會與文化的沖突,而隨著農村城市化進程的進一步發展,傳統文化及其表現形式將會受到更大的沖擊,也許會生發出更多的變異形式。這正如卡西爾所說:“人不可能過著他的生活而不表達他的生活。這種不同的表達形式構成了一個新的領域”[13] 283。民眾正是在這種“變”與“不變”之間,傳統與現代之間尋找著兩者的平衡點,不斷地調適著自己的行為和觀念,從而創造出“新”的文化表達方式。
參考文獻:
[1][10]陶立璠.民俗學[M].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
[2]汛河.布依族風俗志[M].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7.
[3]黃義仁,韋廉舟.布依族民俗志[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5.
[4]王偉,李登福,陳秀英.布依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
[5][8]陳玉平.論布依族“浪哨”與婚姻的關系[M]//貴州世居民族研究(第3卷).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2006.
[6] [清]劉岱.乾隆獨山州志[M].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木刻本.
[7] [清]愛必達.黔南識略[M].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重刻本.
[9]吉國秀.婚姻儀禮變遷與社會網絡重建[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11] [芬蘭]韋斯特馬克.人類婚姻史[M].王亞南,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
[12] Gennep,Arnold Van. The Rites of Passage[M].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0.
[13] [德]恩斯特·卡西爾.人論[M].甘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
[14]龔佩華,史繼宗.布依族婚姻試析[J].貴州民族研究,1981(3).
[15]陸新紀.布依族婚姻研究中有關問題商榷[J].貴州民族研究,1981(4).
[16]韋廉舟.布依族與漢族的嫁娶禮儀[J].南風,1982(2).
[17]楊昌儒.淺談布依族“浪哨”習俗[J].黔南民族,1991(1).
[18]楊昌儒.論布依族“浪哨”文化的演講[J].貴州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增刊).
[19]陳玉平.浪哨:從社交、娛樂到自由擇偶[M]//貴州世居民族研究(第2卷).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2005.
[責任編輯:丹涪]
□武陵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