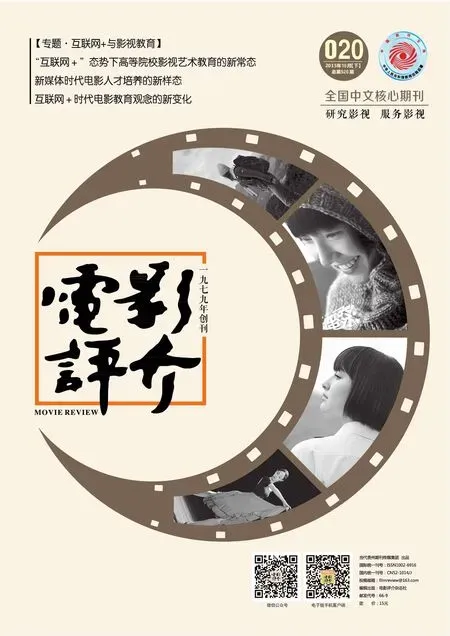德國電影《羅拉快跑》中的女性主義元素
彭 薇
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隨著西方婦女解放運動的興起,在歐美產(chǎn)生一種女性主義的電影樣式。社會經(jīng)濟生活的發(fā)展與父權制文化繼續(xù)維持婦女從屬地位之間矛盾的激化,導致了女性主義的興起。隨著自由主義思想的傳播和工業(yè)革命的深化,男子在社會個體化的過程中獲得越來越多的個人權利,而女性的權利卻始終遭到排斥,無法調(diào)和的沖突促成了女性主義的爆發(fā)。在這種情況下,女性主義電影越來越多的見諸銀幕,以女英雄女豪杰甚至女殺手為主題的電影紛紛搬上銀幕。具體而言,女性主義電影指的是以女性為主角,從揭露、控訴和顛覆父權視角出發(fā),觀照女性生活題材的影片。
縱觀近年來的女性主義電影,德國導演湯姆·提克威于1998年拍攝的《羅拉快跑》無疑是一個亮點。“奔跑”這條主線貫穿影片始終,一頭紅發(fā)的女主角羅拉為了拯救男友不停地奔跑。該片一經(jīng)上映便大受歡迎,成為當年德國最賣座影片,許多德國女孩甚至模仿片中的女主角羅拉,染了一頭紅發(fā)。德國市長更是把自己的肖像印在《羅拉快跑》的海報上制成宣傳廣告,藉此片塑造其貼近年輕人、具有活力的形象。影片中所體現(xiàn)的強烈女性主義色彩成為該片廣受歡迎和好評的催化劑。

電影《羅拉快跑》劇照
本文試以《羅拉快跑》為例,從劇情、角色、語言和道具等方面對該片所反映的女性主義元素進行分析。
一、 不同尋常的劇情
“奔跑”是整部影片的線索,在這個“美女救英雄”的故事里,導演摒棄了常規(guī)的敘事模式,沒有遵循敘事完整歸一、時間呈線性發(fā)展的刻板規(guī)律,而是運用了一種獨特的方式,在不足90分鐘的時間里,將電影情節(jié)和電腦游戲與動畫相結合,將一個簡單的故事反復講述了三遍——在羅拉的三次奔跑中,僅僅因為一些細節(jié)的改變便導致了三個完全不同的結局。這三次奔跑象征著女性對自身的一步步認知以及女性意識的覺醒,預示著最終女性只有沖破了傳統(tǒng)社會為女性設置的障礙與束縛,直至擁有與男性同等的話語權,才能實現(xiàn)真正的兩性平等。
第一回合,羅拉面臨難題:為了解救男友曼尼,她必須在20分鐘內(nèi)籌措到10萬馬克。羅拉無計可施,最終只能求助自己身為銀行家的父親。然而,父親冷酷拒絕了她的請求。在這個場景中,父親象征著傳統(tǒng)上絕對權威的父權和男性主導地位,而羅拉則是代表了長期處于弱勢的傳統(tǒng)女性,面對這個男性掌握話語權的社會,她顯得異常虛弱,無法得到父親的援助,她只能兩手空空地來到和男友約定的地點。這嚴重失衡的力量對比注定了第一回合里羅拉的悲劇結局: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男友搶劫超市,除了順從地成為其幫兇別無他法。然而,她手里握的槍卻隱隱暗示著向男權的挑戰(zhàn)——“槍”。顯而易見,羅拉對男性地位的挑戰(zhàn)自然會遭到殘酷的絞殺,她在倉皇出逃途中被一名男警察一槍結果了生命。羅拉的悲劇結尾象征著在相當漫長的一段時期里,女性的自由被人為地束縛起來,只能約定俗成地接受這些條例,導致其力量逐漸萎縮,并且最終被忽視被遺忘。
第二回合,敘事重新開始。羅拉來到父親銀行的時間略晚,正好遇見父親及其情婦,并無意中聽到情婦向父親坦白自己所懷的孩子并不是他的。結合第一回合中羅拉發(fā)現(xiàn)自己不是父親的親生女兒,這里實際上是在暗示父親的性無能,“父權”的神圣光芒正在逐漸消失。在以男性為主導的社會中,“父權”是男權統(tǒng)治的基本形式,男權對女性的壓迫、女性對男權的依從集中體現(xiàn)為女性對“父權”的屈從。獲悉緋聞后,原有的父親權威形象在羅拉心目中坍塌,而父親對她的漠視,銀行保安對她的輕蔑,激發(fā)了羅拉內(nèi)心的憤怒。憤怒成為其力量之源,她從保安那兒奪過槍用來搶銀行——這一貌似突然的舉動暗示著女性自主意識的覺醒。這一刻,她雖然已是自己的主宰,但是仍需要借助“槍”——這個傳統(tǒng)意義上的男性符號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最終,她達到目的后,將槍隨手扔在大樓前,隱藏起了自己的外在力量的象征。警察包圍了這座大樓,但他們卻誤以為她是無辜的。事實上,這一幕隱含了男權社會對女性的輕視,男性慣于以居高臨下的姿態(tài)審視女性,想當然地賦予女性柔弱、不堪一擊的特質,不愿給予女性和男性同等的地位和權利,并且有意無意地對女性能力進行低估。然而,在這一回合中,羅拉最后還是失敗了。假如這是一部簡單的女性主義電影,編劇也許會讓她贏,但在這部電影中沒有這樣設計。這一次,曼尼被飛馳而來的救護車撞死了。曼尼的死亡隱喻著男性權力的喪失,而此時的羅拉則象征著女性主義的興盛,女性逐漸走出了從屬地位,初步獲得權力。
第三回合,羅拉沒有機會向父親尋求幫助,在絕境中,她到賭場碰運氣。這里暗含了父權的衰落以及女性意識的最終抬頭。在賭場上,羅拉贏得了一大筆錢,與此同時,曼尼也找到了撿到錢的流浪漢,拿回錢后作為交換將槍送給了流浪漢——這意味著“男權”的消解,只有當兩性各自達到自己的目標,并不以犧牲對方為代價時,才能實現(xiàn)真正的平等。
二、 顛覆的兩性角色
影片中,羅拉在明,曼尼在暗;羅拉強勢,曼尼懦弱。這一明一暗、一強一弱的強烈對比顛覆了傳統(tǒng)的男性角色與女性角色的定位,暗示在當今社會,男人不再是能夠掌控一切的強者,與之相反,女人卻在竭盡全力、不屈不撓地向命運抗爭。影片中,男女主人公在對待命運的不同態(tài)度以及行動上的變化和錯位,反映了當今世界男女角色定位的巨大轉變。
羅拉是這部影片當之無愧的主角。她勇敢自信,永遠在奔跑,全身心地愛著自己的男友,當她遇到問題,她會積極主動地去解決問題,與之相反,她的男友曼尼則顯得沒有主見,消極被動,膽小怕事,錢財意外丟失后第一時間不是想辦法補救,而是躲在電話亭里痛哭流涕,首先指責羅拉。
在其他男性配角的身上,更是體現(xiàn)了男性的尷尬地位,暗示著男權的消解。羅拉的父親,一位體面的銀行家,周旋于情人與妻子之間,表面上看來擁有令人的羨慕的社會地位和男性魅力,然而,情人腹中的孩子以及羅拉都不是其親生子。父親的“性無能”則是對男性權威的嘲諷,也暗示著父權的沒落;銀行保安,肥胖臃腫,患有心臟病,在他眼中,羅拉還是當初那個年幼無知的“小公主”,即便被羅拉輕而易舉地搶走了佩槍還嘲諷其不會用槍,這個角色流露出男性對女性的輕視以及對女性能力的低估;流浪漢,窮困潦倒,生活在社會底層,偶然拾得巨款想私自一吞了之,然而面對指著自己腦門的槍口,輕而易舉地將10萬馬克拱手相讓,在他身上再次體現(xiàn)出了男性極端自私與懦弱的陰暗面。
三、 耐人尋味的對白
這部影片中,羅拉和曼尼有兩次躺在床上的對話,分別發(fā)生在故事的第一回合和第二回合結束之后。影片的畫面轉為紅色,兩個主人公赤裸著對話,象征著兩人在混沌的冥界進行交談,將死的一方成為提問者。
第一次,羅拉被警察誤傷斃命,在冥界她向曼尼拋出一系列問題:“你愛我嗎?為什么你可以這樣肯定?我可以是其他女孩子嗎?”這可以解讀為女性對自己身份的追問。在這部影片中,“男權”和“父權”形象彼此交疊,構成一組同義詞。第一回合中,父親沒能給予羅拉幫助,是導致其死亡的間接原因。更讓羅拉無法接受的是,她還從父親口中知道自己并非其親生子。“父”的權威地位逐漸受到了動搖。在情感上,羅拉不再對“父親”無條件的、盲目的、非理性的依賴與臣服。同時,羅拉的提問也為其在第二回合中更加勇敢和果斷的表現(xiàn)進行了鋪墊。
第二次,曼尼在彌留間很現(xiàn)實地問羅拉:“如果我死了,你會怎么辦?”羅拉很干脆地回答:”我不會讓你死……我會想辦法……我會把你丟進海里——休克療法……”與曼尼的脆弱相比,羅拉反而呈現(xiàn)出一種強者的姿態(tài)。羅拉斬釘截鐵的回答彰顯了其強烈的女性意識,此時的她,在兩性情感中居于主導地位,不再糾結于對自身的身份認同感。當曼尼再次逼問:“如果我無論如何都會死呢?”羅拉平靜地據(jù)實回答:“我會去海島上將你的骨灰撒向風里。”這樣的回答象征著女性與傳統(tǒng)的慣性思維間的決裂。相對于男性,女性是“第二性”,有著與生俱來的被動和悲劇特質。必須拋棄這從屬的“第二性”特征,才能謀求與男性同等的權利和地位,
四、 象征意味極強的道具
在羅拉的幾次的奔跑中,除了她那頭火紅惹眼的頭發(fā),就屬羅拉握槍的畫面給人印象最深了。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看,槍是典型的男性象征。因此,一旦把槍作為核心道具——而且大部分時間還是掌控在一個女人手中,難免讓人聯(lián)想到這是對片中男性角色另一種意義上的“閹割”。
在傳統(tǒng)電影中,槍往往代表著勇敢無畏的男子氣概以及男性與生俱來的主宰性和侵略性。然而,在《羅拉快跑》這部電影中,羅拉卻用槍一次次指著她身邊的男性。在羅拉手里,槍并非只是虛張聲勢地嚇唬人的工具而已,她能夠從容而熟練地持槍射擊。
影片中,有三次對羅拉持槍的特寫:第一次,在超市里,她砸暈了超市保安,出其不意地奪下手槍;第二次,在銀行里,她利落地從銀行保安的腰間繳獲了槍支;第三次,她用剛奪下的手槍挾持自己的父親做人質搶劫銀行。所涉及的上述所有男性面對羅拉均無招架之力,手槍在男性手中反而成了虛張聲勢的工具,現(xiàn)代社會的男性已經(jīng)淪落到了讓人尷尬的地步。
影片通過描述“槍”在男性和女性手中的不同效用,進一步強調(diào)了男權的消解,逐步完成了該片對女性主義存在感的建構。
電影是社會思潮在銀幕上的投射,女性主義電影的創(chuàng)作有助于瓦解電影業(yè)對于女性創(chuàng)造力的壓制,以及避免女性銀幕形象的單一化和模式化,同時,能夠在電影工業(yè)化的背景下,勇于對主流意識形態(tài)提出質疑,為女性的生存狀態(tài)和社會地位發(fā)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