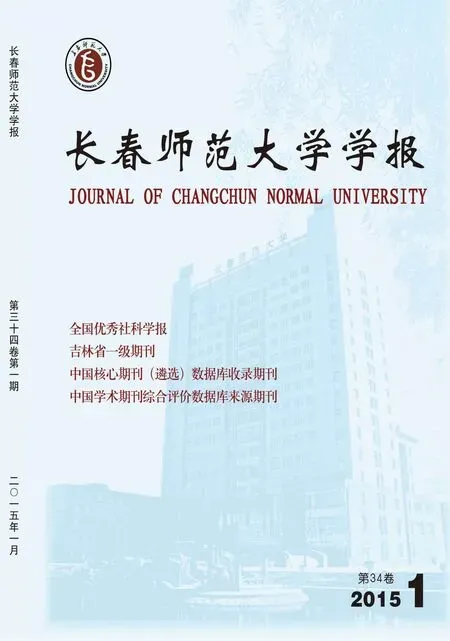我國刑事強制醫療制度之建構
李鄂賢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湖北武漢430074)
在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以前,我國強制醫療措施實施的唯一法律根據是《刑法》第18條,而沒有相對應的訴訟程序予以銜接,造成了《刑法》的內容規范和《刑事訴訟法》的程序在設計上脫節。這給強制醫療的實施帶來了諸多不便,使其本該在實踐當中發揮的作用沒能徹底地展現出來。新的《刑事訴訟法》實施以后,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但在司法實務中又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以更好地發揮它的效用。
一、我國刑事強制醫療的性質定位
在立法過程中,對于強制醫療性質的認定存在著兩種觀點。一種觀點是,我國行政法律法規對精神障礙患者適用的強制醫療是行政行為,這不同于刑事訴訟行為;另一種觀點是,法院可以基于社會安定有序發展的需要,對精神障礙患者作出強制醫療的決定,這是新刑事程序法所要解決的問題。刑事強制醫療應該放在哪個位置,對于正確界定其適用范圍具有重要意義。
(一)刑事強制醫療非刑罰方法
從我國《刑法》第18條規定看,完全不能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無需對自己的行為承擔刑事責任,那么就不可能用一種具有刑罰性質的方法對實施了危害行為的精神病人進行處罰。從這個角度來說,刑事強制醫療不是刑罰。再從我國的刑罰體系來看,我國刑罰種類包括主刑和附加刑;但是從現行《刑法》的規定來看,無論是主刑還是附加刑都不包含強制醫療這種措施,因而刑事強制醫療非刑罰方法。
(二)刑事強制醫療亦非行政強制措施
一方面,行政強制醫療的決定主體是行政機關。而根據《刑事訴訟法》規定,刑事強制醫療的決定主體只有法院,公安機關不具有刑事強制醫療的決定權;即使公安機關在偵查過程中發現精神病人符合強制醫療條件,也只能寫出強制醫療意見書,移送人民檢察院,而無權直接決定對行為人進行強制醫療。因此從決定主體來看,刑事強制醫療不是行政強制措施。另一方面,從刑事強制醫療程序看,對觸犯刑法的精神病人,必須按照《刑事訴訟法》中關于強制醫療特別程序的規定,經過司法審查,由法院決定是否對行為人適用和執行強制醫療。這是一種典型的刑事司法處理行為,排除了非司法部門的參與和處置。從這個角度來說,刑事強制醫療不是一種行政強制措施。
(三)刑事強制醫療是一種“準保安處分”
1.從適用的條件看
有繼續危害社會可能是適用強制醫療的條件之一。從這個條件可以看出,刑事強制醫療注重的是行為人實施再犯的可能性,而不是對行為人已經實施犯罪行為的處罰,而刑罰與行政處罰注重對行為人已實施行為的懲罰。從這個角度來看,刑事強制醫療符合國外保安處分的性質。
2.從決定主體看
我國刑事強制醫療的決定主體只有人民法院,其他國家機關并不具有刑事強制醫療的決定權。即使是作為國家司法機關的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也無權決定對行為人適用刑事強制醫療,這就使得刑事強制醫療具有了刑事司法的性質,從而與一般的行政處罰相區分。且如上文所述,刑事強制醫療不是刑罰,因而從決定主體來看,刑事強制醫療在性質上與保安處分更相似。
3.從刑法的角度看
我國《刑法》并未明文規定保安處分,只是在《行政法》及《刑法》中存在著社區矯正、勞動教養、強制戒毒等類似于保安處分的零散規定,因而直接將刑事強制醫療與國外的保安處分等同并不合適,應將其稱為“準保安處分”較為合適。
二、我國刑事強制醫療制度的缺陷
(一)適用對象范圍有限
從我國《刑法》第18條的規定來看,強制醫療僅僅適用于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而造成危害結果時,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不負刑事責任的情形。對于間歇性的精神病人以及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我國《刑法》都沒有規定對行為人進行強制醫療。而新《刑事訴訟法》第284條進一步明確了適用強制醫療的條件:第一,行為人實施了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嚴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暴力行為;第二,行為人是經法定程序鑒定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第三,行為人有繼續危害社會的可能。我國《刑法》對強制醫療的適用范圍規定得本來就較為狹窄,而新《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進一步壓縮了強制醫療的適用對象。
(二)依法決定主體單一
根據我國新《刑事訴訟法》規定,有權力決定對不需要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適用強制醫療的主體只有人民法院。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即使在偵查、審查起訴過程中發現精神病人符合強制醫療條件,也只能向人民法院提出強制醫療的申請。故人民法院作為唯一決定主體不利于司法實踐。
1.法院把持強制醫療的決定權不符合效率原則
我國法律對強制醫療規定了嚴格的適用條件。在實踐中,公檢法機關都有能力根據這些規則來判斷行為人是否符合強制醫療的條件;但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即使發現精神病人符合強制醫療條件,也依然需要向人民法院提出強制醫療申請,這大大降低了司法機關的行政效率。
2.法院作為唯一的決定主體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
從強制醫療的性質來看,類似保安處分的強制醫療由人民法院決定并無不當之處;但在司法實踐中,公安機關作為直接接觸精神病人的國家司法機關,對精神病人的狀況較為了解。雖然法律規定由法院來決定是否對行為人適用強制醫療,但法院也必須依靠精神鑒定結論以及公安機關的調查結果來進行判斷,這導致法院的決定權形同虛設。因此,賦予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在偵查、審查起訴階段的強制醫療決定權具有合理性。這樣做一方面可以節省司法資源,另一方面可以減輕人民法院的負擔,讓人民法院可以集中精力審理其他重要刑事案件。
(三)費用負擔機制不科學
我國《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及相關的司法解釋并未明確規定強制醫療的費用負擔。司法實踐中,強制醫療的費用一般由精神病人的監護人負擔;如果沒有監護人,則由法院指定親屬負擔;如果既沒有監護人也沒有其他親屬,則由政府負擔。從我國司法實踐的操作來看,這種費用負擔機制不盡合理,體現在幾個方面:從刑事強制醫療的性質來說,作為一種類似保安處分的“非自愿”措施,由國家司法機關予以強制執行,在公眾看來,其費用自然應由國家負擔;精神病人的治療費用較為昂貴,而且精神病的治愈可能性較低、反復性較大,不少精神病人需要長期靠藥物來保持健康,因而對于一般家庭來說,無力承擔昂貴的醫療費用;刑事強制醫療對象也是特定的,其設立目的主要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慮,這部分費用應當由國家負擔。
(四)事后監督機制有待完善
如上所述,精神病的治愈率較低,且反復性較大,許多精神病患者只能在藥物控制下保持健康。因此,對精神病人強制醫療后的效果進行考察、信息反饋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環節。一方面,對強制醫療的效果進行考察,在此基礎上總結經驗教訓,改進我國強制醫療的水平;另一方面,這是防衛社會的需要。被強制醫療的精神病人一般都是具有較大再犯可能性的,如果精神病尚未被治愈或者事后復發,其再次犯罪的可能性仍然較大。而加強事后監督可以及時發現相關問題并采取相應的預防措施,預防其重新犯罪。這樣既可以達到防衛社會的目的,也可以更好地保護精神病人的利益。
三、我國強制醫療制度的完善
(一)適當擴大強制醫療的適用范圍
對于強制醫療的適用范圍,學界爭議頗多,多數人認為其適用范圍過于狹窄。有些學者主張將觸犯刑律的限制行為能力人與犯罪時精神正常但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喪失訴訟能力的精神病人納入刑事強制醫療對象的范圍[1];有學者主張用“精神障礙者”的概念取代“精神病人”的概念,并且將觸犯刑律、不具有治愈可能性的人格障礙者納入刑事強制醫療的范圍[2];甚至有人主張將所有對公共秩序構成威脅的精神障礙者均納入強制醫療的對象范圍。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對于刑事強制醫療的對象界定不宜隨意偏移,不宜盲目擴大[3]。
筆者認為,對于強制醫療的適用范圍確實不宜盲目擴大。如果認為刑事強制醫療是一種保安處分,就不應當將其歸入適用對象范圍以內,因為保安處分的適用對象是實施了犯罪行為,同時具有再犯罪危險性的人[4]。在實施犯罪行為之前,不能對其適用保安處分。但是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適用范圍確實過于狹窄,不利于防衛社會,因而有必要予以適當擴大。出于防衛社會的需要,對于下列幾種精神病人有必要適用強制醫療:(1)犯罪時尚未完全喪失控制能力和辨認能力的精神病人。行為人在尚未喪失認識能力和控制能力時實施犯罪,顯示出了較大的人身危險性。這類人的控制能力比一般人差,其精神病進一步惡化的可能性較高,因而這類人實施再次實施犯罪行為的可能性較高。出于社會防衛的考慮,有必要對其予以強制醫療。(2)在犯罪時精神正常的間歇性精神病人。間歇性精神病人具有極大的不穩定性,一旦受到刺激完全有可能精神病復發。這類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時就已經實施了犯罪,顯示出了較高的人身危險性;那么在精神病復發時,由于控制能力的降低甚至喪失,這類人實施犯罪的可能性要更高,因而對這類人在執行刑罰的同時有必要予以強制醫療。(3)雖未實施暴力犯罪,也未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的人身安全,但是已經顯示出了暴力傾向的精神病犯罪人。我國《刑事訴訟法》對強制醫療的適用對象限定很窄,因而對實施了其他非暴力犯罪的精神病人不能適用強制醫療,但對實施其他非暴力犯罪時顯示出了一定暴力傾向的精神病人也有必要予以強制醫療。一方面,行為人實施了犯罪行為,顯示出了一定的人身危險性。雖然尚未實施暴力犯罪,但是由于精神病人對自己行為的認識能力和控制能力較差,其實施暴力犯罪的可能性較之一般人要高許多,因而有必要予以提前預防;另一方面,精神病人的治療費用較高,導致許多有精神病人的家庭經濟條件較差,加上許多精神病人可能并無其他親屬或者親屬也是精神病人,在精神病人實施了某些毀壞財產的犯罪行為時,被害人的財產損失難以得到彌補。
(二)完善強制醫療費用的分擔機制
作為一種“非自愿”的刑事強制醫療,其費用全部由病人家屬負擔明顯不合理,政府財政應當予以分擔,但不宜全額負擔。倘若規定由國家全額負擔治療費用,可能會導致病人親屬轉嫁責任的現象產生,甚至可能產生親屬教唆精神病人犯罪的情況。經濟條件確實困難的家庭,可以申請減少或者免除醫療費用。
(三)完善事后監督機制
由于精神病的治愈率較低、反復性較大,因而對強制醫療的精神病人的事后監督極為重要。而僅依靠國家機關的力量還難以達到理想效果,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進行強制醫療的機構在治療結束后的一定周期內有必要定期對病人進行檢查,以了解治療措施是否合理、治療手段是否有效。在治療結束后的一定周期內,公安機關需要定期會見病人,以檢查其是否仍然具有人身危險性,是否有再犯可能性。病人所在的村委會或者居委會需要經常了解病人的情況,并及時向公安機關反饋相關信息。病人的家屬要對病人進行看管,需要繼續進行其他治療的,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要盡可能地對病人進行治療。
[1]李玲娜.刑事強制醫療程序適用對象之研究[J].法學雜志,2012(10):37.
[2]張兵.程序·法治·人權:試論我國的強制醫療制度及其完善[J].江西公安專科學校學報,2010(4):43.
[3]奚瑋,寧金強.刑事強制醫療的對象界定與程序完善[J].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13(5):42.
[4]張明楷.外國刑法綱要[M].2版.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