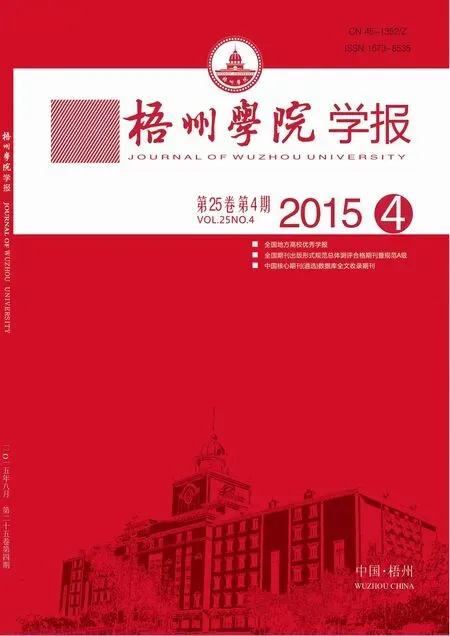醫療損害賠償責任性質的再認識
李瀟
(廣西師范大學職業技術師范學院,廣西桂林541004)
醫療損害賠償責任性質的再認識
李瀟
(廣西師范大學職業技術師范學院,廣西桂林541004)
文章認為醫療損害賠償責任的性質應為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競合說,并認為醫療損害賠償責任之所以由違約責任轉化為侵權責任,其法理基礎有法律對人的尊嚴與價值的尊重以及對人的生命健康的關懷,僅在侵權責任中存在的精神損害賠償及懲罰性損害賠償,以及合同法沒有對醫療合同的規定,這使得在我國產生了醫療損害賠償按照侵權責任進行處理的傳統與習慣。同時文章也認為違約責任在醫療損害賠償責任中在某些特殊醫療合同、時效期間、第三人過錯及責任承擔方式方面具有其獨特的價值。
醫療損害;賠償責任性質;再認識
一、有關醫療損害賠償責任性質的各種學說及評析
關于醫療損害賠償責任的性質,一直存在眾多爭議,有的學者主張侵權說,如張新寶教授就認為由于我國合同法對醫療合同沒有規定,同時理論界也通常不將醫療損害責任歸為違約責任,所以違約說與競合說都不可取,醫療損害責任原則上應定位為侵權責任[1]。而王利明教授則認為醫療損害賠償責任的基礎同時包括侵權責任和合同責任兩方面,但主要屬于侵權責任。在實踐中,又會出現侵權責
任與合同責任的競合[2]528。楊立新教授的觀點與王利明教授的觀點相類似,認為醫療關系的本來性質是一種非典型的契約關系,因而醫療機構在醫療活動中因過失導致患者損害時,屬于違約行為,應承擔違約責任。但如果從醫療過失行為侵害公民的健康權、生命權的角度來看,醫療損害無疑又是一種侵權行為,故楊立新教授是在承認醫療損害構成侵權責任與違約責任競合的前提下,認為應當選擇侵權責任作為醫療損害的性質[3]。再有一種觀點認為,醫療損害賠償責任屬于違約責任,或說醫療損害賠償責任適用違約責任更為合理[4]。
對于以上幾種觀點,筆者認為,第一種觀點得到了我國立法與司法實踐的支持,如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國務院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以及2009年的《侵權責任法》等都是將醫療損害賠償責任規定為侵權責任,同時在司法實踐中我國人民法院處理現實中的醫療損害賠償案件也大都是按照侵權責任進行處理的。但其理由卻難以得到多數學者的認同,因為按照傳統民法理論,與物權設立采取“法定主義原則”不同的是合同設立采取“契約自由主義原則”,所以即使是合同法中沒有明確規定的合同類型,也不能因此而認為當事人不能自由創設某類合同;況且如果否定醫療損害賠償責任的違約責任性質,否認醫患雙方之間存在合同關系,則無法解釋醫患雙方的醫療關系賴以產生的基礎關系到底是個什么性質的關系。第四種觀點應該說是一種目前得到認同度最低的觀點,其主要原因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包括我國無論是學說還是判例對醫療損害賠償問題都基本上是按照侵權責任去處理的,但其對醫療損害賠償按照違約責任進行處理的合理性論述還是非常具有理論價值的。相對而言,第二、第三種觀點也許更為合理。尤其是第二種觀點,可以認為是我國理論界關于醫療損害賠償責任性質的通說。因為這種觀點注意并認同作為醫療損害賠償關系所賴以產生的基礎關系——醫療服務關系的契約性質,但同時又注意到醫療損害賠償關系無論是立法上還是司法實踐上都傾向于按照侵權責任進行處理的基本態度。
事實上,絕大多數學者都認同這么一個事實,即醫療損害賠償關系得以產生的基礎關系——醫療關系是一種合同關系。因為醫療關系得以產生緣于醫患雙方達成醫療合意,這種合意通常以患者方通過選擇醫院并掛號的方式得以形成,由此在醫患雙方之間形成了以提供醫療服務為主要內容的醫療合同關系——醫療服務關系。對于由該醫療服務關系所產生的債務,通說認為系“手段債務”,而非“結果債務”[5]13。即醫療方給患者所提供的醫療服務只是醫療方承諾其提供符合當時醫療科學發展水平的醫療服務,并且只要醫療方在提供醫療服務過程中盡到了與其專業水平相一致的高度注意義務,不管最后治療的結果是否治好了患者的疾病,醫療方均為已完全地、適當地履行了其醫療債務。關于醫療合同的類別,有委任合同說、準委任合同說、承攬合同說、混合合同說、無名契約說、雇傭合同說、技術服務合同說等多種主張[5]16-17。由此可見,醫療關系是基于醫療合同關系而產生的,其與通常在當事人間無任何先前特定法律關系存在的侵權法律關系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二、醫療損害賠償侵權性質的法理分析
如前所述,醫療關系實質上為一種合同關系,那么由這種合同關系所產生的糾紛原則上應根據違約責任規則去處理,才符合傳統民法關于民事責任分類的理論邏輯。可是我國在醫療損害賠償問題上無論是立法、司法還是學說界都將其按照侵權責任去處理,那么這樣的觀點與做法有無法理上的依據?若有,其依據又是什么?依筆者之見,認定醫療損害賠償的侵權責任性質是有其法理基礎的。
1.對人的尊嚴與價值的尊重,以及對人的生命健康的關懷是醫療損害賠償由違約責任轉向侵權性質的最為重要的法理基礎。民法是權利法,始終以對人的終極關懷為已任。因此,在民法中對民事
主體,尤其是對自然人的尊嚴與價值的尊重及對其生命健康與安全的保障是民法的第一要義或第一責任。這是因為民法以人身關系與財產關系為主要調整對象,而在人身關系與財產關系的相互聯系上,它們的地位與作用是完全不一樣的。以人格尊嚴及生命、健康等利益為代表的人格權與財產權相比較,當然應該具有更高、更為重要的地位,它是民法中的最高法益。這一方面是因為現代民法要充分體現人本主義精神,強調對個人的終極關懷,因此將就個人利益而言更為重要的人身利益置于財產利益之前優先給予保護。另一方面,財產權與人身權相比較其處于較低的地位也是因為在民法中,人是主體,而包括財產在內的物是客體,客體因主體的利益而存在,符合主體利益需要的物才能成為民法意義上的“物”,否則,哪怕是客觀上存在的物,因其對主體無法律上的利益而被排除在“民法”上的物或財產的范疇之外[6]93。此外,在緊急避險及正當防衛制度中,也都涉及到對防衛及避險的合理限度問題的考量,都認為在通常情況下人的生命利益要比財產利益具有更高的法律價值[6]610。第三,人格尊嚴、人的生命健康及安全不僅僅涉及主體個人的利益,同時還涉及社會公共利益[7]273。所以對于涉及人格尊嚴、人的生命健康及安全問題,各國在立法上都給予了最為嚴格的保護,設立了從民事責任、行政責任直至刑事責任的完整的權利保護、救濟體系。從權利保護程序的發動上看,從受害人個人啟動的“不告不理”的民事及行政訴訟到由國家主動啟動權利保護程序的公訴制度;從權利保護的力度上看,從賠禮道歉、恢復名譽、消除影響等非財產責任形式到以填補損失為重要目的的財產性責任形式——其中包含對財產損失的賠償與對非財產損失的民事賠償;再到涉及人身自由的行政拘留與勞動教養——以人身自由罰為主要措施的行政責任;直至以剝奪人身自由乃至生命為主要措施的刑事制裁,對人格尊嚴、人的生命健康及安全進行周密而嚴格的保護,以上充分說明了人的尊嚴、生命健康與安全在民法權利保護中的重要地位和重要意義。
對于如此重要的權利所體現出來的法益通過侵權法的保護是最為恰當不過的了。因為侵權責任與違約責任相比較,無論是在權利(利益)的保護范圍、保護力度及保護周全性等方面前者都要優于后者。從權利保護的范圍上,違約責任只保護合同債權,而侵權責任保護除了債權外的絕對權,包括人身權、物權、知識產權與財產繼承權等權利。不僅如此,侵權責任除了保護上述明確的法定權利外,還保護立法上尚未明確為權利的法益。如胎兒或死者的某些人格利益[7]54-55;從二者保護的力度來看,除了共同的賠償損失等救濟方式之外,侵權責任還有精神損害賠償及懲罰性賠償這些違約責任所沒有的責任方式[8];從權利保護的周全方面來說,侵權責任除了財產性責任外,還根據侵權的實際情況,規定了諸如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等非財產責任形態,對受害人的利益保護及利益救濟手段更為豐富周全。
2.就患者方利益而言,適用侵權責任較適用違約責任更為有利,具體表現在適用侵權責任可以得到精神損害賠償或懲罰性賠償。當患者遭受醫療損害后,依據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競合說的觀點,受害人可以選擇主張違約責任或侵權責任。關于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在醫療損害賠償中對受害人的利益影響,一些學者認為二者并無太大的差異[9]。但大多數學者認為,在我國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對受害人的利益影響是不同的,二者之間存在諸多的差異[2]225-229。還有的學者對醫療損害賠償中的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的競合問題進行了專門的研究[10]。在上述研究中,學者們認為,根據我國法律規定,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的最大區別之一是違約責任不適用精神損害賠償,而侵權責任適用精神損害賠償[11]。這種狀況在大陸法系的法國及德國也是基本一樣的[12]39。盡管現在似乎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存在著主張在違約責任中也可以或者應該適用精神損害賠償的傾
向[12]1-39。另一方面,按照我國現行法律規定,我國法律也僅在產品責任及食品安全等侵權法少數領域內規定有懲罰性賠償(1),而對違約責任則沒有規定有懲罰性賠償。我國學者對違約責任是否適用懲罰性賠償問題意見也比較一致,認為在違約損害賠償責任中的一般原則是“補償性原則”,其“補償性”表現之一即是不允許“懲罰性損害賠償”。懲罰性損害賠償在侵權案件中可以判予,但其目的并非賠償原告,而是要表明法院對被告行為的反對[12]7。又如在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起草的《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中國人民大學起草的《中國民法典草案》以及由徐國棟教授主持編寫的《綠色民法典草案》也都是僅在故意侵害他人生命、身體、人身自由、健康或具有感情意義財產;因生產者、銷售者故意或者重大過失使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人身、財產損害的;或故意侵害他人人格權并造成嚴重后果的行為等侵權領域規定了懲罰性賠償[13]。上述例證充分說明了,在我國目前的情況下無論是立法還是學說,都只是在侵權責任中肯定懲罰性賠償的適用,而否定懲罰性賠償在違約責任中的存在。所以,在這種立法與學說背景下,主張以侵權責任處理醫療損害賠償顯然要比按照違約責任來處理對受害人來說更為有利。
3.我國長期以來一直都沒有有關醫療合同的立法,包括1999年的“統一”合同法也都沒有規定醫療合同,相反,相關的立法與司法實踐都將醫療損害問題當作侵權案件來處理。我國從1981年起陸續頒布了《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和《技術合同法》;國務院根據上述相關法律,分別制定、頒布了包括《工礦產品購銷合同條例》《農副產品購銷合同條例》《加工承攬合同條例》《借款合同條例》《鐵路貨物運輸合同實施細則》《倉儲保管合同實施細則》《財產保險合同條例》《技術合同法實施條例》等行政法規或部門規章。最高人民法院也頒布了《關于適用〈涉外經濟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答》等司法解釋。上述有關合同法及其配套法規對確立、促進我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初步確立市場經濟法制體系,維護市場交易秩序等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無論是上述合同法還是1999年的“統一”《合同法》都沒有對醫療糾紛及其損害賠償問題作出任何規定。相反,在1987年由國務院頒布的《醫療事故處理辦法》以及2002年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都是將醫療事故作為侵權責任進行處理的。2001年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四條(八)也明確地將醫療糾紛規定為按侵權訴訟處理(2)。2009年通過的《侵權責任法》也在第七章規定了醫療損害責任。從上述立法情況來看,我國在立法方面的態度是一致和肯定的,就是將醫療損害賠償責任按照侵權責任進行處理。受立法立場的影響,我國相當部分學者一般也都將醫療糾紛作為侵權責任進行考察與研究。司法實踐也與立法和學說界保持一致,通常也是將醫療糾紛按照侵權責任來進行處理的(3)。我國的這一法制傳統也導致醫療損害賠償責任在我國一直是按照侵權責任進行處理。
綜上所述,在我國,醫療損害賠償責任按照侵權責任進行處理,既有其自身的法理原因,也有其中醫患雙方的利益考量因素,同時還與我國固有的法制傳統有著緊密的聯系,是以上因素有機結合的結果。
三、違約責任在醫療損害賠償責任中的價值
如前所述,對于醫療損害賠償責任的性質,盡管學界的意見還沒有完全統一,但無可諱言的是,絕大多數學者都主張侵權責任或以侵權責任為主的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競合說,鮮有學者主張違約責任說的,由此很容易導致一種否定違約責任在處理醫療損害賠償責任中的價值的傾向。筆者認為,在處理醫療損害賠償責任問題上,違約責任雖然在我國目前的立法制度安排下,與侵權責任相比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是其在處理醫療損害賠償責任問題上仍然有其獨特的價值,對此應該予以肯定。
1.在某些特殊醫療行為中違約責任有其獨特
的價值。在現代社會中,隨著社會和生活的發展變化,醫療的含義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并不以單純的治病救人、救死扶傷為唯一的目的追求,一些非以傳統的治療為目的而是為了追求某種生活情趣或美的感受的新的“醫療服務”行為應運而生,這些所謂的“醫療”行為不具有傳統醫療行為所具有的治療性和緊迫性等特征,如人工生育(4)、美容、整形、矯正甚至變性等“醫療服務”行為即是。對于這些新型的“醫療服務”行為,由于不是以治病救人為目的,而是根據“患者”個人的情趣或對美的感受為“醫療服務”目的,因此這種“醫療服務”的內容應該由雙方根據“患者”的具體身體情況、“醫療服務”的目的、現有醫學水平、醫療風險等因素綜合考量,從而通過具體的“醫療服務合同”對雙方,尤其是醫療方的義務,特別是醫療效果加以明確的約定。之所以這些“醫療服務”行為可以通過醫療合同進行約定其具體的內容或醫療效果,是因為這些所謂的醫療行為不具有傳統的醫療性,特別是不具有緊急性,其實質就是一種由醫療機構利用其自身所具有的醫學知識、專業技能和專業設備,為社會大眾提供的非以治療為目的的“準醫療”服務行為。這種所謂的“準醫療”服務行為,較少具有治療性或根本就不具有治療性,而更多的具有面向不特定大眾提供特定“服務”的性質。因此,對于這種所謂的“醫療服務行為”其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更適合于通過合同確定,并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相關規定進行調整。
2.時效期間。時效期間在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的選擇中是一個需要著重進行考量的因素之一。關于時效期間對違約責任或侵權責任選擇的影響要根據我國法律關于時效期間的長短與起算時間的不同規定而進行具體的考慮。首先,關于時效期間的長短對兩種責任選擇的影響。按照民法通則的規定,因身體受到傷害——醫療損害賠償責任針對的正是因不當醫療行為對患者人體傷害的賠償——而提起訴訟的時效期間為1年;而因違約行為而提起訴訟的時效期間為2年。單純從時效期間的長短規定來看,主張違約責任似乎對患者方較為有利,但事實上并非如此簡單。因為在考察時效期間問題時,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需要結合考慮,這就是訴訟時效期間的起算時間。按照法律相關規定,關于侵權責任,其時效期間的計算從知道損害及侵權人開始計算,而違約責任則從違約行為開始時開始計算。由于時效期間計算時間的不同,因此在發生醫療損害后較長的一段時間才發現或確定該損害存在的,則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在時效期間長短方面的差異可能并不存在,因為違約責任的時效期間是從違約行為發生時開始計算的;但如果是在醫療行為發生后隨即發現或確定醫療損害的情形下,則在侵權責任的時效期間完成后,而違約責任的時效尚未完成前的這段時間里,主張違約責任或許是受害人剩下的唯一的救濟途徑。
3.第三人過錯問題。在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中,對于由于第三人的過錯而導致損害的發生或損害擴大的情形,二者的處理規則是完全不同的。在違約責任,由于需要遵循“合同相對性原理”,若違約行為是由于第三人的行為造成的,則法律不會免除違約方的違約責任,違約方也只能是在向對方當事人承擔違約責任后再向第三方訴求其承擔相應的責任。但在侵權責任,若損害(或擴大損失)是由第三人行為造成的,則構成侵權人的免責事由,侵權人可以減輕或免除其責任,而由第三人全部承擔或承擔相應部分的賠償責任。由此可見,在由于第三人過錯引起損害或擴大損害的情況下,違約責任相對于侵權責任來說,更有利于對受害人的利益進行保護。
4.責任的履行方式不同,違約責任比侵權責任更為靈活主動。按照我國《民法通則》第111條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條件的,另一方有權要求履行或者采取補救措施,并有權要求賠償損失;第134條還規定有修理、重作、更換這樣的責任方式;《合同法》第107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承擔繼續履
行、采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而屬于侵權責任方式的主要是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返還財產、恢復原狀、賠償損失、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14]。其中屬于違約責任特有的責任方式的繼續履行;采取補救措施;修理、重作、更換等責任方式與相對“消極”的侵權責任方式相比較則顯得更為積極主動與靈活,在某些情況下對維護患者方的合法權益可能具有重要意義。例如,在現有既定的醫療技術情況下,若某個醫療機構的某種醫療技術或治療方案被公認為最為成熟、最為有效、最為穩妥的情形下,或某醫療機構掌握了某種特有的醫療技術的情形下,同時在僅因為非醫療技術問題所引發的醫療損害并且又有必要繼續治療或采取相應補救措施的特定情況下,簡單地適用侵權責任方式進行處理可能對患者的后續治療或消除原有損害未必是最佳的選擇,因為在侵權責任中沒有繼續履行等相應責任方式,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違約責任中的繼續履行等責任方式在特定的醫療損害救濟中就有其獨特的存在價值。
總之,對于醫療損害賠償責任的法律性質,筆者認為其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競合說是有其充足的法理基礎與依據的,尤其在我國由原本屬于違約責任的醫療損害責任向侵權責任的轉變也是有其歷史原因的。但我們在肯定醫療損害賠償責任主要或著重是侵權責任的時候,也不能輕易地忽略違約責任在處理醫療損害糾紛中的獨特價值與作用,只有這樣我們對醫療損害賠償責任的認識與理解才可以說是全面的和正確的。
注釋:
(1)參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侵權責任法》第47條及《食品安全法》第96條的規定。
(2)《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四條第(八)項規定:“因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由醫療機構就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承擔舉證責任。”
(3)“劉穎訴烏魯木齊新市區大同貿易商行中醫門診部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醫療單位因醫療“嚴重差錯”造成患者人身損害,根據《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二款關于“公民、法人由于過錯侵害國家的、集體的財產,侵害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規定,應該承擔民事責任。http://www.fsou.com/htm l/text/fnl/1176757/ 117675796_1.htm l,2011-8-8.
(4)參見鄭雪峰、陳國青訴江蘇省人民醫院醫療服務合同糾紛案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告》,2004(8).
[1]張新寶.中國侵權行為法[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8:421.
[2]王利明.民法·侵權行為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3.
[3]楊立新.侵權法論:上冊[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556.
[4]耿甜甜:醫療合同研究[D].成都:四川大學,2007.
[5]龔賽紅.醫療損害賠償研究[D].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00.
[6]郭明瑞.民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7]王利明.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及說明[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
[8]王家福.中國民法學·民法債權[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 247.
[9]夏蕓.醫療事故賠償法—來自日本法的啟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05.
[10]艾爾肯.論醫療損害賠償中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競合問題[J].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4).
[11]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375.
[12]韓世遠.違約損害賠償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3]梁彗星.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25.
[14]姚輝.民法學原理與案例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572-574.
A Re-discussion on the Nature of the Civil Liability for M edical Damages
Li Xiao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Teachers College,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 541004,China)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nature of liability formedical damages shall fall in the overlap theory involving the liability for breach of contract and the liability for tort.It also holds that,because of the legal basis that laws always show respect for people’s dignity and worth aswell as consideration for people’s lives and health,the liability formedical damages should be converted from liability for breach of contract into liability for tort.In addition,due to the fact that compensation to mental damages and punitive compensation to damages are included only in the liability for tortand the fact that the existing contractual law is in lack of provisions for medical contract,a customary practice in which liability for medical damages is treated as liability for tort is adopted in our country.Moreover,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liability for breach of contract has its unique value in some aspects of the liability for medical damages,such as specialmedical contract,aging of contract,faultof the third party and methods of bearing liabilities,etc.
Medical damages;Nature of liability;Re-discussion
D923
A
1673-8535(2015)04-0039-06
李瀟(1964-),男,廣西蒙山縣人,廣西師范大學職業技術師范學院副院長,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民商法。
(責任編輯:覃華巧)
2015-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