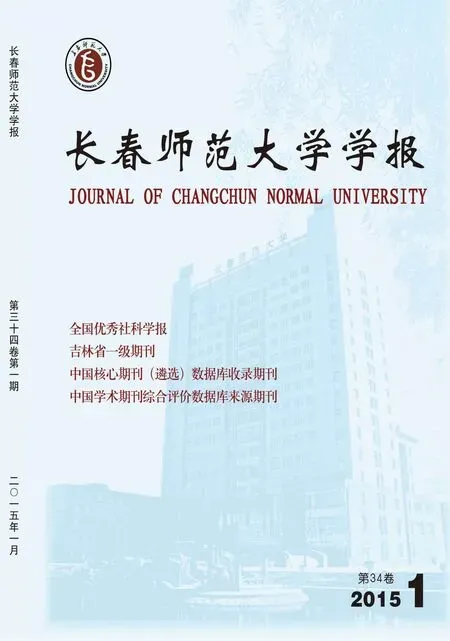論智利軍人政權時期的技術專家
——“芝加哥弟子”與智利的新自由主義改革
吳愷夫
(中國社會科學院 拉丁美洲研究所,北京 100007)
論智利軍人政權時期的技術專家
——“芝加哥弟子”與智利的新自由主義改革
吳愷夫
(中國社會科學院 拉丁美洲研究所,北京 100007)
在智利1973-1990年長達十七年的軍人統治時期,存在著軍人政府和以“芝加哥弟子”為代表的技術專家的聯盟。“芝加哥弟子”在制定經濟發展政策時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在軍政府的護持之下推進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成功地在智利建立起開放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為民主化轉型后20余年經濟改革的深化和穩定的增長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智利;軍人政權;技術專家;芝加哥弟子
1973年,智利軍隊發動“911”政變,推翻了阿連德政府,開始長達17年的政治高壓統治。在經濟領域,智利軍人政權接受了以“芝加哥弟子”為代表的一批技術專家的觀點,開始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成功地在智利建立起開放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回顧和總結“芝加哥弟子”在軍政府統治時期的行為與影響,對理解智利的現代化發展歷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阿連德革命”的失敗與軍政府的戰略選擇
1970年,由智利六個左翼政黨組成的“人民團結陣線”(Unidad Popular)在社會黨人薩爾瓦多·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的領導下贏得大選。阿連德就任總統之后,迅速開展一系列改革措施,試圖用經濟國有化、土地改革、收入分配調整等手段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但是,改革的措施觸動了智利中、右翼集團的利益,也引起了美國的不滿與干涉,加之阿連德政府的調整失誤,到了1973年智利陷入了政治僵持、經濟崩潰和社會動亂的局面。終于在1973年9月11日,智利軍隊在以奧古斯托·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將軍為首的右翼軍官團領導下發動政變,推翻了阿連德政府。
1973年上臺的智力軍人政權由三大軍種和武裝警察司令組成的軍事執政團(Military Junta)控制。此時的軍政府亟需為政變提供合法性與正當性的理由,但智利軍人并沒有系統性的意識形態,在軍事執政團內部存在著意識形態的分歧和派系的競爭。在這種情況下,智利軍隊首先采用南椎體國家軍隊中流行的“國家安全學說”扮演官方意識形態的角色。“國家安全學說”的出現與冷戰的國際環境特別是古巴革命有關。拉美軍人認為自己是拉美社會最訓練有素、最現代化的社會集團,是西方基督教價值觀的捍衛者,因此有責任抵御國際共產主義的威脅,恢復政治秩序,為新的經濟增長創造條件,必要時可以對社會和政府實行全面的控制[1]。在這一學說的支持下,智利軍隊公然拋棄憲政民主制度,解散國會、擱置憲法、禁止黨派活動,對反對派和異議人士開展長期的制度化的鎮壓,“意圖是消滅智利生活中的整個政治和社會運動。”[2]在這個過程中皮諾切特將軍運用各種手段獨攬權力:1974 年頒布第806號法令成為共和國總統;1978年1月通過精心策劃的公民投票,獲得75%的民眾支持,繼續擔任總統職務;同年7月,逼迫軍官團內的對手空軍司令古斯塔沃·利將軍(Gustavo Leigh) 辭職,從此確立起個人統治的絕對權威。
在“國家安全學說”之外,軍政府受到以右翼法學家雷梅·古斯曼(Jaime Guzmán)為代表的“法團主義”思想的吸引。這種思想試圖幫助軍政府效仿西班牙佛朗哥政權,建立一種帶有法西斯主義色彩的排斥民主政治的威權主義政體。在以古斯曼為代表的右翼勢力的支持下,皮諾切特將軍制定和頒布了1980年憲法,用以取代1925年憲法。這部被軍政府稱為“自由憲法”的憲法為了增強軍政府的合法性,對智利未來政治經濟的發展作出兩個承諾:一是明確向民主過渡的期限,到1988 年將舉行公民投票以決定是否繼續由軍方執政,如果獲得通過,軍隊將再掌權8 年,如果未獲通過,軍隊將在1990年還政于民;二是承諾保護私有產權,規定除因國家的普遍利益、國家安全、公用事業、公共安全以及環境保護等因素的影響,私有產權不得侵犯。
但是,無論是“國家安全學說”還是“法團主義”,都很難為智利的政治和經濟改革提供明確的方向。首先,無論是好戰的反共主義還是帶有法西斯色彩的法團主義思想,都無法獲得國內各個政治集團的全面擁護,也很難得到美國和國際金融資本的支持。其次,這些學說也可能被其他政治集團利用以削弱軍人對權力的壟斷。最重要的是,這些學說無法為亟需扭轉嚴峻的經濟形勢的軍政府提供新的經濟發展模式。
軍政府執政之初,軍事執政團任命費爾南多·萊尼斯(Fernando Léniz)和勞爾·賽斯(Raúl Saez)執掌經濟部,領導經濟團隊,推行穩定計劃。萊尼斯等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縮減公共開支、降低工資、控制貨幣發行、減少流動資金、取消價格控制、降低關稅以及返還阿連德政府時期征收的私人企業等。但是,由于執行不力,加之受1973年第一次國際石油危機和國際市場銅價下跌等因素的影響,失業人口繼續增加,經濟困難無法得到緩解。在經濟穩定計劃受挫的同時,萊尼斯和賽斯對軍政府的政治高壓持有不同意見,認為軍政府若能減弱對政治反對派的鎮壓、釋放政治犯,會有利于尋求外部經濟援助[3]。軍事執政團無法容忍萊尼斯和賽斯的經濟團隊對其統治的異議,開始尋找其他經濟穩定方案,這就為“芝加哥弟子”登上歷史舞臺創造了條件。
二、“芝加哥弟子”
“芝加哥弟子”起源于20世紀50至60年代深受凱恩斯主義影響的拉美結構主義經濟思想和以現代貨幣主義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對拉美經濟發展中產生的問題的辯論。二戰以后,以勞爾·普雷維什(Raúl Prebisch)為代表的拉美結構主義思想影響了拉美的許多國家的經濟決策。拉美結構主義主張政府要通過積極干預經濟完成進口替代工業化,這個政策伴隨著貿易保護主義、操控匯率,并且要求采取土地革命、收入再分配等手段刺激消費需求、擴大國內市場。隨著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相繼出現“滯漲”的局面,主張實行自由市場經濟、反對國家干預、強調市場機制作用的現代貨幣主義向占據統治地位的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發起了挑戰。在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大力倡導下,現代貨幣主義以芝加哥大學為大本營,逐漸由理論進入實踐階段,開始影響與西方經濟有著密切聯系的拉美地區。
為了傳播芝加哥學派的新自由主義理論,1955年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主任西奧多·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來到智利,與基督教大學簽訂了一個學術計劃,選取一批學生到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接受研究生教育[4]。這批學生得到了弗里德曼等人的直接指導,成為現代貨幣主義的信徒,確信引入完整自由市場競爭經濟是解決智利發展問題的有效方式。完成學業后,大部分學生回到了智利,迅速在學界、經濟界和政界產生影響。在他們周圍,逐漸形成了一個擁有基本相同的經濟學觀點的技術專家群體,這就是“芝加哥弟子”的主要來源。
1968年,“芝加哥弟子”為準備參加競選的右翼政治家豪爾赫·亞歷山德里((Jorge Alessandri)起草了一份經濟計劃,主張開放的自由市場經濟、取消壟斷、鼓勵私有化、調整社會保障制度、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他們的主張遭到工商業階層的反對,被亞歷山德里擱置。阿連德政府上臺后的經濟混亂狀態使“芝加哥弟子”看到了希望,于是從1972年起開始舉行定期研討會。智利全國制造業協會主席奧蘭多·賽恩斯(Orlando Saenz)為他們提供了資金,并建議他們為未來可能的經濟改革作理論準備。此時,“芝加哥弟子”起草的經濟方案被稱為“磚石計劃”(The Brick),并且通過一份右翼報紙《水銀》(El Mercurio)引起了長期以來關注經濟事務的海軍上層的注意,就此將“芝加哥弟子”引入政府的決策部門。
“芝加哥弟子”認為,智利以往所推行的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戰略實行高關稅的貿易保護政策、過多的國家干預以及阿連德時期激進的國有化政策,使生產資源無法有效配置,壓制了私營企業的積極性,造成工業發展規模狹小、效能低下、國內市場狹小。“芝加哥弟子”認為應該徹底否定阿連德政府的政策,實行徹底而激進的自由市場經濟改革。“芝加哥弟子”為軍政府提供的計劃不僅著眼于經濟,而是通過經濟改革促進智利政治、社會、文化改革,進而產生有利于軍政府的結構性變化:縮減國營經濟和公共部門的規模將會削弱反對派的經濟基礎,將資源重新引向私人資本將會鞏固軍政府的政治基礎,經濟自由化改革會提供新的經濟增長手段以減輕政府對非競爭部門的財政支持,允許市場力量來調節工資將削弱勞工運動在政治上討價還價的能力,舊的政治效忠形式將被削弱, 而新的無階級形式和民族形式將會發展。 “芝加哥弟子”相信,運用自由市場的力量可以調節國家和社會的運行,消除通貨膨脹這個最大的經濟不穩定因素。不過,施行這樣的變革不可避免地會引發激烈的意識形態沖突和利益紛爭,因而需要在嚴格的威權主義控制之下才能完成。
芝加哥弟子為軍政府描繪的是一個理想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藍圖,滿足了軍政府解決經濟困難、鞏固長期統治的“合法性”需求。對于軍人來說,“芝加哥弟子”作為訓練有素的技術學家,能夠保障政府決策取決于技術與科學原則而非意識形態與政治,與軍人的價值觀相契合;對于工商業階層和中產階級而言,“芝加哥弟子”提供經濟平衡和社會秩序的許諾也是頗有吸引力的。更重要的是,“芝加哥弟子”改革方案來自美國學界,有助于得到美國政府的政治支持以及跨國公司和國際金融資本的經濟支持和直接投資。
1974年1月,軍政府解除了經濟部長賽斯的職務,同年7月任命豪爾赫·考阿斯( Jorge Cauas)為經濟部長。“芝加哥弟子”在政府和相關機構中逐漸獲得越來越多的職位,并開始逐步掌握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實施的權力。1975年3月,“芝加哥弟子”在智利基督教大學策劃了一個經濟研討會,邀請了弗里德曼、阿諾德·哈柏格(Arnold Harberger)等一批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在會見皮諾切特將軍時完全支持其弟子們的經濟改革計劃,這促使后者下定了決心。僅僅一個月后,“芝加哥弟子”中的領袖人物塞爾吉奧·德·卡斯特羅(Sergio de Castro)取代萊尼斯,成為財政部長,開始全面推行“經濟復興計劃”,這成為智利新自由主義改革開始的標志。
三、智利新自由主義改革的主要措施和成效
從1975年起,以“芝加哥弟子”為核心的經濟團隊從現代貨幣主義的理論出發,在智利進行了具有濃厚新自由主義色彩的經濟改革。這場變革不僅表現在經濟層面,而且涉及政治、社會和國家的作用等各個方面,為智利經濟的持續增長奠定了基礎。其改革的內容和成效如下。
(一)價格自由化
為建立市場調控機制,使經濟擺脫國家的直接干預,經濟改革首先采取價格自由化政策,即放松對價格的控制、減少政府定價的范圍、對價格補貼的幅度進行調整。然后在政府監督的情況下對私人部門生產的商品價格實行自由化,使資源在市場機制引導下進行合理配置,以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同時開放國內市場,實行貿易自由化,以平抑國內物價。從1973年到1978 年,受國家控制價格的商品從原來的2萬余種減少到8種,商品流通領域基本實現自由化[5]。
(二)金融自由化
智利在金融領域中的改革主要以市場的作用取代政府的干預,建立一個不受國家干預的自由化金融市場,使金融工具能夠在經濟改革中發揮積極作用。為此推行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放松利率管制、歸還過去政府接管的私人銀行并將國有銀行私有化、放寬信貸控制、取消外匯管制。
智利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資本大量流入和固定匯率政策使智利比索匯率被高估,加上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和墨西哥債務危機的影響,使智利難逃債務危機的厄運,釀成1982-1983年經濟危機,也導致了財政部長卡斯特羅被解職。經過幾年的整頓和調整,“芝加哥弟子”的第二位領袖埃爾南·布奇( Hernán Büchi)在1985年2月被任命為財政部長,開始扭轉在危機時期的資本管制和保護主義取向,健全金融體系,加強金融監管,使開放資本市場的措施與其他各項宏觀經濟政策和改革措施緊密配合,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三)貿易自由化
智利的貿易自由化主要是改變內向型的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模式,大幅削減關稅、降低或撤消非關稅壁壘,以提高生產率和資源配置效率,推動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1973年智利的平均關稅為94%,至1979年6月實現10%的統一關稅。債務危機期間關稅有所上調,但自1985年起關稅又逐步下調。在調整關稅的同時,智利基本取消了非關稅壁壘,促進了貿易自由化的發展,同時運用財政刺激手段擴大出口。
(四)經濟私有化
進口替代工業化模式使國家充當了發展經濟的主角,但大多數國有工業企業在政府補貼和貿易保護下效率低下、虧損嚴重,難以起到推動經濟增長的帶頭作用。“芝加哥弟子”推動的私有化改革,其目的是轉變國家職能,將經濟領域中的國有企業向私營經濟轉移,實現所有權的廣泛分配,充分發揮私營經濟的積極性,建立更有效的發展模式。智利私有化進程主要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1974至1980年。在把阿連德政府時期征收的企業和土地無償退還原主之后,軍政府采取了激進的私有化改革,導致生產資本和金融資本很快集中到幾家大財團手中。債務危機爆發后,私人企業由于資金短缺而大量倒閉,對經濟造成極大沖擊。政府不得不再次干預,將私有化的銀行和企業又收歸國有。
第二階段為1985至1989年。軍政府在總結前一時期私有化經驗的基礎上,采取程序化、規范化的手段重啟私有化進程,對企業股權的轉讓采取了靈活多樣的形式,并允許外國資本參與。這次私有化進程進行得較為順利,取得了明顯成效,極大地減輕了政府的財政負擔,降低了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參與,企業管理水平和經濟效益得到普遍提高,一個以活躍的私營經濟為主導的比較穩固的經濟體制得以建立。
經過以上的改革措施,智利在1984-1989年期間出現了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局面。1984-1989年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5.5%,其中1988年增長率為7.4%,1989年高達9%。鑒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拉美各國經濟普遍不景氣、經濟增長率平均僅為1%,可以說由“芝加哥弟子”領導的經濟改革總體上是成功的[6]。但在其實踐過程中也暴露出局限性以及負面影響,廣大中下階層人民為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付出了巨大代價。
四、結語
由“芝加哥弟子”領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為智利經濟的穩定和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而皮諾切特軍政府也憑著在經濟方面的良好表現得以用和平的方式完成了民主化的政權轉移過程。雖然“芝加哥弟子”的領袖布奇作為右翼政治集團的代表在1989年的大選中未能贏得選舉,但是1990年智利恢復文人制度以后的歷屆政府并沒有改變“芝加哥弟子”奠定的自由市場經濟路線。這不但保障了智利經濟發展的成果,也為民主化轉型后20余年經濟改革深化和穩定成長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智利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成為本地區率先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經濟體之一[7]。
智利改革成功的關鍵在于軍人政權和文人技術官僚實現了有效的協調與合作。一方面,軍政府特別是皮諾切特將軍本人極力保護“芝加哥弟子”不受工商業資本家、地主階級、軍隊內部的反對力量以及其它利益集團的干擾,放手讓“芝加哥弟子”去改革,并以強力的方式將決策者的意志和計劃滲透到全國。在1982-1983年債務危機爆發之后,一旦經濟情況有所好轉,皮諾切特將軍又重新讓智利向新自由主義改革軌道回歸。 另一方面,由卡斯特羅、布奇率領的“芝加哥弟子”充分發揮專業素養,全心全意地推進新自由主義改革,在債務危機爆發之后及時吸取教訓,調整激進政策,推進審慎的改革。
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往往是一個被“壓縮”的過程,意味著在同一歷史時空下,不僅要完成早期現代化國家經歷幾百年才得以完成的民族建設、國家建設、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等各項任務,而且還要滿足社會各個階級、階層和集團因受到先進國家示范效應的影響而成倍增加的對參與政治、分享資源和提升福利的要求。因此,一些發展中國家改革的失敗很大程度上在于其無法調和其內部始終存在的巨大的壓力和矛盾。發展中國家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或轉型的過程中,其發展戰略的選擇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智利軍政府統治時期軍人與技術專家共同推進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經驗表明:在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一個有權威的能夠對社會發展進程實施有力領導的中央政府,是社會變革時期能夠以較低成本獲取快速平穩發展的根本保證;改革的沖突在所難免,其成敗往往取決于政府的發展能在多大程度上吸收、消化改革的正、負面作用。
[1]Alfred Stepan.Rethinking Military Politics: Brazil and the Southern Cone[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14.
[2]萊斯利.貝瑟爾.劍橋拉丁美洲史:第八卷[M].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1998:364.
[3]Carlos Huneeus. The Pinochet Regime[M].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7:279.
[4]Patricio Silva. Technocrats and Politics in Chile: From the Chicago Boys to the CIEPLAN Monks[J].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1991,23(2):385-410.
[5]王曉燕.智利—拉美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先鋒[J].拉丁美洲研究,2004(1):30.
[6]Kees Koonings and Dirk Kruijt, Societies of Fear: the Legacy of Civil War, Violence and Terror in Latin America[M].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71.
[7]鄭秉文,齊傳鈞.智利:即將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首個南美國家—還政于民20 年及其啟示[M]∥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發展報告(2010-2011),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1-41.
2014-08-07
吳愷夫(1983- ),男,吉林長春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從事國際政治研究。
K153
A
2095-7602(2015)01-006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