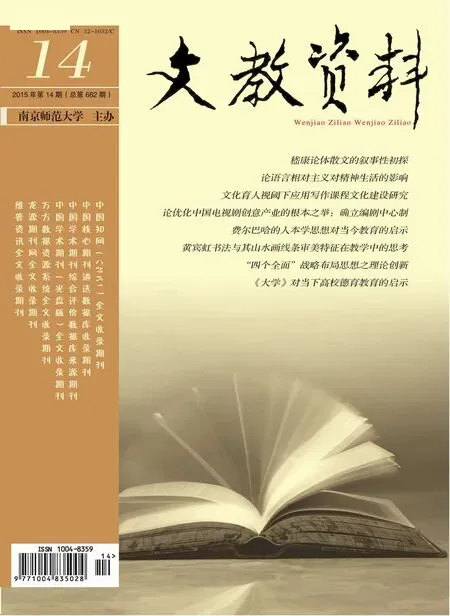論《烏有鄉(xiāng)消息》對(duì)“進(jìn)步”話語(yǔ)的質(zhì)疑
高 瑩 呂姝婧
(濰坊工程職業(yè)學(xué)院 語(yǔ)言學(xué)院,山東 青州 262500)
一、引言
十九世紀(jì),工業(yè)革命仍在英國(guó)大地上如火如荼地進(jìn)行著。不可否認(rèn),隨之而來(lái)的是英國(guó)在經(jīng)濟(jì)、科技和工業(yè)等各方面的飛速發(fā)展與巨大進(jìn)步。此時(shí),一些學(xué)者開始對(duì)工業(yè)革命所帶給英國(guó)社會(huì)的巨大進(jìn)步大肆褒揚(yáng)。例如,英國(guó)著名歷史學(xué)家、文學(xué)家及政治家托馬斯·巴賓頓·麥考利在撰寫的《自詹姆斯二世和威廉三世即位以來(lái)的英國(guó)史》(即 《英國(guó)史》)中不僅稱贊英國(guó)人民是“世界上最偉大、最有修養(yǎng)的人民”,而且斷言“進(jìn)步將在英國(guó)持續(xù)不斷地進(jìn)行下去”[1]156。(筆者譯)在這種社會(huì)環(huán)境下,“進(jìn)步”話語(yǔ)應(yīng)運(yùn)而生并成為此后一段時(shí)期內(nèi)的主導(dǎo)話語(yǔ)。然而,一些文學(xué)家自“進(jìn)步”話語(yǔ)一出現(xiàn)就對(duì)其提出了質(zhì)疑與挑戰(zhàn)。如以查爾斯·狄更斯、喬治·艾略特和威廉·梅克比斯·薩克雷為代表的一些英國(guó)作家清楚地意識(shí)到:在所謂的“進(jìn)步”的光環(huán)下其實(shí)隱藏著各種各樣的社會(huì)問題與危機(jī)。懷著高度的社會(huì)使命和責(zé)任感,他們?cè)谧髌分袑?duì)“進(jìn)步”話語(yǔ)進(jìn)行了質(zhì)疑。因此,這些作家通常被認(rèn)為是質(zhì)疑“進(jìn)步”話語(yǔ)傳統(tǒng)的先行者。
和其他偉大著作一樣,威廉·莫里斯的《烏有鄉(xiāng)消息》自從問世以來(lái)一直是學(xué)者們廣泛評(píng)論的焦點(diǎn)。學(xué)術(shù)界大多側(cè)重于從美學(xué)、文藝學(xué)、建筑、藝術(shù)、人生觀、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觀等角度剖析該作品的重要意義,特別是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觀角度更是學(xué)者們?cè)u(píng)判作品成功與否的重要切入點(diǎn)。例如,英國(guó)20世紀(jì)著名學(xué)者喬治·道格拉斯·霍華德·科爾就曾指出:一方面,莫里斯在這部小說(shuō)中為人們呈現(xiàn)了實(shí)現(xiàn)共產(chǎn)主義的奮斗目標(biāo),另一方面,莫里斯從一開始便意識(shí)到該小說(shuō)無(wú)法被當(dāng)做是“對(duì)未來(lái)社會(huì)的預(yù)言”。在科爾眼中,莫里斯的社會(huì)主義觀無(wú)疑是“不可救藥地陳舊與迂腐的”[2]2。(筆者譯)文化學(xué)大師雷蒙·威廉姆斯認(rèn)為:《烏有鄉(xiāng)消息》阻礙了莫里斯社會(huì)主義觀的進(jìn)步,因此這部小說(shuō)不具有可行性[3]159。然而,筆者認(rèn)為,我們?cè)趯?duì)該作品的價(jià)值進(jìn)行評(píng)析時(shí),應(yīng)將其產(chǎn)生的社會(huì)背景考慮在內(nèi)。事實(shí)上,《烏有鄉(xiāng)消息》誕生之時(shí)正是“進(jìn)步”話語(yǔ)與反“進(jìn)步”話語(yǔ)呼聲并存與對(duì)抗之時(shí)。莫里斯則義無(wú)反顧地加入了質(zhì)疑“進(jìn)步”話語(yǔ)的作家行列,延續(xù)了英國(guó)小說(shuō)家們對(duì)“進(jìn)步”話語(yǔ)質(zhì)疑的傳統(tǒng)。
與其他質(zhì)疑“進(jìn)步”話語(yǔ)的小說(shuō)相比,《烏有鄉(xiāng)消息》的新穎之處就在于它對(duì)夢(mèng)境形式的運(yùn)用和對(duì)威廉姆·格斯特這一特殊人物形象的塑造。首先,夢(mèng)境的形式為小說(shuō)敘述者格斯特進(jìn)入一個(gè)全新的“烏托邦”理想社會(huì)并最終返回他所生活的19世紀(jì)末英國(guó)資本主義社會(huì)開辟了通道。其次,格斯特這一名字暗示終究有一天小說(shuō)敘述者要從夢(mèng)境中醒來(lái),重新面對(duì)19世紀(jì)末罪惡的資本主義社會(huì)。然而,與傳統(tǒng)意義上的“客人”不同,小說(shuō)敘述者抵達(dá)“地上樂園”的真正目的不在于享受或者游山玩水,而在于探索與追尋。最終,格斯特作為“客人”行走于新舊兩個(gè)世界之間,不斷地揭示著未來(lái)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和十九世紀(jì)末資本主義社會(huì)之間的巨大差異。筆者認(rèn)為,《烏有鄉(xiāng)》對(duì)“進(jìn)步”話語(yǔ)的質(zhì)疑主要體現(xiàn)在莫里斯對(duì)新舊世界中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和人際關(guān)系兩個(gè)方面差異的對(duì)比上。
二、對(duì)“進(jìn)步”話語(yǔ)的質(zhì)疑
19世紀(jì)末,隨著英國(guó)工業(yè)化進(jìn)程的加快,不少社會(huì)問題也出現(xiàn)了。作為一位極富洞察力的作家,威廉·莫里斯清楚地意識(shí)到:在“進(jìn)步”面具的掩蓋下,工業(yè)化已經(jīng)打破了人與大自然間原本的和諧關(guān)系。首先,這時(shí)期的英國(guó)人認(rèn)為大自然與人類是相分離的,甚至堅(jiān)持大自然應(yīng)該屈服于人類的意志,人類定能戰(zhàn)勝大自然。在《烏有鄉(xiāng)》中,莫里斯借克拉娜之口對(duì)人們這一錯(cuò)誤認(rèn)識(shí)進(jìn)行了清晰的展現(xiàn):“他們將所謂的‘自然’當(dāng)作一種東西,而把人類當(dāng)作另一種東西。具有這種觀點(diǎn)的人當(dāng)然會(huì)企圖使‘自然’成為他們的奴隸,因?yàn)樗麄冋J(rèn)為‘自然’是在他們之外的東西。 ”[4]223其次,在莫里斯生活的年代,大批人為囤積物質(zhì)財(cái)富而不擇手段,不惜以殘忍地破壞大自然為代價(jià),正如哈蒙德在《烏有鄉(xiāng)》中所敘述的那樣:“接近十九世紀(jì)的末期,鄉(xiāng)村差不多全部消滅了,除非它成了制造業(yè)區(qū)域的附屬地帶,或者本身變成了一種較小的制造業(yè)中心。人們聽任房屋損壞傾頹;為了粗劣的木柴所能換到的幾個(gè)先令,人們肆意砍樹。建筑物變得難以形容地丑陋難看。”[4]89格斯特一針見血地指出:某個(gè)團(tuán)體中的一些成員“為了表示他們沒有閑著,就隨時(shí)隨地做一些破壞的事情;像砍伐樹木,從而毀壞了河岸;疏浚河道(總在不需要疏浚的地方進(jìn)行),而把挖出來(lái)的東西堆在田地上,使田地受到損害,等等”[4]246。
然而,格斯特在“烏托邦”社會(huì)中看到的是另外一番景象。剛剛踏入新世界,他便驚奇地發(fā)現(xiàn):“那肥皂廠和它的吐著濃煙的煙囪不見了;機(jī)械廠不見了;制鉛工廠不見了;西風(fēng)再也不再由桑奈克羅弗特造船廠那邊傳來(lái)釘打錘擊的聲響了。”[4]9在反復(fù)與19世紀(jì)末的英國(guó)資本主義社會(huì)進(jìn)行比較后,他清楚地感受到在那花園般的社會(huì),大自然已經(jīng)不再淪為人類的奴隸,人類深深地依戀并熱愛著他們棲息的每一寸土地。人們悉心呵護(hù)大自然,“喜歡看見所有的東西都十分整齊清潔,井井有條,明朗軒敞”;“在和大自然打交道的時(shí)候,凡是不合理的,他們就要加以改變。 ”[4]91“烏托邦”社會(huì)中人們的出行方式極為環(huán)保,他們不會(huì)選擇乘坐工業(yè)化的產(chǎn)物——冒著黑煙的蒸汽火車,而是選擇劃船或者乘坐馬車。當(dāng)許多學(xué)者對(duì)工業(yè)化進(jìn)程所帶來(lái)的“進(jìn)步”與“文明”大肆稱贊時(shí),莫里斯卻在《烏有鄉(xiāng)》中啟發(fā)讀者們對(duì)人與自然之間關(guān)系的思考,這恰恰有力地證實(shí)了他對(duì)“進(jìn)步”話語(yǔ)的質(zhì)疑與挑戰(zhàn)。
《烏有鄉(xiāng)》中所刻畫的“烏托邦”社會(huì)的魅力不僅體現(xiàn)在人與自然間的和諧相處上,而且體現(xiàn)在平等和諧的人際關(guān)系上。隨著19世紀(jì)工業(yè)化進(jìn)程的步伐不斷加快,資產(chǎn)階級(jí)與無(wú)產(chǎn)階級(jí)間的差距越來(lái)越大,他們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資產(chǎn)階級(jí)每天無(wú)所事事,靠剝削無(wú)產(chǎn)階級(jí)囤積大量財(cái)富,享受著奢侈生活;無(wú)產(chǎn)階級(jí)起早貪黑,終日勞作,卻仍舊無(wú)法擺脫貧困與饑餓的困擾。這時(shí),即便是同一階層的人們之間也存在著疏遠(yuǎn)與隔離。只有在利益與金錢的驅(qū)動(dòng)下人們才會(huì)主動(dòng)與別人交流,否則他們更傾向于將自己與外界隔離起來(lái)。一旦涉及利益的沖突,所謂的“友誼”就會(huì)瞬間分崩離析。工業(yè)化的進(jìn)步非但沒有拉近人們之間的距離,反而使原本的溫情與愛消失殆盡,并培養(yǎng)出了越來(lái)越多的偽君子。哈蒙德曾對(duì)此現(xiàn)象進(jìn)行了極為精辟的總結(jié):“十九世紀(jì)的人是偽善者,他們表面上裝得很仁慈,可是不斷地在虐待那些他們膽敢虐待的人,把這些人無(wú)緣無(wú)故地送進(jìn)監(jiān)獄。”[4]54此外,性別歧視也充斥著這個(gè)所謂的“進(jìn)步”社會(huì)。女性追求平等的呼聲越來(lái)越高,“婦女解放運(yùn)動(dòng)”此起彼伏。然而,莫里斯在《烏有鄉(xiāng)》中卻為讀者構(gòu)建了一個(gè)充滿溫情與愛的理想社會(huì)。在那里,虛偽與狡詐不見了蹤影,每個(gè)人都熱情好客,善于溝通。格斯特所到之處都受到了當(dāng)?shù)厝说氖⑶榭畲@甚至讓一向生活在冷冰冰社會(huì)中的他一開始感到有些不自在。很快,他就發(fā)現(xiàn)熱情好客、真誠(chéng)待人其實(shí)是當(dāng)?shù)厝说囊环N習(xí)慣。在新世界中,沒有階級(jí)分化和階級(jí)沖突,真正實(shí)現(xiàn)了男女平等。男女工人和諧地在一起工作,手工作坊與其說(shuō)是生產(chǎn)產(chǎn)品的場(chǎng)所,不如說(shuō)是大家暢快交流之地。女性還可以自由選擇職業(yè)和愛情。例如,克拉娜在發(fā)現(xiàn)自己已經(jīng)不再愛迪克之后,提出了分手,但她的這項(xiàng)決定并沒有受到他人的指責(zé)與非議,因?yàn)樵诋?dāng)?shù)厝丝磥?lái),女性同樣擁有追尋幸福與尋找真愛的權(quán)利。通過對(duì)19世紀(jì)末英國(guó)資本主義社會(huì)中扭曲的人際關(guān)系與理想社會(huì)中平等和諧的人際關(guān)系進(jìn)行比對(duì),莫里斯成功地實(shí)現(xiàn)了對(duì)“進(jìn)步”話語(yǔ)的質(zhì)疑與挑戰(zhàn)。
三、結(jié)語(yǔ)
《烏有鄉(xiāng)》可以被看做是一部延續(xù)了英國(guó)小說(shuō)家質(zhì)疑“進(jìn)步”話語(yǔ)傳統(tǒng)的偉大著作,并彰顯了莫里斯深刻的人文關(guān)懷。直至今天,莫里斯的思想對(duì)我們飛速變革、發(fā)展的中國(guó)社會(huì)仍頗具啟發(fā)意義。當(dāng)享受著所謂的社會(huì)“進(jìn)步”帶來(lái)的各種便利時(shí),我們是否應(yīng)該靜下心來(lái)對(duì)當(dāng)下人與大自然的關(guān)系和人際關(guān)系方面所存在的突出的社會(huì)問題進(jìn)行深刻的反思呢?毫無(wú)疑問,莫里斯在一個(gè)多世紀(jì)之前創(chuàng)作的《烏有鄉(xiāng)》中已經(jīng)為我們提供了答案。
[1]Maline,JulianL.and James Berkley.Visionaries and Re alists,1789-1900[M].New York:L.W.Singer Company,1967.
[2]Cole,G.D.H.William Morris as a Socialist[M].London:William Morris Society,1960.
[3]Williams,Raymond.CultureandSociety1780-1950[M].Harmondsworth:Penguin,1971.
[4]莫里斯.黃嘉德,譯.烏有鄉(xiāng)消息[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6.
- 文教資料的其它文章
- 國(guó)內(nèi)外關(guān)于自主聽力的研究
- 網(wǎng)絡(luò)教學(xué)環(huán)境下高中生英語(yǔ)自主學(xué)習(xí)能力研究
- 大學(xué)英語(yǔ)教師網(wǎng)絡(luò)信息素養(yǎng)調(diào)查與對(duì)策研究
——以南通地區(qū)高校為例 - 淺析中小學(xué)教學(xué)中存在的兩大問題
- 南通大學(xué)醫(yī)學(xué)專業(yè)大學(xué)生專業(yè)滿意度調(diào)查
- 助力困難學(xué)生生涯發(fā)展,開創(chuàng)就業(yè)幫扶新模式
——來(lái)自徐州工業(yè)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就業(yè)幫扶的成功實(shí)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