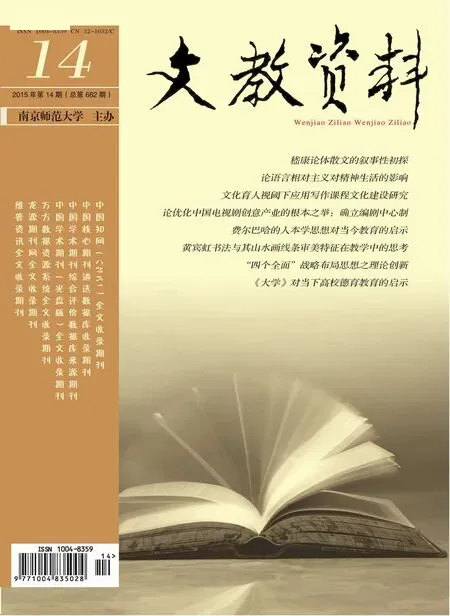論《士兵突擊》作為時代精神寓言的標本價值
李超
(湖北師范學院 文學院,湖北 黃石 435002)
論《士兵突擊》作為時代精神寓言的標本價值
李超
(湖北師范學院 文學院,湖北 黃石 435002)
《士兵突擊》以普通士兵和軍營生活為載體講述故事,樸素的人物和故事背后包含的是信念的堅守和不屈的精神,作品樹立的是堪稱時代精神寓言的標本價值。
《士兵突擊》 精神寓言 標本價值
《士兵突擊》改編自話劇《愛爾納·突擊》,編劇是蘭曉龍。2003年在第八屆中國戲劇節(jié)上,《愛爾納·突擊》獲得曹禺戲劇文學獎劇目獎、優(yōu)秀導演獎等多項大獎。2005年話劇《愛爾納·突擊》還獲得第三屆老舍文學獎優(yōu)秀戲劇劇本獎。以優(yōu)秀的文學劇本為藍本的電視劇 《士兵突擊》于2006年上映,上映后作品沒有讓人失望,引起熱烈反響,并先后獲得第27屆飛天獎、第24屆金鷹獎優(yōu)秀電視劇獎等多個獎項。
那么,一部軍旅題材電視劇為何有如此反響,引起民眾、影視甚至學術界的廣泛討論?《士兵突擊》的編劇蘭曉龍在參加中央電視臺《藝術人生》欄目,談到劇本的創(chuàng)作時說道:“《士兵突擊》創(chuàng)作的靈感來自于自己觀看的一次話劇,話劇講述了一個連隊改編的故事,這個話劇讓我很受感動,而后我了解到這個劇竟然是由一個真實的故事改編而成的。”①也就是說,作品本身的立意和素材來源于真實的生活,這使得作品從創(chuàng)作伊始就扎根實際,超越虛構空想的層面,更重要的是,作品樹立的是堪稱時代精神寓言的標本價值。
一、“不拋棄、不放棄!”——超出故事本身意義的人生哲理
《士兵突擊》講述了一個農(nóng)村出身的類似于“阿甘”的普通士兵許三多從鄉(xiāng)村到軍營的成長故事。作品以士兵許三多的經(jīng)歷為主線,以他所在的草原五班、鐵血鋼七連、老A等場景為故事發(fā)生地,細致、用心刻畫了一系列真實感頗強的人物,愚拙如許三多,精明如成才,高傲如連長高城,深邃如袁朗……描繪出了一幅鮮活生動的當代軍人群體形象畫面。作品著重突出許三多在軍隊嚴酷的訓練中歷經(jīng)磨難,隨著人事變遷自身不斷成長蛻變,不拋棄、不放棄,最終成為一名出色的特種兵。觀眾在作品中很容易看到自己的影子,作品對于個人內(nèi)心的自卑感、每個人為實現(xiàn)夢想的拼搏精神的著筆刻畫,讓人產(chǎn)生共鳴,并迸發(fā)出踏實干事、自強不息的正能量。
上海大學影視學院石川教授評論這部作品時說:“看《士兵突擊》,就好像一個進入城市的白領冷不丁想起自己的農(nóng)村生活,遭遇久違的價值觀。”石川教授貌似隨筆,卻指出了作品最本質(zhì)的藝術支撐點,即價值觀的久違和認同,這是切中觀眾情感和內(nèi)心需要的關鍵點。這種價值觀在作品中濃縮為“不拋棄、不放棄!”的六字箴言,這六個字原為“鋼七連”的立連根本,但是,經(jīng)過許三多在不同環(huán)境下的演繹,這貌似遠大和久遠的精神性符號得以落地,讓人覺得真實并產(chǎn)生情感共鳴。這六個字已經(jīng)遠遠超出了個體本身所表達的意義,這種超越可貴而又著實不易,仔細梳理和分析,這種超越源于作品所要表達的價值觀在三個層面的延伸。
從第一個層面看,主人公許三多從懵懂愚笨的農(nóng)村少年參軍,落荒到草原五班,執(zhí)著踏實修路成名,到七連后從“孬兵”做起一路成長為兵王,再到老A經(jīng)受住了嚴酷考驗,最終成長為出色的特種兵,從農(nóng)村少年到特種兵,這種歷練的過程是個體的堅守,同時是封閉的農(nóng)村少年開始接受外世價值觀影響后個體精神層面的升華,這是價值觀的第一次延伸;從第二個層面看,從許三多這一個體延伸開來,“不拋棄、不放棄!”本身是七連的立連之本和驕傲根源,許三多不斷經(jīng)歷人事變遷及后來經(jīng)歷嚴酷選拔來到特種大隊后,這一價值觀被無意識延伸到軍營的不同場景并被其他人接受,這是“不拋棄、不放棄”所代表的價值觀在高一層面上的群體意義上的延伸;第三,從受眾角度考慮,有一組數(shù)據(jù)頗能說明問題,山東師范大學的張麗軍教授做過這樣的統(tǒng)計:“《士兵突擊》上映一年來,關于《士兵突擊》的感想有30多萬條,關于許三多的有169萬條,發(fā)帖量很大。”②精彩故事濃縮形成的價值觀是引發(fā)觀眾內(nèi)心共鳴和深存觀眾腦海中的主體信息,這更是作品傳達的價值觀在更廣泛意義上的延伸。作品由“不拋棄、不放棄!”所凝結成的價值觀的三個延伸構成了其立身和具備持久藝術生命力的根本。
二、“好好活,做有意義的事”——循環(huán)論證的樸素真理
作家史鐵生在《中國青年報》上評論作品時說道:“許三多的憨話妙語:人要做有意義的事情。有意義就是好好活著。好好活著就是要做很多有意義的事。這看似可笑的循環(huán)論證卻著實道出了一個樸素的真理。”
回顧作品我們發(fā)現(xiàn),這句“顛倒”的話語最先出自班長史今之口,只不過這是他在拒絕許家人當兵要求時為了安慰許三多說出來的冠冕之詞,但是,這句話后來被許三多的父親許百順在送兒子當兵時的火車站,作為離別贈言送給了兒子后,許三多便牢記于心。從新兵連直接發(fā)配身處草原身處的五班后,面對戰(zhàn)友的消極和無聊度日,他通過看似愚笨的“修路”將這一人生信條落實為行動并收獲了成功,從此,這一人生信條更是扎根于許三多內(nèi)心,在后來的整個軍營生活和人生道路上化為人生基石再未有所改變,當然,許三多并不是因為收獲到了物質(zhì)或者名譽之上的成功才有目的性地堅守,這種執(zhí)著是源于主人公內(nèi)心真正找到的人生的目標感及由此轉化為力量產(chǎn)生的源泉。特別是在許三多來到老A隨隊友執(zhí)行第一次任務時有一個細節(jié)頗值得玩味:當面對手持手雷劫持女人作為人質(zhì)的毒販時,許三多赤手空拳,但是許三多用簡短的幾句話對毒販試圖做說服工作,許三多說:“你把那個放下,你這樣活沒意義。”毒販聽到這句話后喟然一笑,一向木訥口拙的許三多在極端環(huán)境下最先想到的就是自己視為真理并試圖傳達給他人的“好好活,做有意義的事”。只不過最簡單的真理在以命相搏的毒販看來空虛而又可笑。當這種堅守化為內(nèi)心力量的來源和基石后,他就不再局限于軍營和戰(zhàn)爭場景下的行為準則,他放之四海而皆準成為了個體化解困難和處理問題的正確方式,所以從七連解散后許三多獨自一人看守連部半年,到家庭遇到重大變故肩扛重擔,這些都是遇到的軍事訓練意外的新的問題,但他都一一挺了過來,雖看似愚笨,但事實證明,恰恰是這一樸素的人生信陪伴他成長并度過了一個又一個溝坎。
我們說,生活中的事情,看似快,實則慢,說的就是這個道理,看似聰明的我們實際于人于己周旋的多是脫離根本的“繞路”之舉,剖析一下這種心理,這與“市場化和利益化,掩蓋了的一種擺不上臺面的價值偏向”有相當大的關系。史鐵生說:“意義就是一種善和美的維度。追求有意義的生活,追求善和美的維度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本能,是支撐、呵護我們內(nèi)心的東西。”
《士兵突擊》導演康洪雷在接受采訪時曾談道:“許三多骨子里流露出的是中國優(yōu)秀的農(nóng)耕文明,許三多是一個最強大的人,他的智商要比我們所謂的聰明人要高得多,他是唯一讓我們汗顏的人。他讓我們反思我們的生活方式,回過頭來尋找我們的傳統(tǒng)。”③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是一種生活哲學。許三多強調(diào)的“好好活著,要做有意義的事”由他的父親真正鑲嵌入他的心底,溯源而上,這股力量是從鄉(xiāng)土中國的背景產(chǎn)生而來,許三多雖無意識,但是他在鄉(xiāng)土中國文化中尋找意義,這擺脫了個體生存需要和法則的層面,這更帶有一種象征與寓言的味道。
三、成長之痛和孤獨面對——直戳時代匱乏的精神痛點
《士兵突擊》講述的是一個成長的故事,故事中伴隨主人公的每一次環(huán)境的改變都代表著成長,下榕樹、五班、七連、老A,他們不再是簡單地代表一個個獨立的場景,它們得以牽連成為許三多、成才、伍六一等人物一次次直面孤獨和成長之痛后的見證和印記,當許三多在七連改編后獨自堅守的半年里,在一向剛強,對加入老A欲望極強的伍六一面對考核的最后三十米時,因為自己受傷不想拖累許三多自己拉響求救彈后,這故事的處理和苦處,使個體成功與否的概念得以淡化,概念落腳成一個道理:即個體每一次不能接受或者試圖接納的不單是成長而是自己。
《士兵突擊》處理的是兩個非常深刻的、具有普遍性的命題:個體如何面對成長及成長不可避免的孤獨,和一個人如何面對生命中重要的人和環(huán)境與自身的剝離。當我們看到許三多面對班長史今的離去而痛苦,面對七連的解散無助卻不得不一個人堅守的時候,這種面對孤獨學會成長和面對珍惜的人和事一一離開卻無所適從的感覺,從情感上產(chǎn)生的共鳴是相當強烈的。《士兵突擊》之所以拍出來了吸引人的內(nèi)容,激烈的時候它吸引人,平淡的時候它更吸引人,靠的就是對人性中深處的力量的挖掘。
相當容易形成比較的是,當生活的節(jié)奏不斷加快,現(xiàn)實的我們正愈來愈遠的脫離這種堅守和呵護,試想還有什么會在我們的內(nèi)心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記,還有什么可以真正成為值得我們堅守和不舍的留戀。從作品創(chuàng)作角度考慮,這不單是《士兵突擊》對藝術和生活平衡點的精準把握之處和成功之道,它只是真情的表達和流露,這種成長和真情簡單而又真實,卻是急于渴望成功和速成的現(xiàn)代人容易忽視和淡忘的精神關懷。
文學作品和影視劇同根同源,現(xiàn)實主義在文學作品中的描寫,再展現(xiàn)于影視劇中除了注重表面器物、服飾、語言等表面的吻合,更應該重視情感和精神層面的還原和再現(xiàn)。與傳統(tǒng)的軍事題材電影一樣,《士兵突擊》也不乏武器,戰(zhàn)爭、演習等頗具畫面沖擊力的戰(zhàn)斗場面,但是,作品里邊真正最吸引人的地方卻不在于此,作品用樸實的語言描述事實,故事情節(jié)如同語言一樣循序漸進地展開,這種平實的背后是精準的精神和力量的傳達。當然,《士兵突擊》也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例如過于完美化的表達欲望讓作品有過猶不及之感,極個別情節(jié)設置之處的不合理,但是單就現(xiàn)實主義表現(xiàn)手法來說,《士兵突擊》作為藝術加工沒有丟失最可貴的真實性,而且做到了真實之上的精神性的提升。
從媒體的角度看,《士兵突擊》的熱潮似乎已經(jīng)過去了,但是,真正以精神、情感、價值為支撐的藝術作品是具備持久的藝術生命力的,它可以經(jīng)受得住時間的考驗而常說常新,這樣的作品也不會淹沒于時間的洪流,我們更應該要做的是從人文關懷意識和時代精神狀況角度使之存于人們的視野和藝術瀚海之中。
注釋:
①中央電視臺.藝術人生,2007年12月05日
②張麗軍.士兵突擊與時代精神狀況[J].藝術廣角,2008,(04).
③康洪雷.拍電視劇是抒發(fā)我內(nèi)心真實的通道[J].中國文化報,2010.
[1]蘭曉龍.愛爾納·突擊[M].法律出版社,2015.
[2]蘭曉龍.士兵突擊[M].花山文藝出版社,2007.
[3]孫曉燕.士兵突擊人物形象解讀[D].首都師范大學,2009.
[4]王志明.突擊:從話劇到電視劇——比較《愛爾納·突擊》與《士兵突擊》.電影文學,2009(09).
[5]張麗軍.士兵突擊與時代精神狀況[J].藝術廣角,2008(04).
[6]張海生.探究《士兵突擊》的多重價值[J].作家,200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