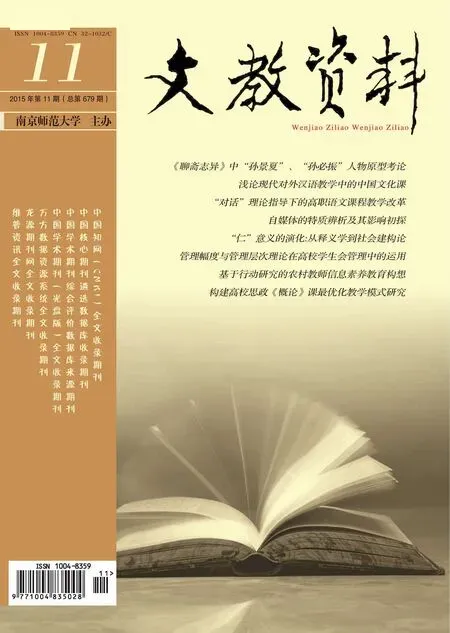對翻譯本體的幾點思考
高文峻
(廣東農工商職業技術學院 外語系,廣東 廣州 510507)
一、譯者翻譯的動力何在
翻譯工作,無論筆譯還是口譯,都是一種勞動,需要持續地運用身體機能。
缺少來源于興趣或來源于利益 (獲得利益最終也是為了滿足譯者的某些興趣或欲求)的內在驅動力,譯者是無法啟動的。具體有哪些驅動力呢?或許有以下幾種:
(一)外語原作精彩、有內涵。譯者本人深得閱讀該作之趣或深受啟發、為其折服,欲讓不諳原文的目標語讀者共享。這種動力比較原始,是一種純粹的分享欲,尤其在朋友間常見。
(二)外語原作在世界文壇或學術界取得成功,贏得了眾多原語讀者的稱贊;或者獲得了像諾貝爾文學獎這樣的國際性獎項。在此情況下,即便譯者本人不甚喜歡該作品,也會在國內讀者的巨大期待中欣然動筆翻譯。
(三)職業譯者。翻譯是他/她的全職工作,當長期合作的出版社指定一部作品希望其來翻譯時,職業精神使得他/她便不推辭地答應了。譯博爾赫斯多部作品和杰克·凱魯亞克小說《在路上》而廣為人知的王永年就在此列,盡管他坦言并不喜歡凱魯亞克的作品。
(四)還有一些出于其他現實動力而進行的翻譯,如為了評職稱、完成科研工作量或兼職賺點譯文稿費等。
二、原文是否可譯
翻譯行為是不是一種無用功?與此問題緊密相連的乃是另一個問題:原作究竟可否譯成另一種語言?對此在翻譯界(包括翻譯理論界)有兩種對立的看法——可譯論和不可譯論。
哪些人持可譯論,哪些人又是持不可譯論的呢?具體到人群的歸類,筆者嘗試分析如下:
(一)從事翻譯工作的譯者基本上都是持可譯論者。否則,他們若認為不可譯的話就不會去進行翻譯實踐了。
(二)在不從事或者較少從事實際翻譯操作的翻譯理論工作者中,大多數人屬于可譯論陣營。此陣營中還可細分為:(1)完全的可譯論者(如功能對等派等)。 (2)部分可譯論者。即主張除了詩詞等藝術性、文學性高的文本不可譯外其他文本可譯的學者。他們認為“語言的可譯度是不相同的。工具性語言可譯度很高,思想性語言可譯,但難度極高,而文學性語言則幾乎不可譯”。 (朱恒,2015:8)(3)承認詩詞等藝術性高的文本難譯,要運用專門對策處理這些文本的有條件可譯論者。
(三)在不從事或者較少從事實際翻譯操作的翻譯理論工作者中,少部分人屬于不可譯論者,如解構主義者和哲學解釋學派等。他們或是運用“延異”、“不在場”等概念強調原文文本的不可把握和不可復制性;或是通過剖析原文本產生時的復雜心理過程,揭示出原文本不一定就表達出了原作者最本真的意思。這樣,在他們看來,去翻譯本來就不確定的原文是徒勞的,沒有意義的。原作是不可譯的。
三、譯文是否需要完全忠實于原文
(一)認為譯文需要對原文完全忠實,用“信達雅”作為標準,首先強調“忠”(即“信”)的,仍是目前的主流意見。二十世紀很有影響力的語言學家喬姆斯基認為,不同語言之間存在著一種共通的深層結構(deepstructure),透過原語可以抵達這種深層結構,譯文對原文完全忠實就體現在,目標語就是要把這種深層結構表達清楚。另一位著名的語言學家奈達深受喬姆斯基上述學說的啟發,他用了自創的一個術語“核心句”(kernelsentence)來表達“深層結構”這個意思,在他看來,好的翻譯就是功能對等的忠實翻譯,其標志就是目標語要把蘊涵在原語里的“核心句”清楚準確地還原出來。
(二)目前學術界存在一種認為譯文無需對原文完全忠實的趨勢。這種趨勢主張運用更寬容的視野,更著眼于用歷史的、具體的眼光理解當時譯者的處境和用意,認為有時譯文不完全忠實于原文也是合情合理的。“合情合理”的情形或許有以下幾種:
1.譯文受制于當時強大的政治壓力,想避免被取締的風險,所以先考慮如何扎根下來,再謀求進一步發展。例如,佛經剛譯入中國時,不得不暫時部分引入原文中沒有的例如“孝”、“忠”等儒家概念。“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佛家弟子要剃須發、不娶妻(不娶便無后,而‘不孝有三,無后為大’)、不敬養父母等,完全違背了孝道;而佛教主張的出世主義則不理民生、不事王事、不敬王者等,又完全違背了忠道。這一切都與在本土文化中占主導地位的儒家“忠孝”意識形態直接沖突。為了攀附儒教,佛經翻譯只好入鄉隨俗,因入儒家思想。”(王東風,2003:18)如果說譯文不作改寫,完全忠實于佛經原文,任由其與官方主流意識形態沖突的話,就很可能此譯本根本就無法面世了。因為“統治階級對于佛經翻譯的扶持也不是盲目,對于那些有違其意識形態的譯本則是堅決壓制,如宋真宗就認為佛教經典《金剛薩綞說頻那夜迦天成就儀軌經》有違儒家的‘仁恕之道’而令其不得入藏頒行,而且明令今后不許再翻譯有類似內容的經典”。(楊曾文,2001:459-460)
2.譯文是懷著高遠抱負的譯者的“別有用心”的“不忠”。例如嚴復,學貫中西,英文造詣很高,本來要做到譯文忠實原文是很容易的事,但他為何要在翻譯時故意對原著進行不少的刪改和“修正”而落下“不忠”的罵名呢?“他之所以這樣做并不是因為他的英語理解能力不濟,而是有著他作為一個啟蒙思想家的‘政治議事日程’,那就是為我們這個已被西方列強逼到絕境的泱泱中華敲響警鐘,對那些仍然沉浸在中世紀美夢的封建士大夫進行思想啟蒙。經過嚴復‘歪曲’或‘改寫’的《天演論》中的思想,與他在此之前發表的……四篇論文的思想構成一體,闡發了尊今叛古、尊民叛君、‘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思想……尤其是他引進了‘法治’憲政思想,這是包括‘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先驅所未注重的,然而這恰恰是民主與自由的保證,是中國最缺乏的思想。這種具有政治家和思想家的高屋建瓴的理論提煉功夫顯然不是只精通西語的翻譯家所能做到和理解的。”(王東風,2003:21)
3.譯者的主體性使然。譯者的主體性包括三個部分,即不受任何約束的自然屬性(或“本我”);調節不羈的“本我”和原作之間達成妥協,展現譯者對文本解釋性和創造力的心理屬性(或“自我”);高度理性,代表譯者完美而不快樂地過于注重原作的文本意義和讀者的反應,從而找不到譯家的翻譯風格的社會屬性(或“超我”)。 (劉軍平,2008:53)所以,譯文中必然有譯者“本我”和“自我”部分自由發揮而部分地僭越了原作的內容。“在我們看來,……沒有譯者創造性的干預,讀者從原文中將一無所獲。”(劉軍平,2008:53)譯村上春樹的林少華就屬此列。他并不諱言其強烈的想寫作、想創作的“本我”沖動是其翻譯的主要動力之一,并坦然面對有些評論者對其不少譯文不完全忠實于原作的批評。
4.如果說上述第三種是受強烈的內在表達欲所驅動的熱情的不忠的話,還有一種是譯者冷靜思考后所選擇的不忠。當譯者為了照顧目的語讀者的價值觀、審美觀和語言表達習慣時,他/她就有可能選擇不保持與原作一樣的評價標度;就有可能增加原著沒有的評價意義,或減去原著的評價意義。(張美芳,2002:27)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譯者的價值觀和原作中的評價意義一樣,是一定的文化體系的產物”。(張美芳,2002:15)換句話說,就是譯者并非生活在真空中從事翻譯工作的,他/她在一定程度上是身不由己,是受到外部條件嚴格制約的。這些制約條件包括在譯者某個具體的翻譯行為發生時譯入語國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詩學范式和翻譯行為的贊助者的意圖等因素。所以譯文需不需要對原文忠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忠實,這也是譯者本人綜合考慮各方面利害得失之后自己理性選擇的結果。
[1]朱恒.語言的維度與翻譯的限度及標準[J].中國翻譯,2015(2).
[2]王東風.一只看不見的手——論意識形態對翻譯實踐的操縱[J].中國翻譯,2003(5).
[3]楊曾文.宋代的佛經翻譯[A].楊曾文,等編.佛經與歷史文化[C].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轉引自王東風.一只看不見的手——論意識形態對翻譯實踐的操縱[J].中國翻譯,2003(5):19.
[4]劉軍平.從跨學科角度看譯者主體性的四個維度及其特點[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8(8).
[5]張美芳.語言的評價意義與譯者的價值取向[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