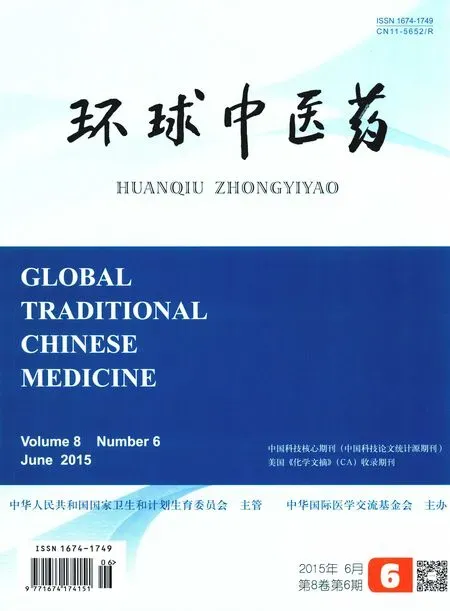魯衛(wèi)星衷中參西治療心血管疾病經(jīng)驗
張淼
魯衛(wèi)星教授,北京市朝陽區(qū)首批中醫(yī)專家學術(shù)經(jīng)驗繼承工作指導教授,主任醫(yī)師,博士生導師。師從廖家楨先生,臨床30 余年來,從事心血管內(nèi)科的教學、臨床、科研工作,魯衛(wèi)星教授在長期臨床實踐中精研經(jīng)典,遵從古訓,反復臨證,尤其對高血壓、冠心病、高脂血癥的治療有著豐富的臨床經(jīng)驗。筆者有幸跟師侍診,略得一些體會,現(xiàn)將魯衛(wèi)星教授治療心血管疾病的臨證理念及治療經(jīng)驗作以總結(jié)。
1 魯衛(wèi)星教授臨證理念
1.1 顧護脾胃為先
魯教授雖擅治心血管疾病為長,但卻以顧護脾胃為先,因“脾為后天之本”也。脾胃為生命之根,化生之源泉,李東垣認為“元氣之充足,皆有脾胃之氣所無傷,而后能滋養(yǎng)元氣,若胃氣之本弱,飲食自倍,則脾胃之氣既傷,而元氣亦不能充,而諸病之所由生也”,即脾胃內(nèi)傷,百病由生。臨證魯教授總會詢問病人的食納情況,注重脾胃本源的盛衰,施以調(diào)理。“胃不和則臥不安”,睡眠狀態(tài)是體現(xiàn)脾胃職能的又一體現(xiàn),臨床中無論患者有無睡眠問題,于顧護脾胃的同時,酌加養(yǎng)心安神之品,夜寐安以使脾胃職能更好的運行。魯教授認為納食和睡眠情況的好壞,影響著人體機能是否正常運行,即使久病纏身,只要食納及夜寐情況尚佳,則人的正氣不壞,治病就事半功倍,正是“正氣存內(nèi),邪不可干”,而顧護脾胃,使得“胃和而臥安”,足以體現(xiàn)養(yǎng)護脾胃的重要意義。“胃虛則臟腑經(jīng)絡(luò)皆無以受氣而俱病”,脾胃受損是疾病發(fā)生的內(nèi)在原因,臨證時從機體的整體觀出發(fā),臟腑辨證為核心,強調(diào)以脾胃為本,注重脾胃中氣,處處以運脾和胃為法度,調(diào)補脾胃,顧護脾胃。
治脾益心是魯衛(wèi)星教授臨證治療的一大特點。中醫(yī)認為心血管疾病的病位在心胸,心胸之氣血陰陽的盛衰關(guān)系到疾病的癥狀類型。喻嘉言曾述:“蓋胸如中太空,其陽氣所過,如離照當空,曠然無外。設(shè)地氣一上,則窒塞有加。故知胸痹者,陽不主事,陰氣在上之侯也。”[1]胸中的陽氣即宗氣,它的充沛與否直接關(guān)系到心肺功能的正常運行,具有“貫心脈而行呼吸”的功能;宗氣貫注入心脈之中,幫助心臟推動血液循行,協(xié)助心氣推動心脈的搏動、調(diào)節(jié)心律的作用,宗氣的這一作用影響著人體心搏的強弱、節(jié)律和血液的運行,而宗氣的盛衰與脾胃功能的正常運行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脾胃為水谷之海,氣血化生之源,通過飲食物而化生水谷精微,滋生或促進宗氣充足。宗氣足則“助氣行血”如常;宗氣不足,不能助心行血,就會引起血行瘀滯,所謂“宗氣不下,脈中之血,凝而留止”[2]。從脾治心,不僅考慮到脾胃與胸中陽氣密切關(guān)系,且由五行生克規(guī)律中,心為脾之母,補子實母也是顧護脾胃治療心系疾患的原則的依據(jù)之一。
魯教授在遣方用藥上以黃芪、黨參、茯苓、白術(shù)之類健脾益氣,并靈活加減木香、升麻、柴胡、蒼術(shù)、羌活等,升脾胃之陽,燮理中焦,扭轉(zhuǎn)樞機。脾胃運化氣血精微職能正常,通過調(diào)節(jié)脾胃氣機,清得以升布,濁得以降下,使五臟六腑、四肢百骸接受精氣濡養(yǎng),中焦樞紐正常,則治病事半功倍,在臨床中也收到了良好的療效。
1.2 善用活血化瘀法
自《金匱要略》將胸痹病因病機概括為陽微陰弦后,歷代多有闡發(fā),認為不僅陽氣虛衰,心陽不振,瘀血痰濁會痹阻心脈,同時若陰精不足,心失濡養(yǎng),心血瘀滯亦會致胸痹心痛。中醫(yī)學認為心血管疾病雖然發(fā)病于心,但與肝、脾、腎三臟的失調(diào)有密切關(guān)系,因心主血脈的運行賴于肝主疏泄,脾主運化及腎藏精主水等功能,其病性常虛實夾雜,其中實者多為血瘀。
情志不暢、飲食不節(jié)等因素也會造成瘀血,《靈樞·百病始生》云:“內(nèi)傷于憂怒,則氣上逆,氣上逆則六俞不通,溫氣不行,凝血蘊里而不散,津液澀滲,著而不去。”樞機不利而氣滯血瘀,更年期綜合癥患者多見;《素問·五臟生成》云:“是故多食咸,則脈凝泣血變色。”《靈樞·五味論》也云:“血與咸相得,則凝。”偏嗜咸味,傷及血脈,導致血瘀,高血壓病常見;過食肥甘厚味,釀生痰濕,痰濁阻滯,閉阻經(jīng)脈成瘀,或長期食辛辣,飲酒過量,陰液受劫,煎熬津液成痰,痰濁阻滯,痰瘀同生,多為高血脂癥病機;心血管病日久,再加年邁臟衰,氣血生化不足,血少不充,脈道凝澀,而發(fā)血瘀。《靈樞·營衛(wèi)生會》云:“老者之氣血衰,其肌肉枯,氣道澀。”久病邪氣羈留,傷及血絡(luò),血脈不暢,而致瘀血。
魯教授在辨證論治的基礎(chǔ)上,兼以活血化瘀之法,除配伍丹參、赤芍、桃仁、紅花、生山楂、延胡索、益母草等行氣活血化瘀之品,還靈活使用水蛭、全蝎、土鱉蟲等蟲類藥增加破血散結(jié)的藥效,治療心血管疾病頑癥、重癥,療效明顯。
2 魯衛(wèi)星教授臨床經(jīng)驗總結(jié)
2.1 高血壓多從肝腎論治
《素問·至真要大論》云:“諸風掉眩,皆屬于肝。”患者就診源于情緒波動而頭暈?zāi)垦0Y狀加重期,高血壓的發(fā)病往往與情志因素密切相關(guān),這是高血壓的“實證”或“虛實夾雜”中的“標實”;老年高血壓病人,因病久耗傷肝腎陰精而眩暈。由此可見,其病位主要在肝,肝之氣血陰陽的變化在高血壓病發(fā)生發(fā)展變化中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不良的情志刺激使肝失條達,肝氣郁結(jié)。肝失疏泄,郁久化熱,肝火亢盛,可使肝陰暗耗,肝陽上亢,出現(xiàn)頭暈、頭痛等不適癥狀。肝腎同源,肝陰耗損后日久,必下及于腎,致肝腎陰虛,相火用事,而發(fā)生腰酸、盜汗等一系列肝腎不足的癥狀。不論是肝陽上亢、肝腎陰虛、肝腎陰陽兩虛的病機特點,均與肝腎相關(guān)。因此,魯教授在臨證時多從肝腎入手治療,以天麻鉤藤飲加減為基本方,天麻、鉤藤、夏枯草、葛根、槐花、桑寄生、牛膝、杜仲等為主,經(jīng)過辨證酌情加入活血化瘀藥、理氣藥或補益肝腎藥,收到較好的療效。
2.2 冠心病從氣血關(guān)系論治
隨著冠心病手術(shù)治療的普及,來就診的冠脈支架術(shù)、搭橋術(shù)后病人不在少數(shù),而中醫(yī)藥治療冠脈術(shù)后存在較大的優(yōu)勢。魯教授認為手術(shù)治療解決了冠脈大血管的問題,但是小血管病變?nèi)源嬖冢Y(jié)合中醫(yī)藥方法,促進血管再生、側(cè)支循環(huán)再建立、改變小血管供血,預防再狹窄的發(fā)生成為主要的治療方向。
《金匱要略》提出“胸痹”一詞,指出其病機為“夫脈當取太過不及,陽微陰弦,即胸痹而痛。所以然者,責其極虛也。今陽虛知其在上焦,所以胸痹心痛者,以其陰弦故也”,表明陽氣不足,而致血脈瘀阻作痛,即發(fā)胸痹,可見氣血的相互關(guān)系與冠心病的發(fā)生相關(guān)。《素問·痿論》“心主身之血脈”,《血證論》提出“氣為血之帥,血隨之而運行”。血液在脈中環(huán)流不息,濡養(yǎng)全身,有賴于心氣的推動。若心氣異常,不論是虛或滯,均可產(chǎn)生血瘀。魯教授在臨床治療冠心病患者時,多從氣血理論分析其發(fā)病機理,認為冠心病屬本虛標實之證,氣虛血瘀為其基本病機。治療上運用益氣溫陽、活血通脈的方法。針對老年冠心病患者而言,機能衰退使元氣不足,氣化失常則病理因子作祟,使得再傷元氣,臟腑紊亂更加嚴重,形成惡性循環(huán),所以在治療老年病患時,魯教授更加重視對元氣的調(diào)補,元氣充足,則氣化如常,病理因子無從擾亂。
魯教授在處方時,益氣溫陽類和活血化瘀類為治療冠心病的核心藥物。以自擬健中消癥湯為基礎(chǔ)方,配伍黃芪、茯苓、白術(shù)等益氣之品為君,健運中氣以調(diào)補元氣;丹參、赤芍、桃紅、水蛭、地龍等活血化瘀藥為臣,活血化瘀,消癥散結(jié);再佐用合歡皮、珍珠母、首烏藤等鎮(zhèn)靜安神之類,安心神、護精氣,以達“治未病”之意。
若出現(xiàn)心功能不全,伴水腫癥狀,魯教授以益母草、澤蘭、葶藶子、豬苓、車前子、桑白皮等健脾利水、瀉肺利水。在使用活血藥及利水藥的同時,還配伍理氣藥以加強活血化瘀、行氣利水作用,體現(xiàn)了“氣行則血行”、“氣行則水行”的中醫(yī)理論思想,在選用藥物時,也相當嚴謹,要求理氣而不破氣、活血而不傷正,常用郁金、合歡皮、延胡索、枳殼、柴胡等。
久病患者常從氣虛逐漸發(fā)展至陰陽虧虛的階段,若心腎陽虛,魯教授喜用桂枝、薤白、淫羊藿、附子等溫陽通陽之品;氣陰不足,則配伍斂心氣、滋陰增液之品,如黃精、玄參、麥冬、生地、山茱萸、玉竹、五味子。以益氣活血為基本治則,再配合具體辨證,從整體分析治療冠心病,體現(xiàn)了魯教授的治療特點。
2.3 高脂血癥從脾論治
高脂血癥是心血管科的常見病之一,也是很重要的危險因素之一,很多患者血脂高了就服用他汀類降脂藥,雖然見效很快,但時間長了會損傷肝腎功能,并出現(xiàn)便秘、胃脹等癥狀。結(jié)合中醫(yī)藥治療不僅能改善西藥帶來的不良反應(yīng),還可從“本”治療高脂血癥。
中醫(yī)認為,高脂血癥的病因并非血脂本身,而是人體臟腑功能失調(diào),出現(xiàn)濕、痰、瘀所為。脾位中焦,為人身之樞紐,氣血生化、津液代謝之所在,如脾虛運化失常,不能將水液轉(zhuǎn)輸布散到全身各處,滯留于體內(nèi),則產(chǎn)生濕、痰等患。而濕、痰郁久阻滯氣機運行,氣不暢則血不行,又成血瘀為弊,究其根源,究責于脾。故魯教授治療高脂血癥多從治脾入手,以健脾、祛痰、化濕、活血化瘀為主,自擬健脾降濁湯為基礎(chǔ)方加減應(yīng)用。方中黃芪、白術(shù)、茯苓、葛根健運中氣、升清降濁為君;瓜蔞、昆布、荷葉、石菖蒲降濁消脂,山楂、蒲黃、丹參、赤芍、五靈脂、桃紅活血化瘀,共為臣藥,其余再隨癥加減。同時囑患者改變不良飲食習慣適當運動,對于血脂異常病情不甚者,能起到改善癥狀、降低高血脂數(shù)值的作用。若有血脂甚高的病人,魯教授在中醫(yī)藥治療的同時,囑繼用西藥類降脂藥,2 ~3 個月復查肝功、腎功,避免藥物對肝功腎功的損害。魯教授常說“只要對疾病有療效的方法,都會去使用”,這也體現(xiàn)了魯教授中西醫(yī)結(jié)合治療的理念,一切以患者的利益為重,用療效說話。
3 衷中參西的診治方式
魯衛(wèi)星教授先習西醫(yī),后師從廖家楨教授進行中醫(yī)學習,不僅對西醫(yī)心血管疾病發(fā)生發(fā)展的理論及藥物機理有扎實的功底,而且通過30 余年的臨證實踐,將中西匯通,兼收并蓄,辨證與辨病靈活相結(jié)合,察色按脈與現(xiàn)代檢查并用。
魯教授根據(jù)患者西醫(yī)檢查結(jié)果,中醫(yī)望聞問切四診資料,運用微觀與宏觀相結(jié)合及西醫(yī)辨病與中醫(yī)辨證方式,協(xié)同分析病因病機,最終制定治療原則。例如冠脈介入術(shù)后的患者,復查冠脈CT 提示支架部分血管血流情況良好,但存在微小血管的狹窄,出現(xiàn)胸悶心痛諸癥,魯教授處方時,會考慮到小血管的病變,配伍活血化瘀藥物進行治療,同時吸收現(xiàn)代藥理研究結(jié)果遣方用藥,增強療效。對于西藥的使用,魯教授更是得心應(yīng)手,如根據(jù)高血壓合并疾病的不同特點,選擇不同類型的降壓藥,盡量減少不良反應(yīng),并告知患者服藥時間及劑量,以達到最佳療效。
4 結(jié)語
魯衛(wèi)星教授臨床中西醫(yī)相結(jié)合治療心血管疾病經(jīng)驗豐富,兼取西醫(yī)治病與中醫(yī)治證的方法,充分體現(xiàn)了衷中參西的臨床特點,正如魯衛(wèi)星教授所說:“無論中醫(yī)還是西醫(yī),二者共同追求的目標都是緩解患者病痛。西醫(yī)不能解決的問題,用中藥來彌補;兩者相輔相成,治療疾病才是最終要達到的目的。”
[1]喻昌.醫(yī)門法律[M].北京:中醫(yī)古籍出版社,2002:135.
[2]馬蒔.黃帝內(nèi)經(jīng)靈樞注證發(fā)微[M].北京:科學技術(shù)文獻出版社,2000: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