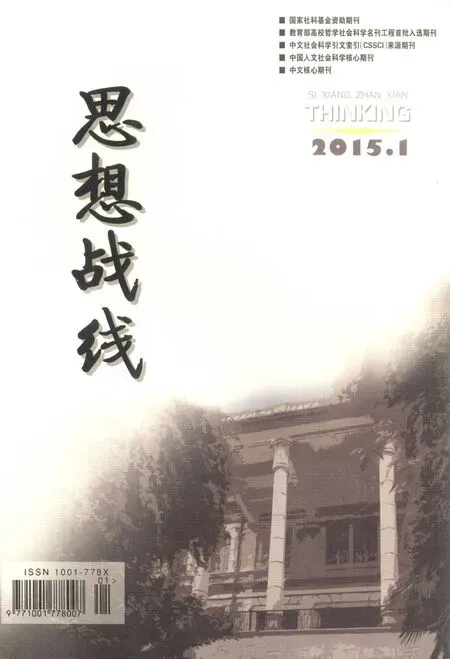“以德配天”:復論我國傳統文化遺續的崇高性
彭兆榮
“以德配天”:復論我國傳統文化遺續的崇高性
彭兆榮①
在我國傳統文化遺產的形制中,“崇高性”值得討論和重視;它的認知邏輯為“天人合一”,這也是我國傳統文化價值的核心所在。崇高性在諸如 “帝—王—皇”、“天命”、“恒德”等“天、地、人”相“參”的關系中同構為一個敘事共同體和表述范式,形成社會結構中循環往復的禮制秩序,為文化傳統價值的重要垂范,同時凸顯了中國文化遺產中的崇高性。今天,在中華民族文化復振之時,重塑“以德配天”、“以民至上”文化價值觀,對于施政無疑極其重要;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其比“以人為本”還符合中國傳統范式。然而,追求政治上“德政”的大一統——特別表現在朝代更替的歷史轉變,時常卻傷害了文化遺產的傳承和保護,而成為我國一筆特殊的“負遺產”。
崇高性;帝—王—皇;天命;德
題 旨
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是“天人合一”,它是人類彌足珍貴的遺產。*季羨林先生認為,“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文化對人類的最大貢獻。參見《“天人合一”新解》,載《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創刊號,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9~16頁。“天人合一”在品性上集中表現為“崇高性”。作為一個原則,崇高性的表現形態復雜多樣:君王“天命神授”的政治意圖與之契合,“帝王—天子”由此擁有“家天下”的至高權力和權威,構成了中國傳統等級社會金字塔建制中必需和必備的核心部分。“以德配天”由是成為帝王政治作為的一個檢驗指標,“德高望重”為所需品質和所立功業,并藉以垂范。崇高性在整個中華文化遺產中一以貫之,一脈相承;人們以特殊的禮儀方式與祖先達成“先驗—經驗”與“和諧—踐行”邏輯依據,同時化作社會明鑒。凸顯崇高性對我國當下正在實行的文化戰略,特別是重建“以德治國”的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參鑒價值。
帝(禘)—王—皇“正名”崇高

王國維曰:“帝者蒂也。”……帝之興,必在漁獵牧畜已進展于農業種植以后。蓋其所崇祀之生殖,已有人身或動物性之物而轉化為植物。古人固不知有所謂雄雌蕊,然觀花落蒂存,蒂熟而為果,果多碩大無朋,人畜多以賴之為生,果復含子,子之一粒復可化而為億萬無窮之子孫……天下之神奇,更無有過于此者矣,此必至神者之所寄。故宇宙之真宰,即已帝為尊號也。人王乃天帝之替代,而帝號遂通天人矣。*郭沫若:《郭沫若全集》第1卷(考古編),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年,第52~54頁。
據此觀之,“帝”與“祖(且)”通,其來源與生殖崇拜似存有關聯,與婦女之生殖(器)崇拜或存在關系,*許進雄:《中國古代社會:文字與人類學的透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9頁。然而,兩性皆成生殖意象缺乏歷史清晰線索,很難圓說此字符既為女性生殖崇拜,又為男性生殖崇拜。作為常識,文字時代的“帝”皆為男性,所述當處于父系氏族后期,特別是當“帝—王—祖(且)”配合時,生殖崇拜當作男性。《說文》釋:“帝,禘也,王天下之號,王天下也。”*禘,古代帝王、諸侯舉行大祭(主要是祭天、宗廟,比如禘、郊、祖、宗等)的總稱。顯然,“帝—蒂—禘”已經超出了文字訓詁的范疇。

在中國古代的傳統社會里,凡所崇之事,必配以祭祀,這是禮儀世界最為常見之事。“帝—禘”由此建立起了另外一種崇拜祭祀的禮儀形制。在商人心目中,帝棲于天而為居于一切之上的主宰者,能命降風雨、策動雷電、左右陰晴、禍福災佑,至高無上。*參見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北京:考古出版社,1956年,第571~573頁。因此,“禘”即祭帝(天)。*陳夢家認為,殷人的商不接受祭祀,而周人的天已經是祭祀的對象。這應當與周人的天命有關。即商人只有“帝命”之說,周人有“天命”說。故帝不接受“禘”祭;而既然周在人間的統治的大命是天所授,周王就理應祭祀上天。參見陳夢家《古文字中的商周祭祀》,《燕京學報》第19期,1936年;陳 來《殷商的祭祀宗教與西周的天命信仰》,《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2期。《爾雅》云:“禘,大祭者,禘是揔名。”即總稱的意思。具體的祭法如《祭法》所云:“祭天圓丘亦曰禘。”*參見鄭 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61頁。《禮記·明堂位》:“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丁山認為,在殷商時期,禘的意思是汜祭各神之名。*參見丁 山《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第496~497頁。由此可知,崇高性需由神圣的禮制、禮儀和禮事來實施和完成。
祭儀的本質反映了遠古時的認知,人們對天的自然經驗和認知轉為先驗與神秘。從商代的卜辭看,帝在天上,有時也降臨人間,宗廟即為帝降臨之處,故祭祀之。*趙 誠:《甲骨文簡明詞典——卜辭分類讀本》,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2頁。《國語·魯語下》:“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帝者,禘也。“禘”便是古代最重要的一種祭天神典祀,《禮記·祭義》:“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禮記·祭統》:“禘嘗之義大矣哉!”《禮記·禮運》:“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記·王制》說得更具體:“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按照這樣的記載,禘祭是帝王諸侯于宗廟祭祀上天祖宗的祭祀,并依照不同的季節各有不同的名稱。值得一說的是,所謂的“禘心”,一種解釋是,以“心”為“心宿”;也解釋為“以心祭上帝”。《史記·天官書》謂心為天王,享禘祭正合。無論何解,以“心”通天大抵為共識。*參見胡建升《“通天”之心》,載葉舒憲,唐啟翠編《儒家神話》,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1年,第180頁。“心”既是人的身體和生命“中心”,“心宿”與“星宿”或許存在關聯。也配合“天”,以“心宿”配合“星宿”;以“禘”祭“帝”,“天人合一”之垂范也。
禮制、禮儀和禮俗原脫不了以高山合天的經驗性認知的“崇高”,并配合以相應的祭祀儀禮,逐漸演化成為歷代帝王“山祭—祭山”的傳統;同時,這又構成了我國古代建筑史上的符號性“崇高形制”。許進雄考釋了古代燎祭、封禪與明堂建筑之間的關系,認為燎祭最早見于甲骨卜辭,形象為架木焚火、火焰騰灼之狀,是殷代一種很重要的祀典。燎祭的特點有二:一是在高處舉行,二是用火。這兩個特點與封禪相同,推斷二者存在淵源關系。*參見許進雄《燎祭、封禪與明堂建筑》,載《許進雄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52~53頁。傳說封禪自黃帝始,由于沒有更充分的材料證明,姑作存疑。但相關的高山祭祀儀禮已成傳統,封禪為代表。封禪指帝王的一種祭祀儀式,即到中岳嵩山和東岳泰山(古代帝王到泰山行封禪祭儀盛行)祭天的專屬活動,*秦山的“秦”在《易經》中表示“天地交而萬物通”。民間盛傳秦山娘娘碧霞元君為東岳大帝之女,故崇信者眾,相信她能送子給人間。參見居閱時,高福進等《中國象征文化圖志》,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0年,第241~242頁。在文獻中多有記載:
《書·舜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祡,望秩于山川。*《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26頁。
《史記·封禪書》:秦以冬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于咸陽之旁……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史記·封禪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376~1377頁。
唐代張守節釋《史記·封禪書》云:此泰山筑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昆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白虎通》云:或曰封者,金泥銀繩,封之印璽也。”《五經通義》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何?天命以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報群神之功。”此疏甚明。*轉引自湯貴仁《泰山封禪與祭祀》,濟南:齊魯書社,2003年,第2~5頁。按禮制要求,人世之事,濟世之功必報神稟天,《國語·魯語》有“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民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顯見,就“國之大事”而言,禘(祭天)的崇高行為為君王所表率和表彰。
這也是為什么中國的君王政治史的“崇高”與“登山(高)”、祭天總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原因,封神足以明之。由此可知,祭祀圣典不是在高山,就是在郊外的高處,或是高臺上,其中有河川源自于高山,有興云致雨的力量,*參見許進雄《燎祭、封禪與明堂建筑》,載《許進雄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53頁。更有神明棲居于“山頂”、“天界”的代有普遍性的認識。所以,帝王襲以登高封禪、祭祀。以秦始皇為例,嬴政統一中國,稱以“皇帝”,一生5次巡游,每次都登高刻石,留下7處紀功昭示天下之舉,計有:出雞頭山(今寧夏降德縣)、上鄒嶧山(今山東鄒縣)、窮成山(今山東榮成縣)、命罘山(今山東煙臺北芝罘島上)、登瑯琊筑瑯琊臺(今山東膠南縣)、登泰山(他兩度登泰山,曾宿絕頂),游云夢澤(洞庭湖),望祀虞舜于九嶷山,上會稽山,祭大禹等等,*參見路 遠《碑林語石——西安碑林藏石研究》,西安:陜西出版集團 三秦出版社,2010年,第2~3頁。公元前210年,其在巡游途中重病死于沙丘平臺(今河北廣宗縣)(參見《史記》卷6《秦始皇本紀第六》)。他在《嶧山石刻》中刻下這樣的文辭: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暴滅六強 ……登于嶧山,群臣從之……陀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路 遠:《碑林語石——西安碑林藏石研究》,西安:陜西出版集團 三秦出版社,2010年,第16頁。
由此可見,登山、祭(禘)天為君王必備的功課。
“天命”寓于生命崇高
在中國傳統的文化遺產中,人的生命無法獨立自主,需與“天”合一而謂“天命”;人的生命具體無不在“天”的俯視和指引下運行。寓崇高于性命。“天命”在表象上表現為生命不可違背和抗拒的符旨,其實卻首先是思維,即宇宙觀。生命的形式集中反映在時空制度之中。“天命”就是由特殊的時空制度所建構:時間上,相信人的生命形態的不同,與祖先同構成為世代交通。空間上,與所謂的“天”構成交流互動。在傳統的文化結構中,它被賦予不尋常的、闡釋性的政治含意。“天命”在周代就已有表現,并附帶了“命運”的無可言說性和不可抗拒性。周以一個小邦,取代強大殷的統治,實在使人感到“天難諶,命靡常”(《尚書·咸有一德》),“天命不于常”(《尚書·康誥》),連孔子也不免嘆惜:“大哉天命。”也即我們通常所說的“天命不可違”。
“天命”在不同時代的名稱和闡釋不同,被賦予的涵義也有所差異。據傅斯年考,“命”之一字,作始于西周中葉,盛用于西周晚期,與“令”字僅一文之異形。*“令”在甲骨文中多有出現,但“不出王令天令之二端”,王令即天令;曰“大令”,則天令也。參見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8頁。其“天命”一義雖肇端甚早,然天命之命與王命之命在字義上亦無分別。*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頁。此說與陳夢家的觀點合:“商人稱‘帝命’,無作天命都,天命乃周人之說法。”*陳夢家:《尚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07頁。“天命”在商代還有“由天斷命”的意思,《書經·盤庚》:“卜稽曰:‘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這說明,祭祀占卜對各詢問事項做出反應,為商王即將舉行的活動提供根據和理由。*張光直:《商文明》,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第219頁。當然,在不同的朝代,“天命”也相應出現語境化變遷,比如,周人替代了商人而改朝換代,周人不再視商人的祖先為至尊,所以,“天命”除了有“天授之命”的意義外,還附加上了“上帝僅授天命予有德者”。*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第429頁。此外,“性”與“命”常被拆而言之。故有明人尹真人高弟著書《性命圭旨》解說:
性命原不可分。但以其在天,則謂之命;在人,則謂之性。性命實非有兩,況性無命不立,命無性不存。而性命之理,又渾然合一者哉。故《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此之謂也。*尹真人高弟:《性命圭旨》,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第9頁。
集合諸學者的觀點:(1)“命(天命)”雛形于商,成形于周。(2)“天命”與“王命”通。(3)“天命”有“天意”的意思。(4)“天命”在“變”與“不變”之中辯證;“命”與“運”便是一種表示。(5)“天命”是政治統治必需借用的絕對理由。(6)“天命”經常由祭祀占卜“告知”。(7)無論“帝命”還是“天命”,天地相通、天人互動構成了基本的實踐圭臬。
無論對“天命”有多少種解釋,都包含著將性命融入崇高性的文化表述,也符合“天、地、人”一體并重的道理。《帛書老子》:“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國中有四人,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周易》講得更清楚: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立之,故《易》六畫而成卦,他陰分陽,選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周易·說卦傳》)
“三才”即“天、地、人”,是三者鼎峙關系的一種觀念,是肯定三者居于對等地位的關系。*參見王爾敏《先民的智慧: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的經驗》,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10頁。如是說,對“天命”多了一種解釋。“王”者,三才組合,符合“天命”,“天”者,大人頭頂著“天”。皆強調“天、地、人”相通,不可拆解。這與西方的“二元對峙律”根本不同。“三合一”是整體,而且通融。


夫元氣者,大道之根,天地之母,一陰一陽,生育萬物。在人為呼吸之氣,在天為寒暑之氣……故學道者,當取四時正氣,納入胎中,是為真種,積久自得心定神定息定,龍親虎會,結就圣胎,謂之真人胎息。*尹真人高弟:《性命圭旨》,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第127頁。

“天命”的重要指喻為“命運”。在我國傳統意義上,“命”常指示不可違、永固的意思;而“運”則強調變化、變遷和變動。它可指自然變遷,也可指人的生命際遇和變化。“命運”之“命”具有傳世特性,它與貴族之胄(帝王或貴族后代)存在關系。故有“帝室之胄”、“王室之胄”之說;與之關聯,亦泛指世系。在這層意義上,“崇高”也有高貴之胄的含義。這也為我國漢族的宗族譜系“擬祖”時的“英雄化祖先敘事”提供了一個文化基因。古代的“名門望族”是具有世襲的崇高的社會地位的豪族大姓,*[美]伊沛霞:《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范兆飛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頁。并具有地方聲望和特殊的生活方式。最好的描述是氏族(clans,早期的人類學譯為“克郎”)。*[美]伊沛霞:《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范兆飛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0頁。氏族的特征之一便是特定族群內部的傳承。順便說,當代我國的社會政治結構中,傳統的“貴族”已徹底地退出社會政治舞臺,這樣的結果是民眾的家園主人翁意識慢慢喪失。近代以降,貴族的“厄運”連續不斷,茍延殘喘的貴族“鼻息”根斷。而徹底根除貴族門第的社會崇高性,無疑是發生20世紀中期的“文化大革命”。及至今日,我們終于在具有“黑色幽默”的歷史劇中看到完全沒有崇高感、沒有高貴氣息的“土豪”群體的崛起。鑒于此,我們今天似乎要做些恢復“高尚之德”、“高貴之氣”、“高雅之俗”的工作。“天命”的邏輯離不開“天人合一”。其主要表述形而上的價值觀念,但實際上,在“天、地、人”之間存在著一個介體式的“參”(即“叁”)。參的一個解釋,指我國古代天文學及民間對“參宿”一、二、三(即獵戶座ζ、ε、δ)三顆星的稱呼。也

圖1:我國古代二十八星宿之“參宿”簡圖*“參宿”屬于古代星象學中西方白虎七宿之一。我國古代的星象圖在描繪上存在差異。可參閱潘 鼐編著《中國古天文圖錄》,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75頁、第319頁、第362頁等。
稱“三星”(特指);亦可指其他數組三顆相接近的星(泛指)。“三星”還有“天作之合”的意思。民間也稱之為“福、祿、壽”三星,*參見百度百科之“參宿三星”,http://baike.baidu.com/view/1001168.htm。暗合天命體性,也是完整的“性命”意象和生命表達。
“天命”的觀念一直盤亙在中國古代的文化脈理中,也一直是民間倫理中最為樸素的價值觀。事實上,在天命論中,方家的表述差異甚大,但無論是“表”還是“理”,都圍繞著人來講述,也都是從人出發的。《禮記》中說,人是天地的靈魂。天地是一切事物的父母,在人之上,高于人的是天地。在儒家觀念中,天或上帝至高無上,但卻不是萬能的,需要人的輔佐,所以需要“天子”,就像君主需要臣子一樣。因而“參(叁)”也是配合、輔助。《禮記·經解》:“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參”即“叁”,和天地并列為叁,故為“天子”、“大人”、“圣人”、“君王”;同時又是參與,參與對天地的作用,也就是輔佐天地。輔佐的方法,就是根據天地的意志,比如天命、天道,加以合理的動用。*李 申:《道與氣的哲學:中國哲學的內容提純和邏輯進程》,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54~55頁。普通百姓的“命運”也是能完全自主。由此,“參”既表明“天、地、人”的“共體”關系(叁),也表明三者之間交通、感應、互動的“介體”關系。所以“命”首先是一個哲學概念,即“上天的命令”。具體包括:(1)上天對君主的任命。(2)人的生死壽夭也是上天的安排。*李 申:《道與氣的哲學:中國哲學的內容提純和邏輯進程》,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88頁。
“德”之崇高垂范
崇高性的另一個重要表現在于“德”。換而言之,“德”屬于一種標準的中國式思維的崇高性——對“德”的關懷和追求。“德”字語義復雜,它首先關涉宇宙觀的道理,《老子·二十一》:“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闡明“德從道”的哲理;而“道德”之至高要理乃“中和”、“和諧”、“均調”,《莊子·天道》:“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地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地和者,謂之天樂。”所以,“道德”是宇宙觀的終極關懷,它具有“永恒”的意義,中國上古就有“恒德”之說。《易·系辭下傳》有“九德”,其一為恒,故云:“恒,德之固也。”“恒德”與“恒星”對應,春秋常作此言。*參見饒宗頤《帛書系辭“太恒”說》,載湖南省博物館編《馬王堆漢墓研究文集》,長沙:湖南出版社,1994年,第30頁。《說文》:“恒,常也。”《易·序卦傳》:“恒者,久也。”
長沙馬王堆帛書易經,恒列于辰(震)宮之末卦,其卦爻辭云:“恒,無咎,利貞,利有攸往。”九三:“不恒其德,未承之羞。”饒宗頤釋,不恒其德之人,即指“二三其德”之人,不能行“一德”。*參見饒宗頤《帛書系辭“太恒”說》,載湖南省博物館編《馬王堆漢墓研究文集》,長沙:湖南出版社,1994年,第29~30頁。什么是“恒德”?易經《恒》卦彖辭云:
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異而動,剛柔皆應。恒,亨,無咎利貞。勻而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有利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7頁。
由是觀之,“德”可以指經年亙古而不變的“恒常”,也可以在具體對象中表明“美德”之德性。
邏輯性地,帝—王—皇互通的憑照即“德”;由于其為“天子”,故“德”首先表現為一種“參”,它既是“天、地、人”交通的參照性圭臬,同時也是一種媒體。《荀子·天論》有:“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而“德”為三者通融的關鍵機關。《周易·乾·文言》:“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參見李 申《道與氣的哲學:中國哲學的內容提純和邏輯進程》,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53~57頁。“德”被認識為和諧的邏輯(因),也被想象為理想的結果(果);它被建構為完整的形制(象),也被制造為交通工具(法)。
很自然,“德高”因此成為一個無形的、高尚的道德示范。“以德配天”形成了帶有普遍性的社會價值,包括禮儀和生活皆循此規范,并對后世產生“垂范”作用。*《赫赫宗周——西周文化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館(臺灣),2012年,第79頁。《中庸》有: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圣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朱 熹:《四書集注》之《中庸》,長沙:岳麓書社,1987年,第37頁。
“大德者”如舜一樣,受命于天,保民安泰,其因德而得位、受祿、享名、長壽。所以,“敬天修德”成了君(君王、君子)功業之重要組成部分。商周時代,特別在周代,天命觀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德”的強調,“德”成為周王有資格得到上帝保佑的理由,也是周人得到天命、周王得到人民擁戴的理由;二是對人的重視。*邵學海:《先秦藝術史》,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0年,第270頁。事實上,自古以來,“天、地、人”的關系在《莊子·天下》中總結得最為精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所以,歷代帝王大多以“順乎天”、“應乎民”為體。《尚書·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以便是雍。”說的是俊朗通天的美德,從“親九族”到“平章”(“百官”忠于職守)到社會“協和”到民眾友善。*王云五:《尚書今注今譯》,屈萬里注譯,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第4頁。
“德”同時也有“天人合一”宇宙觀的特色表述,其中充滿了陰陽五行的色彩,它與“天”的崇高性關系幾乎可以在所有重要的領域獲得虛構和建構,同時,所有這些虛構和建構又無一例外地返回到社會現實中來。當然,這種崇高性的現實功能最為直接的,首先是為了使帝王的權威、權力贏得無法兌現又不可置疑的“正名”;甚至五行家還虛構出一套五行運轉的“帝德”學說,認為每一個朝代的君王都具有五行中的某一行性質,是為“帝德”。因而,每一朝代君主的始祖都是五帝中某一天帝的兒子,稟受天命而統治天下,而君主死后靈魂又重返天上,由此而產生“天主”的觀念,并把君主稱為“天主”,以后又由“天子”演化出帝王將相死亡被認為“天星歸位”說。*李冬生:《中國古代神秘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頁。
“以德配天”的直接關系即“德”與天、天象形成一種直接相互觀測和呈象,有學者認為,“德”原本就是一種觀測日影的呈象方式,即“德”可以解釋為一種天文觀測記錄,以區分和映照地文、人文;這可以從“德”的字形構造上判知,“德”與天上的“德星”有關,而封禪祭儀,實乃報德星。*參見《漢書·郊祀志》:“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心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顏師古注:“德星,即填星。”填星即土星。但在古代典籍中有不同的說法,認為“德星”是“景星”、“歲星”,如《史記·天官書》有:“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于有道之國。”《史記·武帝紀》:“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索隱》:“德星,歲星也。購星所在有福,故曰德星也。”所指都是木星。另,“德星”有偶指彗星、流星。參見《辭源》“德星”條。換言之,德實為以測天文、天象、天星之垂范地文、人文。*泰祥洲:《仰觀垂象:山水畫的觀念與結構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8~29頁。“德”在甲骨文、金文的字形中都帶有“垂直”的意思,周代以降,“通神”、“昭德”在圖像表述中時常成為形意的關聯體、關系體。西周時期,“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德”遂為王權確立和持續的依據。*泰祥洲:《仰觀垂象:山水畫的觀念與結構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6頁。“德”進而成為朝代更替的歷史性理由,比如周武王伐紂,乃商紂“失德”之故,《尚書·牧誓》羅列具體的罪狀,“今予發惟共行天之罰”(今奉天之旨意懲罰之)。《尚書·無逸》中則將殷商的大戊、武丁、祖甲、周文王并稱,皆為敬天保民、修德尊禮的形象。*李學勤:《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430~433頁。“德”成了映照“天意”的明鑒,也成了確立“地王”的鑒證。
順理成章,“德”與“鼎”——可以延伸為德行與政權的內在邏輯,而二者的關系在王孫滿的名句“在德不在鼎”中得到經典的解釋,《左傳》中一段對“問鼎”的對話,謂: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也,遠方圖物,貢金九枚鑄鼎像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逮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奸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郟鄏,卜世三十,卜提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左傳·宣公三年》)
這一段話清楚地昭示了二者的關系。而據學者考據,“德”與“鼎”原本為一“物”,“德”為土星,“鼎”為“德”的投影成像。*泰祥洲:《仰觀垂象:山水畫的觀念與結構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7頁。聊備一說。“鼎”在皇權的歷史象征和禮制的運作中,雖二者的邏輯關系已為實際的儀軌所遮掩,即更多關注“問鼎”、“九鼎”的指稱和指喻,然“德”的垂范作用卻從來未曾改變過。
以德垂范一直以來都是我國傳統對圣人、君王、先師、智者等,尤其是所謂的“德政”的實現圭臬,也是一種文化上的無形遺產,世代傳頌。孔子有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意思是說,周遵鑒繼承夏、商二代之文化傳統,我遵從周朝這一垂范。這是崇高性的另外一種意義,它建立了一種以“德”為基本的家國規約。有意思的是,“垂范”、“傳統”雖有時空形制,即先前某一朝代、帝王的功業為典范,在傳統中卻以“不朽”、“永恒”被固化。同例,不獨孔子從周,武則天亦從周,是故改朝立國為“大周”,并自封為“曌”。質言之,“德高”之垂范已經成為傳統封建帝國的一個政治標準,納入“正統”軌道,轉入為權威至上的規矩;《郭店楚墓竹簡》中有《六德》一篇,文中提到君、臣、父、子、夫、妻“六位”,而以圣、智、仁、義、忠、信“六德”配“六位”。*姜廣輝:《義理與考據:思想史研究中的價值關懷與實證方法》之“郭店楚簡與早期儒學”,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13頁。換言之,我國傳統價值確認的終極關懷即為“天”——至高無上,無論是名、事、書*比如在《尚書》之書名考據中,就有一家之言,如緯書《尚書璇璣鈴》說:“《尚書》篇題號,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節茺。書也,如天行也。”受此影響,鄭玄也說:“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蓋言若天書然,故曰《尚書》。”參見姜廣輝《義理與考據:思想史研究中的價值關懷與實證方法》之“郭店楚簡與早期儒學”,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25頁。、器等皆然。
在我國,“家”與“國”是并置的,一體的;“家國天下”是謂也。因此,德也就成為君王的功罪和國勢強弱最高級別的衡量指標。“德”之于國如此,之于個人(尤以君王)亦屬同理,所以孔子說要“修己”才能“明德”,朱熹則借此提出“明明德”。*參見王陽明《傳習錄》,于自力等注譯,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3頁。說的都是君王的“德”除了天授以外,親民、自修都是必要和必需的。也就是說,通天大德者可達天下大治也。而君王者,“王德”、“仁德”同謂也。《管子·兵法》:“通德者王。”《白虎通·號篇》:“仁義合者稱王。”《七經義綱》:“德合仁義者稱王。”而有仁德者便能夠得到天下。《戰國策·秦策》高誘注曰:“王,有天下也。”其中的關系是:王通“天、地、人”,以仁德以昭彰,故可得天下者。所以,君王的“載天”之德尤為神圣。反過來,如果天象有“異”,比如日食、大災害,皇帝是需要自行責罰的,比如漢代的“罪己詔”,包括一些“思過”方式。*李 申:《道與氣的哲學:中國哲學的內容提純和邏輯進程》,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83頁。
1976年12月15日,在寶雞市扶風縣發現了一個西周時期的青銅器窖藏,其中最珍貴的文物為墻盤。墻盤內底部鑄刻有18行銘文,追述了列王的事跡,歷數周代文武、成康、昭穆各王,敘述了祖先和當世天子的文功武德,并祈求先祖庇佑,為典型的追孝式銘文。 是為考古史上之大事,眾所周知,此不贅述。但西周何尊、墻盤等考古文物上所刻銘文對后人至少有幾點啟示:(1)三代,尤其是周,一直以“受命于天”(天命)、“以德配天”(崇德)為圭旨,為后世楷模。難怪孔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2)周滅商最重要的“理由”即商“失德”。(3)但是,過分強調“德政”的后果是:前朝因“失德”而遭諸天譴、天誅,致使新朝對舊朝所遺留下來的文化遺產進行有效的甄別,更談不上保護。因此,在滅前朝正統時也毀損了文化遺產。導致代際交替(包括朝代更替)以求“一統”,卻以摒棄、損毀和破壞之前歷代、歷朝所創造、遺留歷史文物為價值。這種道理仿佛今日之“全球化”不必定要毀滅文化的“多樣性”。(4)如果以西周所傳承的政治、宗氏和遺產為典范的話,秦朝的統一伴以“焚書坑儒”,開創了一個朝代更替的“連續性”,卻以損毀文化遺產“斷裂性”為價值。這種“負遺產”傳承慣習一直延續至20世紀的“文化大革命”。(5)我國政治傳統的根據以宗氏傳承為脈絡,這是中國宗法社會的根本,也是中國文化遺產之要者。而“德”之正統性未必能夠成為宗法制度賴以繼承的文化遺產。(6)我們為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的“連續性”而驕傲時,也為我們的地上“文物”幾無所剩而嘆惋。“幸而”先祖們不僅為我們留下“死事與生事”的墓葬傳統,更為我們留存了許多珍貴的文物。 換言之,我國的歷史上的“家—國”(君王的宗氏)傳承和斷裂與文化遺產的傳承和斷裂常不一致。
結 語
我國傳統文化敘事的基礎與基調是“天人合一”;其意義表述為“天、地、人”相互形成一個認知和敘事的共同體,“參”(“參星”)故而重要,它不僅說明“三合一”(“參”即為“叁”,此指“天、地、人”)的重要性,而且突出了崇高性的社會垂范作用,值得重提和重塑。而今人們所常說的“以人為本”多少帶有西方“人本/神本”對抗、轉換的歷史語義和敘事邏輯。我們當然可以取而注入新的意義和意思,畢竟任何偉大的思想都是人類共同的文化財富;但筆者更愿意強調要直接傳承自己的遺產,因為那是我們幾千年所形成的文化血統。
(責任編輯 段麗波)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體系探索研究”階段性成果(11&ZD123)
彭兆榮,廈門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旅游人類學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福建 廈門,36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