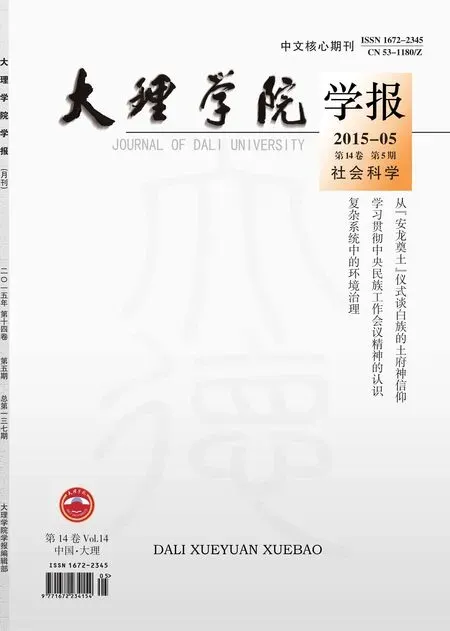視覺性白族文化元素在旅游開發中的創新性應用分析
曹 星
(大理學院,云南大理 671003)
云南民族眾多,民族文化豐富多彩,各個少數民族絢麗多姿的民族風情和異彩紛呈的民族文化一直以來都是吸引海內外旅游者紛至沓來的重要吸引物。如何通過具有視覺沖擊力和文化內涵的顯性民族文化元素構建獨特的民族身份識別標志,是民族文化傳播和民族地區旅游開發需要重視的問題。白族作為云南主要的世居民族之一,歷史悠久、文化積淀深厚、民族風情自然淳樸,對旅游者具有特殊的吸引力。通過視覺性民族文化元素的提煉與展示,增加大理旅游的吸引力和文化內涵,是大理旅游業發展中一個值得關注的課題。
一、大理旅游升級離不開民族文化元素的形象展示
(一)大理旅游是多元素整合型旅游,體驗是其核心內涵
大理旅游起步較早,這個具有世外桃源特性和東方瑞士風光特色的地方,從20 世紀80 年代以后成為了眾多旅游者非常感興趣的旅游目的地。電影《五朵金花》對大理的宣傳效應毋庸置疑,它引起人們對白族風情的濃厚興趣;而蒼洱風光旅游也一直是大理旅游的保留節目,滿足了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旅游浪潮初起之際人們游山玩水、體驗民族風情的旅游需求。隨著工業化與城鎮化的發展、生活方式和交通方式的改變,人們的旅游需求日益多元化、個性化、定制化,并更加注重主體選擇與體驗;大理旅游因應而變,展示了自己在生態旅游、休閑旅游、文化旅游、鄉村旅游、宗教旅游等多方面的潛力和魅力,使大理旅游逐步升級為以體驗為中心的多元素復合型現代旅游,從而能夠滿足不同旅游者的需要,并在此過程中逐步完成了大理旅游產業的升級換代。
(二)白族文化展現是大理旅游的題中之義和重要吸引物
民族文化是少數民族地區旅游活動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它既是旅游吸引物,也可構成獨特的旅游產品或成為其他旅游產品的重要元素,展示功能、營銷功能、商品功能兼而有之,文化價值、經濟價值、體驗價值、美學價值數美齊備。做好民族文化這篇文章,能夠使區域旅游經濟獲得有力的支撐與可持續發展的內在動力,是21世紀民族地區旅游業發展不可忽略的支撐點和增長點。大理作為白族聚居區,以白族文化為旅游吸引物和展示主體,可謂順理成章、天經地義。集中展現白族文化元素不是排他,不是說不要其他民族的文化,而是突出重點,展示精華,增加大理以及大理旅游業的內在吸引力。許多旅游者到大理,本身就是沖著白族文化和白族風情而來,他們希望了解白族的歷史、體驗白族的文化、感受白族人民的熱情好客,在白族人民世代居住的山水之間陶冶自己的性情、放松自己的身心。白族文化元素在旅游目的地呈現得越集中、越鮮活,他們越能滿足自己求知的愿望與體驗的興趣;相反,旅游者到了大理卻看不到鮮明生動、隨處可見的白族文化元素,感受到、體驗到的是和其他地方大同小異的東西,難免會產生失望的情緒。事實上,《云南印象》與《希夷之大理》的成敗得失,也能從一個側面給我們以深刻的啟示。
(三)旅游二次創業應注重視覺性民族文化元素的提煉和系統展示
云南旅游正在努力實現二次跨越,以期實現量和質的雙提升。大理作為云南重要的旅游目的地,理應在云南旅游的新跨越中有所作為。在大理旅游二次創業中,總結以往的經驗、參考別人的做法,應該打破“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傳統營銷理念,花大力氣重視視覺性白族文化元素的研究、提煉和系統展示,形象展現大理作為全國唯一的白族自治州所特有的民族文化魅力。就過往而言,白族文化呈現總體過于內斂,對視覺性白族文化元素缺少提煉和系統規劃,使大理旅游的民族文化品格顯得平淡、模糊,這是客觀存在的問題,必須在今后予以改變。隨著21世紀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民族文化視覺化、單元化、新媒體化成為新的趨勢。大理應把握住這次新的機遇,力爭為大理旅游增添新的內涵和活力,改變蒼洱山水自在、白族文化自顯、旅游經營者自為、旅游者不得不到處自找的無所作為狀態,使視覺性白族文化元素獲得系統的開發、形象的展示、有效的提升,從而為大理旅游注入更為強大的活力。
二、可助推旅游開發的視覺性白族文化元素分析
白族文化自成體系、內涵豐富、形式多樣,包含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可視性文化與非可視性文化。從文化保護的角度說,所有的文化都應該納入保護范圍;而從旅游開發角度說,則只有那些適合于市場化、產品化、交互化、視覺化的白族文化元素能夠獲得優先重視〔1〕。視覺性白族文化元素的類型與代表(見表1)。

表1 視覺性白族文化元素的類型與代表
上述各種類型的視覺性白族文化元素,在各地旅游開發過程中被部分吸納和利用,很多已成為了旅游者耳熟能詳、頗感興趣的旅游吸引物。例如喜洲的新老嚴家大院等四合院是旅游者必到的景點,霸王鞭是絕大多數演出中必備的節目,白族服飾的魅影經常出現于舞臺之上,周城扎染、劍川木雕和布藝、鶴慶銀器首飾等白族手工藝品是旅游者熱衷采購的東西,白族酸辣魚、生皮是很多人津津樂道的食物,“一街趕千年”的三月街人流如織……但是毋庸諱言,與白族文化的豐富多彩和大理旅游提升換代的內在需要相對比,目前的開發利用情況尚不夠理想,很多方面仍需著力拓展。在視覺性白族文化元素開發利用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第一,市場化程度低,公眾對其認識還不夠廣泛、深入。在市場經濟背景下,視覺性民族文化元素必須借助恰當的載體和路徑,走市場化這條路,敢于接受市場檢驗,經受市場經濟淬火。遺憾的是,大多數視覺性白族文化元素的商品化屬性尚未被充分激活,產品化開發與包裝更尚未提上議事日程,完全是手工作坊式的小敲小打、自彈自唱,不說躲在深山人不識,起碼也是知者不多、識者有限、市場占有量偏低。這樣的狀況,對于旅游市場營銷與擴大區域旅游經濟影響力是不利的,必須通過有效的市場營銷和推廣,切實改變這種被動局面。
第二,和旅游開發的結合程度不夠緊密,各行其道現象較為突出。“文化是旅游的靈魂”是一句眾所周知的話語,但文化和旅游如何結合這道題,在大理的旅游開發實踐中未必得到很好的回答。各地在旅游開發與經營中往往過于注重旅游的經濟屬性,輕視或忽略旅游與文化的有機結合,二者像鐵軌一樣各走各道、平行運行,輕則不重融合,重則互不交集,由此帶來的后果是旅游缺少文化內涵支撐而顯得急功近利,白族文化不能借助旅游弘揚而同樣跛足難行,這種“兩張皮”現象帶來的資源浪費和內涵消解,無論對于大理旅游還是白族文化,都是實實在在的損失。必須牢固樹立“旅游產業發展離不開文化添彩、民族文化展示需要有恰當載體和舞臺”的共享共榮意識,實現旅游與文化互為支撐、聯動發展。這一點,只有當它變成一種自覺的意識與行為,體現在管理者、經營者、服務者的各方各面中時,才是白族文化和大理旅游雙贏之時。
第三,識別特征不夠明顯,容易和其他民族相混淆。云南世居民族相雜而居現象較為突出,各民族之間文化交流頻繁而自然,某些民俗、節慶共有,生活方式相同或相似,這些都是無可厚非的,關鍵在于白族自身的特點何在,白族與其他民族的差別在哪里,如何通過具有鮮明識別特征的視覺性民族文化元素展現白族文化與眾不同的特點和魅力?“市場開發者必須把他們的品牌組合‘全球地方化’,以精確地滿足顧客的個人需求”〔2〕。在這些方面,目前所進行的研究與采取的措施都是遠遠不夠的。火把節為白、彝、傈僳等民族共享,這是歷史形成的事實,但白族火把節有何特點、如何開發為宜,似乎再無人進行深入的探討,結果楚雄火把節熱鬧紅火、人山人海,大理火把節不溫不火;沒有什么傳統民族建筑的楚雄尚且打造出了個4A級景區彝人古鎮,守著喜洲古鎮、大理古城的大理,卻在白族建筑風格弘揚上無所作為;白族扎染和彝族蠟染,也很能讓人區分出太大的不同……不是本無區別,而是無所用心、聽之任之,致使魚目混雜、特色漸失,在一般里泯滅了自己,殊為可惜。
第四,政府倡導力度不夠,規格、標準制定闕如。例如在建筑風格上,應改變建房者自行其是的做法,對建筑的外觀風格樣式作出統一的要求:內部不做規定,外部風格必須相對統一,這樣才能獲得整齊、統一的視覺效果,也更能彰顯白族建筑的風格和特色。白族服飾的樣式應有相對統一的規范,以免弄成四不像,讓人不知面對者何物。對白族菜系的菜品、食材、制作工藝、命名等,也應有較為規范的要求,便于識別和推廣……總之,在規范標準和引導推廣等方面,政府花的心思、力氣和投入都是遠遠不夠的。大而化之的號召多,實實在在的研究少;口頭上的文章多,切實可行的措施少;落在紙上的扶持政策多,真金白銀的實際投入少。這些方面若是與楚雄、涼山等周邊的民族自治地方相比,差距是較為明顯的〔3〕。
三、視覺性白族文化元素在旅游開發中的廣譜應用與實現途徑
(一)編制視覺性白族文化元素指南與圖譜
文化存在與公眾認知之間,往往會存在著一定錯位和隔閡,要克服這種認知性文化障礙,政府、媒體和相關文化機構應在認真篩選的前提下,編制視覺性白族文化元素指南,并積極利用媒體尤其是新媒體向公眾進行普及教育,供社會公眾認識和選擇;同時繪制視覺性白族文化元素圖譜及其分布圖,讓視覺性白族文化元素的使用者和旅游者能夠按圖索驥,找到原汁原味的白族文化元素,從而實現使用、消費、認知、傳播一體化。靜態的視覺性白族文化元素是沒有生命力的,只有讓它存在于大庭廣眾之下、應用在日常生活之中,以其民俗性、文化性、審美性、娛樂性、實用性而獲得公眾認可并主動應用和傳播,才會帶來視覺性白族文化元素充滿活力的遍地開花〔4〕。在這方面,一定要去除孤芳自賞與神秘化的心態,讓白族文化走向大眾、走進生活,并獲得多媒體支撐,這樣才能獲得廣泛堅實的群眾基礎。
(二)規范視覺性白族文化元素的應用
旅游開發想走特色化道路本無可厚非,但缺乏一定規范和忽略了白族文化內核同一性隨心所欲對白族文化元素的所謂“特色化”運用恰是目前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對視覺性民族文化元素,濫用與肆意篡改使用,是導致其變形與矮化的最大風險〔5〕378。需知對于視覺性白族文化元素的運用,內在同一性越強,外在識別性才越高〔6〕,對白族建筑元素、圖騰元素、服飾色彩元素、飲食食材與加工元素即成品樣式和命名,均應有較為規范的約束和管理,以避免使用中的隨意更改和加工過程中的隨意歪曲,從而失去白族文化本來的內涵。民間建筑與公共建筑應有意識地使用和摻雜某些白族建筑文化的視覺元素,從而增加民族建筑形象識別功能;服飾應體現白族尚白喜紅的特點,選擇民族服飾設計主色調,在此基礎上融合區域特色,形成百花齊放格局;圖騰視覺元素應突出白族一方面信仰虎崇拜、同時喜歡溫順動物、圖騰圖案比較人性化的特點,設計出與其他民族不同的視覺性圖騰元素并應用于裝飾、藝術設計、工藝品制作等各個方面;飲食上,體現白族食材選擇和飲食制作生產與生活一體化、精細化、審美化的特色,對白族菜系和食譜進行發掘與開發,形成半標準化的食材、菜品和制作工藝。多元化和百花齊放是我們對待白族視覺性民族文化元素應有的態度,但應用上的規范性、傳播上的標準化或準標準化,同樣是確保其生命力延續的保證,應改變以往任其自由發展、政府不聞不問的狀況,加強引導,形成必要的規范。
(三)將視覺性白族文化元素納入非物質文化遺產范圍中進行管理
白族視覺性文化元素絕大多數是活態非物質文化遺產,它們在白族人的現實生活之中仍然在使用、延續、傳承著。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需要找到依托點和抓手,以視覺性白族文化元素作為保護和傳承的主要對象,可以起到典型化與事半功倍的效果;視覺性白族文化元素需要找到強有力的政策支持,納入非物質文化遺產范圍中進行管理,可以借力發力,何樂而不為?在這方面,政府和媒體都應該有更加自覺、有效的行動。不要等瀕臨滅絕才想到保護,而是把保護和利用、生活和文化有機地統一起來,使之獲得更為廣闊的天地〔7〕。
(四)扶持視覺性白族文化元素的創新開發與新媒體應用
白族視覺性文化元素的開發,必須創新思維,融入新的元素,采用更加靈活多樣的開發方式使之增添時代氣息。譬如與文化創意產業結合,通過影視化、動漫化、卡通化等形式,讓白族歷史獲得新的表達,讓白族文化更加靈動鮮活,增加青少年對白族文化的感知與興趣。同時,注意借助網絡、微信、微博、電子書等新媒體載體加以傳播,以擴大白族文化的影響。
政府可以采用委托開發、合作開發、懸賞開發、購買產品、設立風險投資基金等形式,對相關的文化創意企業進行扶持,以實現視覺性白族文化元素產品化、系列化、市場化;同時,對民間文化創新——特別是民族工藝品設計開發上的創新予以獎勵,使公眾感知到政府的熱情和鼓勵,同樣能夠獲得激活效應〔8〕。
四、結語
視覺性白族文化的開發應用,既需要相關主體尤其是政府部門在觀念、手段和方法上的轉變,但更應當認識到,視覺性白族文化的內核仍然是白族文化,因此,應當牢牢把握文化的開發必須遵循識別性與同一性這一原則〔5〕211,明確視覺性白族文化元素的旅游開發,應當是多樣性的,豐富多彩的,這是文化開發的識別性所決定的;而文化開發的同一性,是指公眾在體驗的過程中,雖然形式載體可能各不相同、豐富多彩,但公眾體驗后,又總能將體驗和認識歸結到“白族文化”上來,而不會將白族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混淆,即無論以何種方式開發視覺性白族文化元素,滿足何種類別公眾或旅游者對于白族文化消費的需求,白族文化的內核都不走樣。顯然,這個課題有待今后更加深入的探索。
〔1〕馬木蘭,汪宇明.非物質文化遺產旅游產品化的轉型模式〔J〕.桂林旅游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8(2):282-287.
〔2〕弗蘭克·費瑟.未來消費者〔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72.
〔3〕楊穎.涼山少數民族文化旅游資源及其在旅游開發中的利用〔J〕.貴州民族研究,2012(3):80-83.
〔4〕廖文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態保護與文化產品開發〔J〕.商業時代,2013(14):125-126.
〔5〕秦啟文.形象學導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6〕胡貴華.文化元素在旅游規劃中的表達〔D〕.成都:四川師范大學,2012.
〔7〕鄧阿嵐,趙紅梅.云南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旅游開發:以昆明調為例〔J〕.旅游縱覽,2012(8):12-14.
〔8〕陳曉曦.羌繡視覺元素在新北川旅游商品包裝設計中的應用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學,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