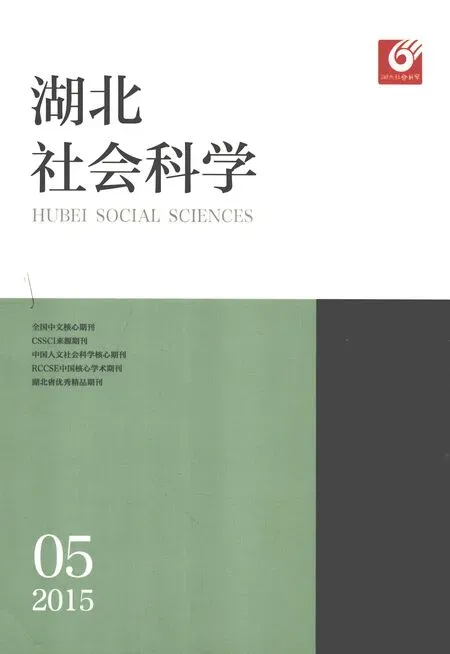司法審查正當性之立論與補強
江國華,黃 普
(武漢大學法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違憲審查制度是當今世界各憲政國家所共有的制度,它與代議制度、權力制約體制以及人權保障制度并稱為支撐憲政國家的四大支柱。[1]其是指依據憲法程序或憲法慣例,由特定的國家機關對法律進行合憲性審查并作出判決的制度,旨在保障憲法授予的各項權利不被侵犯,確保憲法穩定、有效地實施。當今世界各國的違憲審查模式不盡相同,[2](p335)但無論這些模式如何變化,違憲審查的權力大都掌握在司法者手中。這一習慣得益于美國開創的司法審查制度,作為違憲審查模式的鼻祖,司法審查制度肇始于1803年“馬伯里訴麥迪遜”①5 U.S.137(1803)。一案,該案確立了美國由司法機關行使違憲審查權。此后,世界各國也紛紛借鑒美國的經驗,確立了司法審查制度在防止權力濫用、保障基本人權從而促進憲政民主機制良性運行方面獨一無二的地位。
然而,在發揮其功能作用的同時,司法審查制度卻飽受質疑和非議。最重要的問題有三:第一,民主性問題,即由司法機關審判權力機關通過的法律,有反民主之嫌;第二,合憲性問題,即司法機關進行違憲審查并非都得到了憲法的授權;第三,違憲性問題,即司法審查權是否會打破憲法所確立的權力之間的相互制約與平衡。基于以上正當性拷問,司法機關并不當然被認為是憲法的代言人,更有甚者將其描述成是披著黑色法袍、打著憲法旗號,表達少數人看法、維護個別集團利益的寡頭政治集團。[3](p127)
一、司法審查正當性之立論
上世紀60年代以來,面對質疑,學者們通過收集大量案例與數據,在經過嚴謹的假設與求證后仍毅然為司法審查辯護,其中最著名的有“人民意志至上”、“二元民主”、“最小危險部門”等證立司法審查正當性的理論;也有學者提倡在實踐中調整和打磨原有的制度,使之趨于完善。根據這些理論的出發點,可以將其分為實體理論與程序理論兩大類。
(一)“人民意志至上”論。
司法審查制度的正當性基礎發軔于此,這一古典理論源自于美國開國元勛漢密爾頓在其《聯邦黨人文集》第78-83篇關于司法權的討論中。首先,他通過考察各國權力部門,察覺到司法部門“對于憲法中所規定的政治權利總是危險最小的”,因為行政機關能分配榮譽,且能控制國家的暴力機關,立法部門掌握財政權,且直接規制公民權利與義務。相比之下司法部門“既無武力也無意志,而只有判斷”,故其干擾和危害公民權利的能力肯定是最小的。其次,為了確保人民意志的至上性,他提出“有限憲法”的概念,即憲法中應包含對立法機關權力的限制,例如法律不能剝奪公民權和財產權,不能溯及既往等。在立法機關內部設置監督機構是不可行的:這既與中立原則相悖,也沒有憲法依據,況且,人民的意志也不能屈服于其自己選出來的代表們。此時,法院可以充當人民和立法機關之間的調解員,使立法機關在其權限范圍內行使權力。要保持此種限制,最好的辦法是通過中立的法院行使違憲審查權;況且,因為憲法必須被法院視為最基本的法律,于是解釋憲法及其制定程序也是法院義不容辭的責任。
賦予法院違憲審查權,并不是說司法權凌駕于立法權之上,它僅表明人民的權力同時高于兩者。[4](p395-398)當通過法律表達的立法意志違抗通過憲法表達的人民意志時,法官應該接受后者。每當具體的法規抵觸憲法時,司法審判官的責任是罔顧前者遵從后者。[5]
(二)“最小危險部門”論。
美國耶魯法學院教授比克爾在1962年出版的《最小危險部門——政治法庭上的最高法院》中為證立司法審查制度開啟了新篇章。首先他明確提出違憲審查在國家日常制度運行中的必要性。其次他認為相比之下,法院是“最小危險部門”。具體說來,法院具有立法機構和行政部門所不具備的處理原則問題的技能。首先,法官受過嚴格的法學教育和司法訓練,潛移默化地受法治精神的影響,保持著“一種始終如一的制度性習慣”,故會“超然地遵循那些追尋治理之目的的學者的方式行事”,更能篩選這個社會永久性、長遠性的價值,從而確立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則;其次,法院所具有的另一種優勢是法院的實踐優勢。立法機構極目所見不過抽象的法律文本,行政機關則難以對所執行法律深入思考,只有法院可以通過處理現實案件,給所有的文本呈上一個個能擴展、修正人們視野的論據,從而推動了社會制度設計與生活實踐的磨合。依此,法律原則不僅能得到遵循,還可借由某種過程而發生演進。[6](p26)
法官所擁有的“自由”并非絕對的、任意的自由,他不能一味追逐自己的美善理想,不能天馬行空地作出決斷,也不容許隨意創新;此外,他也不得屈從于“容易激動的情感”和“含混不清且未加規制的仁愛之心”。法官應該做的是篩選那些經歷了實踐的重重考驗且深得人心的原則,并從中汲取啟示;法官自由裁量的依據應以傳統為知識根據,以類比為方法,受到制度的紀律約束,并服從“社會生活中對秩序的基本需要”。[7](p88)
(三)“二元民主”論。
就在司法審查的擁躉者從實體價值層面為“反多數難題”所困時,美國耶魯大學教授阿克曼從程序正義的角度巧妙地提出了辯解意見。他在《我們人民:憲法的根基》中,認為之前司法審查的支持理論雖百家爭鳴,但其根基都在于“民主要求將制定法律的權威賦予解釋普選獲勝的人們”,即一開始就推定所有的立法都是民主的,在此基礎上,學者們“竭力通過一兩次機敏的辯論保全最高法院”。然而,此種代議民主是值得推敲的,憲法與普通法律的根本區別在于“我們人民”與“我們的政治家”,于是他根據民主的不同表達程序渠道,提出了“二元民主”的憲法理論:第一種是由“我們人民”在所謂“憲法時刻”所作的決定,即“憲法決定”;第二種則是由其政府作出的,即由人民選舉的政治家們在日常立法所作的決定,即“普通立法決定”。[8](p5)在民主的層面上,憲法價值比法律高,因為它來自于“更高層次的立法”,是由大量被動員的公民一起爭論深思熟慮后所確立的。制憲或修憲者在人民高度動員、參與的“憲法時刻”所形成的憲法決定具有高度正當性,換言之,所有的“普通立法決定”都最終受著“憲法決定”的約束。所以,即使“普通立法”系統運作良好,也必須設計出一種制度框架,防止民選的政治家借由普通法令廢除由人民在“憲法時刻”作出的評判。
此時,現代法院被認為是“憲法決定”最好的守護者,因為在探知憲法真意方面,它最具有優勢:法院以捍衛由民眾反對的精英政治腐敗的原則來維護民主,以其“值得依賴的工作詮釋了我們人民在奠基、重建和新政時期千錘百煉得出的憲政原則。”如是所述,阿克曼教授巧妙地解開了“反多數難題”,司法審查也進一步成為憲法的守護者、憲政民主的捍衛者,對于維護“憲法決定”、防止政府“普通立法”侵害方面舉足輕重。[9]
(四)“代表性補強”論。
有學者并不回避司法審查理論上的正當性缺陷,他們認為不能僅僅從價值導向層面作自圓其說的努力,因為這無益于解決價值的來源或標準問題,相反,應該直面正當性缺陷,并在實踐中通過一些制度性改良來補正,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伊利的民主強化方案。
伊利把聯邦法院比作比賽場上的裁判,其關注的只是比賽過程是否正常,而不是結果如何;同樣,聯邦法院也應只監督代議程序是否正當,而不是代議機關的價值判斷,如是,聯邦法院就不能干預代議機構最終通過的實體性決定,而只能審查作出這一決定的過程,如是,司法審查不僅不違背美國的代議民主制,而且還完全支持它,因為“它致力于通過監督代議程序來完善代表制,確保我們選舉出來的代表真正代表我們”。[10](p99)
伊利進一步指出,“政府失靈”即代議程序不值得信任的情形大體有二:一是體制內的掌權者控制權力更迭渠道,防止體制外的無權者進入體制內;二是少數群體雖然有事實上的政治權利,但是他們的權利沒有得到相應的重視和保護。[11](P103)
基于以上“政府失靈”的弊端,法院必須要強化民主。于是,伊利所謂“代表性補強”的程序性方案——一種“參與導向的、強化代議制的”司法審查理論應運而生。
針對第一種政府失靈的情形,司法審查的功能在于疏通政治變革的渠道,確保民主參與途徑的暢通。具體來說,在保障言論自由方面,只要言論確實能促進政府利益,那么司法審查至少必須消除對這些忠言逆耳的壓制。對言論的不當壓制不容姑息,除非對促進國家利益來說有必要,否則不得壓制第一條憲法修正案所保障的自由。沃倫法庭期間①指1953年至1969年厄爾·沃倫任首席大法官時期。選舉領域的大量判決體現了司法審查旨在加強代議制這一點,能動的司法審查對選舉權的保障重點在于平等公正地重新分配議席。1964年的“雷諾茲訴西姆斯”②377 U.S.533(1964)。案中聯邦法院所選擇的“一人一票”標準具有里程碑式意義,它打破了美國傳統的“政治問題”回避原則,越過議席分配問題,使司法機關積極介入,切實保障阿拉巴馬州每一位公民在事實上都能夠享有與其他人一樣的平等投票權;同時,類似案中持少數意見的斯圖爾特大法官在此基礎上還增加了另一項要求:系爭制度設計“必須是不會讓全體選民的多數意志遭受系統性的挫敗”,③Lucas v.Colorado Gen.Assembly,377 U.S.713,753-54(1964)。這就是所謂的“共和政體條款”,它和前述“平等保護條款”一起維護了美國代議民主制的公正和公平,促進了美國的民主化進程。
針對第二種少數群體權利被忽視的情形,司法審查則承擔著強化代議制,“確保少數人的利益得到代表”的功能。雖然“一人一票”原則的確立對于保障公民投票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但這也易于促使形成握有多數票的利益集團,他們可以通過投票使自己獲利而犧牲他人的利益。此種利益分配的失調,原因存在于產生此種分配結果的程序當中,而司法審查正是一種程序導向的審查機制的運作方式。在沃倫法院時期,聯邦法院努力將保護對象擴展到種族分類這一核心類型之外,外國人、“非婚生子女”甚至窮人等都被列入了受法律特別保護的名單之中。繼承了斯通大法官在“卡羅琳產品案”中指出的“‘分散而孤立的’少數人有權獲得憲法的特別保護,避免受到政治程序的侵害”,④United States v.Carolene Products Co.,304 U.S.144(1938)。布萊克門大法官又代表聯邦法院作了重述:“作為一個階層的外國人,是‘分散而孤立的’少數人的最好例子……對于這些人……給予更多的司法關懷是恰當的。”①Graham v.Richardson,403 U.S.365,372(1971)。
二、司法審查正當性之典型詰難
由于馬伯里訴麥迪遜案本身的政治性和偶然性,最高法院具有“篡權”行徑之嫌疑,司法審查制度自脫胎起便伴隨理論上的質疑和擔憂,大致有三:憲法依據不足、司法專權和“反多數民主”。這三種質疑分別從權力來源、權力分立和權力制約的角度挑戰了司法審查權的正當性,而后歷史也在某種程度上證實了此種擔憂。
(一)民主性詰難:“反多數難題”。
民主的多數議決制一向被認為是民主理論的基石。然而司法審查卻是民主體制中的一種“反多數力量”,例如在美國,制定法律的權力機關是由人民或人民代表組成的,而進行司法審查的法官卻是由政府或其分支任命,而且為了保證司法獨立,還規定了法官終身制及其優越的福利待遇。[12](P127)非民選的最高法院能夠否決民選代表們通過的法律,如是民主的情感便受到損害,這就是司法審查的“反多數難題”。司法審查是由不直接對選民負責的少數幾位法官審查多數選民選舉產生的議員半數以上所通過的法律,而且,司法機關并不對人民及其代表負責,為了體現司法獨立,司法部門的判決意見也往往不受公眾輿論的左右,這種做法顯然是“不民主”甚至是“反民主”的。因此有人提出,防止國家機關因違憲而濫用權力的保護者不應該是法院,憲法最好的守護者應該是人民自身。鑒于以上觀點,法院在進行合憲性審查和裁決時也難免顯得底氣不足,法官內心充斥著“不安感和甚至有些負疚感”。
對于此種民主性詰難,許多司法至上的主張者亦感到無言以對,特別是若最高法院的判決偏離占優勢的公眾意見最終致使社會動亂,面對聲勢浩大的輿論和鐵證如山的事實,想為其辯護都無從下手。例如,19世紀末至20世紀30年代,最高法院一味試圖發揮市場經濟的無限作用,撤銷了大量的經濟立法,最終因忽略社會公平正義和財富分配問題而加劇了社會矛盾,直到四五十年代,羅斯福總統以國家干預經濟的“新政”才終結最高法院這一行為。而后,人們開始將目光更多地投向社會公平、人權保障等方面,社會上的政治少數派和得不到充分代表的人們開始得到更多的同情和幫助,然而,法院往往并不為這些思潮所動,于是在處理共產主義、少數民族權利、宗教自由等新問題時,一些與民意背道而馳的判決將矛盾又推向了風口浪尖。
(二)合憲性詰難:憲法依據不足。
國家機關權力的行使應當有憲法明確的授權,一部民意憲法是該國人民意志的反映,無憲法授權的權力會有傷害人民權利之風險。然而,在最終通過的美國憲法文件里并沒有明確地規定違憲審查權由司法機關行使,只是在第六條第二款規定:“本憲法與依照本憲法的合眾國法律,及以合眾國的權力所締結或將締結的條約,均為全國的最高法律。即使與任何州的憲法或法律有抵觸,各州法官均應遵守。”這僅表明聯邦制定法優于州制定法,州法院對此有審查權,但沒有規定聯邦法違反聯邦法的審查由什么機關審查的問題。[13]由此可以看出,無論是默示的還是明示的,都不能在憲法中找到法院擁有違憲審查的憲法依據,開國先輩們也從來無意向司法機關授予這類權力。[11]試想,法院自己的權力都缺乏憲法依據,何談有資格審查國會通過的法律是否違憲?據此有學者認為,司法審查完全是最高法院一廂情愿的篡權行為,來源不明的權力在行使時勢必會引起人們的不滿,從而引發社會矛盾。
司法審查實踐所產生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射了此種觀點。例如,19世紀中期的“斯科特訴桑弗德”案②60 U.S.393(1857)。。在判決中,最高法院認為“非洲裔美國人,無論是否為奴,都不是美國公民,在法院沒有訴訟權利”,還宣布國會通過的廢奴法律違憲,確立了奴隸制度的合憲性。這個明顯帶有歧視、違背人權的判決一經作出立馬引發了南方反奴隸制諸州的強烈不滿。事實證明,此判決不僅引發了美國1857年的財政危機,還成為后來南北內戰的間接催化劑。
(三)違憲性詰難:司法專權,打破三權均衡格局。
一切有權力的人都趨向于濫用權力,而且還趨于把權力用之極限,這是一條亙古不變的經驗;為了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14](P67)三權的明確分工與制約是美國的開國元勛引以為豪的制度,三權分立的原文表述是the check and balance of three powers,直譯為“三權的相互審查與平衡”,即在這一格局下,權力能夠相互制約與監督。司法和立法、行政一樣對憲法解釋具有同等效力,它的判決不約束政府的其他部門(其他部門當然也不能約束司法),這就是權力的分離、分立與制衡的含義。[15]任何一種權力——即使發揮到其最大效能——都無法單獨實現憲政,權力之間必須相互制約與配合方可使國家制度良性運轉,換句話說,分權的最終目的在于讓權力最有效地發揮其功能和價值。[16]然而司法審查則會導致權力的平衡被打破,因為司法否決權是對立法權的篡奪,當法院在具體的憲法案件中宣布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因違憲而無效時,司法成為一種終局性的權力,踐踏了立法機關所制定的法律,限制了立法權的行使,侵犯了立法機關政治形成的空間。
由此不難產生此種擔憂:司法權會凌駕于立法權之上,造成司法專權。麥迪遜曾提到,如果一種權力能夠操縱其他權力的行使,那么自由憲法的諸原則必將不復存在。所以,如果認為司法審查是正當的,但憲法卻并沒有對最高法院的權力作出限制,法院在宣布立法機關的法律因違憲而無效時,僅憑主觀推斷并不明確的“法律精神”或“立法者意圖”,那么它對憲法的解釋可能會超越其權限,并可通過模糊或彈性的司法審查基準來不斷擴充權力;更為可怕的是:它不對人民及其代表負責。換言之,最高法院或將演變成一種獨立于人民及社會的“意志”,只有使用武力才能加以“控制”。
關于司法專權之隱患這一點,連法官們自己都不否認。首席大法官沃倫毫不避諱地承認法院實際上是在立法。另一位首席大法官馬歇爾更是坦然解釋何謂“司法立法”:“法院立法不是有意識的,立法并非旨在侵犯國會的權力,而是我們工作的特征。如果兩個訴訟人來到法院,他們對國會的法律文本存在歧義,最終我們認定它是某種意思,這就意味著,我們其實是在制定法律……”。[17](P353)
現實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證明這一點。例如,在1905年的“洛克那訴紐約州案”①198 U.S.45(1905)。中,最高法院宣布紐約州一項限制面包師勞動時間的法案違憲,因其違反了憲法第十四條公民自由權。因為此案,這一時期被命名為“洛克那時代”。法院以實質正當程序和保護市場經濟、契約自由為由,在1899-1937年間共宣布180多部法律違憲,導致貧富分配的更加不均等,社會矛盾愈加劇烈。直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羅斯福總統確立了國家干預經濟的“新政”,洛克那時代才宣告結束。在洛克那時代,最高法院被描述為“司法積極但政策保守”。[18](P386)洛克那時代因其激進的司法積極主義而受到廣泛批判,其判決意見過分偏離了國會意志,阻礙了公正分配社會權力和財富的政策實施。
三、違憲審查正當性之補強
兩百多年來,面對司法審查的種種質疑聲,破解的方法也和質疑本身一樣多。對于違憲審查存廢問題的討論,其價值已經超過了這一制度本身。
(一)民主性補強:實質民主觀。
對于“反多數難題”的破解,大多數學者的立論點都是:單純的議會民主是一種“理想民主”,存在憲政所謂“多數暴政”之隱憂。理想的民主所遵循的實際上是多數的絕對推崇和無限肯定,少數可能被孤立,并往往被多數決策規則所傷害,少數提出的政策通常被否決或漠視,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人權的保障與權力的控制。[19]
美國學者德沃金認為最終為大多數人所贊成的決定并不一定能反映民主的本質,也不可作為民主的檢驗標準,因為多數至上主義的前提是不能否認個體擁有受大多數人尊重的重要道德權利。他認為“多數至上主義”已經禁錮了美國憲法學者們的思維,使他們不容置疑地認為司法審查損害民主制度。但多數人至上主義最大的弊端在于沒有考慮到如果少數人的權利得不到尊重與保護,國家的民主性質本身就值得懷疑。據此他提出“實質民主”理論,這是一種“結果導向性”的民主概念,著重考量政治運作是否具有公平的結果;他進一步討論了“民主的合憲性構想”,認為民主并不能一味地旨在保障大多數所贊成的集體決策。他所重新理解的民主目標是:作出集體決定的政治機構必須予以社會共同體中的每一成員同等尊重和關注,具體體現為這些機構的組成和運行都要有充分的政治代表。這種構想要求多數至上的程序出發點是對公民平等地位的關注,而不是對多數裁定規則(即半數以上的人有權作出全體必須服從的決議)的承諾。[20](P13)
而最高法院調解矛盾必須在“多數決”和“保少數”之間尋求一個最佳平衡點。實質民主致力于全體人民的利益,包括多數和少數,不僅應該確認和保護多數決,更需要重視少數人的特殊權益,尊重和反思他們的意見。[21]法院最終的目的是協調各利益集團之間的訴求,維護民主秩序,進而保障所有公民的權利。因此,司法審查不僅與民主相協調,而且它本身的民主性質是不證自明的。
在知識經濟時代,社會需要一批既懂專業知識又能將理論快速運用到實際操作中的人才。因此,在《商品學》課程的授課過程中,一方面要讓學生掌握必要的商品學基礎理論與方法,奠定必要的商品知識;另一方面將理論與實踐相聯系,增強學生的商品品種和質量意識,提高學生在實際工作和生活中的能力。但是,在現在的教學中,許多高校僅側重于理論教學,實踐教學尚未開展或重視不足,導致《商品學》教學效果不理想。本文將實踐教學與理論教學方法分別運用于兩個不同的班級,通過定量分析方法探討兩種教學方法對教學效果的不同影響。
民主的基本內核是人民對政府的選擇權和終極意義上的控制權;在人民既不能自由的選擇自己的政府形式,也不能控制統治自己的政府權力運行的地方,就很難有民主發育的條件。[22]保證民選的和任命的官員最終都對其所作所為向人民負責也是真正民主的任務之一。從司法機構——法院的設立來看,它亦是民主的:它首先是依法產生的國家公共機構。于是法院應該被法律視為人民意志的體現,其職權、活動原則、行為方式等,都受法律的制約,當然也最終受人民意志的控制;不僅法庭的組成和司法程序必須“依法”,而且判決本身在特定情況下也要有“法定”依據。法治的概念包含司法判決必須合理,在特定情形下,判決依據必須合法。司法審查的正當性來源于法院判決的法治因素,獨立于法官個人信仰的內在價值和所追求的結果。[23]所以法院并不是法官或其他人隨心所欲設立和運轉的機構,從理論和制度淵源上來說,它是依據憲法、法律,最終也是依據人民意志而組建的國家機關。
還有學者提出區分“政治正當性”和“民主正當性”,認為后者只是前者的一個組成部分,而政治正當性還有很多其他的源頭。雖然司法審查在某種程度上缺乏民主正當性,但是公民之所以遵守他們并不贊同的政治決定,一個很好的原因是這些決定是由設計精良的守護民權的組織作出來的。[24]
(二)合憲性補強:實質合憲論。
這種理論認為,精確、具體地保護人民權利的前提是使違憲審查成為國家制度設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換言之,違憲審查必須存在,否則,當立法部門創制出有損人權的法律時,公民便會因為缺乏救濟途徑雖飽受災難卻也無可奈何,故國家以多數決通過的法律需要接受是否違憲的審查,特別關注其是否侵害人民的基本自由和權利。這一點馬歇爾大法官一開始就意識到了,他在馬伯里訴麥迪遜的判決書開頭便寫道:“一件與憲法相矛盾的法案是否能夠成為這個國家的法律,這個問題對于合眾國來說是一個具有極大利害關系的問題。”也就是說,一部成文的至上的憲法當然應該“以公民生活”為終極關懷,確立合理的政府結構以為公民謀求一種更為優良的生活方式,[25]但更為關鍵的則是將憲法付諸實踐及解決憲法爭議,而不僅僅是將憲法停留在政治或哲學宣言層面。此時,在一個憲政政權中,制度所發揮的最顯而易見的作用是賦能,以使得各種行動和結果可能發生。從法律運行機制來看,將法律廣泛而抽象的規定與普遍要求轉化為社會成員的具體單個的行為,并形成一定的法律秩序,必須要經過司法這一中介環節。[26]
實質合憲論,因其內在地獲得了實用主義或者現實主義的某種秉性,故此可稱之為現實的立憲主義,是一種側重于從價值層面解釋憲法判斷之依據的憲法哲學。基于這種哲學,憲法價值或者原則成為判斷既存事實之合憲性的基本準則。[27]司法審查能促使純理論性的、抽象的自然法價值和高級法理念具體而有效的熔鑄于實定法規之中,切實保障了憲法成為真正至上的規范。從此意義上說,司法審查捍衛憲法精神的屬性當然具有合理性、正當性。
雖然憲法沒有明確將違憲審查的權力授予司法,司法審查沒有憲法的直接依據,但也可以算是有法律依據的,第一屆聯邦國會于1789年制定的《司法法》第25條規定:“凡州最高法院判決合眾國法律無效,或在州法律的效力同合眾國的憲法或法律的關系上發生爭執判決州法律有效時,對其判決可向聯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訴。”所以,當最高法院宣布州立法機構的某一活動無效時,它也可以承諾在全國范圍內對同樣的活動都予以撤銷。應當說這一規定默認了聯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審查權。
(三)違憲性消解:實質法治主義。
關于司法權凌駕各權之上的觀點,有學者持商榷態度,他們認為司法審查只是阻止立法機關違法權力的行使。故關于司法部門會侵犯議會權力亦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因為首先,司法對立法的作為空間是相當有限的,它充其量只能對具體個案所涉及的某部法案的某個條款作出違憲性裁判,但相對于整個法律體系而言,可供司法盡情演繹的機會并不太多。[28]其次是眾議院有權對司法人員提出彈劾案,參議院有權審理該案,倘若法官采取一系列篡奪議會權力的行為,就有可能激起議會的一致憤怒,從而被撤銷職務。[29](p1039)所以,認為司法審查原則與三權分立制度相互矛盾,實乃皮相之論。
結語
綜觀先賢大師們對于司法審查制度的質疑詰難及消解理路,在司法審查制度是優是劣這一問題上,從理論上也許永遠無法精確證明,在實踐中也不能從一而論。對于人文科學來說,真理并非越辯越明,也不一定能在某天水落石出,但這一場場高山與高山的對話最終的落腳點并不在證明理論,而在完善社會。關于司法審查,雖然沒有一家言論能做到滴水不漏,但都是立足于社會現實需要和實際運轉情況,將自己的信念和希望,放在天平的某一側,然后做出評估:指針可以移動多大幅度。
法律理論作為一種思想理論的實際存在,雖然不具有客觀物質的決定力量,但對人們的行為選擇、價值取向起到潛移默化的指導作用。[30]所以在此,無論如何我們都應當感謝美國所確立的司法審查模式,不僅因其在不同的時代解決社會糾紛的功能作用,更重要的是無數先賢圍繞這一制度互相博弈、互取所長做出的思考與改善,極大地豐富了法哲學的思想內涵,為法學理論的精深和制度的完善提供了豐富的資源,也為憲法監督模式的構建提供了理性的前提和有力的思想武器。
違憲審查是憲政的核心要素之一,其對于中國的憲政建設而言意義非同凡響,而就其現實性而言,在我國建立違憲審查制度的時機已基本成熟,完全可以在現有體制的框架建立起切實可行的違憲審查制度。[31]所以這場論戰也為違憲審查制度在我國的移植設想提供了經驗土壤,更為我國借鑒西方法律,利用本土資源,銜接時代背景提供了參考依據。
[1]周葉中.關于憲法的幾點認識與憲法實施的幾點建議[J].湖北社會科學,2004,(6).
[2]江國華.憲法的形而上之學[M].武漢:武漢出版社,2004.
[3]陳力銘.違憲審查與權力制衡[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
[4]Alexander Hamilton,James Madison,John Jay.The Federalist Paper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5]熊敏瑞.確立司法審查制的理性思考[J].湖北社會科學,2004,(6).
[6][美]亞歷山大·M·比克爾.最小危險部門——政治法庭上的最高法院[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7][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過程的性質[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8][美]布魯斯·阿克曼.我們人民:憲法的根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9]B.Ackerman.The Storrs Lectures:Discovering the Constitution [J].93 Yale Law Journal 1013(1984).
[10][美]約翰·哈特·伊利.民主與不信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11][美]艾伯特· P·梅隆,喬治·梅斯.美國司法審查的起源與現狀——篡權問題與民主問題[J].法學譯叢,1988,(6).
[12]陳力銘.違憲審查與權力制衡[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
[13]陳云生.違憲審查的原理與體制[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14]江國華.憲法哲學導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15]Powe Jr,Lucas A.Are the People Missing in Action (and Should Anyone Care) [J].Texas Law Review2005(2004).
[16]江國華.憲政與憲法訴訟[J].理論與現代化,2002,(4).
[17]陳紅梅.美國司法審查的民主正當性之辨[J].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1).
[18]Agnew,Jean-Christophe,and Roy Rosenzweig,eds.A Companion to Post-1945 America[M].New Jersey:John Wiley&Sons,2008.
[19]趙春麗,劉彩霞.理解民主的兩種思維方式及其評析與啟示[J].湖北社會科學,2007,(5).
[20][美]羅納德·德沃金.自由的法——對美國憲法的道德解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21]胡肖華,江國華.民主、憲政民主與憲法訴訟[J].湘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1,(5).
[22]周葉中,江國華.82年憲法與中國憲政——寫在82年憲法頒布實施20周年之際[J].法學評論,2002,(6).
[23]Tremblay L B.20 YEARS UNDER THE CHARTER:Legitimacy of Judicial Review:Special or General?[J].Windsor YB Access Just21(2002).
[24]Richard H.Fallon.The Core of an Uneasy Case for Judicial Review[J].121 Harvard Law Review 1693(2008).
[25]江國華.中國憲法學的研究范式與向度[J].中國法學,2011,(1).
[26]石晶.制度建構視域下的近代司法獨立研究[J].湖北社會科學,2013,(5).
[27]江國華.實質合憲論:中國憲法三十年演化路徑的檢視[J].中國法學,2013,(4).
[28]江國華.常識與理性(四):走向綜合的司法改革[J].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2,(2).
[29][美]漢密爾頓.聯邦黨人文集[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30]那述宇.憲法監督模式選擇的成就因素述論[J].湖北社會科學,2003,(12).
[31]江國華.劉松山先生的《違憲審查熱的冷思考》質疑[J].法學,2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