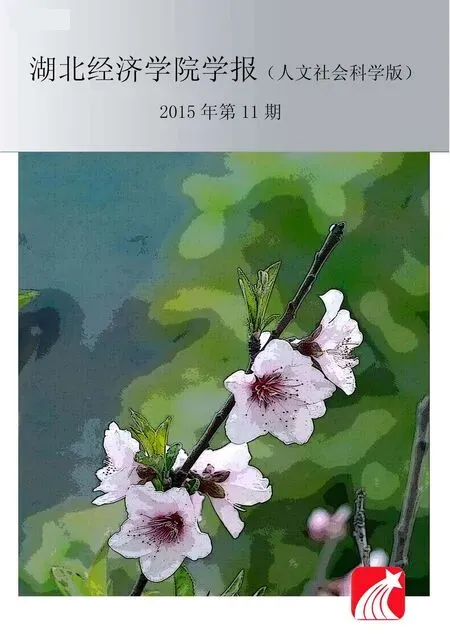馬口陶“八仙壇”裝飾紋樣的藝術特色
胡蘭凌
(湖北經濟學院,湖北 武漢430205)
漢川馬口窯的“八仙壇”陶器,具有繪畫性強,造型別致的特點,其人物形象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生變化,蘊涵著自明清時代起至近代各個歷史時期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包括倫理道德、民俗風情、繪畫藝術等豐富的信息,具有珍貴的歷史研究價值。同時它的造型、裝飾特色對研究中國特色的現代設計理論也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漢川馬口窯陶器具有典型的民俗特色,因豐富的物質基礎和深厚的文化底蘊而得到滋潤,燒造從最初的實用性走向工藝性,逐漸發展成為一種獨特的藝術,其造型和裝飾紋樣都別具一格。“八仙”是我國民間廣為流傳的神話人物形象,表現了勞動人民對美好生活最為質樸的愿望,也是我國民間藝術廣泛采納的創作主題。
一、“八仙壇”題材的起源與衍義
漢川馬口窯以生產各類壇子著稱,故又稱“壇子窯”。馬口老陶藝人擅長信手揮刀,在壇面上飛快刮刻出花卉人物,刀法老練、簡潔大氣、虛實相生。“八仙壇”是馬口窯陶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以民間神話傳說的“八仙”為主題,人物造型古雅大方、釉色古樸厚重、刻花裝飾講究,主要部分以劃花剔地的陽紋為主,次要部分以刮花陰紋作陪襯,主次分明。經過上釉,柴窯燒制之后,陶器呈現出一種暖色調的古銅色,質樸淳厚。八仙人物造型也極具特色,并且表現手法隨著時代發展和社會歷史的變遷而變化。這些民間陶器藝術承載著厚重的歷史,也刻畫了荊楚勞動人民質樸生活的喜怒哀樂和期盼強國富家的美好愿望。
馬口窯“八仙壇”陶器造型多為長形大罐,高約30至50公分。造型厚實挺拔、兼具實用功能和裝飾美感。通常是兩個為一對,每只罐上以“開光”形式刻畫四個人物肖像,合為“八仙”。所謂“八仙”,乃是中國民間傳說中的八位神仙,即李鐵拐、漢鐘離、藍采和、張果老、何仙姑、呂洞賓、韓湘子、曹國舅。一般作為酒器,主要功能是貯存酒。其造型豐肩矗立,兼具梅瓶的神韻,但短頸廣口的造型特征又不完全與梅瓶相似,卻更為有力大方,于渾樸厚拙中挺立秀顏。造型集雄渾、壯闊、秀美于一體。[1]
“八仙壇”采用的裝飾題材最早可以溯源自漢代,是號稱“淮南八仙”的八個文學家,當時稱作“八公”。《小學紺珠》記載:“淮南八公:左吳、李尚、蘇飛、田由、毛披、雷被、晉昌、伍被。”由此可見,淮南八仙只是八個文人,并非神仙。但后來因為有淮南王成仙的傳說,后世便附會在他門下的八公也成仙了,稱作“八仙”。
晉代譙秀所著《蜀紀》中,載有:“蜀之八仙”,依次是:“容成公、隱于鴻闬;李耳,生與蜀;董仲舒,亦青城山隱士;張道陵,今鶴鳴觀;莊居平,卜肆在成都;李八百,龍門洞在成都;范長生,在青城山;爾朱先生,在雅州。”上述的“八仙”與現在所傳的八仙,都毫無關系。自從明代吳元泰的演義小說《東游記》一書問世后,“上洞八仙”人物才選定了。吳元泰排定了八仙的順次:一、鐵拐李,二、漢鐘離,三、藍采和,四、張果老,五、何仙姑,六、呂洞賓,七、韓湘子,八、曹國舅。這八仙的組成及排名次序,已經與現在所傳八仙完全吻合,并流傳至今。
到了清代,進一步增加衍化出所謂上八仙、中八仙、下八仙。有人將元、明以來的鐘呂等上洞八仙列為“中八仙”,又增列出“上八仙”和“下八仙”。由于上、下八仙人員的組成,在《何仙姑寶卷》、《八仙上壽寶卷》、《孫悟空大鬧蟠跳會》等書中各不相同,因而上、下八仙都有好幾組。但這些由后世增湊的上下八仙,并沒有被民間接受,也逐漸被世人遺忘。
廣為流傳的民間八仙過海的神話故事,據現有資料考證最早是由明朝吳元泰的《東游記》話本載錄。相傳八仙東渡東海時,不屑于乘風而過,而是將各自的一件仙器投于波濤之中作為舟楫,拐杖(鐵拐李)、搖扇(漢鐘離),紙驢(張果老)、雙劍(呂洞賓)、簫管(韓湘子)、荷花(何仙姑)、快板(藍采和)、玉版(曹國舅)。于是這八件神器就成了八仙身份及無量神通的象征。它們常常出現在建筑裝飾、年畫、剪紙、印染等民間藝術之上。是一種標準、典型而華美的裝飾圖案,稱之為“暗八仙”。都隱喻著吉祥如意、辟邪去惡的文化內涵。這一經過抽象和簡化的八仙集體人格形象,以美學的眼光看,優勢多樣豐富性與內在統一性,局部的異彩紛呈與集合的完善統一交匯融合的整體構成。
宋、元以來,人們不斷把民間的種種傳說附加到八仙的身上,使得八仙的傳說故事越發豐富,幾乎發展成了老百姓心目中神仙的總匯。而到了明、清時期,更是出現了許多以八仙故事為題材的文學作品,作者一方面,作為道家的信徒,在書中宣揚道教宗旨,勸誡世人拋棄榮華富貴,割舍骨肉親情,經受磨難、考驗,以追求得道成仙。另一方面,則是民間傳說附著于神仙的故事,使本來面目呆板的神仙兼具了人情事故,而活靈活現。同時,與市井生活巧妙地融為一體,從而更加生動。這也是使八仙故事受到群眾喜愛、流傳不衰的原因。
傳說八仙分別代表著男、女、老、少、富、貴、貧、賤,由于八仙均為凡人得道,所以個性與百姓較為接近。正是如此,似乎不能找出一個比這一樸素解說更切近百姓們篤實誠樸的意愿。八仙群體的確定恰好是在社會思想發生深刻變化的明代,大力提倡平民,群眾哲學的泰州學派的學說在當時已經使得“大江南北如醉如狂。”市井田間的村婦匹夫們衣食行旅、勞作休憩的自然,就是天下之至道。“道本不遠人”。圣人也是人,他們既不能高飛遠舉棄絕人世,那么何妨不也同匹夫村婦一樣,在這同一個樸素的天地間,水土中生活為人。八仙的意義在于,把千百年來橫在圣賢與凡夫俗子之間的天塹被填平了,八仙不正像來自于壟畝街衙,成仙得道后仍然出沒于民間的圣賢嗎。在這里,所謂“富、貴、貧、賤、”者,意義上都是平民思想,也反應出廣大勞動人民祈求風調雨順、豐衣足食、生活幸福,這些最質樸的理想和美好愿望,飽含著樂觀與自信,洋溢著幸福、喜慶、祥和的氣氛,給人以生存的希望和生活的信念。[2]
二、“八仙壇”陶器的審美意蘊
宗白華先生認為一切美的光來自心靈的源泉,沒有心靈的映射,是無謂美的。藝術家以心靈映射萬象,所表現的是主觀的生命情調與客觀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滲,成就一個鳶飛魚躍,活潑玲瓏,淵然而深的藝術形式,卻非模仿自然的意境。[3]馬口“八仙壇”陶器作為中國民間美術,它們都服務于某一生活實用目的或附于某一實用物品之上。裝飾功能與物質實用功能的結合方式,大致有兩種類型:一、一體二用;二、裝飾基本上外在于使用功能,只有對裝飾主體的表層依附關系。第一種關系結構保留著審美現象的原始生成意義,也保留著原始時期的那些形式的形態。這些日用陶器在陶器的發生和發展階段中,體現著由實用創造漸次向形式自律的審美創造過渡的歷程。但在人的文明史上,實用的創造意向與審美的追求眼光自古就展現著相交合的趨勢。民間陶瓷器皿的造型常常體現出實用與審美的完美交融。這種交融不僅是那種美輪美奐的陶瓷觀賞品所給予的美感享受,而是指形式抽象和實用兩種相互沖撞的心態完美的耦合在一起。民間陶瓷的這種完美性的可貴之處,在于進行美感審視的同時從不忽視對實用目的的篤守。
眾多民族藝術品從表現上僅僅是單純的形式裝飾,而實際上卻同某些含義相關聯,并且能夠被人所理解。[4]看民間文化關于一切審美對象都有自己獨特的比喻象征體系,獨特的情感和理解思維體系,以及聯想和暗示的方式。作為一種淡化了的巫咒文化,民間的藝術形象一般含義體系是具有明顯指向性的。[5]例如,花鳥魚蟲,在民間美術中則具有獨特的形——意組合體系。“連年有魚”或“魚兒鬧蓮”圖像里的魚,比之河湖港灣里游動,捕獲的現實對象,在審美主體心理上所引起的激動,就已經發生了質的飛躍。它與文人畫筆下的《落花游魚圖卷》里悠然自在的抒情形象也判然有別。圖像文化內涵的識別,要經過現實功利性的觀照到審美意態,再由審美直觀到特定的文化定式思維這樣的多重轉換。喜鵲立于梅枝的圖式——“喜上眉梢”;蝙蝠、桃構成的圖式——“福壽如意”;馬、猴、蜜蜂組成的剪紙——“馬上封侯”等等,這類圖像的精確含義,實際上都有明確的文化識別關聯。一只虎頭,一顆樹,都包含著比單純美感意向更多的心理需求,情感祈愿。民間美術造型中暗喻象征體系的存在,使得自然形象的輕盈與厚重的文化內涵之間,存在著審美主體的感受顯著的心理張力。
馬口八仙壇陶器都是成對。這也符合中國民間成雙成對、吉祥喜慶的寓意,與廣大勞動人民的日常生活、審美習慣有著緊密的關聯。八仙壇用來盛酒,透氣卻不漏水,釉色也無鉛無毒,用以盛裝食品也不餿不壞,器具質地堅硬如鐵不易損壞,屬于民眾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也是八仙壇廣為流傳的因素。它表達的樸素真理是,對于人類這樣一種天地間的人,在群里中的每一個個體,也會蘊藏著難以估量的巨大潛能。只要他不缺少對自己靈性的自覺和實踐的勇氣,同時,有這樣成員構成的集體,將有可能渡過任何艱難險阻所匯聚成的海洋,終將抵達彼岸,中國傳統的集體主義相交匯的人文精神,在這里表現的非常充分。
八仙壇的出現也正是藝術中“崇高”的一種體現。造物主與被創造的事物之間的關系是藝術用作內容和形式的基礎,才使得藝術具有真正的崇高性格。使“神”成為可以觀照的對象。[6]這種人格化的形象與他們自身的物質存在卻相去不遠。刻畫于器皿之上的八仙,就如同八個音符一般的人物,姿態,大小幾乎完全相似,這種同音反復的構圖旋律,正像是攝影機的連續拍攝下的統一物體的運動進程。以連環畫的形式反復出現,變化而產生出一種跳躍遞進的動感,引導觀看者的思緒聯接天界與人間。他們看似離奇卻實質上很平易的“道”,扶助、勸諭、撫慰、鼓勵他們所出身和曾經棲身與其中的平民百姓們。他們之間,如果說要有什么差別的話,只是前者具有更多出眾的才能以及在觀念中時永生不滅的一點。是世俗觀念依賴于在疲困肉體和精神無助時,能得到撫恤和支撐,生活中缺少現實的,有形的物質扶助,便在觀念張假設出冥冥之中那未來的,無形的,高尚而有人情味的形象。
三、結語
作為神的“八仙”就是人性與神性的對立統一體,也是再現客觀事物與表現主觀態度的對立統一,在中國傳統藝術美學觀念中被反復論及。[7]在馬口窯陶器藝術中,隨處都充斥著生活消費的藝術,對雖然不豐裕甚至貧瘠苦澀的現實生活,它通過民間匠人的智慧創造,給生活增添了無窮意味。始終保持著樂天達觀的態度和執著的熱情,在衣食住行這類基本生存需要得到的滿足形式上,仍賦予它以審美的,情感的絢麗色彩。比之對神明和命運的有形或無形的依托和祈求,“八仙壇”這一類生活的實用藝術具有更可愛的人文精神。民間的現世生活大都是深沉的,而中國大多數民眾對來世的信仰都極為渺茫。他們一生中真正的精神愉悅和安撫,很大程度上都來自這些勞作之余的轉泥弄紙,飛針走線,鼓舞歡騰所帶來的快慰和情感,這也是中國民間藝術審美活動中最哲學化的“現實功用”。
(注:本文系2015年湖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項目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5Y114;2013年湖北經濟學院青年科研基金項目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XJ201320)
[1]李正文.即將消逝的文明[M].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5.42.
[2]左漢中.中國民間美術造型[M].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6.153.
[3]宗白華.藝境[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151.
[4]弗朗茲·伯厄斯.原始藝術[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59.
[5]徐煉.中國民間美術[M].武漢: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5.228.
[6]黑格爾.美學(第二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91.
[7]王朝聞.審美談[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