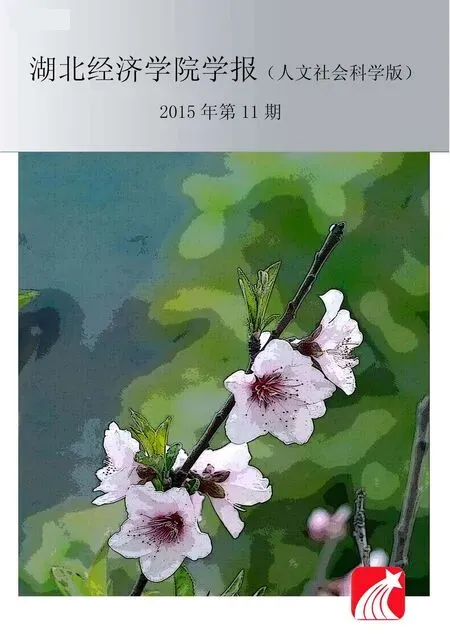從比較法的角度論我國違法所得沒收程序證據規則的適用
史 茜
(安徽大學,安徽 合肥230601)
一、我國違法所得沒收程序證據規則之適用緣由
《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款規定:“對于貪污賄賂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緝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規定應當追繳其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的,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沒收違法所得的申請。”①該款雖確立了違法所得沒收制度,但仍存在一些疏漏。就證據規則方面而言,罪證事實與違法所得二者存有實質性的聯系的證明;取證主體是檢察院一方還是檢察院與利害關系人雙方的判定;證明標準是“優勢證據”還是“排除合理的懷疑”的采納等問題有較多爭議。因此,我國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證據規則的適用仍需改進,下面將從我國違法所得沒收程序證據規則適用的現實因素與域外因素兩方面論述。
(一)違法所得沒收程序證據規則適用之現實因素
理論上,對于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證據規則法條中無明文規定;實踐中,該條款的實際效果也遠不如預期。有鑒于此,“兩高”的司法解釋對此做了補充,如《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535條規定:“人民法院對沒收違法所得的申請進行審理,人民檢察院應當承擔舉證責任”;《最髙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513條規定:“其他利害關系人應當提供申請沒收的財產系其所有的證據材料”,第516條規定:“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申請沒收的財產確屬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的,除依法返還被害人的以外,應當裁定沒收”。[1]可見,該解釋將違法所得沒收程序與一般程序一視同仁,均適用“排除合理懷疑”的標尺衡量,這引發了諸多問題,如:該程序本身屬于特別程序的一部分,若被告不在場的情況下強加適用,易加重取證主體的負擔;取證主體定位不清,易混淆檢察機關與利害關系人之間的地位和關系;證明標準界定不清,“排除合理懷疑”未限定合理的范圍。基于上述現實因素,有必要對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證據規則的適用予以規制。
(二)違法所得沒收程序證據規則適用之域外因素
“誰主張,誰舉證”是美國的沒收程序中通用的證據規則。美國政府主動證明罪證事實與違法所得二者存有實質關系;公民若不服法院的相應判決或是政府的相關決定,則“誰主張,誰舉證”。相關利害關系人若對某項財產宣稱主權,那么要承擔相應的證明責任。在民事沒收程序中,法官采用的是民事訴訟的“優勢證明標準”,哪一方提供的證據材料的證明力占有優勢(哪怕是微弱優勢),則采納哪一方的主張。[2]這種做法,不僅可以緩解檢察機關的負擔,而且給證明標準予以寬松的定位,有利于贓物的追回。
英國則采用了復合的沒收機制,其特點是“民刑并重”,在英國《2002年犯罪收益(追繳)法》中規定了民事、刑事并行的證明規則。它認為單純的刑事程序會導致證明規則的僵化,過分注重沒收程序刑事懲戒性將會忽略對人權的保障。可見,英國強調民刑并重的證明標準,將刑事的犯罪所得違法沒收程序與民事沒收程序相銜接,有利于節約司法資源,降低司法活動的成本,保障人權。
二、從比較法的角度論我國違法所得沒收程序證據規則的適用
(一)證明對象的角度——與《布萊克法律辭典》、《美國聯邦民事沒收程序改革法》比照
證明對象,是指本案所需要證實的事實,即當事人得以進行證明活動的基礎因素。不同的學者對證明對象有著不同的見解。主要的爭論點在于,證明對象是僅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證屬實,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逃匿或死亡,通緝一年后仍無法到案;還是涵蓋涉案的相關財物與犯罪行為之間的實質關聯。這在實踐中引發了一些問題,如:所涉財物的所有權歸屬和定性問題;貪污賄賂、恐怖活動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或死亡后涉案財產的追繳問題;罪證事實與違法所得之間實質聯系的證明問題。
依據《布萊克法律辭典》的規定,違法所得沒收程序屬于對物(違法所得)的訴訟,與對人訴訟不同的是,對物訴訟指法院一旦確定了對物的所有權的判決以及對該物宣稱所有權的當事人的判決,那么這項判決對之后再主張該物所有權的人也有效。與一般的刑事訴訟程序的不同點在于它主要用于財物的確定和查處。這一規定解決了所涉財物的所有權歸屬問題,而且將該程序定性為對物的訴訟,有利于節約司法資源,但是卻未解決違法所得的沒收對象問題以及罪證事實與違法所得二者存有實質關聯問題。
根據《美國聯邦民事沒收程序改革法》,民事沒收需要證明的事實是擬沒收涉案財物具有“可沒收性”,亦即檢察機關不僅需要證明存在犯罪行為,而且還要證明擬沒收涉案財物來源于犯罪行為,或為犯罪工具,或為便利犯罪實施的財物。[3]而我國的沒收對象的范圍包含了犯罪所得的孳息、違禁品、用于犯罪的本人財物等。這一規定明確了違法所得的沒收對象,而且規定違法所得需源于罪證事實,有利于證明罪證事實與違法所得二者存有實質性的聯系。
綜上,我國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證明對象問題可借鑒上述兩部法典的相關規定,進一步確定所涉財物的所有權歸屬和定性問題,準確的認定罪證事實與違法所得二者存有實質性的聯系。
(二)證明責任的角度—與《美國法典》、《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相比照
證明責任,分為兩個層次,即“客觀證明責任”和“主觀證明責任”。所謂客觀證明責任,系待證事實至審理最后時點仍然無法確定或未經證明時的法律效果問題,也是證明責任的重心與本質;所謂主觀證明責任,系當事人為避免敗訴起見,負有以自己之舉證活動證明系爭事實之責任。[4]爭論的焦點是證明責任如何合理配置的問題,即違法所得利害關系人是否需對自己的主張承擔舉證責任以及在何種情況需對自己的主張承擔多大程度的舉證責任。有學者認為利害關系人若對此項主張不服并提出了反對,則應“誰主張,誰舉證”,這引發了檢查機關和利害關系人的證明責任之爭。
《美國法典》的精神是“誰主張,誰舉證”。相應機關應當證實相關涉案財物是由犯罪行為的收益而組成的,同時需證明相關涉案財物是源于違法行為所得,這就賦予了相關的利害關系人強制證明的義務,只有在證實自己的善意所有人身份,財產是其正當所得的前提下,才可使自己的財產免于被沒收。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規定:“締約國可以考慮要求由罪犯證明這類所指稱的犯罪所得或者其他應當予以沒收的財產的合法來源。”②這有利于規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身舉證責任的推卸風險,同時也有利于對利害關系人的監督。
因此,域外經驗賦予了利害關系人證明主體的地位,若對此項主張不服并提出反對,則應“誰主張,誰舉證。”反觀我國法律,《刑法》對此也有所保留,比如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就設置了特別的舉證責任制度,規定犯罪人需盡到證明其巨額財合法的責任。所以順應刑法對貪賄犯罪的零容忍態度,舉證責任主體不僅包含檢查機關,還應包含利害關系人。若利害關系人對此項主張不服,則需承擔相應的責任。
(三)證明標準的角度——與英國《2002年犯罪收益追繳法》相比照
對于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證明標準問題,學理上爭議頗多。有學者認為作為刑訴的特別程序,本質上仍然屬于刑事訴訟,應嚴守刑事訴訟“證據確實、充分,排除合理懷疑”的普遍要求;另一部分學者則認為,從節約司法成本,提高訴訟效率的角度,該特別程序可以適用民事訴訟“優勢證據標準”。此外,還有學者認為應給“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予以明確的限定,因此,這引發了有關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證明標準之爭。
英國《2002年犯罪收益追繳法》采取了較為寬松的標準,單獨設置了刑事、民事兩類沒收制度。在刑事追訴中,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潛逃,則對其犯罪收益的追繳直接適用刑事沒收制度;若潛逃或死亡使得難以適用刑事沒收,則轉而適用民事沒收制度。兩套制度的證明標準均規定:法院秉承優勢證據標準的理念,進行了三個層次的分析:犯罪行為的判定;在此基礎上,被告是否通過普遍的犯罪行為獲益的判定;如不符合上述兩個條件,特殊的行為的犯罪收益的判定。英國沒收程序與民事訴訟證明標準是一致的。因此,無論是刑事、民事沒收制度,英國的兩套制度的證明標準相同的,即“優勢證據”。
因此,由于對象是貪賄、恐怖等嚴重案件,若采用優勢證據標準,可能會導致個人權益的侵犯;若采取嚴格的刑訴證明標準,可能會導致取證難度加大,訴訟成本增加。從其本質上來看,違法所得沒收程序屬于物的訴,不妨采取較為寬松的證明標準。檢察院沿用“證據確實、充分,排除合理懷疑”的普遍標準;利害關系人可以運用“優勢證明標準”。
三、借鑒與啟示
(一)證明對象:罪證事實與違法所得二者存有實質性的聯系
我國的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證明對象,應當進一步確定所涉財物的所有權歸屬和定性問題,準確的認定罪證事實與違法所得二者存有實質性的聯系。證明對象分為兩個層次,不僅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事實確鑿,并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經死亡或者逃匿,在通緝一年后仍不能到案;還需同時證明申請沒收的財物與該犯罪行為之間存在實質關聯。同時,檢察機關需證明行為人主觀上想將其用于犯罪行為,客觀上涉案財物源于當事人的正當所得;且違法所得來源于犯罪行為的直接或間接所得。
(二)證明責任:利害關系人的合理定位
首先,舉證責任主體是雙向的,不僅包含檢查機關,還應包含利害關系人。違法所得的性質決定了檢察機關是其主要主體,它被賦予了公訴以及追繳犯罪所得的權利,同時檢察機關舉證責任的承擔也是其義務的體現。這樣的設置有利于犯罪事實的認定,以及罪證事實與違法所得二者存有實質性的聯系的判斷。其次,利害關系人應當是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次要主體。主要指:在被告人近親屬、其他利害關系人提出認為其涉案財物是其合法所有的主張時,那么“誰主張,誰舉證”,即由被告人近親屬、其他利害關系人肩負相應的證明責任。綜上,我國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舉證責任主體可以設置為雙向的,在規定檢察機關舉證責任的同時,也同時規定相關利害關系人舉證主體的地位以及其證明責任如何分配的相關問題。
(三)證明標準:寬松的證明標準
針對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證明標準,我國宜采取寬松的證明標準。分為兩步:“證據確實、充分,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這用于檢察機關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行為的判斷以及涉案財產是否源于及涉案財產是否源于違法所得的裁斷;“優勢證據標準”,即針對相關利害關系人負相應證明責任的情形,也就是說,相關利害關系人對涉案財物提出歸屬與自身所有的主張時應當相應的承擔一定的舉證責任。
注 釋:
①《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款:“對于貪污賄賂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緝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規定應當追繳其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的,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沒收違法所得的申請。”
②《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第31條第8款:“締約國可以考慮要求由罪犯證明這類所指稱的犯罪所得或者其他應當予以沒收的財產的合法來源。”
[1]熊秋紅.從特別沒收程序的性質看制度完善[J].法學,2013,(9).
[2]陳衛東,徐美村譯.美國刑事法院訴訟程序[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126.
[3]浦雪章,韓東成.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證明問題研究[J].廣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4,(2).
[4]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總論編)[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