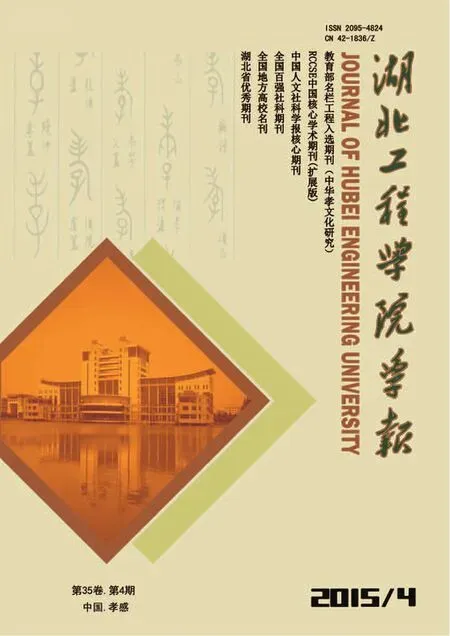炫技、交游與唱和
——清詞中興成因新探
祝 東
(蘭州大學(xué) 國際文化交流學(xué)院,甘肅 蘭州 730000)
炫技、交游與唱和
——清詞中興成因新探
祝 東
(蘭州大學(xué) 國際文化交流學(xué)院,甘肅 蘭州 730000)
關(guān)于清詞中興問題,學(xué)界前輩時賢多認(rèn)為其與明清易代的政局相關(guān),特別是與當(dāng)時勃興的文字獄關(guān)系密切。然而,考察清代文字獄研究史料可知其并未達(dá)到如此夸張殘酷的地步,不足以直接引發(fā)詞體文學(xué)之復(fù)興。清詞中興應(yīng)與文人間互相比拼才情、夸飾技藝的風(fēng)尚有關(guān)。中國古典詩歌發(fā)展至清代,傳統(tǒng)詩歌平仄格律已不能滿足文人士子的需要,而格律音韻相對復(fù)雜的詞則更能顯示文人們的才情。由此,清人對詞體文學(xué)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文學(xué)圈內(nèi)的交流酬唱則直接促成了清代詞體文學(xué)的復(fù)興。
清代詞學(xué);文人興趣;文學(xué)場;清詞中興
詞體文學(xué)發(fā)軔于唐季五代,興盛于兩宋,元明相對衰微,復(fù)振于有清,已成學(xué)界共識。昔日王觀堂論文學(xué)一代有一代之盛,那么一度衰微的詞體文學(xué)為何會復(fù)興于清代?學(xué)界前輩時賢多從社會歷史關(guān)系入手,認(rèn)為清詞中興是“文禍”促使下以詞寫心的避難策略。這種說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然完全以社會歷史決定論來探究文體興衰,而相對忽略了作為創(chuàng)作主體的作家群體,則未免有失偏頗。本文試從文人唱和與文學(xué)場之關(guān)系來探討清詞中興的具體成因。
一、“文禍”中興成因說與清代文禍實(shí)況
傳統(tǒng)清詞中興成因的觀點(diǎn),一般將其與明清易代的特殊政治背景聯(lián)系起來思考,在方法論上即是社會-歷史批評的方法,聯(lián)系明清之際的政治文化背景來考察,特別是文字獄事件對清人心態(tài)的影響。民國時期的王易是較早將文禁時局與清詞中興聯(lián)系起來進(jìn)行考察的學(xué)者,他認(rèn)為易代之后,文人之所以選擇以填詞的方式吟風(fēng)弄月,目的在于避禍,即避免文字獄的迫害[1]274,開清代詞學(xué)復(fù)興探究之風(fēng),此后學(xué)者們在探討清詞復(fù)興的原因時大抵都采納這一基本觀點(diǎn)。如嚴(yán)迪昌先生在《清詞史》中論及清詞中興成因時聯(lián)系清初文字獄對士人心靈的震撼和控制作用,指出:“從來被人們視為‘小道末技’的詞卻正好在清廷統(tǒng)治集團(tuán)尚未關(guān)注之際應(yīng)運(yùn)而起,雕紅琢翠,軟柔溫馨的習(xí)傳觀念恰恰成為一種掩體,詞在清被廣泛地充分地作為吟寫心聲的抒情詩之一體日趨繁榮了。”[2]孫克強(qiáng)先生在《清代詞學(xué)》中亦曾指出,清代文字獄重點(diǎn)關(guān)注打擊的對象是詩人,“而無一例為詞”[3],因?yàn)樽怨啪陀小霸娧灾荆~言情”的傳統(tǒng),故文人士子喜弄筆填詞,抒情釋懷,由是造成了清詞的中興之盛。這種觀點(diǎn)經(jīng)過學(xué)者們的不斷揄揚(yáng),逐漸成為通論,學(xué)界在論及清詞中興成因時大都會從此論點(diǎn)出發(fā),進(jìn)行延展。
既然學(xué)界皆將詞學(xué)中興與清初政治特別是文字獄聯(lián)系在一起,那么很有必要檢視一下清代文字獄的具體狀況。據(jù)胡奇光《中國文禍?zhǔn)贰芬粫y(tǒng)計(jì),清代順治朝18年文字獄至少有5起,康熙朝61年大約11起,雍正朝13年大約25起,而乾隆朝60年大約有135起,總而言之,順康兩朝文字獄實(shí)寬,而雍乾兩朝則趨嚴(yán)。[4]185-186但清代詞體文學(xué)在順康兩朝就已經(jīng)形成中興之勢了,而雍乾兩朝詞體文學(xué)實(shí)際上是相對衰落,因此雍乾兩朝文禍不能作為詞體文學(xué)復(fù)興端緒之因由。再來看順康兩朝的文字獄情況,其打壓的主要對象是在意識形態(tài)上公開唱反調(diào)或者在政治態(tài)度上公開不合作的士人,如黃毓祺案、莊廷龍《明史》案皆是如此。此外還有部分文禍實(shí)是政治斗爭的副產(chǎn)品,文人文字罹禍乃牽連所致。如僧函可的《變紀(jì)》書稿案即為巴山與洪承疇之間政治斗爭的產(chǎn)物,張縉彥詩序案則是清初漢族官僚集團(tuán)之間黨派斗爭釀成的悲劇。真正因詩文罹禍的文字獄案件并不多,“康熙朝僅有何之杰、陳鵬年兩人因詩得禍,也均從寬發(fā)落”。[4]140可見單純寫詩作文并不一定就會遭受文字橫禍,清初統(tǒng)治者也絕非昏庸糊涂之輩,況無故亂起文字獄遭致漢族知識分子的反感,于滿族王權(quán)統(tǒng)治也無益。胡奇光先生指出:“順康雍三朝文字獄打擊的主要對象是官紳、名士,即‘欽定’的政治上反對勢力及思想上有反滿傾向的士大夫。”[4]87這個結(jié)論發(fā)人深省。清代有文字獄是實(shí),但打擊的主要對象是不服從滿清統(tǒng)治的文人士大夫,特別是江南士子,因?yàn)椤斑@些地方是人文淵藪,輿論的發(fā)縱指示所在,反滿精神到處橫溢”。[5]遭受文禍者多是因?yàn)檎紊瞎_反滿,而對于政治上已經(jīng)迎合清朝,即便此前有過反清復(fù)明舉動者,也是既往不咎,如陳維崧、朱彝尊諸人,在易代之際或明或暗從事過反清活動,但后來皆入博學(xué)鴻詞科,可謂政治上“投誠”了,他們詩文中的故國之思、亡國之痛雖多處可見,卻并未因此遭受打壓,因此文人士子寫詩作文動輒罹禍的觀點(diǎn)有待商榷,“文禍”并非詞體文學(xué)復(fù)興的直接原因。
同樣,認(rèn)為詞體文學(xué)是小道末技,并未引起清初統(tǒng)治者的注意也不太恰切。康熙朝詞體文學(xué)兩次破天荒地立了“國家級重點(diǎn)課題”,即《歷代詩馀》和《欽定詞譜》,此二書從立項(xiàng)到完成,皆受到康熙帝的關(guān)注與重視,并且親自御制序文進(jìn)行闡發(fā):
朕萬機(jī)清暇,博綜典籍,于經(jīng)史諸書有關(guān)政教而裨益身心者,良已纂輯無遺。……宋金元明四代詩選,更以詞者繼響夫詩者也。乃命詞臣輯其風(fēng)華典麗,悉歸于正者,為若干卷,而朕親裁定焉。……茍讀其詞,而引申之,觸類之,范其軼志,砥厥貞心,則是編之含英咀華,敲金戛玉者,何在不可以“思無邪”之一言該之也![6]
從序言中可以看出玄燁早已將詞與詩比肩,納入詩教傳統(tǒng)中了。此亦足以證明滿清統(tǒng)治者并沒有忽視詞體文學(xué),詞體文學(xué)亦在清代文網(wǎng)之內(nèi),如雷夢辰《清代各省禁書匯考》中就有清初詞學(xué)選本《瑤華集》(這部詞選因以詞存史,多及易代時事,內(nèi)容上有違礙,故遭禁行) 。[7]因此詞并非如前輩學(xué)者所言,因是小道末技不被重視。只要在政治意識形態(tài)上犯禁,不管詩詞,俱會遭禁受罰。
因此,總體而言,清初文禍并非胡亂打壓漢族士子,而有其針對性,清初文禍也不單是詩文罹禍,而與政治斗爭、朋黨傾軋關(guān)系密切,文人往往充當(dāng)了政治斗爭的犧牲品。既然文禍高壓并不是清詞復(fù)興的端緒,清詞緣何復(fù)興?筆者認(rèn)為可以從清代文人生態(tài)環(huán)境進(jìn)行考察,特別是文人興趣嗜好的轉(zhuǎn)移入手進(jìn)行觀照。
二、夸飾才情與詞體復(fù)蘇
在以往文學(xué)研究中,人們過于重視社會歷史對人的影響,忽視了創(chuàng)作主體的個性特征。在同一社會條件下,作家選擇這一文體而非另一文體,不僅與歷史現(xiàn)實(shí)相關(guān),而且與作家的才情、興趣、愛好及師友交游酬唱等文人生態(tài)環(huán)境有關(guān)。
清代文化經(jīng)數(shù)朝之積累,已成造極之勢,文人士子多飽學(xué),杜甫所云“讀書破萬卷”的事情于清人來說已經(jīng)很平常了。為了超越前人,甚至出現(xiàn)了“竹垞以經(jīng)解為韻語,趙甌北以史論為韻語,翁覃溪以考據(jù)金石為韻語。雖各逞所長,要以古人無體不備,不得不另辟町畦耳”[8]的文壇景觀。文人在一起交游唱和時喜歡夸飾才情文筆。如王晫《今世說·賞鑒》中記載浙江的鑒湖社,參與者把詩文糊名謄抄,然后進(jìn)行評比,“一聯(lián)被賞,門士臚傳,其人拊掌大喜,如加十賚”[9]58。此足見文人之間爭奇斗艷的風(fēng)尚。況且清代詞人亦多兼為學(xué)人,故能摒棄明詞空疏淫艷之習(xí),學(xué)人弄筆填詞者亦蓋過兩宋。這個現(xiàn)象晚清詞學(xué)家譚獻(xiàn)、今人錢仲聯(lián)亦多有關(guān)注:“清詞人之主盟壇坫或以詞雄者,多為學(xué)人……蓋清賢懲明人空疏不學(xué)之敝,昌明實(shí)學(xué),邁越唐宋。詩學(xué)家稱學(xué)人之詩與詩人之詩合,詞學(xué)家亦學(xué)人之詞與詞人之詞合。而天水詞林則不爾,周、程、張、陸不為詞,朱熹僅存十三首,葉適一首而已。以視清詞苑之學(xué)人云集者,庸非曹鄶之望大國楚乎?”[10]清代詞人的雙重身份及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積淀,傳統(tǒng)詩歌格律對他們來說已不足以顯示才情學(xué)問,于是需要有新的文體來夸耀才情炫示學(xué)問,“詞有定格,字有定數(shù),韻有定聲”,其繁瑣的規(guī)則難以把握,相對于格律詩來說,詞體文學(xué)是一種形式更為考究、限制更為嚴(yán)格的文學(xué)樣式,如謝元淮言:“詞之為體,上不可入詩,下不可入曲。要於詩與曲之間,自成一境。守定詞場疆界,方稱本色當(dāng)行。至其宮調(diào)、格律、平仄、陰陽,尤當(dāng)逐一講求,以期完美。”[11]其規(guī)矩講究比詩歌和曲子嚴(yán)格得多,于是自然成為一種能夠夸耀才情的文體,由此在明人不遺余力的詩歌復(fù)古革新運(yùn)動失敗之后,清人重新“發(fā)現(xiàn)”了詞體文學(xué)。此可在李漁的《耐歌詞自序》中得到印證:
三十年以前,讀書力學(xué)之士,皆殫心制舉業(yè),作詩賦古文詞者,每州郡不過一二家,多則數(shù)人而止已;余盡埋頭八股,為干祿計(jì)。是當(dāng)日之世界,帖括時文之世界也。此后則詩教大行,家誦三唐,人工四始,凡士有不能詩者,輒為通才所鄙。是帖括時文之世界,變而為詩賦古文之世界矣。然究竟登高作賦者少,即按譜填詞者亦未數(shù)見,大率皆詩人耳。乃今十年以來,因詩人太繁,不覺其貴,好勝之家,又不重詩而重詩之馀矣。一唱百和,未幾成風(fēng)。無論一切詩人皆變詞客,即閨人稚子,估客村農(nóng),凡能讀數(shù)卷書、識里巷歌謠之體者,盡解作長短句。[12]
序文寫作時間為康熙戊午中秋前十日,即康熙十七年(1678),往前推三十年則是明末清初之際,明代文人以攻舉子業(yè)為尚,易代之后,政局混亂,故明舉業(yè)告退,士子轉(zhuǎn)而為詩,但詩太簡單,不足以展示才情,作詩“為通才所鄙”,文人為了爭奇斗勝,轉(zhuǎn)而填詞,詞填得好,亦可給作者帶來巨大的聲望。如王士禛《蝶戀花·和漱玉詞》中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的句子,“長安以此遂有‘王桐花’之目”[9]49,影響之大可以想見。由是改變了文壇風(fēng)尚,詩人皆變詞客,而文壇風(fēng)向一旦改變,則會引起文人們的群起效仿,此或可謂之“蝴蝶效應(yīng)”。如顧貞觀《與陳栩園書》中所言:“而余因竊嘆天下無一事不與時為盛衰,試即以詞言之,自國初輦轂諸公,尊前酒邊,借長短句以吐其胸中。始而微有寄托,久則務(wù)為諧暢。香巖、倦圃,領(lǐng)袖一時。唯時戴笠故交,提簦才子。并與燕游之席,各傳酬和之篇。而吳越操觚家聞風(fēng)竟起,選者作者,妍媸雜陳。”[13]975由于有才學(xué)之士以詞寫心,改變了以詩言志的套路,使得一直萎靡不振的詞壇得到了一個發(fā)展的契機(jī),于是習(xí)詞填詞者漸多,最后到了“吳越操觚家聞風(fēng)竟起”的地步,填詞蔚為風(fēng)氣。有文人甚至受到當(dāng)時詞壇風(fēng)氣影響由攻詩轉(zhuǎn)為專力為詞,據(jù)蔣景祁《陳檢討詞鈔序》記載:
其年先生幼工詩歌,目濟(jì)南王阮亭先生官揚(yáng)州,倡倚聲之學(xué),其上有吳梅村、龔芝麓、曹秋岳諸先生主持之,先生內(nèi)聯(lián)同郡鄒程村、董文友,始朝夕為填詞。……迨倦游廣陵歸,遂棄詩弗作。[14]卷二
陳維崧為清代詞壇大家,填詞兩千余首[15]98,當(dāng)之無愧的詞壇第一作手,但他起初是主攻詩歌的,少時還師事陳子龍、昝質(zhì)名流學(xué)詩,至順治七年(1650)才始學(xué)填詞,據(jù)其《任植齋詞序》中所云:“憶在庚寅、辛卯間,與常州鄒、董游也,文酒之暇,河傾月落,杯闌燭暗,兩君則起而為小詞。方是時,天下填詞家尚少,而兩君獨(dú)矻矻為之,放筆不休,狼籍旗亭北里間。其在吾邑中相與為倡和者,則植齋及余耳。”[15]53后來游歷廣陵,結(jié)識王士禛等人之后,受其影響才專力填詞。正是由于當(dāng)時文壇風(fēng)尚的轉(zhuǎn)變及與師友酬唱交流的影響,才成就了陳維崧這位詞壇巨擘,這里就涉及到另外一個文人生態(tài)問題,即是文人之間交流唱和對詞體復(fù)興的影響。
三、交游酬唱和與躋身“圈內(nèi)”
明清易代,面對神州陸沉,有皈依新朝者,有反清復(fù)明者,有持觀望態(tài)度者,有甘作遺民隱士者,不一而足。易代致使諸多士子或失業(yè),或失去生活來源。賦閑的困頓使文人士子不得不游走于仕宦之間,旅食他鄉(xiāng),游幕成為當(dāng)時文人生活的一道風(fēng)景線。如尚小明言:“眾多才華橫溢卻屢躓場屋、難入仕途的貧寒士人,為求得一謀生之路和讀書治學(xué)的環(huán)境,亦紛紛投至各級官員幕下。士人游幕成為當(dāng)時普遍的社會現(xiàn)象……對清代學(xué)術(shù)文化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16]為維持生計(jì),很多文人不得不放下身段,游身乞食,或依傍名流大佬,靠他們的接濟(jì)維生,如清初詞壇大家朱彝尊就一度靠游幕維持生計(jì),陳維崧依靠冒襄度日竟長達(dá)8年之久,京華落魄文人被龔鼎孳接濟(jì)的更是不可勝數(shù)。
由于文人交游頻繁,逐漸形成文人圈子,文人要想進(jìn)入圈子,需要一定的條件,借用法國社會學(xué)家布迪厄的觀點(diǎn)來說,圈子即場域,進(jìn)場必須攜帶一定的資本作為“入場券”才行,由此我們引進(jìn)了布迪厄所云的“場(field)”的觀念:“從場的角度思考就是從關(guān)系的角度思考。”[17]一般來說,一個文學(xué)圈子里的主盟人物擁有雄厚的社會資本,能給文人雅集提供足夠的空間和物質(zhì),而要進(jìn)入這個場域的文人,必須攜帶相應(yīng)的文化資本。并且,“場域中的權(quán)力、資本的分配結(jié)構(gòu),決定著位置與位置之間的關(guān)系,如支配關(guān)系、屈從關(guān)系或結(jié)構(gòu)上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18]文人要進(jìn)入圈子,依附于擁有社會資本和經(jīng)濟(jì)資本的人,來謀求生活資源,在場域內(nèi)處于被支配的地位,為了保持其在場域內(nèi)的位置,他們必須積極貢獻(xiàn)自己的文化資本,比如場域中處支配地位的人物有詞作的話,那么被支配者必須竭力唱和,以保證其在場內(nèi)應(yīng)有的地位,否則可能會“出圈”。故而我們會在清初詞壇上看到諸多大型唱和的文學(xué)景觀。如康熙元年(1662)王士禛主持的虹橋唱和,就曾經(jīng)是清初詞壇上的一次盛舉。據(jù)王士禛《紅橋游記》所言:“壬寅季夏之望,與籜庵、茶村、伯璣諸子,偶然漾舟,酒闌興極,援筆成小詞二章,諸子倚而和之。籜庵繼成一章,予亦屬和。”[19]另據(jù)李斗《揚(yáng)州畫舫錄》記載,當(dāng)時參與唱和的文人有杜濬、陳允衡、丘象隨、陳維崧等十人,時王氏為揚(yáng)州推官,雅好詩文,“總持風(fēng)雅”,“晝了公事,夜接詞人”,他自己率先作了三闋《浣溪沙》為“虹橋唱和集”[20],王士禛在揚(yáng)州任上,主盟文壇,對詞壇產(chǎn)生了極為深遠(yuǎn)的影響。而納蘭容若在京師主持的詞壇,亦吸引了眾多旅食者,“吾友容若,其門地才華,直越晏小山而上之,欲盡招海內(nèi)詞人,畢出其奇,遠(yuǎn)方骎骎漸有應(yīng)者”[13]975,容若以其貴戚身份,雄厚財力,足以能夠承擔(dān)窮途文人們所需的生活補(bǔ)助,故而流寓京師的文人多趨之,“海內(nèi)名為詞者皆歸之”[21]如嚴(yán)繩孫、顧貞觀、陳維崧等多曾從其游,主客唱和,彬彬稱盛。
此外,康熙四年(1665)曹爾堪、王士祿、宋琬等人的江村唱和,康熙五年(1666)曹爾堪、王士祿主持的廣陵唱和,康熙十年(1671)曹爾堪、龔翔年等人在京師的秋水軒唱和,皆是一唱百應(yīng),蔚為風(fēng)氣,參與唱和的成員大抵皆是能夠躋身“圈內(nèi)”的人物。康熙十二年(1673)陳維崧在家鄉(xiāng)宜興與蔣景祁、徐喈鳳等16人修禊東溪,參與者皆有詞作唱和。而釋大汕在康熙十七年(1678)為作《其年填詞圖》后為陳維崧攜至京師,在京名士梁清標(biāo)、王士禛、彭孫遹、朱彝尊、毛奇齡等三十余人多有題詠,蔚為風(fēng)氣,堪稱壯觀,據(jù)馬祖熙先生《陳維崧年譜》所考:“《迦陵填詞圖》經(jīng)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四朝,歷一百五十年,續(xù)有題詠”[22],足見這種唱和不僅在當(dāng)時而且在后世亦引起廣泛關(guān)注與參與,可謂流風(fēng)余韻,不絕于縷。陳維崧不僅為此獲得了巨大的榮譽(yù),而且此等盛況也應(yīng)極大刺激了他的創(chuàng)作欲望,這件雅事在詞壇引起的震動與追慕亦不容小覷。而莊澹庵評康熙十九年(1680)所刻王晫《峽流詞》中《滿江紅》詞時云:“此調(diào)和者如云,幾累千百。”[23]卷下這首詞是追和江村唱和《滿江紅》而作,江村唱和在士人圈子中的影響自不必云。
可以這么說,清詞的中興,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人之間的交游唱和引起的群體效應(yīng)。而唱和又容易刺激文人之間爭奇斗勝的創(chuàng)作欲望,促進(jìn)詞體文學(xué)的繁榮。清初浙西陽羨詞體巨擘朱彝尊、陳維崧莫不如此。這樣他們在交游或游幕中,既多了閑暇的時間從事創(chuàng)作切磋,又逐漸形成了一定的文人圈子,如以王士禛為中心的廣陵詞人群體,以曹爾堪為中心的柳州詞人群體,以納蘭性德為中心的京華詞人群體等。文人在一起可以喝酒寫詩作文,是為詩酒風(fēng)流,同時可以夸耀才情。文人進(jìn)入“詞學(xué)場”內(nèi),不僅可以獲得一定的物質(zhì)資源,還可以進(jìn)一步擴(kuò)大自己的名聲與影響,名利雙收,而由此帶來的文學(xué)景觀則是詞體文學(xué)的復(fù)蘇。
四、小結(jié)
清詞中興固然與明清易代下的文字獄有一定的關(guān)系,但清初文字獄并非我們想象中的那么荒唐,它的打擊對象是有針對性的,對詞學(xué)復(fù)興并未起到關(guān)鍵性作用。清代詞體文學(xué)的興盛與清人的興趣愛好及生活境況有關(guān)。文人之間的交游唱和及夸耀才情的需要,使得他們不自覺選擇了在格律音韻上更難把握的詞體文學(xué),因?yàn)榇藭r詞體文學(xué)已經(jīng)發(fā)展成為一種長短不葺的新體格律詩。但這種文體的文類等級地位不高,故而清代詞壇一直在不遺余力地推揚(yáng)詞體。清代詞學(xué)中不斷出現(xiàn)的辨體與尊體工作,與文人的興趣轉(zhuǎn)移相關(guān),正如江曉原所言:“文人們從來不缺乏為自己的興趣尋找正大理由的動力,能找到的理由還總能與時俱進(jìn)。”[24]
一種文體的興衰,并不是個別作家能夠左右的,它必定會受到群體力量的影響,文人之間的交游酬唱,以及夸飾才情、謀食糊口等,都會對文體的興衰產(chǎn)生具體的影響。研究文學(xué)史,不能從抽象的理論出發(fā),而應(yīng)該把文學(xué)現(xiàn)象還原到歷史的過程之中,以生活在歷史之中的作家活生生的物質(zhì)、精神需求等來作為考察依據(jù),由此來研討一定的文學(xué)現(xiàn)象,豐富我們對文學(xué)史的認(rèn)識。這種研究方法于詩文詞曲皆如是。
[1] 王易.詞曲史[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274.
[2] 嚴(yán)迪昌.清詞史[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9.
[3] 孫克強(qiáng).清代詞學(xué)[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04:9.
[4] 胡奇光.中國文禍?zhǔn)穂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xué)術(shù)史[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16.
[6] 康熙.歷代詩馀序[M]//沈辰垣,等.歷代詩馀.上海:上海書店,1985:3-4.
[7] 雷夢辰.清代各省禁書匯考[M].北京:書目文獻(xiàn)出版社,1989:59,74.
[8] 吳仰賢.小匏庵詩話·卷一[M].光緒八年刊本.出版者不詳,光緒八年(1882).
[9] 王晫.今世說[M].上海:古典文學(xué)出版社,1957.
[10] 錢仲聯(lián).全清詞序[M]//程千帆.全清詞:順康卷.北京:中華書局,2002:2.
[11] 謝元淮.填詞淺說[M]//唐圭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2509.
[12] 李漁.李漁全集·冊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377.
[13] 顧貞觀.與陳栩園書[M]//繆荃孫.國朝常州詞錄.南京: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1.
[14] 陳乃乾.清名家詞[M].上海:上海書店,1982.
[15] 陳維崧.陳維崧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6] 尚小明.學(xué)人游幕與清代學(xué)術(shù)[M].北京:社會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1999:11.
[17] 包亞明.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shù)——布爾迪厄訪談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41.
[18] 張意.文化與權(quán)力符號:布爾迪厄的文化社會學(xué)導(dǎo)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05:273.
[19] 王士禛.漁洋山人自撰年譜[M]//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82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207.
[20] 李斗.揚(yáng)州畫舫錄[M].北京:中華書局,1960:220-221.
[21] 龍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詞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76.
[22] 馬祖熙.陳維崧年譜[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14.
[23] 王晫.峽流詞[M].刻本.霞舉堂,康熙十九年(1680)
[24] 江曉原.從《詩》三百到《夾竹桃》:艷情詩之中國篇[J].萬象,2008(1).
(責(zé)任編輯:李天喜)
Showing off, Making Friends and Chiming in with Others:A New Study on the Revival of Ci Poetry in the Qing Dynasty
Zhu Dong
(SchoolofInternationalCulturalExchange,LanzhouUniversity,Lanzhou,Gansu730000,China)
About the issue of the revival of Ci poetry in Qing dynasty,most academia seniors thought it associated with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from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especiall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writing prison. However, by examining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writing prison in the Qing dynasty, it was found to be not so exaggerating or cruel. Hence it might not directly lead to the revival of Ci poetry in the Qing dynasty. Instead, the revival of Ci poetry in the Qing dynasty might be brought on by the fashion of literati competition with each other and exaggerating accomplishment. When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developed up to the Qing dynasty, pingze and rhythm couldn’ 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literati, but Ci poetry's metrical phonology was relatively complex and could more commendably display the literati’ s artistic talents. Hence the literati in the Qing dynasty developed a strong interest in Ci poetry. And The communication and singing in literary circle directly facilitated the revival Ci poetry in the Qing dynasty.
Ci study in the Qing Dynasty;literati interest; literature field; the revival of Ci poetry in Qing Dynasty
2015-05-23
祝 東(1982- ),男,湖北孝感人,蘭州大學(xué)國際文化交流學(xué)院副教授,文學(xué)博士。
I207.23
A
2095-4824(2015)04-005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