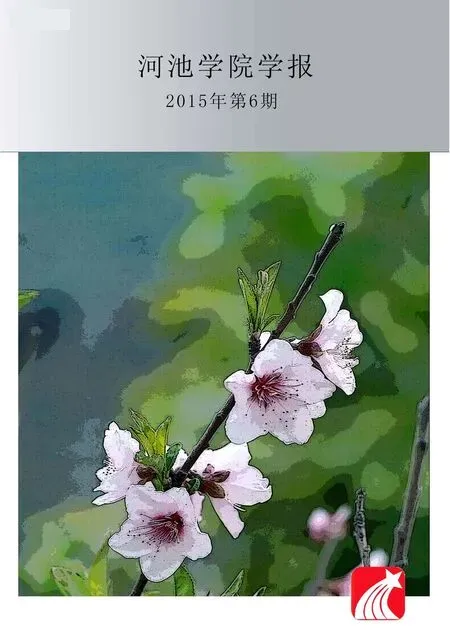毛南儺戲的戲劇藝術探微
譚為宜
(河池學院 文學與傳媒學院,廣西 宜州 546300)
在中國唯一的毛南族自治縣——廣西河池市環江毛南族自治縣至今還流行著一種民俗活動——“肥套”。“肥套”是毛南語“還愿”的意思,“肥套”盛行于明清時期,主要活動地域是在環江縣下南鄉一帶。該項活動被列為2006年5月20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代號為:465Ⅸ-17)。
毛南族肥套活動包含了儺歌、儺舞、儺樂、儺故事、儺戲等形式,其中以儺戲為主要形式,毛南儺戲神秘、古樸、貼近生活,深受當地百姓喜愛。盡管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斥之為“封建迷信活動”,幾乎遭到毀滅性的打擊,但“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新時期這一民間藝術的奇葩又在毛南山鄉綻放,每年演出十數場至數十場之多。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后,吸引了中外專家學者研究的興趣,考察、欣賞、獵奇者紛至沓來。一項民間藝術活動為何有如此頑強的生命力,在當下傳統的民族民間藝術普遍不景氣的大趨勢下,儺戲這一較為古老的民族戲劇頗顯得“一枝獨秀”,這確實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通過對實地演出的考察和對音像資料的分析研究,毛南儺戲之所以受到老百姓的歡迎,表現了頑強的生命力,從戲劇藝術的角度考量與其具備的特征密切相關。
一、戲劇的程式化與幕表戲特征
毛南儺戲是一種綜合了宗教還愿祈福儀式與戲劇表演藝術的文化現象,至今仍保留其原生態的演出形式和藝術內容,包括口口相傳的故事、手抄唱本、山歌唱腔、木制面具、打擊樂器、有特色的服裝道具、張揚的程式化舞蹈動作等,實際上是一種程式化和幕表戲的表現。
(一)演出的程式化特征
毛南儺戲的程式化外延是大于傳統皮黃戲曲的程式的。皮黃戲曲的程式由戲劇美學與接受美學共同塑造,是一種約定俗成的表演與接受程式,即“執鞭如乘馬,推敲似有門,疊椅為山,方布作車,四個兵可代一支人馬,一回旋算數千里路……”[1]144;而毛南儺戲的程式除此之外,還是一種儀式化的程式,由于儺戲源自于祈神的活動,對于還愿主家來說,可謂關乎一家老小平安,子孫后代繁榮的大事,因此十分莊重、神圣,逐漸就形成了嚴格的固定程式。我們在演出現場考察中發現,盡管不同的師公隊伍的表演會有形式和內容上的差異,但那些差異基本上不是本質的顛覆或程序的迥異,換句話說,他們的程式是大致上一致的,尤其是迎神、敬神、送神的關鍵性情節幾乎沒有差異,產生差異的多是在演出細節上,例如樂器的節奏、唱詞的選擇以及演員的風格與一些即興發揮(尤其是在與主家對話或與周圍的觀眾對話時會因人而異)。
儺戲的程式化還表現在,“肥套”(還愿)主家在確定進行這項活動的時候,會根據需要來選擇還大愿還是還小愿的程式,選擇的緣由主要是根據家庭的財力、生活現狀、還愿的目的和需要,大愿的程式包括了肥套的幾大愿:婆王(萬歲娘娘)愿——庇佑子孫繁衍,雷王愿——求財路興旺,三界公愿——祈求家庭成員平安,神農愿——風調雨順,靈娘愿——生意、求學事事順遂等。也有還小愿的,即選擇其中某種或幾種愿,如有孩子上學或有人在做生意的,由于家庭財力有限(操辦一般的小愿需1萬元左右),就只還靈娘愿了;如果是有子有女的就還婆王愿,但據師公介紹,婆王愿必須和雷王愿同時辦,不可拆開。
儺戲程式化的第三種表現就是演出根據儀式的程序進行,絕不會因為觀眾(主家)的喜好隨意改變。由于是固定的儀式程序,毛南族觀眾一般都熟悉演出的順序,演出的戲目,以及戲目的大致情節。
角色的化妝也是固定的,最主要的化妝是戴上木制的儺面,毛南儺戲有36具儺面,也就是有36個固定的角色;其次是與角色相對應的戲服,或短裝、或長袍,或純色、或雜色,戲服的裝式和花飾都帶有毛南族服裝特色,個性鮮明;再就是手持固定的法器,有寶刀、簡笏、笏筶、手鈴、朝鏢等,根據劇情翩翩起舞。
(二)演出過程的幕表戲特征
幕表戲是與劇本戲相對而言的,幕表戲是“劇團在排演和正式演出時,只有一個大致的分幕分場表,相當于劇情的梗概,完全由演員自由發揮,去填補細節空間,臨時編出臺詞,隨意性很大”[2]25。毛南儺戲曾有過戲劇劇本,據河池市戲劇家協會主席任君先生回憶:“1959年夏,商靄如(執筆)、韋志彪、韋志華、戴崇和以毛南族民間故事《三娘與土地》為基礎,重新梳理、構思、創編了新的同名劇本。……豈料風云突變,‘文革’狂掃,藝術橫遭厄運,《三娘與土地》也就化為烏有,稿子從此絕世。時至今日,毛南戲尚無一個劇本刊印問世,怎不令人唏噓感嘆”[3]172-173。在毛南儺戲中,沒有劇本,更談不上分鏡頭,有的只是手抄本的經書類唱詞。在《三娘與土地》一劇中,是土地、小土地、三娘的三神舞。三娘與土地是毛南民間傳說的一對情人,而土司蒙官卻垂涎于三娘的美貌,多次派出差兵欲強搶豪奪,三娘與土地不屈服于土司的淫威,在鄉親們的幫助下巧與周旋,但最終還是難逃魔掌,雙雙殉情,幻化為巴音山頂的一對鳳凰,成為毛南族的“梁祝”,毛南人為了紀念他們而奉為愛神加以祭奉。當下排演該劇沒有劇本可依,演員大致按這一故事情節現場演出,有固定的音樂節奏(主要是祥鼓、嗩吶、鑼、鈸和手鈴等合奏),有配合這一節奏的較為固定的舞步,有固定的服裝面具。毛南儺戲基本上處于“搭橋戲”階段,因此結構相對松散,《瑤王拾花》《仙官架橋》《花林仙官送花》等戲目劇情都較為簡單,排練主要是師傅教徒弟,有專門的傳授過程,徒弟一是由師傅手把手地教,二是在現場現學,然后自己訓練。肥套活動開始后,有的師公會列出簡略的演出提綱,而主要情節已熟記在演員的腦子里,按程式進行,相互提醒,演出過程當然會因演員個人的素養和演出環境而異。毛南儺戲的幕表戲特征是較為明顯的。
程式化與幕表戲是一把雙刃劍,它利于演員掌握、表演,也符合老百姓的欣賞習慣;但同時它又限制了戲劇藝術的發展和創新,話劇引入中國之初也經歷過一段幕表戲階段,由于劇團演出的主觀隨意性、不可知性嚴重影響了演出質量的提高和藝術的創新,很快就淘汰了。毛南儺戲在文化多元化變革的時代,也應該與時俱進,從生存和發展的角度,思考這一定式的突破,關注劇本的整理與創作,藝術化地提高演出質量,擴大演出影響,應該是極為迫切而又十分有益的。
二、神秘元素的陌生化效應
毛南儺戲吸引觀眾的原因之一,就是這種源于宗教儀式的戲劇演出所產生的陌生化效應。亞里斯多德被認為是最早闡釋“陌生化”的哲人(盡管他沒有使用“陌生化”一詞),他認為“一切‘發現’中最好的是從情節本身產生的、通過合乎或然律的事件而引起觀眾驚奇的‘發現’。”[4]60他認為:藝術并不是像歷史學家那樣“敘述已經發生的事情”,而是“敘述可能發生的事情”。藝術家往往給平常的事物賦予一種不平常的氣氛,而人們喜歡被不平常的東西所打動。而且這種不平常是被人們所認同的。毛南儺戲的陌生化效應也是十分明顯的,具體表現為:
(一)演出氣氛的陌生化效應
縱觀毛南儺戲表演,雖然它具有中國戲曲的程式化特征,比如以特有的上下起伏的舞步來表示仙人的飄飄降臨,用軟拜步、甩袖和輾轉繞圈等表演超度、架橋、送花、坐殿等,以及儺戲面具的善惡象征(類似戲曲的臉譜),和“花”的生殖象征意義貫穿始終,但是這種程式化并不能掩蓋儺戲表演現場迥異于日常生活的靜態和動態的場景所產生的陌生化效應,在演出現場,神龕設置的隆重與繁雜,神像懸掛的莊嚴與威儀,儺樂的激越與鏗鏘,師公的專注與莊重,共同營造了一種肅穆、神圣的“不平常”的氣氛,這種氣氛拓展了觀眾對于“可能發生的事情”的期待空間。
(二)宗教神秘色彩的陌生化效應
我們在演出現場考察發現,“肥套”活動一般選擇下午進場,其中“師公”7人,廚師2人(按程序要求負責整個活動過程中的貢品祭祀和主客的伙食),花公花婆各1人或各若干人(根據主家的家族參與戶數而定)。在“肥套”活動過程中紙花是重要的道具,要剪貼大量的紙花,“花”象征生殖,紙花造型是壯實的男性和生殖器官發達的女性。活動從“起壇”(迎神)開始,師公設壇焚香禱告,伴著特有的打擊樂聲,宗教色彩十分濃厚;隨之“起樓”,活動主家的堂屋很快就裝飾起一個神龕。肥套活動的眾神是一個比較復雜的組合,體現了毛南民族文化的包容性,既有漢民族的崇拜神如“三光”“雷神”“魯班”“土地”“社王”等,亦有毛南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供奉神如“三元”“萬歲娘娘”“六官”(壯族莫一大王的六弟)“瑤王”“三娘”及“花林仙官”等。這些神靈以道教神為主,兼有佛教神,也有來自神話和民間傳說的形象,有的則是歷史人物,當這些形象走上神壇,成為信仰、敬畏和崇拜的對象,就會與民眾的實際生活產生疏離、陌生,成為一種主觀的、或然的存在,也就具有了神秘感,它是儺戲之所以會長期激起民眾的欣賞趣味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幕表戲”特征帶來的陌生化效應
據我們了解,在環江縣有近50名從事肥套活動的“師公”,他們大都能獨當一面,可以表演儺戲中的任一角色,例如我們去考察的幾個班子,他們每位師公都曾經作為“牽頭者”操辦過肥套活動。而每位師公對肥套活動的細節的理解是有一定差異的,演出風格也不盡相同,這使他們的每一次演出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敘述可能發生的事情”,這又增加了演出的“或然律”,也就同時增加了儺戲的趣味性和藝術魅力。
切入點選擇正確,并能形成邏輯流程控制,從而證明作為故障流程排查切入點的準確性,避免在業務故障處理時入手的隨意性,從而延誤處理或錯判故障點而造成事故。
(四)儺戲技巧性表演所產生的陌生化效應
公認毛南儺戲最精彩的一出是《花林仙官送銀花》,這也是整個“肥套”活動的高潮,要給主家的祖母送“長生雞”,因為祖母是這個家庭子孫繁衍的功臣,這時“林娘”作法,將一只雄壯的公雞定在男主人的背上,這只雞居然會一直停留在上面,男主人弓著身子從堂屋登樓,樂聲不斷,背上的公雞也不會驚慌,師公尾隨一同走向祖母屋中,祈請老人健康長壽,儀式便告成功。往往“肥套”師公也將這一情節作為儺戲的重頭戲,十分認真、謹慎,當地毛南人或熟悉這一情節的觀眾在觀看儺戲時特別期待觀賞“定雞”這一絕技。這些神秘元素的介入,增加了毛南儺戲的藝術成分,使得一種祈神儀式被注入了藝術審美的內涵。這也是毛南儺戲會引起群眾圍觀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與現實緊密結合的戲劇內容
據《中國毛南族》一書所載,“古時,起愿和還愿是毛南人一生中最主要也是最普遍的敬神活動,毛南族先民認為,人生所發生的一切都與神靈有關,作為陽間的人,必須對神靈有所表示,方能避兇趨吉。”[5]204如魯迅先生所言:“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茍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6]35先生把人生要務歸納為“生存”“溫飽”和“發展”,不僅在過去,即使是今天又何嘗不是這樣?
(一)緊密結合著“生存”“溫飽”和“發展”的社會現實
眾所周知,生存的前提是生育繁殖,而生育繁殖的人口生產在醫藥科技落后的很長一段歷史時期,是人們十分渴求而又懼怕、擔憂的一個生活環節,產婦分娩可謂“九死一生”,因此“肥套”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生育的還愿祈福,由家庭的繁衍到民族的生生不息,這就是肥套活動藝術形式將生育擺在第一位的主要原因,它承載著家人、族人和民族的希望,其中“仙官架橋”“瑤王拾花”“三娘配土地”“花林仙官送銀花”“萬歲娘娘送金花”等都與婚戀生育有關。我們甚至可以說,“肥套”的儺戲表演主要是毛南人的一種生育繁衍文化的隆重儀式。
(二)“感恩”的精神寄托
如果說早期的“肥套”活動還是基于古代人們對大自然的敬畏、依賴和不理解,那么,隨著時代的進步,則逐漸演化為一種“感恩”的精神寄托。這種精神寄托中,基于對大自然的敬畏和恐懼的心理在減弱,而對大自然的慷慨賜予與生活的惠澤的銘記和感激的心理在增強。一當“肥套”儀式成為民族認同的鄉俗后,它又在客觀上產生了鞭策的作用,因為是否完成了“肥套”儀式成為獲得社會認可的一個標志,誰沒有完成這一儀式,就會有無形的壓力,就像“剩男”“剩女”們遭受的社會壓力一樣,因此,還愿、感恩與鞭策這三者是融為一體的。
按毛南習俗,“每一家每一代人都必須舉行一次大的還愿祭祀儀式,用18只牲口作祭品。這一代不還,下一代也要補還。第二代補作的還愿,用牲要加倍,即36只。最遲不能拖過三代,若拖到第三代再補還,殺牲就要遞增到72只……”[5]。這種壓力可以看作是一種正能量的傳遞,它用民俗的力量,催促人們為舉辦儀式而積累物質財富,催促人們追求“生存”“溫飽”和“發展”,催促人們感恩心理的迅速成長。從某個角度看,毛南儺戲是“肥套”活動的伴生物,或者說,它們彼此相依存。“肥套”借助儺戲來表達意愿;儺戲則憑借“肥套”這種有現實意義的民俗活動,造就了生存的環境。
四、“第四堵墻”的虛無化帶來的親和
在實地考察中,毛南儺戲讓我們看到了一種“疏離”與“親和”的辯證現象:一方面,它的神秘感帶來了“疏離”的戲劇效果,而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將“第四堵墻”虛無化的親和特征。
自從法國戲劇家讓·柔璉在1887年提出戲劇的“第四堵墻”這個概念后,就作為一個戲劇表演學的重要話題得到長久的討論。被國際戲劇界稱之為戲劇“三大體系”的代表人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萊希特、梅蘭芳都在各自的戲劇實踐中闡釋了這一理論:斯氏主張演員要表演得像在自己家里那樣,不去理會觀眾的反應,任他鼓掌也好,反感也好,舞臺前沿應是一道第四堵墻,它對觀眾是透明的,對演員來說是不透明的。“舞臺上的真實就是演員真誠地相信的東西。在戲劇中,就連最明顯的虛假也要變成真實,這樣才能成其為藝術。”[7]146而布萊希特是要推翻這堵墻,提出了“間離化效果”,要求演員在情感上與角色保持距離,觀眾同角色之間也保持距離。“演員一刻都不允許使自己完全變成劇中人物……演員自己的感情,不應該與劇中人物完全一致,以免使觀眾的感情完全跟劇中人物的感情一致。”[8]322梅蘭芳則充分展示了中國古典戲曲用藝術夸張和寫意的手法突破舞臺空間和時間的限制,他的表演是從演員內心走向角色的真情流露,“都是把實際生活的特點高度集中,用藝術夸張來表現到觀眾的眼前,使觀眾很清楚地抓住演員每一個動作的目的性。”[9]26因此在他的表演體系中根本不存在“第四堵墻”,也就無需“建設”或“推倒”了。正如蘇聯戲劇家梅耶荷德說的那樣,“中國人民完全明白中國舞臺上所出現的一切,他理解這些舞臺藝術詞匯,他能夠自由地深入到梅蘭芳所表演的戲劇內容中去”。[8]72
毛南儺戲從它的一些戲劇元素來看,它是屬于梅蘭芳戲劇體系的,我們從下面幾個角度來分析,它并不存在“第四堵墻”。
(一)從演員構成來看
演員與觀眾有天然的聯系。毛南儺戲的演員(“肥套”師公)都是本地毛南族人,作為演員和觀眾的群體他們平時是親戚、鄰居、朋友、熟人,一起生產種地,一起閑坐聊天,在舉行“肥套”儀式時演員們集結起來,才會臨時改變身份。他們與觀眾(鄉親)之間自然會有一種親切感,雖然師公身上散發著宗教的神秘,但“演員”和“鄉親”的雙重身份使他們對于觀眾具有了潛在的親和關系。
(二)從演出場地來看
“肥套”儀式是一種家庭行為,是以各家各戶為單元進行的活動,活動通常是在堂屋完成,堂屋的面積就是“舞臺”和“觀眾席”(觀眾坐在靠大門一側)的面積,毛南族民居的堂屋一般為20平方米左右,觀眾基本上是儀式主家全體成員和村民鄰居,老幼青壯婦孺皆有,而有些劇目中演員是直接和觀眾對話的,由此可知演員和觀眾之間幾乎就是“零距離”的接觸了。值得一提的是,毛南儺戲中有不少與生育和性愛有關的場面,演員甚至拿著生殖器官的象征物進行表演,但在場的男女老少并不忌諱,亦可將之看作是一種性教育的普及形式。這種天然的地緣化場地使他們不會像看舞臺劇那樣隔著“一面透明的墻”。
(三)從儺戲唱詞來看
毛南儺戲的演出是一次文化普及活動。聰明的毛南族人將一些生產、生活知識融入其中,比如在表演《仙官架橋》時,角色不僅會交代戲劇的故事情節,同時還會借助于這些情節承載知識的傳授,他要介紹自己從哪來,于是開始交代地理方位、時令季節,講述沿途所見所聞,尤其是一些跟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人和事,以及接人待物的禮儀等,然后再來講架橋的意義,架橋的過程與方法等等。這樣不僅生動地再現了戲劇情節,傳授了生活的知識和做人的道理,還增加了戲劇的趣味性,也進一步拉近了演員與觀眾的距離。
正是由于環江毛南族儺戲是從毛南山鄉生長出來的,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其戲劇藝術一方面接受了其他劇種的影響,同時又全方位地與它的受眾融為一體,與它的生長環境融為一體,從它的受眾和藝術環境中獲得了生存、發展的力量,找到了戲劇藝術與實際生活的契合點,從而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這也許對于其他地方戲種的延續、發展會有一定的啟發意義的。
[1]熊佛西.佛西論劇·國劇與舊劇[M].新月書店,1931.
[2]譚為宜.戲劇的救贖——1920年代國劇運動[M].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
[3]任君.任君戲文選·毛南山鄉第一戲[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12.
[4]亞里斯多德.詩學[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
[5]譚自安等,中國毛南族[M].銀川:黃河出版傳媒集團、寧夏人民出版社2012.
[6]魯迅.華蓋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7]龍飛,孔延庚.斯坦尼斯拉夫斯基[M].沈陽:遼海出版社,1998.
[8]陳世雄.三角對話:斯坦尼、布萊希特與中國戲劇[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
[9]梅蘭芳.梅蘭芳戲劇散論[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