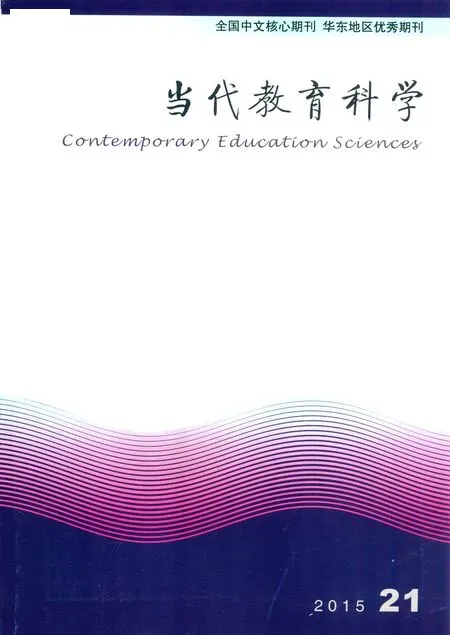我國研究型大學本科人才培養模式變革探析*——基于“985”高校的策略選擇
● 韓 萌
本科教育是大學人才培養的基礎。人才培養模式的優劣,決定著本科生教育質量的高低。《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明確指出:“要牢固確立人才培養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關鍵是更新教育觀念,核心是改革人才培養體制,目的是提高人才培養水平。”我國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進程中,研究型大學的發展備受矚目。但傳統本科人才培養過程中所存在的重傳授輕啟發、重理論輕實踐、重共性輕個性等弊端,卻與人才培養目標相去甚遠。隨著現代科學技術對大學創新創業的驅動和要求,以“985”高校為代表的研究型大學正在突破傳統教育模式,從教學理念、行動反思、實踐創新等方面深化探索,開啟人才培養模式的“新常態”。
一、研究型大學本科人才培養模式中存在的問題與歸因
研究型大學作為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戰略資源,對加強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提高高等教育質量、建設創新型國家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在國家創新發展需要及政策傾斜的支持下,研究型大學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科研漂移”的現象。尤其是在人才培養過程中,研究型大學將辦學資源更多地投入到相對容易產生學術聲譽、經濟效益的科研領域和研究生培養領域,本科教育所占的份額和比重逐漸削弱,導致以人才培養為目標的教學功能日趨弱化和邊緣化,本科教學活動在學校整體資源配置中偏離了應有的主體地位。
張紅霞等學者(2007)對研究型大學在內的72所高校進行本科教學情況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在對“教授授課質量”滿意率上,研究型大學為69%,普通高等學校為93%;在“對一至三年級50%以上所修課程”滿意率上,研究型大學有46%的學生不滿意,普通高校為22%;在學生參與教師課題的廣泛程度上,研究型大學為15%,普通高校為57%;此外,教授在幫助學生學術成長及人際交往等方面,研究型大學也遠遠遜色于普通高校。[1]由此可見,在人才培養方案的制定和培養途徑的選擇上,研究型大學并沒有很好地發揮其優勢和特色,本科教育與教師科研活動、學科建設之間存在著嚴重的結構性矛盾。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研究型大學存在著教師、學術、物質資源對本科生教育關注不夠、投入不足、措施不力等問題,也存在著教學內容及互動方式不能激發學生的研究志趣、難以滿足學生的學習愿望及需求等問題,從而嚴重制約了研究型大學本科教育的健康發展。
從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程來看,這主要歸結為兩方面原因:其一,我國在建設研究型大學的過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大躍進”現象。部分高校試圖通過擴大研究生教育規模、增加博士點與碩士點數量,達到盡快實現研究型大學的高遠目標,使得本科教育在大學內“失寵”,其典型表現就是中國大學內部普遍形成了一個概念:“研究型大學=強大的研究生院=研究生數量多于本科生數量”。[2]事實表明,大學資源存在著有限性,如果研究生規模過大,必將占用本科生享有的教育資源,造成分配不公;同時,本科教學的邊緣化使得教師不重視本科教學,導致本科生陷入一方面就業壓力大、另一方面卻無法滿足社會需求的 “兩難境地”。出現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研究生領域比較容易在短期內獲得階段性成果,而本科生教學資源投入多、見效慢,難以很快看到創新之處和發展成果。洪堡曾言,大學的偉大功效須在25年后方能看到。上述現象蔓延的直接后果是,本科教育質量明顯下滑,中國本土人才培養的競爭力嚴重下降。
其二,國家政策和大學對科研的強化措施影響到教師的教學觀念。人們對研究型大學存在一個普遍的認識誤區:若想躋身世界一流大學行列,就必須將科研置于首要或核心位置,擁有全球領先的技術和成果。受此誤導,我國大部分高校在有關教師的聘用與淘汰、經費的分配與使用、學科的生存與發展等方面,無一不與科研成果緊密掛鉤。這使得人們不自覺地形成一種思維模式,似乎研究型大學就是在大學中做研究,科研成果是衡量研究型大學的首要指標,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是科研成為中心工作,本科教學明顯弱化。教師名為“教”師,實為科研附庸。
大學教育的本質是培養人,大學里的科研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它們有益于人才培養,同時教學又是科研的“隱形動力”。對于大學而言,如果學校無法讓教師感到本科教育是最具挑戰性、最受尊重、最值得奉獻的工作,教師就難以投入全副精力去對待這原本是教師天職的工作,其工作重心即會隨之轉移,實際上這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發展觀和大學理念。[3]
二、基于“985”高校的我國研究型大學人才培養模式變革
在知識經濟與全球化發展時代,研究型大學承載著培養精英、創新知識、引領社會發展的歷史使命。自上世紀末至新世紀以來,世界范圍內圍繞現有人才培養模式及知識生產展開了深度反思。就實踐層面而言,人才培養主要包括學校為學生構建的知識、能力、素質等結構,以及筑建這些結構的方式,包括人才的培養目標、培養規格、課程體系改革和基本培養方式等,這不僅是一項循序漸進的知識深化過程,更是一項系統復雜的育人工程。目前,我國研究型大學本科人才培養模式的變革主要是基于學生的學業水平和實踐需要,從“以教師為中心”向“以學生為中心”轉變,構建“教、學、研、做”多模塊、多層次的聯動培養育人平臺。本研究以“985工程”大學作為考察對象,以其本科教學改革策略為研究依據,對研究型大學人才培養模式的具體實踐進行總結與歸類分析,探討其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趨勢與發展方向。
(一)從通識到專、職:“交叉”培養模式
1.基于認知規律的“階梯式”培養
美國教育學家布魯姆(B.Bloom)認為,認知領域的教育目標分為記憶、了解、應用、分析、評鑒、創造六個層次,認知過程是按照上述層次漸進發展的,課程進度也應循序漸進、以階梯式前行。
本科生階段的分層教學法,旨在通過低年級實施通識教育,夯實基礎,發現興趣,高年級著力專業教育,鼓勵自主探究,實行個性化培養。通識教育強調記憶和了解各個領域的基本知識,培養學生從多元視角觀察問題,增強他們交叉思考的能力,為專業教育的深化與拓展打下堅實基礎。如清華大學實施不同年級在教學計劃和導師指導下開展自由選課學分制和自主選擇專業制;山東大學在本科一年級構建由通識必修課、核心課和選修課構成的三層次課程,同時開設國學修養、創新創業、藝術審美、人文學科、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等“七模塊”通識教育體系;二年級時可根據自己的興趣通過考試和面試的方式轉換專業,給予學生自主選擇的機會。
2.基于學科培養與發展路徑相結合的“對接式”培養
人力資本理論表明,凝聚在人身上的知識、技能及其表現出來的各種生產力主要靠后天培養。教育是人力資本形成的主要渠道。研究型大學的專業設置與未來職業的關聯度和對接程度相對較高,如果在本科教學中將學科培養與發展路徑相結合,能在更大程度上積累并發揮人力資本在社會生產中的作用。如南京大學通過“三三制培養模式”將本科培養與后續發展形成對接,劃分為大類培養、專業培養、多元培養三個階段,在交叉復合、專業學術、就業創業三條路徑上予以指導;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則根據不同目標定位和學生自主需求設置多模塊課程平臺,對學生實施早期職業化的對接培養,有利于其就業、創業、升學、留學等個性化需求。
(二)從縱向到橫向:“跨經歷”培養模式
傳統人才培養以縱向的課堂傳輸知識為主,“跨經歷”培養強調橫向交流的重要性。它具有兩方面含義:一是跨學科、跨學校、跨國境;二是實踐經歷、校園經歷和海外經歷。學生在校期間通過體驗不同的教育環境、理念和學習方式,既能鞏固課堂所學知識,也能將知識轉化成生產力,實現從“學而知之”向“實而用之”的轉變。
1.共生模式:全方位的“院校協同育人”
“共生”作為教育生態學的關鍵概念,是指不局限于內部和睦的共存共榮,而是相互承認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活動和參與機會、積極建立起相互關系的一種社會結合。[4]“院校協同育人”的“共生模式”,是一種寓教于研的校際協同、校所協同、國際合作等全方位人才培養模式,既能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并增強其創新本領,又能帶動和促進高校與科研機構相互配合和支持,易于實現科教結合的有效推進、合作共贏。如北京大學-斯坦福中心作為中美一流大學協同創新的平臺,致力于整合現有合作資源,開展國際學生實習、學生交換等合作項目,并促成“斯坦福北大分校項目”、斯坦福孔子學院等一批合作成果的誕生;中國地質大學與中科院等8個研究所共建 “C2科教戰略聯盟”,為學生參加野外地調以及地質工程現場開展專業實踐活動創造了優越的條件。[5]
2.合作模式:多需求的“校企聯合培養”
一流大學本科生素質的養成,既要以學生發展為本,又要為學生提供優質的可供教育實踐的場所。校企合作模式在這方面具有顯著優勢,主要體現在:首先,專業課程能及時把握市場動態和學科前沿,教學效果顯著,學生在實習過程中能培育團隊精神、拓寬發展空間、有效提升綜合素質;其次,高等院校尤其是工科院校,可以通過學生在企業的實習實踐情況,檢驗其應用型專業培養的目標和方案是否符合市場需求,以便對專業進行定位和修正,這既是實現教學改革和教育創新的重要舉措,也為高校應用型專業深化教學改革提供有益經驗。特別是對理工科、醫科的學生,校企合作模式的實踐意義尤為重要。如中國藥科大學在學生入學伊始就逐步進入實驗室和醫藥生產研發領域,培養其創新創業的能力,將校企合作優勢從科研項目拓展到實際需求中,成為學校未來人才培養模式轉變的一個方向。據統計,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同濟大學、南京大學等實用性、實驗性課程占課程總比例的90%以上。
(三)從共性到個性:“特色”培養模式
1.寬口徑、多文化交流的“書院制”
研究型大學建立書院制的核心理念,是給予學生自主選擇的權利。一般認為,書院制是在借鑒西方大學住宿學院的基礎上承襲了中國書院的古老傳統。學院負責學生的專業教學和科研,書院則承擔學生全面發展的生活環境,有學者曾將其分喻為“父親”和“母親”。[6]這種模式為所有寬口徑入學的本科生創造了一個亦師亦友的平臺,運用多元文化環境影響并促進學生的自我管理和發展能力,通過提升人際交往能力和社會適應能力,達“以文化人”之效。復旦大學和西安交通大學將建設書院制看作改革本科生教學制度、提高本科生培養質量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尊重學生個性與選擇為根本,突破專業學習局限,提供公共空間和指導教師,實行一對一關懷,更易為學生所接受,形成多元文化交流的書院精神。
2.基于人才培養特色的“拔尖人才計劃”
相對于寬口徑培養的書院制,拔尖人才計劃以創新教育理念為指引,針對在某領域具有一技之長或天賦異稟的學生,既注重通才教育,又強調專業特色。它以導師為核心、以學生興趣和全面發展為目標的專業培養,實施專業有計劃、指導有方向、學生有目標的導師學徒制。如北京大學“元培學院”、武漢大學“弘毅學堂”、上海交通大學“致遠學院”、浙江大學“竺可楨學院”等,其共同特征是在本科階段將學生劃分為不同的基礎科研方向,以教授為教學導師,為每位學生定制個性化培養方案,實行彈性管理,選用國際一流教材小班授課,采用探究性和研討式教學,將住宿學院制、游學制和導師制有機結合,成為極具特色的拔尖人才培養模式。
三、研究型大學本科人才培養模式變革的多元取向
吉本斯(Gibbons)等學者在知識生產的新模式中提出,傳統的知識生產以學科和大學為中心,而新的知識生產則更多來源于實際問題。[7]本研究通過分析“985”高校的策略選擇發現,研究型大學的人才培養模式具備多層次和多維度,尤其是研究型大學的教學活動逐漸從傳授高深知識轉向以“學生發展”為中心、兼顧科學研究與服務社會的改革中來,呈現出本科人才培養在新理念下的多元取向。
(一)研究取向
博耶將教學活動作為學術研究的重要部分,[8]這表明教學本身就具有研究取向。對于研究型大學的人才培養而言,教學與研究本應融為一體,如何使傳授知識、接受知識、反思知識、創造知識成為一個自然而然發生的過程,在教學中滲透研究取向是關鍵所在。研究型大學的主要任務是培育具有獨立科學研究能力的精英人才,而這種能力主要是在大學階段培養出來的,如果從教學中剝離研究的成分,那么培養學生研究能力的關鍵時期就會錯過,研究型大學的資源優勢就無法得到彰顯。[9]人才培養理念應著眼于“育人”而非“制器”,教學活動應使學生成為一名“思想者”而不是“適應者”。[10]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我們需要意識到學生既是學習者也是研究者的“雙重身份”,最大程度地為其提供研究機會,使本科生成為研究群體中的活躍參與者,深切體驗科研的過程并享受科研的樂趣。研究表明,教師通過將研究活動中獲得的見解與成果直接應用于教學,能夠培養學生的研究創新能力,為其成長和發展創造良好的學術場域。這種研究取向在階梯式培養和特色培養模式中表現尤為突出。
(二)應用取向
高等教育階段的知識積累不僅僅在于對知識的掌握程度,還在于將知識應用于實踐的程度,即發揮人力資本在社會生產力中的作用。就學生而言,無論高等教育的教與學形式如何,其個體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將來在社會上獲得更好的發展,實現其社會價值。因此,個人需求的實現必然要求“第一課堂”與“第二實踐課堂”之間形成有效鏈接,將知識應用于實踐。這種將知識生產逐漸轉變為社會實踐的過程,正是研究型大學人才培養活動的本質屬性,也更能比一般大學體現出服務社會發展的辦學理念。
以理工科為主的研究型大學人才培養中明顯呈現出這種應用取向,如“對接式”培養和校企聯合培養模式。由于教學本身是一個協助學生將高度抽象的專業理論知識應用于具體實踐活動的過程,因此將知識應用于實踐的技能和通過技能改造世界的態度和意識,本身就是對知識的生產和再發展。學校在專業設置時如果能優先考慮到與社會相關行業、企業等領域的合作,以及畢業生的就業趨向和實際需求,那么這種應用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將會成為未來大學教學改革的新方向。
(三)道德取向
人們在談論研究型大學時,往往注重的是其學術屬性。但無論何種類型的大學,首先是作為大學而存在的,培養人才是其根本任務。新人文主義理論認為,教育強調的是培養人的理性和道德,從教育的本質出發,高校教學的最終目的在于關心“教育本身”和“心靈培養”。我國“985”高校正在普遍推行的通識教育模塊和獨特的書院制人才培養模式,其落腳點就是對學生心靈的培養。洪堡認為,教學固然能讓學生發現問題并自己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但大學“乃是民族道德文化薈萃之所,其立身之本在于探索深邃博大之學術,并使之用于精神和道德的教育”。[11]可見,大學以育人為本、以科學為根、以道德為魂,給予學生們的除了知識之外,還包含價值觀、道德觀、榮辱觀、思維方式、行為習慣等,獨特的大學精神是提高教育教學質量和人才培養質量的治本之策。本科人才培養模式改革必須確立“以學生發展為中心”的育人理念,將教書育人與學生個性結合起來,實現群體文化構建、文化育人的歷史使命。
[1]張紅霞,曲銘峰.研究型大學與普通高校本科教學的差異及啟示[J].中國大學教學,2007,(4).
[2]秦春華.重新認識研究型大學[N].中國科學報,2014-06-19.
[3]朱崇實、潘懋元.科學發展觀引領高教前行——本科教育:高校立校之本[N].中國教育報,2005-04-01.
[4]井上達夫.走向共生的冒險[M].東京:每日新聞社版,1992:24-25.
[5]王焰新.構建高水平行業特色大學——一流本科教育體系的思考與實踐[J].教育研究,2012,(10).
[6]姜泓冰,楊彥,尹世昌.書院制改變了什么[N].人民日報,2011-09-16.
[7]Michael Gibbons.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M].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1994.
[8]Boyer E L.Scholarship Reconsidered:Priorities of the Professoriate[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24.
[9]鄭家茂,張胤.論研究型大學本科人才培養模式的特點[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08,(1).
[10]韓萌.大學多元文化育人功能的思考[J].教育研究,2010,(8).
[11]陳洪捷.德國古典大學觀及其對中國的影響[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