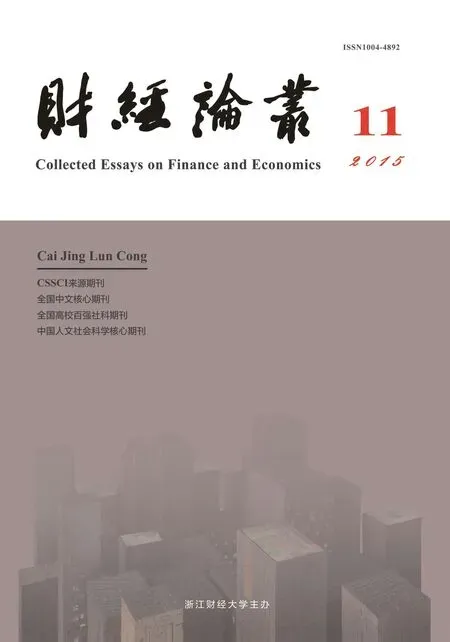從價規制與從量規制孰優孰劣?——基于可再生能源產業上網價格政策與配額制的比較研究
孫 鵬,李世杰
(海南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海南 海口 570228)
一、引 言
能源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物質基礎。林伯強(2010)指出能源安全、能源稀缺、能源高成本以及減少環境的負面外部性都可能對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構成挑戰[1]。未來大力開發可再生能源正是解決這些能源問題的關鍵所在。近年來,可再生能源產業的發展得到了世界各國和地區相關政策的大力支持。上網價格政策和配額制是兩種最為常見、也最為有效的規制政策,世界范圍至少60個以上的國家已經應用了這兩個政策中的一種(Lund,2009)[2]。上網價格政策(Feed-in tariff,FIT)本質上是一種價格規制政策,其以德國、西班牙、丹麥和我國為代表。它是指電網公司有義務收購由可再生能源貢獻的電力,政府制定一個高于市場價格收購價格,給予可再生能源發電產業以政策優惠,可再生能源電價與市場電價的差值由政府或消費者進行分攤(Menanteau et al.,2003)[3]。而配額制(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RPS)本質上則是一種從量規制,它以英國、美國與澳大利亞等國為代表,是指政府制定一個可再生能源占全部發電量的一個最低比例,電力生產者有義務在生產化石能源電力同時必須配套生產相應最低比例的可再生能源電力(Jaccard,2004)[4]。
實踐中,各個國家實施兩種政策的效果千差萬別,學術界對兩種政策孰優孰劣一直爭論不休,到底在何種市場環境和政策目標下,應該采用何種規制政策才能實現既定目標,學者們目前也未給出一個合理解釋。本文旨在運用博弈模型探討兩種規制手段的各自優缺點,為在特定的市場環境和政策目標下的政策選擇提供理論依據。
二、文獻綜述
到底FIT和RPS哪種政策更有效?不同的出發點以及視角可能會得到了不同的答案。一部分學者認為FIT比RPS更有效。Lewis and Wiser(2006)檢驗了不同國家和地區在支持風能發電裝備制造產業政策的重要性。他們指出FIT可以直接提供一個穩定的、高收益風電開發市場,這會形成生產者的一個良好預期。而RPS則會創造市場的不確定性,并且降低企業的收益水平,進而不能最大化的激勵嘗試實現特定的環境目標[5]。Lipp(2007)比較了丹麥、德國(使用FIT)和英國(RPS)在扶持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的政策效果。結論是FIT在產業發展以及創造就業方面要好于RPS[6]。Cory et al.(2009)認為FIT給開發者和投資者一個支付保障,而RPS則未能給予市場一個承諾和預期,故FIT是比RPS相對有效的規制政策[7]。Butler和Neuhoff(2008)提出英國采取的RPS與德國采取的FIT相比,在理論上應該有更低的開發成本,然而實踐中并不如此。德國采取的FIT使得德國的風能發電市場擁有更低的輸送成本、更高的市場競爭以及更快的產業發展[8]。
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RPS在一些方面要強于FIT。Schmalensee(2011)指出通過德國和英國關于FIT與RPS的比較中,不能得出FIT就一定比RPS好。這種比較只能說明政策的應用方面德國做的要比英國好,而從在美國德克薩斯州RPS的應用來看,其同樣可以達到FIT的規制效果[9]。Tamás et al.(2010)指出如果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兩種政策效果應該是相同的。如果市場競爭是不完全的,在一個較寬的參數變化范圍內,RPS社會福利都始終高于FIT[10]。Ringel(2006)指出在理論上判斷,RPS更有利于形成競爭優勢,從而降低成本[11]。Menanteau et al.(2003)指出FIT在增加發電機組裝機容量以及激勵效果方面更具優勢,但在成本控制,動態效率以及技術改變方面,RPS要優于FIT[3]。
我國當前主要實施的是以FIT為核心的可再生能源發展支撐體系,但未來是否引入RPS的爭論也從未停歇。一部分學者鑒于目前FIT發揮的巨大作用,認為應在堅持當前政策的同時,對FIT的具體實施手段進行優化調整。史丹和楊帥(2012)認為上網電價政策是目前推動可再生能源發展最為成功的機制,但這一機制發揮重要作用的關鍵還在于如何結合我國的國情[12]。時璟麗(2008)指出雖然FIT發揮了巨大作用,但還存在著諸多不足,我國應吸取國外的成功經驗,對政策予以適時調整,完善價格政策體系。另一部分學者則指出未來我國還應積極實施RPS政策以解決FIT的不足[13]。姜南(2007)指出FIT下由政府規定的固定的價格會與實際的成本價格和市場價格脫節,無法保證開發成本最低,從而會使供電商的利潤受到影響,損害他們的積極性,引入源配額可以解決這方面的弊端[14]。樊杰等(2003)論證了實施可再生能源RPS在東部沿海地區能源結構優化過程中的意義及其途徑[15]。
我們無法從一個視角來評估不同政策的好壞,事實上,FIT和RPS都有其優勢和劣勢,因此需要根據不同的市場條件和政策目標來選合適的政策。基于此,本文構建了一個包含能源產量以及R&D投入的兩階段博弈模型,并運用數值模擬的方法來分析兩種政策下不同的影響機理,旨在為我國未來扶持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的政策選擇提供理論借鑒。
三、基本模型構建及求解
一個寡頭企業生產兩種能源電力產品:可再生能源電力和化石能源電力。我們將在兩種規制方式下正式建立一個能源替代的博弈模型,定義兩種能源電力分別為R和D。
需求方:對于i∈{R,D},P為價格,Qi為能源產量。效用函數為:

其中α>0為常數,表示市場規模。反需求函數可以對式求偏導得到:

供給方:市場中有唯一的電力能源生產企業。該企業在不同的技術成本下同時生產兩種能源電力。在給定的規制政策下,企業在第一階段選擇R&D的投入水平,第二階段選擇兩種能源電力的產量。以下將正式在FIT與RPS兩種方式下建立企業的利潤函數。
(一)FIT下模型構建及求解
在FIT下,能源企業可以獲得額外的價格補貼,此時企業的利潤函數如下:

其中,ζ>0是固定溢價水平;c為常數表示化石能源的邊際成本系數;c()2為規模報酬遞減的化石能源總成本。由于可再生能源發電技術的不成熟性,其開發成本要高于化石能源,X為基于成本節約的R&D支出。可再生能源的邊際成本系數為c+me-μX,0<μ<1表示研發效率,m>0表示可再生能源與化石能源的初始成本差距。


R&D最優投入量與補貼價格水平ζ、市場規模α以及成本系數相關。將代入式,就會得到均衡時兩種能源電力的產量和,再將其代入到(3),可以得到最優的企業利潤πF*。
(二)RPS下模型構建及求解
在RPS下政策制定者規定了可再生能源電力必須滿足總能源電力產量的一個最低比例。假設最低的比例為λ∈[0,1],有QR/(QR+RD)=λ,即QR=λ/(1-λ)QD。此時生產方利潤函數為:

根據逆向歸納法,按照相似的求解路徑,可以得到在RPS下均衡解。為了簡化表達式,假設λ/(1-λ)=k,即=。對(6)式關于和分別求偏導得:

將(7)式代入到(6)式中并對XR求偏導,我們得到PRS方式下均衡時最優R&D投入為:

(8)式最優R&D投入與最低可再生能源電力比例k,市場規模α以及成本系數有關。同樣我們可以得到RPS下最優能源電力、以及最大利潤πR*。
四、上網價格規制與配額制間的效果比較
在上文得到的最優R&D投入和兩種能源的最優產量基礎上,將比較兩種政策下不同的激勵效果,包括R&D投入、兩種能源電力產量、消費者剩余以及社會福利。由于表達式的復雜性,將借助數值模擬的方法進行比較,對參數進行賦值并得到參數變化情況下數值解路徑,所有的程序設定以及圖形描繪都將在MATLAB7.0中完成。
在兩種規制政策下,一種規制變量為價格,另一種則為產量。無法在兩種規制變量同時變化時來比較不同規制政策的影響機理,因此必須對兩種規制政策進行標準化處理。為了保證不同政策間將達到等價的效果,需要建立起參數ζ與k的一座橋梁。正式的定義等價效果為:
定義1:如果兩種規制政策實現了相同的可再生能源電力市場份額,就說此時這兩種規制政策的效果是等價的。
定義1為建立兩種政策比較的統一標準系提供了途徑。所以由式(4)可知,FIT下兩種能源電力產量比率為/=[cα+(1+c)ζ]/[(c+me-μXF)α-ζ],而在RPS下的兩種能源電力比率為k。由定義1可知,如果兩種規制政策是等價的,則令k=[cα+(1+c)ζ]/[c+me-μXFα-ζ],這表示為實現RPS與FIT同樣的可再生能源市場份額,當FIT下的規制水平為ζ時,RPS下的規制水平需為[cα+(1+c)ζ]/[(c+me-μXF)α-ζ]。故為獲得與FIT同樣的市場份額下,PRS政策下有:

其中f∈{X,Q}。以下我們只需要比較FIT下的fF*(ζ)與RPS下的fR*([cα+(1+c)ζ]/[(c+me-μXF)α-ζ])即可。至此,我們將不同的規制手段(ζ與k)比較轉化成了統一的比較變量(ζ),這樣可以在一個函數圖像上描繪出兩種規制手段的差異性。
(一)最優R&D投入比較
首先比較兩種規制政策下的R&D投入XF*(ζ)和XR*([cα+(1+c)ζ]/[(c+me-μXF)α-ζ])。有命題:
由命題1可知,隨著市場規模α,研發效率μ以及初始成本差異m增加,最優R&D投入水平都顯著地增加。同時,規制水平(ζ,k)提高也顯著提高了企業R&D投入量。通過數值模擬方法可以模擬出兩種政策方式下哪種規制手段對激勵R&D投入更加有效,結果如下:

當且僅當cD(S)時等號滿足。

圖1 R&D投入比較(c=1,α=30,μ=0.12,m=2)
如圖1所示,R&D投入隨著補貼水平(即ζ與k)的提高而提高,這就證明了激勵性的規制政策能顯著提高企業基于成本節約的R&D投入,并且能顯著提高企業生產效率。但兩種規制政策下將帶來不同程度的激勵效果:在相同市場份額的目標下,FIT政策下的最優R&D投入水平要高于RPS政策下的水平,這意味著在激勵企業基于成本節約的R&D投入方面,FIT要比RPS更加有效。這一理論分析的結論也得到了實證的支持,如Lewis和Wiser(2007)[5]、Lund(2009)[2]等通過實證研究都得出在激勵R&D投入方面FIT政策是較有效的規制手段。
(二)能源產量比較
繼續遵循定義1條件,可以比較兩種政策下可再生能源以及化石能源的最優產量以及市場價格的大小。由(4)-(8)式,可以得到兩種能源的最優產量以及市場價格水平,有以下命題:
由命題2可知,兩種規制政策對于提高可再生能源產量、抑制化石能源生產,從而實現能源結構調整的路徑不盡相同。由數值模擬有:


圖2 可再生能源產量比較

圖3 化石能源產量比較(c=1,α=30,μ=0.12,m=2)
如圖2,圖3所示,隨著補貼水平(ζ和k)的提高,FIT下的可再生能源產量要高于RPS下的產量。但在RPS下化石能源產量下降的幅度卻要高于FIT下幅度。故可以得到以下基本結論:FIT政策在促進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方面更具有優勢。但另一方面,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給我們帶來了大量的諸如氣候變暖、空氣污染等環境和社會問題,因此在降低對化石能源的過度依賴,降低能源消耗的碳排放以及實現環境改善方面,RPS方式會發揮更大的作用。
造成兩種規制手段規制效果上差異的原因這在于兩種能源存在替代關系,規制政策可以從兩個方面實現可再生能源對化石能源的替代:一是提高可再生能源電力的產量,這可稱為激勵效應(Incentive Effect,IE);二是抑制化石能源的產量,這可稱為抑制效應(Disinhibition Effect,DE)。FIT政策下,政府給予了可再生能能源電力一個高于市場價格的補貼價格,這使得可再生能源電力產量迅速增加,但化石能源電力產量并未得到有效抑制;而在PRS政策下,政府規定了可再生能源電力與化石能源電力的一個最低比例,企業在生產決策時既可以提高可再生能源產量,亦可以降低化石能源產量,此時對化石能源的抑制效應要顯著的大于FIT政策下的抑制效應,而對可再生能源的激勵效應卻小于FIT政策下的激勵效應。即IEF>IER,DEF<DER。
(三)消費者剩余比較
由式(1)可知,在自由市場以及沒有市場失靈條件下的消費者剩余為CS=(QD+QR)2/2。如果這一條件發生變化,消費者剩余函數將會改寫。以下考慮在消費化石能源時存在負外部性的情形,假定消費化石能源時的污染函數為:

(13)式為污染排放量的二次形式(孫鵬 張力,2014)[16]。并且有?f(QD)/?D>0以及?2f(QD)/>0,表示隨著對化石能源的消費所產生的負外部性是以遞增方式遞增的。γQD為污染排放量,γ∈[0,1]為常數表示能源的排放強度。w為污染的損害系數。w以及γ越大,負外部性水平越高,消費者剩余就越低。在FIT政策下,會存在一定的規制成本ζQFR,實踐中一種常見的方法是將這種成本在消費者中分攤(中國、德國、丹麥等國都是采用這種方式),故在兩種政策下消費者剩余可以表示為:

通過式,可以數值模擬出兩種規制手段下消費者剩余的高低,結果如下:

由圖4所示,RPS方式下的消費者剩余顯著地高于FIT下的消費者剩余。由于FIT政策是一種政策實施成本相對較高的手段,其在實施過程中會產生額外的規制成本ζQFR,隨著對可再生能源產業扶持力度不斷提高,消費者必須承擔這一高昂的規制成本;而在RPS方式下,消費無需承擔額外的成本,因此FIT下的消費者剩余顯著的低于RPS下的消費者剩余。
(四)社會福利比較
我們將社會福利函數視為廠商利潤與消費者剩余的和,即:


圖4 消費者剩余比較
通過數值模擬可以比較出兩種政策下社會福利的高低,如圖5所示:

圖5 社會福利比較(c=1,α=30,μ=0.12,m=2,γ=0.1);在(A)中w=100,在(B)中w=400
化石能源消費過程中產生的負外部性水平高低決定了哪種規制政策在提高社會福利方面更加有效。如果污染損害系數w相對較低(w=100),FIT下的社會福利較高;而如果污染損害系數w相對較高(w=400),RPS政策下社會福利較高。這一結論就為可再生能源規制政策的選擇提供了依據,即當化石能源負外部性較低時,采用FIT政策更優;當負外部性較高時,RPS政策更優。福利偏好是影響最終決策的關鍵性因素。如果廠商利潤以及可再生能源長期的發展更加受到重視(極端情形下Wi=πii∈{F,R}),那么決策者就會選擇FIT政策;反之,如果決策者更偏好于消費者剩余的水平(極端情形下Wi=CSii∈{F,R}),他將會選擇RPS政策。
五、結論
FIT和RPS是在扶持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降低碳排放以及促進能源結構調整中最常見也是最有效的兩種政策。幾乎所有發展可再生能源產業的國家都采用了這兩種政策中的一種,但是不同國家的實踐效果卻有較大差別。本文從一個理論視角檢驗了兩種政策下的R&D投入、能源產量、市場價格、消費者剩余以及社會福利的差異。本文的一部分的結論得到了其他一些學者研究結論的支持(Lipp,2007;Menanteau et al.,2003;Cory et al.,2009;Lewis and Wiser,2006)[3][5][6][7],也得到各國實踐結果的支持,即FIT在提高可再生能源產量(裝機容量),激勵基于成本節約的R&D投入方面都顯著地優于RPS,這也是應用FIT的國家可再生能源產業的發展水平的國家顯著高于應用RPS國家的原因。
但是本文的結論也指出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水平并不是評價一種規制政策效果的唯一標準。在降低碳排放以及提高消費者福利方面,RPS要比FIT做的更好。與一些現有的研究成果(Tamás et al.,2010)不同的是[10],本文的結論無法獲知兩種政策下哪種社會福利較高,決策選擇取決于化石能源負外部性的水平的高低。當負外部性水平較高時,RPS下社會福利要優于上FIT下的社會福利。
從世界各國的政策實施過程來看,兩種政策適用于產業發展的不同階段和不同的經濟環境。王仲穎等(2012)指出FIT適用于產業成長階段,有利于降低可再生能源市場的交易成本、穩定可再生能源市場、支持實施統一發展規劃、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等。而RPS適用于產業成熟階段和市場經濟體系健全的國家,通過結合市場機制和政府管制,可更大程度地推動產業發展和市場競爭[17]。本文的結論恰恰證明了在產業不同的發展階段FIT與RPS兩種政策將會發揮不同功效,而政策制定者需要做的是在確定的產業發展階段以及市場環境下權衡這些政策的優劣,選擇一個相對較好的政策并在實踐中使之發揮最大的功效。
[1]林伯強,姚昕,劉希穎.節能和碳排放約束下的中國能源結構戰略調整[J].中國社會科學,2010,(1):58-71.
[2]Lund P D.Effects of energy policies on industry expansion in renewable energy[J].Renewable energy,2009,34(1):53-64.
[3]Menanteau P,Finon D,Lamy M L.Prices versus quantities:Choosing policies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 energy[J].Energy policy,2003,31(8):799-812.
[4]Jaccard M.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J].Encyclopedia of Energy,2004,5:413-21.
[5]Lewis J.I.,Wiser R.H.Fostering a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y industry: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wind industry policy support mechanisms[J].Energy Policy 2007(35):1844-1857.
[6]Lipp J.Lessons for effective renewable electricity policy from Denmark,Germany and the United Kingdom[J].Energy policy,2007,35(11):5481-95.
[7]Cory K S,Couture T,Kreycik C.Feed-in tariff policy:Design,implementation,and RPSpolicy interactions[J].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2009.
[8]Butler L,Neuhoff K.Comparison of feed-in tariff,quota and auction mechanisms to support wind power development[J].Renewable Energy,2008,33(8):1854-67.
[9]Schmalensee R.Evaluating policies to increase the generation of electricity from renewable energy[J].Energy policy,2011.
[10]Tamás M M,Bade Shrestha SO,Zhou H.Feed-in tariff and tradable green certificate in oligopoly[J].Energy policy,2010,38(8):4040-47.
[11]Ringel M.Fostering the use of renewable energ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the race between feed-in tariff and green certificates[J].Renewable energy,2006,31(1):1-17.
[12]史丹,楊帥.完善可再生能源價格的政策研究——基于發電價格補貼政策與實踐效果的評述[J].價格理論與實踐,2012,(6):24-28.
[13]時璟麗.關于在電力市場環境下建立和促進可再生能源發電價格體系的研究[J].中國能源,2008,(1):23-27.
[14]姜南.可再生能源配額制研究[D].濟南: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
[15]樊杰,孫威,任東明.基于可再生能源配額制的東部沿海地區能源結構優化問題探討[J].自然資源學報,2003,(4):402-411.
[16]孫鵬,張力.可再生能源產業價格補貼該由誰來看買單?[J].財經論叢.2014,(2):90-97.
[17]王仲穎,任東明,高虎.可再生能源規模化發展戰略與支持政策研究[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