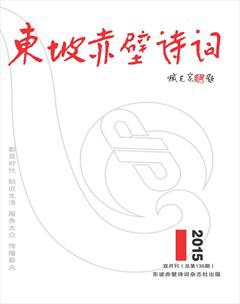青荷一葉馨香脆
此前我在報刊上,讀過王小燕的散文。留給我的印象,清新明快,質樸自然。后來,又在詩詞刊物上,讀到她的不少詩詞,一如她的散文。讀她的詩詞,很輕松,很愉悅,沒有晦澀感,也沒有那種時下所說的做秀感。隨著她的詩句,你便可以走進她所描繪的田園境界,體驗她的詩情畫意。
緣事而詠,平實淡雅。這是給我的整體印象。如《宋埠良種場甜玉米示范基地行吟》:“青紗百里蔚成林,布谷催春曙色深。喜雨和風襄助力,秋來遍野拾黃金。”起筆從大景著手,寫玉米青苗,一望無涯,蔚然成林,晴空萬里,布谷催春,更有喜雨沐苗,惠風吹拂,傾力襄助。因為作了這樣的鋪墊,所以,定會迎來異日的碩秋,遍野的黃金。回看詩題,便知作者是很用心意的。詩題點明,這是對良種甜玉米示范基地的吟詠。因為是“示范基地”,詩中的“布谷”“喜雨”“和風”,便有特殊的喻意了。而“青紗百里”,便是那“布谷催春”的豐碩成果。全詩所描述的景物,緣事而詠,一氣呵成,平實之中,還蘊有幾分淡雅。這正如熊文祥先生所說:“我喜歡平實的風格,不見經營而其實隱藏著詩人的苦心經營。”(《東坡赤壁詩詞》2014年第2期)文祥先生的看法,道出了作文吟詩的個中奧妙。
作者的《辛卯正月赴菊花之鄉福田河建示范茶園感懷》,描寫的是示范茶園,也是對時政的正面歌頌,也是緣事而詠。首聯“一犁新雨沐農家,野草枯藤探綠芽”,清新而質樸。“一犁春雨”,詩味很濃。正是這春雨的沐浴,即便是“野草枯藤”,也都探出了那一片片嫩綠的春芽。頷聯、頸聯,寫“惠政”,給山鄉帶來了巨大變化。“千疇菊”“萬擔茶”,并非為了對仗而夸張,是直寫,也是真實的寫照。正因如此,才有尾聯的山鄉情景:“從此春秋隨興至,拾薪汲井煮煙霞。”直述山鄉的富裕、農民的安居樂業,享受歲月的安適與恬靜。
《下鄉雜興》是王小燕的組詩。這里只選了其中幾首。這是作者下鄉的真實感受。也是作者對農村生活、鄉俗民情的真實描寫。作者幾乎不作任何渲染,所歷所見,直白吐出,展現在讀者面前的,卻又是一幅幅鄉村的鮮活畫面。車離了城鎮,駛進了菊鄉,一眼望去,那迂回曲折的田間小道,那滿畈漾出的田田新綠,越過車窗,盡收眼底。走在山崗上,一陣山風吹過,襲來繞臂的清涼;霏霏細雨,濕透行人衣裳;不必憂慮這山風細雨,會給滿畈的綠菊帶來摧殘,因為綠竹林中,早有建好的烤房,會給雨后的菊花,帶來百倍的“溫暖”。探訪田家小坐,可見房前屋后,倚墻紅棗滿樹,鮮花綠草簇擁,家犬迎來,繞膝而待。更有純樸的菊農,捧上新煮的咸水花生,殷勤款待來客。
我以為作者體會了陶淵明《歸園田居》的寫作神韻。雖然都是直詠農家生活,直吟山村物事,直抒田園感觸,但絕然不同的是,陶翁的筆下,是“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日入室中暗,荊薪代明燭”。其描寫的田園風景,讓人感覺的是荒蕪孤寂。而王小燕的筆下,是“十月繁花應滿筐”,是“綠竹依依掩烤房”,是“農家總是殷勤甚”,是一片興旺、歡樂、溫馨的樂景。陶翁詩中,吐出的是欲遠宦海之后的激憤,而王小燕卻是走進菊鄉之后的熱愛。因為她的筆下,傾吐的是山鄉農家,豐收之后滿懷喜悅、熱情待客的心情。同時,也道出了農家素有的純樸善良的品質。顯然,這是兩個不同時代的真實寫照。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詩中也寫出了農家的憂慮。如《春旱》一詩,因為天旱,雖是麗春,卻柳屈千枝,塵飛兩岸,剛歷嚴冬的春苗,正當花黃的油菜,卻得不到春雨的滋潤。所以作者吟出:“只盼清明揚透雨,絲絲潤我后村田。”這是對大自然的渴盼。而《下鄉雜詠》中“收成豐欠休相問,不及泥工半月多”,則寫出了社會對農民的不公平。顯然,這是作者對社會深層次的思考和關注。這是對社會的渴盼。
正是這樣質樸而自然的傾吐,更可看出,作者對山鄉農家的真摯情感。而這真摯情感,源于作者對山鄉生活的長期了解。作者出生農家,長于農家,畢業于農校,后又工作于農業部門。應該說,她是一位具有文化素養的特殊的“當代農民”。她對“三農”的深入了解,對站在壟畝上耕作的農民,自然更有自己的獨特見解。因為她站得高,望得遠。所以,她的詩作,既能寫出山鄉變化的背后,黨和國家對“三農”政策的支持和作用,也能寫出農民生活中的喜與憂。所以,她的田園詩詞,更能較深地反映當代田園生活的真情實景。
隨情而抒,清新明快。可以說,這是作者給我的深層印象。這得益于作者的語言。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而傳統詩詞,尤其強調語言的藝術性。田園詩的語言,自古以來,因其吟詠對象的特殊性,即以自然山水、鄉村景物、田園生活為吟詠對象,將細膩的筆觸,投向恬靜的山林,閑淡的田野,創造出一種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借以傾瀉詩人的復雜情感,表達對恬淡平和生活的向往。故其作品的語言,隨情而抒,多呈現自然清新、輕松明快、韻致高遠的特點。可以說,王小燕也繼承了這一特點。語言清新,要在一個“新”字上。出語新奇,貴在煉意。這須具功力,需要才氣,亦需磨礪。這當然不易。王小燕的語言,固然還顯稚嫩,但她在努力。她的詠物詩,可以看出她的經營。如《梔子花》:“和風縷縷送晨光,苦雨新晴正艷陽。鄰里植花窗戶后,一盆梔子一樓香。”梔子花,本是鄉村極普通之花。但進入作者視角后,吟進了詩里,可就別有情致了。連雨之后,晴空萬里,一派清新,鄰里窗前,那梔子花吐出的清香,溢滿樓院,縷縷春風吹過,陣陣清香,溢過院墻。這鄉村的春意,芬芳馥郁,沁人心脾。詩的語言,是鮮活的,清新的,自然的。尚如《菩薩蠻·福田訪菊》詞:“福田山上天飛瀑,福田山下生佳菊。菊餅沐秋陽,家家門帶香。蜂兒追逐我,共采花千朵。歸去笑陶家,南山空自夸。”簡直是快人快語。輕松愉悅的心情,清新明快的詩語,讓人讀了,如一泓飛瀑,從天而瀉,心中塊壘,滌之干凈。王小燕的《童年組詩》,這里也只選了幾首。其語言,也是一樣地暢快淋漓。讀著她的詩句,一位天真活潑的山村小姑娘,扎著沖天的小辮,赤著嫩嫩的小腳,從《下秧田》詩中,向我們樂巔巔地走來,站在面前,嚼著甜脆的荸薺,帶著一嘴的清香,溢出滿口的泥花。一會兒,她又溜著鐵環,從村北穿過,飛過村南的稻場;一會兒,她又爬上山崗,采滿了夏枯球,捎到公社賣了,先嘗了冰棍,再買了食油回家。最讓她陶醉的是,像鼻涕蟲一樣,纏著鄰家兄長不放,為的是要看那本《隋唐》小人書。詩的字里行間,不顯半點雕琢痕跡,平實吟來,卻情趣盎然,清新灑脫。鄉村小姑娘的天真活潑,聰明伶俐,勤勞向學,讀來如立眼前,格外逗人喜愛。
概之王小燕的詩詞,無論是緣事的述寫、畫面的描繪,還是情感的傾吐、語言的表達,我以為皆具有一種樸素美。寫到這里,我記起許多年前,陳明剛先生指導我的散文寫作時,曾說過一段話:“自然樸質永遠是一門復雜而艱深的藝術呵!應該說,樸素美是一種爐火純青的藝術境界,是很不容易達到的。我以為,南東求的散文還沒有達到這種藝術美的境界,但是作者懷有此種追求,作者為人具備了樸素的品質,他的散文亦具備了樸素美的基本品格。在現今物欲橫流的現實世界和大紅大紫的文壇角斗中,抱樸如石多么難能可貴呵!”雖然陳先生談的是散文,但詩詞創作亦是如此。因此,我想將陳先生這段坦誠之語,再轉送給王小燕。相信她經過日后的勤奮與磨礪,不斷提高詩學素養和創作實踐能力,從而達到理想的詩詞藝術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