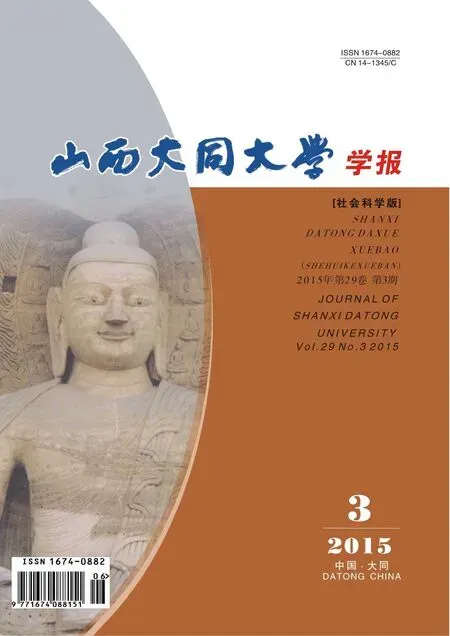《小爾雅》考述及辨正
屈王靜,趙 琦
(山西大同大學(xué)文學(xué)院,山西 大同 037009)
《小爾雅》是繼《爾雅》之后又一部按義類分篇的訓(xùn)詁專書,也是第一部廣雅之作,主要收錄《爾雅》漏收的先秦古語和《爾雅》之后出現(xiàn)的通用詞語。《小爾雅》之名最早著錄于《漢書·藝文志》之六藝略孝經(jīng)類,今本《小爾雅》是南宋陳骙自《孔叢子》中輯錄出來,多被學(xué)者視作偽書。在清代以前,據(jù)目錄記載可考的僅有東晉李軌《小爾雅略解》以及宋代宋咸為《小爾雅》摭入《孔叢子》第十一章而為作的注。在清代由于考據(jù)學(xué)大盛,學(xué)者對于《小爾雅》的注釋、輯佚逐漸增多。現(xiàn)代學(xué)者對于《小爾雅》的研究僅是單篇論文及語言學(xué)史、訓(xùn)詁學(xué)史等著作中的概括性介紹,對于《小爾雅》的真?zhèn)巍⒆髡呒俺蓵鴷r代等方面的問題,至今仍是眾說紛紜,未有統(tǒng)一認識。筆者著重從文獻學(xué)角度對《小爾雅》進行探討,對前人的考證工作做概述,并對其中個別觀點加以辨正。
一、 辨《小爾雅》的源流演變
《小爾雅》篇幅雖小,卻引發(fā)眾多爭論,主要原因在于其成書之后的源流演變多不能廓清。近幾年來學(xué)者才對其源流有了較為公允的看法。
黃懷信在論及《小爾雅》的源流情況時有如是說法:“《小爾雅》著錄在我國最早的目錄著作《漢書·藝文志》(以下簡稱《漢志》)中,本屬單行,沒有撰著者名氏。《漢志》本于劉歆《七略》,可見其書在劉歆編《七略》之時已有流傳。東漢晚期人編訂《孔叢子》,有將之作為第十一篇而編了進去,所以其書又有《孔叢子》本。到了宋代,由于原單行之書亡佚失傳,于是宋人又從《小爾雅》中抽出,印出新的單行書,并仍依《孔叢子》之舊而題作孔鮒撰,這就是現(xiàn)存的《小爾雅》單行本。”[1](P53)
竇秀艷在《中國雅學(xué)史》中對于此問題有更為詳盡的說明,她認為《漢書·藝文志》中著錄的《小雅》即是《小爾雅》,漢魏六朝時《小爾雅》單行,唐時摭入《孔叢子》,北宋嘉祐四年(1059年)宋咸為《孔叢子》作注時,《小爾雅》即是其中一篇,遂一并作注。后單行本《小爾雅》亡佚不傳,至陳骙撰《中興館閣書目》,從《孔叢子》中輯出,是為今本《小爾雅》,即宋咸為之作過注解的《小爾雅》,故在陳振孫私家書目《直齋書錄解題》中說:“《小爾雅》一卷,《漢志》有此書,亦不著名姓氏,《唐志》有李軌解一卷,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蓋即《孔叢子》第十一篇也……當時好事者抄出別行。”[2](P86)是以《宋史·藝文志》著錄《小爾雅》為孔鮒撰。由于其單行本亡佚,后從《孔叢子》中輯出別行,其單行本也題作孔鮒撰。清人對《小爾雅》多有注疏之作問世,如:王煦《小爾雅疏》、胡承珙《小爾雅義證》、宋翔鳳《小爾雅訓(xùn)纂》、葛其仁《小爾雅疏證》等,是今人研究《小爾雅》的較好版本。
故現(xiàn)今學(xué)術(shù)界在《小爾雅》的源流問題上大致的意見是統(tǒng)一的,可概括如下:古本《小爾雅》→《孔叢子》本《小爾雅》①→后古本《小爾雅》亡佚→今本《小爾雅》。②
按:1.東晉李軌《小爾雅略解》是《小爾雅》曾經(jīng)單行的證據(jù)。
2.酈道元在《水經(jīng)注》卷六、卷十三分別引文《孔叢子》和《小爾雅》,亦可證明二書曾分別行于世。
3.《小爾雅>》當是在唐代方摭入《孔叢子》的。在唐代出現(xiàn)《孔叢子》與《小爾雅》二書相混言的現(xiàn)象。
二、前人征引《小爾雅》的情況
胡承珙《小爾雅義證·序》中對《小爾雅》的征引情況作過考證,概括為:“漢儒訓(xùn)詁多本《爾雅》,毛公傳詩,鄭仲師、馬季長注禮,亦往往有與《小爾雅》合者。”[3](P2)由此可見《小爾雅》被征引之早,且有漢一代均有征引。
據(jù)考,除胡承珙列舉的情況外,東漢許慎撰《說文解字》,晉杜預(yù)注《左傳》,晉郭璞注《方言》、《爾雅》,劉宋裴駰《史記集解》,北魏酈道元注《水經(jīng)》,隋唐間陸德明輯《經(jīng)典釋文》,唐李善注《文選》,司馬貞《史記索隱》,玄應(yīng)撰《一切經(jīng)音義》,孔穎達、賈公彥作《五經(jīng)正義》,宋邢昺疏《爾雅》等著作中均有對《小爾雅》的征引。
三、《小爾雅》的真?zhèn)巍⒆髡呒俺蓵鴷r代的考述
至清代,學(xué)者對《小爾雅》的真?zhèn)翁岢鲑|(zhì)疑。
戴震《書小爾雅后》:“《小爾雅》一卷,大致后人皮傅掇拾而成,非古小學(xué)遺書也……其解釋字義,不勝枚數(shù)以為之駁正。故漢時大儒,不取以說經(jīng),獨王肅、杜預(yù)及東晉枚賾奏上之,《古文尚書》、《孔傳》頗涉乎此。”[4](卷六P293)其弟子段玉裁贊同戴說,其觀點見于《與胡孝廉世琦書論小爾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亦說:“漢儒說經(jīng),皆不援及,迨杜預(yù)注《左傳》,始稍見徵引,明是書漢末晚出,至?xí)x始行,非漢志所稱之舊。”[4](卷三)
戴震的另外一種觀點:“或曰:‘《小爾雅》者,后人采王肅、杜預(yù)之說為之也。’”被臧鏞采信并予以發(fā)揮,其后臧鏞又引其高祖臧琳之說,確定為王肅偽造。其在《小爾雅徵文》中說:“余……考之有年,知郭璞之前,王肅是首引此書,余高祖玉林先生曰《孔叢子》為王肅偽作,而《小雅》在《孔叢》篇第十一。又自王肅以前,無有引《小雅》者,凡作偽之人,私撰一書,世之人未知之也,必作偽者先自引重,而后無識者從而群然和之,世遂莫有知其偽者矣。然則《小雅》之為王肅私撰,而《孔叢》書之由肅偽作,皆確然無疑也。”[2](卷三)
在清代有一種觀點與以上兩種說法截然不同,認為《小爾雅》即古小學(xué)遺書,而后采入《孔叢子》,此說以胡承珙、王煦、朱駿聲等為代表,持這種觀點的學(xué)者皆有《小爾雅》的注釋義疏之作傳世。
胡承珙在其《小爾雅義證自序》中也說:“…此可見《孔叢子》多刺取古籍,而所取之《小爾雅》,猶系完書,未必多所竄亂也。”[3](P1)
自清以來,學(xué)術(shù)界的觀點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胡樸安《中國訓(xùn)詁學(xué)史》“《小爾雅》一書,必謂是孔鮒所著,固無的鑿之證據(jù)。即謂今之《小爾雅》確系《漢志》所稱之舊本,亦嫌證據(jù)不充分。若謂如戴氏震所云:‘后人采王肅、杜預(yù)之說為之,’則確乎其非。《小爾雅》之訓(xùn)詁,與毛鄭賈馬相同者頗多,即曰掇拾群書而成,必不是采王肅杜預(yù)之說。至遲亦在許叔重之前,以《說文》所引之‘ ’字知之。《小爾雅》所作之人,雖不能確定,其則京在《爾雅》之后,許叔重《說文》之前也。”[5](P69)
(二)何九盈《中國古代語言學(xué)史》“《漢書·藝文志》載有《小爾雅》一書,不著撰人。成書于魏晉時代的《孔叢子》,內(nèi)有《小爾雅》一篇,題為孔鮒撰。清朝人考證的結(jié)果,認為《孔叢子》中的《小爾雅》是偽書。這種性質(zhì)的偽書,只不過作者‘偽’,時代‘偽’而已,如果我們不把它看成是孔鮒的作品,把它放在魏晉之前的東漢末年來處理,它就不‘偽’了。”[6](P52)
(三)濮之珍在《中國語言學(xué)史》“《漢書·藝文志》記載《小爾雅》一卷,既沒有作者名氏,即使是古代傳下來的書,也很難確定這本書就是孔鮒所作。若是說王肅偽造,也不大可信,因為書中與《鄭志》合者甚多……《小爾雅》也不是掇拾王肅、杜預(yù)之說而成書的,因為《說文》已引《小爾雅》‘ ,薄也’。總之關(guān)于《小爾雅》作者,還是清戴震等證的是后人纂輯而成,較為合理。”[7](P166)
(四)黃懷信在《新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三則》之《〈小爾雅〉提要》 “《小爾雅》1卷,舊本或題孔鮒撰。考《漢書·藝文志》”《孝經(jīng)》類“有《小爾雅》一篇,無撰人。《隋書·經(jīng)籍志》及兩《唐志》均有李軌解《小爾雅》1卷。其書唐末五代間已佚。今所傳者,乃宋人自《孔叢子》抄出別行者,固有孔鮒之題。然作為《孔叢子》第十一篇之《小爾雅》,實即漢世相傳之舊也。其書作于漢成帝間,作者據(jù)考當為孔安國曾孫、玄孫子立、子元父子。平莽間孔氏編《孔叢子》,以其同為孔家作品,而叢入其中……。”[1](P60)
劉鴻雁在《小爾雅綜論》中論及《小爾雅》的成書時代及作者,從后人征引、個別詞匯語法、大量新詞的補充、與《方言》比較四個方面推斷,《小爾雅》成書于西漢。再從方言詞匯角度做出推論,認為《小爾雅》的作者可能是西漢時的楚人。
竇秀艷在《中國雅學(xué)史》中:“至于《小爾雅》的作者到底是誰,今已無從考證。但從《小爾雅》所載內(nèi)容上跨先秦下迄魏晉、《漢志》著錄于《爾雅》之后,晉李軌曾為之注解、魏晉唐宋學(xué)者征引不斷及隋唐史志著錄等情況看,《小爾雅》大約產(chǎn)生于秦漢間,至少不晚于西漢中期,東漢以后,不斷有人增益。”[8](P6)
四、對以上幾種舊說的初步檢討
對于胡樸安先生所說“《小爾雅》一書,必謂是孔鮒所著,固無的鑿之證據(jù)”,不能因為今本《小爾雅》采之于《孔叢子》,就認定《小爾雅》的作者是孔鮒。再者,據(jù)現(xiàn)代學(xué)者考證,認為《孔叢子》亦非全然出自孔鮒之手。先是黃懷信認為《孔叢子》系仲淵最后編訂,時間推定在西漢桓帝永康元年(167)至靈帝建寧元年(168);趙東栓、孫少華考證結(jié)論為《孔叢子》最后編修時間在魏黃初二年(221)左右,孔羨是《連叢子》下的作者及《孔叢子》全書最后的編訂者;而楊軍則認為《孔叢子》其書的史料價值和學(xué)術(shù)品位宜在全面審核的基礎(chǔ)上重新定位,他認為《孔叢子》的前六卷出自孔鮒之手,第七卷為東漢延光三年(124)孔氏后裔補綴,等等說法,不一而足。
又《孔叢子》一書的真?zhèn)我嗖豢刹槐妫瑮钴姷目捶ㄝ^為可信,他說:“《孔叢子》中孟子與子思四段對話是杜撰的。《孔叢子》一書中《雜訓(xùn)篇》的內(nèi)容,以至《居衛(wèi)篇》、《巡狩篇》、《公儀篇》、《抗志篇》所載子思的言論,其真實性值得懷疑。與此相聯(lián)系,以《孔叢子·雜訓(xùn)篇》等五篇作為主要來源之一的《子思子》一書的價值也應(yīng)受到懷疑。”[9](P50)
胡先生認為“即謂今之《小爾雅》確系《漢志》所稱之舊本,亦嫌證據(jù)不充分。”現(xiàn)在已經(jīng)證明,今本《小爾雅》系南宋陳骙從《孔叢子》中輯出別行,胡先生之說概非無見。
以上主要列舉了現(xiàn)今學(xué)界關(guān)于《小爾雅》的幾種代表看法,但關(guān)于《小爾雅》的作者及成書時代均存在紕漏,胡樸安、何九盈、濮之珍、竇秀艷等人均是采取中允的看法,不偏不倚。黃懷信則依據(jù)孔子世系推斷《小爾雅》的作者,個人認為,《小爾雅》托名孔鮒,其作者恐與孔氏族人沒有多少關(guān)系,黃懷信所認為的《漢志》著錄《小爾雅》于孝經(jīng)類,《隋志》入論語類,而后摭入《孔叢子》,故斷定其為孔氏族人所撰的做法有失省慎。《隋書·經(jīng)籍志序》:“《爾雅》諸書,解古今之意,并五經(jīng)總義,附于此篇”,《隋志》認為《爾雅》之類的著作是用來解經(jīng)明義的,故收錄于論語類,其目的在序言中交待的很清楚。而劉鴻雁關(guān)于方言詞匯角度作出推論認為其作者是西漢時的楚人,因其只是出列數(shù)據(jù),不知其詳,但其舉例《史記·陳涉世家》也可商榷,《說文》:“夥,齊謂多為夥”,而不是《史記索隱》所認為的“夥”為楚人方言,《說文》較《史記索隱》更近于《史記》問世的時代,故應(yīng)更可信。黃懷信關(guān)于詞匯的相關(guān)統(tǒng)計亦與劉鴻雁之結(jié)論有出入。他認為:“《小爾雅》所收釋的詞語,有40%以上可釋于《三禮》,30%左右可釋于《左傳》,近20%可釋于《詩經(jīng)》中語,近10%為《尚書》中詞語,”[1](P40)并說《小爾雅》是以關(guān)西及秦晉間的方言作為通語而釋他地方言的。《小爾雅》收釋經(jīng)典之詞,以通語釋方言,這是每種辭書都必須做到的。至于馬端臨《文獻通考》中引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作:“楚孔鮒撰”,恐是因有記載孔鮒曾做陳勝的博士,陳勝、吳廣起義建立的是“張楚”政權(quán),故《郡齋讀書志》有“楚孔鮒”之說。何九盈在《中國古代語言學(xué)史》中有《爾雅》星野分域之說,而《小爾雅》作為第一部廣雅之作,無補秦、楚之分野,若其作者為楚人,兩廂恐難照應(yīng)。
《二十五史補編》收有孫德謙《漢書藝文志舉例》,其中之一為“不知作者例”,其引《論語·子路篇》說:“子曰:‘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說,如果以強不知以為知,那么必有穿鑿附會之弊,對于我國目錄家們,對于書無作者姓名者,往往闕之,他認為這是一種正確的治學(xué)態(tài)度,對于后人的對待疑問的妄加論斷的做法甚為痛惜。所因此,在現(xiàn)今資料稍嫌不充分的情況下,我們對于《小爾雅》的作者的推論及考證應(yīng)采取省慎的態(tài)度,以俟有更多的材料的發(fā)現(xiàn),現(xiàn)今闕疑,不失為一種嚴謹?shù)膽B(tài)度。
五、從《小爾雅》之《廣義》、《廣名》看其釋義方式及特點
筆者據(jù)中華書局1998年版胡承珙《小爾雅義證》及文淵閣四庫全書版《小爾雅》作了相關(guān)統(tǒng)計,《小爾雅》大字1909字,加上小字共計2012字,收釋條例373條,均與傳統(tǒng)看法有出入。前已述及《小爾雅》所收釋的詞語,有40%以上可釋于《三禮》,30%左右可釋于《左傳》,近20%可釋于《詩經(jīng)》中語,近10%為《尚書》中詞語,故筆者選取《廣義》、《廣名》兩篇來探討《小爾雅》訓(xùn)詁術(shù)語及訓(xùn)詁方法的問題。
1.關(guān)于《廣義》、《廣名》兩篇訓(xùn)詁術(shù)語的使用情況:在《小爾雅》的《廣義》、《廣名》兩篇中,其術(shù)語主要有三個,即“謂之”、“曰”、“也”,其中在《廣義》篇中,“謂之”使用5次,“曰”使用9次,“也”使用3次;在《廣名》篇中,“謂之”使用13次,“曰”使用3次,“也”使用2次。
“謂之”不僅可以釋義,而且還用以區(qū)分同義詞或近義詞間的細微差別,使用“謂之”這一訓(xùn)詁術(shù)語,被釋的詞放在后面,如“非分而得謂之幸”、“詰責(zé)以辭謂之讓”。
“曰”的作用與“謂之”相似,其在《廣義》、《廣名》兩篇中多用于釋義,如“請?zhí)熳用晃纯梢云菹韧酰堉T侯命曰未可以近先君,請大夫命曰未可以從先子”。
“也”字如數(shù)字連釋,則前數(shù)字之也可省,其末字釋語之也不可省,若沒有必系缺文。則可知“也”字除了作為釋語詞綴,還可以用于古籍文獻的校勘,用以校補缺文。另其有“某,某1也。某2也……”等格式,則屬于一字之意不足盡,或者是展轉(zhuǎn)相釋。
《廣義》、《廣名》兩篇是《爾雅》原書所未有的,其中《廣義》收釋一些專指、較特殊的語詞,多與儀禮、禮節(jié)有關(guān);《廣名》多載有關(guān)疾病、喪葬、丘墓之事。
2.編排特點:劉鴻雁在總結(jié)《小爾雅》的編排特點時,特別舉例《廣名》,她說:“《廣名》于疾喪丘墓之事,援引最詳”,這一篇對被釋詞的排列儼然講述了喪葬的整個過程:從生到祈命,再到備棺、助喪之事。先總述埋柩被稱之為“”,具體而言,埋柩之坑被稱為“池”,挖墓穴叫做“竁”,下棺叫做“窆”,積土蓋棺被稱為“封”,封后的土包叫做“冢”,而冢所在的墳地叫“塋”,未成年即死去的人稱之為“殤”。《廣名》對于詞語的分類體系統(tǒng)一,井然有序。
六、結(jié)語
關(guān)于《小爾雅》的源流演變,學(xué)術(shù)界多已認同,其古本、《孔叢子》本、輯本的演變脈絡(luò)是清晰的。再輔以前人征引情況來看,《小爾雅》當是古小學(xué)遺書。自清儒以來,對《小爾雅》的考究漸多,關(guān)于其作者和成書時代有日趨考實的傾向。筆者認為在目前證據(jù)尚不成熟的條件下,應(yīng)采取謹慎的態(tài)度,不應(yīng)坐實,如此,才算是嚴謹?shù)膶W(xué)術(shù)態(tài)度。
注釋:
①《孔叢子》援引《小爾雅》作為其第十一章,是為《孔叢子》本。
②南宋陳馬癸又從《孔叢子》中輯錄出今本《小爾雅》。
[1]黃懷信,古文獻與古史考論[M].濟南:齊魯書社,2003.
[2](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胡承珙,小爾雅義證[M].北京:中華書局,1998.
[4]戴 震,戴震文集[M].北京:中華書局,1990.
[5]胡樸安,中國訓(xùn)詁學(xué)史[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8.
[6]何九盈,中國古代語言學(xué)史[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6.
[7]濮之珍,中國語言學(xué)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竇秀艷,中國雅學(xué)史[M].濟南:齊魯書社,2006.
[9]楊 軍,《孔叢子》考證[J].蘇州科技學(xué)院學(xué)報,2005(04):49-51.
[10]孫德謙,漢書藝文志舉例[M].北京:中華書局,1957.
[11]宋 琳,《小爾雅》綜述[J].古籍整理研究學(xué)刊,2004.
[12]劉鴻雁,《小爾雅》綜論[D].銀川:寧夏大學(xué)碩士論文,2003.
[13]劉鴻雁,《小爾雅》補證[J].延安大學(xué)學(xué)報,2005(06):110-112.
[14]永 瑢,四庫全書總目[M].北京:中華書局,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