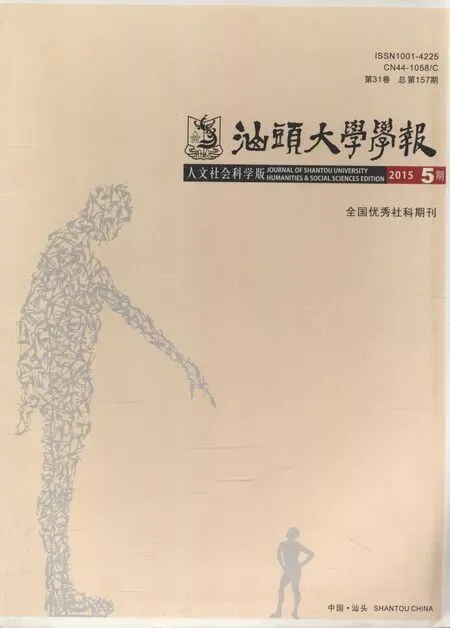論未成年犯非刑罰處遇措施的優先性——基于《刑法》17條第四款的刑事政策評析
喻浩東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北京,100088)
論未成年犯非刑罰處遇措施的優先性——基于《刑法》17條第四款的刑事政策評析
喻浩東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北京,100088)
《刑法》第17條第四款規定的針對免于刑事處罰的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的兩種處遇措施,應當優先于刑事處罰而成為應對未成年人犯罪的首選辦法。具體在家庭管束中應防止家庭本身的問題對未成年犯帶來的不利影響,不適宜由家庭管束時應交由政府收容教養。在收容教養方面也應制定相應的法律來規范其執行和監督,以使其促進未成年犯受到良好教育,重返社會。建議未來單獨制定一部包含實體和程序規范的應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法律,以給予未成年犯特殊的保護。
未成年犯;家庭教育;收容教養;處遇措施
一、《刑法》17條第四款之疑問
我國《刑法》第17條第四款規定,因不滿16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他的家長或者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這是我國刑法總則對于未達到完全刑事責任年齡的未成年人犯罪免于刑罰后的處遇措施。從字面意思來看,對于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犯罪,若免于刑事處罰,則有兩種處遇措施,一種是交付他的家庭繼續來管束和教育,一種是政府動用自身力量、通過限制自由的方式教育未成年犯、幫助其重新做人、回歸社會。從處遇措施選擇的順序上來看,顯然本款的語法解釋為,優先交付他的家庭來管教,而在某些“必要的時候”才會由政府親自來收容教養。結合我國當前對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1)注重保護、預防為主;(2)“教育、感化、挽救”和“教育為主、懲罰為輔”(以下簡稱“六字方針與八字原則”)——筆者擬在此語境下對本款的規定提出如下三方面問題:
其一,定位問題:本款的處遇措施僅僅作為因不滿16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替代措施,其地位是否較之刑事處罰顯得不適?也即,出于對未成年犯主要是保護而非懲罰的立法目的,那么本款的處遇措施是否應優先于刑事處罰而成為解決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問題的首選辦法,而非根據現行法解釋為次要辦法?
其二,適用問題:首選“家長管束”或“家庭教育”的方式作為處遇未成年人犯罪的措施是否在任何情況下都顯得合適?基于矯正未成年犯及特殊預防的刑事政策的角度,適宜在“家庭”進行管束教育的合理條件是什么?(“家庭”是否會在某些情況下并非矯正未成年人的理想場所?)那么如果“家庭”不適宜作為矯正場所,政府又應在何種“必要的時候”介入進來,親自處理未成年人犯罪的矯治與預防事務呢?
其三,立法問題:僅僅在刑法總則“刑事責任年齡”中規定針對未成年人應對何種犯罪行為負責、刑事處罰原則及免于刑罰的處遇措施,是否能足以貫徹當前我國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指導思想,將對待未成年人刑事犯罪與對待成年人犯罪區別開來、合理對待未成年人犯罪問題?也即,我國大陸是否需要單獨出臺一部特別處理未成年人犯罪問題的法律,以獨立于《刑法》和《刑事訴訟法》,規定未成年人犯罪的預防、處理等刑事實體及程序?
筆者將在我國當前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包括預防和處理政策)語境下,參照聯合國關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系列刑事司法官方文件,對《刑法》17條第四款的規定之適用及修法問題作出評論,以求得我國關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司法和立法能盡量與國際接軌,符合當代國際刑事法律解決未成年人犯罪問題的理念與精神。
二、未成年犯非刑罰措施的優先適用
(一)條款其法條地位不甚合理
“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犯罪免于刑罰后的處遇措施”,規定在《刑法》總則第二章“犯罪”、第一節“犯罪和刑事責任”下的第17條第四款,其地位不甚合理。本款的處遇措施,按法條的體系解釋來看,只能屬于次要于刑事處罰的第二位的處理規則,然而這與應當對“犯罪的未成年人”教育和保護的刑事政策相違背。因為如果按照本條的規定,對于不滿16周歲的人犯罪的,要先參照成年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予以定性處罰,其中免于刑事處罰的才適用本條第四款的規定。不論是當前我國關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還是國際上已簽署的一系列處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文件,都將“刑事處罰”作為解決問題的最后手段,這也是“刑罰謙抑性”在未成年人犯罪問題上的具體體現。例如聯合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利雅得規則”中一般原則第3條提到“青少年不能僅僅看成社會化或者社會控制的對象或客體”①原文為“Young persons should have an active role and partnership within society and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as mere objects of socialization or control”.United Nations Guidelines for the Prevention of Juvenile Delinquency(The Riyadh Guidelines),這說明對待青少年犯罪的處遇措施,應當以青少年為主體,盡量以促進主體的健康成長為目的制定法律規則;我國臺灣地區處理未成年人犯罪問題的單行法律——“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一條(立法目的)就規定,為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調整其成長環境,并矯治其性格,特制定本法②臺灣地區“少年事件處理法”(公布日期,1962年1月31日,修改日期,2005年5月18日)。;而《聯合國保護被剝奪自由少年規則》中一般原則的第一條也規定,少年司法機構應當秉持保護少年的合法權利及安全、促進其身心健康成長的宗旨。監禁措施應當具有最后手段性③原文為“The juvenile justice systemshould uphold the rights and safetyand promot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well-beingofjuveniles. Imprisonmentshould beused as alastresort.”。《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又稱“北京規則”)則更加明文強調“應酌情考慮在處理未成年犯時盡可能不提交下面規則14.1中提到的主管當局正式審判”④《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準側》第二部分“調查與檢控”第11條(11.1)應酌情考慮在處理少年犯時盡可能不提交下面規則14.1中提到的主管當局正式審判。14.1少年罪犯的案件未(按規則11)轉送觀護機構時,則應由主管當局(法院、仲裁、委員會、理事會等)按照公平合理審判的原則對其加以處理。。這些規則的出臺都說明,對于未成年人犯罪(或少年犯罪)的處遇措施,應以刑事手段作為最后訴求,而首先應以非刑罰的教育、管束和矯治等為合理措施,以保護這個特殊群體的身心健康,促進他們回歸社會。
這一做法背后的正當性理由,在于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本質上的差異,進而導致對未成年人犯罪的處理方法應當區別于成年人。首先,未成年人和成年人有著根本性的差別:生理年齡劃定了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之間的不同的“本性”,例如未成年人大多處于成長的“反叛期”,比較希望獨立自由,自我意識較強,但做事時往往不夠成熟冷靜,意氣用事,激情沖動,思考問題并不周全審慎。這種特殊本性決定了未成年人在“需求”和“知情意行”方面與成年人不同。隨著年齡的增長,人的社會危害行為就越有可能被稱為是一種“惡”,到了青春期人所出現的特定的身心變化和越軌行為,就可能被社會認定為可以用法律來進行約束和訓誡——這是必須得到理解的少年司法的生物學基礎。[1]其次,成年人犯罪往往是基于理性選擇而對社會的一種“自覺性反抗”,未成年人犯罪往往是未成年人成長過程中的一種伴隨性的“自然現象”,是未成年人在不良生活環境和尚未發育成熟的身心條件的雙重影響下的被動選擇,而不完全是自由意志選擇的結果[2]。另外,從未成年人犯罪的英文單詞“Juvenile Delinquency”和成人犯罪的英文單詞“Crime”來看,也深層次體現了法律界對于這兩種犯罪定義的有意區分、差別對待:第九版布萊克法律詞典對前者的定義是“未成年人的反社會行為,特別是可能參照成年人標準被判定為觸犯刑法的行為,但這種行為只能用專門適用于未成年人的法律來懲罰”①原文為“juvenile delinquency.(1816)Antisocial behavior by a minor;esp.,behavior that would be criminally punishable if the actor were an adult,but instead is usu.punished byspecial laws pertainingonlytominors.”Black's Law Dictionary(9th ed.2009), juvenile delinquency.。
因此,《刑法》第17條第四款所規定的刑罰之外的處遇措施,應當擁有其優先于刑事處罰的法律地位,也即,筆者建議至少在《刑法》修改時將此條款獨立出來,作為單獨一條予以規定,并且明確規定非刑罰的處遇措施是針對未成年人犯罪所應當優先采用的。
(二)非刑罰處遇措施的解釋及商榷
在17條第四款中,所謂“責令”,是司法機關在作出對犯罪未成年人免于刑事處罰的判決后發出的、對該未成年人家庭應當對其加以管束和教育的責成和命令;“家長”在這里是指“對孩子進行生養、監護、教育和作出適當決定”的孩子的負責人[3]。“管教”則是管理和教育,這里更多指在孩子作出偏差行為時對其予以制止和教導。實際上,這里使用“責令“一詞,其潛臺詞為對未成年人家長或監護人設立強制義務,或者是對其沒有履行好管教義務的一種懲罰,這樣解釋恰恰可以反映“責”字的含義。不論這里“責令”一詞的使用是否適當,在未成年人犯罪免于刑罰后,司法機關首先想到的是對其家庭科處“義務”,這一點值得商榷。固然“家庭保護構成了中國未成年人犯罪防治的第一道防線”,[4]然而除家庭以外,社會、社區以及自然環境等其他因素也是導致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原因,不能說這一“義務”就一定得科處于涉案家庭。另外,對涉案家庭“科處管教義務”是否在任何情況下或者大多數情況下都合理,仍然是個問題。關鍵是,萬一涉案家庭本身就是有問題的,并且經過調查分析確定這些問題正是導致該未成年人犯罪的深層次原因,或者家庭的再次管束只會“火上澆油”,不僅不能正確地矯治未成年犯,反而增加其人身危險性、阻礙其重返社會,這時司法者還能對涉案家庭“科處義務”嗎?這樣做不是“無效率”的徒勞之舉嗎?
這里我們必須反思“家庭”對于“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所可能存在的不利影響,尤其是家庭本身出現問題如“家庭暴力”、“父母離婚”、“父母任何一方婚外情”等等導致家庭結構不穩定和可能深刻影響未成年人成長的負面因素。社會學習理論認為,犯罪行為和其他行為一樣是經由學習之方式得來,而觀察模仿是一個很重要的學習過程,特別是青少年正處于人格塑造時期,若接觸越多暴力性質的訊息,模仿學習暴力行為的機會會更多。僅目睹家庭暴力仍會使孩子學習到暴力行為,甚至影響他們對男女關系的態度,孩子長期承受家庭暴力的創傷及壓力,不僅無法學習到正向的人際及兩性互動關系,更會養成用暴力解決問題及處理壓力的模式,容易也成為施加暴力者[5]。有關研究發現,曾經目睹父母間暴力的幼年經驗,也與配偶間的攻擊有關,幼年時曾遭受暴力的男性,在長大后比沒曾遭過暴力的男性更常容易攻擊配偶。因此,若家庭本身存在諸如家暴這樣的問題,那么孩子長大后犯罪的概率就自然升高,且把犯罪后需要矯治的孩子再責令其家庭進行管教,則孩子又會陷入暴力的惡性循環中,矯治、教育則無從談起。另外,家長及監護人對孩子管教方式的不當,也會引發孩子實施偏差或犯罪行為。為了更好地說明上述問題,筆者引用一則我國臺灣地區發生的案例作為輔證:
少年XXX,2011年4月的某日下午,在隔鄰之鄉公所前行竊壹部自行車代步,失主報案后,警方透過路邊監控器畫面循線查獲到少年,移送少年法庭后,因其無前科且犯行實屬輕微,法官裁定責付交家長帶回,等待后續的調查、審理。一個星期后的某日半夜,少年又在住家附近的便利商店內竊取戰斗陀螺側背包,被店員當場查獲而報警處理,再度移送少年法庭后,法官以少年再犯、責付顯不適當為由予以收容,經調查、審理后,裁定少年交付保護管束,并于同年8月開始執行。[5]
該案負責調查的人員事后發現,該少年的父母雙方十六七歲就結婚,婚后吵吵鬧鬧多年,終于在少年犯案前3個月時協議離婚,父親為少年的親權人,家中事務多由祖母負擔,雖然家庭收入尚可,但父母親工作屬起早摸黑,根本無法有效管教少年。另外,調查人員了解到,該少年從小被父母丟來丟去,且一不聽話父親就會打他比打狗還重,會用木棒、皮帶、水管甚至椅子拿起來就砸,少年常被打得全身是傷。而在對該少年的管束上,祖母可能盡到了最大義務,然而其經常以“直接關掉少年喜愛之電腦”的方式來約束他,不僅沒能管住,反而造成少年對于祖母的氣憤和討厭。如此看來,(1)家庭暴力代際傳遞和父母離婚的不穩定性影響,(2)家庭管束方式的不當,是該少年犯罪行為的重大影響因素。根據犯罪學一般化緊張理論(a general strain theory),偏差或犯罪行為經常是一種調適緊張的過程,而緊張的來源主要來自三個方向,其中之一是當個人失去生活中正向的刺激時,例如生活中喜歡的人、事、物消失、離去或是被剝奪時,都會對個人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而導致緊張及憤怒的情緒產生,此時若個人無法以正當的宣泄方式面對這些因素,便容易出現犯罪等方式作為主要的反應模式[5]。因此,對于該少年,臺當局司法官最終將其交付給保護官收容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可以期待其促進該少年的矯治。
那么,對于17條第四款前半段而言,應當怎樣適用才合理呢?筆者認為,法官要決定是否將犯罪未成年人交付“家庭”教育之時,應提前做好該未成年人的家庭狀況、社區狀況的詳細調查。在上述案例中,司法官對于該少年的處遇決定是基于“責付顯不適當”也即對家庭再教育的可能性否定之后作出的選擇。而之后保護官在執行保護管束之前,也根據審前調查結果暫定了處遇目標,并在執行中一直對該少年的家庭予以持續的關心和關注。其實,我國大陸地區的司法實踐并不缺乏這樣的社會調查制度:以北京市崇文區法院少年法庭的探索為例,該法庭的“關愛工程”有所謂的“兩個延伸”即審前社會調查與判后幫教安置,審前調查即聘請具有相當法律知識和社會工作經驗的司法助理員作為專職社會調查員,并制定《社會調查提綱》,社會調查員根據《社會調查提綱》對涉案少年的犯罪信息與個人情況的調查,作為對犯罪少年進行個別化量刑的參考[4]。筆者以為,這樣的好經驗可以在全國的少年法庭試點和推廣,且不光將調查結果作為個別量刑的參考,更作為對未成年犯采取處遇措施的參考。刑事程序上,新《刑事訴訟法》增加的第268條規定了“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社會調查的規定”[6],這也為推行這種做法提供了程序上的依據。如此,司法機關和政府有關部門通過參考調查結果,結合未成年人犯罪的具體情況,理性地作出決定是值得期待的。
但這僅僅是事后解決未成年人犯罪問題的思路,為了更好對未成年人犯罪進行一般和特殊預防,還需要從根本上解決“家庭”的問題。德國刑法學大師李斯特曾說“最好的社會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①原文為“…perhaps the most effective and best way to significantly reduce juvenile crime and delinquency would be to strengthen and upgrade the quality and stability of marriages in homes where there are children.”,筆者在這里要改寫為“最好的家庭政策就是最好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利雅得準則》第12條寫道:正因為“家庭”作為一個核心單位要對孩子的初始社會化過程負責任,因此需要政府和社會的力量來努力保護家庭的完整,以及家庭的持久①原文為“Since the family is the central unit responsible for the primary socialization of children,government and social efforts to preserve the integrity of the family,including the extended family,should be pursued”.。而當家庭本身的不良因素造成孩子的不健康成長,或者家庭環境不再適宜孩子成長時,《利雅得準則》第16條又寫道,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和設立一些項目,讓家庭成員了解家長(應有的)角色和義務,這一做法基于孩子的發展和孩子的照顧②原文為“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and programmes developed toprovide familie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about parental roles and obligations as regards child development and child care”.。我國大陸地區目前沒有這樣的類似措施和項目,但臺灣地區司法實踐中已經有了模范。在上文所述案例中,保護官針對案少年所暫定的處遇目標中一個方向便是,鼓勵案父參加親職教育課程,提升其教養能力。雖然執行過程中遇到案父的消極對待和抱怨,但少年問題的嚴重性讓案父逐漸意識到了自己的責任,保護官也一直在協助案父認識自己在教養方面的困境,并提供其有效的親職技巧訓練;另一方面,保護官也計劃增加案父對于精神疾病及相關治療的認識,以協助少年未來的就醫及人格正向發展。從這一實踐案例可以看出,未成年人犯罪的處遇和再預防,的確需要家庭、社會和政府多方的共同關注和持續努力,任何一方都需要認真地對待和切實地履行自己的職責。筆者以為,我國大陸地區有條件的少年法庭可以試學習和推行這樣的好經驗,最好是立法機關可以出臺單獨的法律法規將親職教育等措施法定化,這樣執行起來有一定約束力,不至于使這種做法流于形式。
(三)政府干預的必要性
若“家庭”這個力量難以應對未成年人犯罪問題時,政府的干預就顯得必要了,它充當了“第二家長”的角色。《刑法》17條第四款后半段規定了“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筆者覺得這里的“也可以”使用得不甚恰當,仿佛讓人看到政府保護的不主動和不積極,政府恰恰應當在“必要的時候”主動積極地履行自己的“教育、感化、挽救”職責。當然,“收容教養”這種方式是否一定有利于未成年犯的矯治和促進其健康成長值得討論。我國臺灣地區及國外政府對未成年犯的官方管束并未使用“收容教養”一詞,而是采用“保護管束”以及“安置教養”等詞語,但無論詞語如何變化,其共同本質在于——半監禁化,限制未成年犯的人身自由。因此,正如《利雅得準則》第五章“社會政策”第46條規定,將青少年安置教養的做法,作為最后的手段,而且時間應盡可能短,應把他們的最大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應嚴格規定允許采取此種正規干預的標準,并且一般只限于下述幾種情況:(1)孩子受到父母或監護人的傷害;(2)孩子受到了父母或監護人的性侵犯或身體上、精神上的虐待;(3)孩子受到了父母或監護人的疏忽、遺棄和剝削;(4)孩子因父母或監護人的行為而遭到身體或道德方面的危險;(5)孩子的行為表現對其有嚴重的身心危險,如采取非安置教養辦法,其父母、監護人或孩子本身,或任何社區服務,均無法應付此種危險③原文為“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youngpersons should be a measure oflast resort and for the minimumnecessaryperiod,and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young person should be of paramount importance.Criteria authorizing formal intervention of this type should be strictly defined and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situations:(a)where the child or young person has suffered harm that has been inflicted by the parents or guardians;(b)where the child or young person has been sexually,physically or emotionally abused by the parents orguardians;(c)where the child or young person has been neglected,abandoned or exploited by the parents orguardians;(d)where the child or young person is threatened by physical or moral danger due to the behaviourof the parents or guardians;and(e)where a serious physical or psychological danger to the child or young person has manifested itself in his or her own behaviour and neither the parents,the guardians,the juvenile himself or herself nor non-residential community services can meet the danger by means other than institutionalization.”。這一國際準則給政府干預設置了很多前提條件,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旦將未成年犯收容進特定場所,他們的人身自由就受到暫時的限制,處于半監禁的狀態,而人身自由是憲法賦予未成年犯的最基本的權利,因此限制其行使這一權利必然要受到諸多條件的制約。
我國的“收容教養”制度并未形成專門的成文法律,而是規定在一些陸續頒布的司法解釋和行政法規里,是我國特有的對未成年犯罪人進行收容、集中教育管理的一項制度。早在1956年2月7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內務部、司法部、公安部《對少年犯收押界限、捕押手續和清理等問題的聯合通知》中規定,對于13周歲以上未滿18周歲的少年犯,“如其犯罪程度尚不夠負刑事責任的,……,對無家可歸的,則應由民政部門負責收容教養。”“刑期已滿的少年犯,應當按時履行釋放手續,……無家無業又未滿18周歲的應介紹到社會救濟機關予以收容教養。”從該規定看,最初收容教養的性質帶有較強的社會救濟性質,而處罰性較弱。但是,從1979年刑法和1997年修訂刑法的有關規定看,收容教養具有明顯的懲戒處分性質,而社會救濟性趨弱;并且,收容教養制度早期由民政部門和社會救濟機關負責執行,而現在實踐中,執行收容教養的場所不一,各地差異很大。有的地方將收容教養人員送進工讀學校進行教育,有的則送進收容所,有的則是在少年犯管教所,還有的則是在勞動教養場所(勞教制度廢止前),但具體應在上述哪一場所執行,法律則沒有具體規定,也沒有出臺相關的法規和規章。如今,只能說《刑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是目前中國收容教養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據①《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39條也規定:“已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人犯罪,因不滿十六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其家長或者其他監護人加以管教,必要時,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但由于缺乏具體的規定,缺少配套的法規、規章,在實踐中出現了一些問題,影響到收容教養制度的正確有效實施。
首先,應明確未成年犯收容教養的性質,特別應將它區別于已被廢止的勞動教養制度,且在新時期應當重新對其內容作出闡釋。以未成年犯的矯治和重返社會為目的的收容教養制度,既不是上文中所說的社會救濟措施,更不是行政處罰或者保安處分。而勞動教養則更類似于保安處分措施,甚至可以稱為準刑罰措施,它更多地是立基于社會防衛思想,由于并非根據行為人罪責的程度來確定其嚴厲程度和期限,而是僅僅與符合比例的基本原則相聯系,因此可允許國家擁有比刑罰所允許的更多的干涉力[7];勞教制度被廢止,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其執行標準不具有罪刑法定性、卻與刑罰無法撇清關系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收容教養制度顯然不應該只是刑罰的補充替代措施,有學者結合《刑法》、《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為收容教養制度提供法律依據的條文規定,認為收容教養是國家在必要的時候對實施了犯罪行為而免于刑事處罰的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適用的強制性教育、保護和矯治措施[8]。但筆者仍然認為這樣定義收容教養不能夠充分發揮其制度性作用。基于上文中筆者對未成年犯與成年犯犯罪本質所作的區分,未成年犯不論是違法還是犯罪,都是其成長過程中因某些內在和外在因素所引發的不良行為,(即使是程度較高的違法行為)如果不加以約束,那么積惡成罪,不僅不能及時對違法的未成年人進行矯治和教育,而且也會給社會治安帶來極大的隱患。
其次,根據《刑法》第17條第四款的規定,對未成年犯適用收容教養,應當“在必要的時候”,而什么時候是“必要”的,《刑法》及其司法解釋、其他的法律法規都沒有規定,導致公安機關的自由裁量權很大,極其容易濫用職權。實踐中,家庭破碎、家長或監護人無法管教,案件社會影響較壞以至于群眾和受害人強烈要求政府收容教養,家庭、單位或學校因不想管主動要求收容教養,未成年犯重新違法犯罪的幾率大,或劣跡太多較難教育等等都是公安機關較常認為的“必要的時候”[9]。筆者認為,這樣的標準過于主觀隨意,且家庭、社會大多借此推卸責任,根本不應收容教養的最后都適用了收容教養。
筆者認為,參鑒《利雅得準則》“安置教養”的標準,以及考慮未成年犯自身、家庭、社區、政府各方面的因素,考慮“必要的時候”應包括以下幾點:
(1)未成年犯自身人身危險性較大,再犯罪幾率較大;其不愿與家庭成員接觸、共同生活;其自身本領欠缺,社會經驗不足,難以短期內適應社會。(2)家庭的經濟條件、家庭環境、家庭的教育條件等難以適應該未成年犯當前所需;家庭本身存在的對未成年人不利的影響,可能會阻礙其矯治和成長。(3)社區環境惡劣,未成年犯很難融入其中;社區不具備讓未成年犯進行社區服務和改造的項目條件。(4)地方政府自身(鑒于我國各地經濟條件的差異)應擁有足夠的財力、人力、特定場所和設施來收容教育未成年犯,相關工作有豐富經驗,能夠切實促進未成年犯的矯治和教育。(5)其他應當考慮的因素,等。
筆者認為上述實質標準應當在立法過程當中逐漸轉化為正式法律規定,讓“必要的時候”的適用有法可循,增強解釋的正當性和合理性。
再次,收容教養制度本身仍然存在諸多問題,亟需修改完善:如,應在實體法中明確收容教養的宗旨和目的,確立收容教養的基本原則、對象范圍,規定收容教養的條件和期限,在程序法中制定收容教養的司法程序,明確收容教養的執行場所,確定收容教養的管理方式等[10]。具體來說:
(1)要先明確收容教養是一種對未成年犯的保護處遇措施,而非刑事處罰、行政處罰,更非刑事強制措施,因此其宗旨和目的應當是為了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與最大幸福,教育、矯治和幫助未成年犯重返社會和健康成長。(2)收容教養因具有半監禁化性質,因此具有最后訴諸性,它不應當作為優先適用的處遇措施,政府針對未成年犯的教育矯治可以優先采取其他種類的替代措施。且收容教養本身也應擁有其他執行方式,如觀護、社區服務等等。(3)根據《聯合國保護被剝奪自由少年規則》第2條和第11條的具體規定,必須由司法機構而非行政機關來決定(監禁)執行的期限,不排除盡早釋放的可能性①原文為“The length of the sanction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the judicial authority,without precluding the possibility of his or her early release.”;被(暫時)剝奪自由的未成年人的年齡下限應當有法律明文規定②原文為“The age below which it should not be permitted to deprive a child of his or her liberty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law.”。因此,為了與之接軌,我國司法機關(少年法庭)應執掌收容教養的決定權,保證收容教養制度的依法執行,限制其在正當范圍內適用,且立法機關應當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規定收容教養的年齡下限(目前各地執行標準不一,有的定為12歲,有的14歲)。(4)收容教養的對象應不限于免于刑事處罰的未成年犯,而應包括實施不良行為或違法行為的未成年人以及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未成年人。(5)收容教養的一系列正當程序應當在程序法中加以詳細規定,以保障司法機關的決定和執行。同時也方便社會大眾對之予以監督。(6)收容教養的場所應特定化,不得與刑事處罰、行政處罰的場所相混同,在此特定場所也不得將未成年犯和其他違法犯罪人混合關押,以免“交叉感染”,反而給未成年犯以不利的影響。但場所的設置應多樣化、人性化,要考慮未成年人的心理特點、生活環境需求等因素。(7)收容教養的管理方式也應當考慮未成年人與家庭的接觸、便于其與社會環境相融合,因此不宜使用過多的警備,最好采取開放的管理方式。在收容場所,應當遵循教育和保護的目的,盡量要為未成年犯提供同等的教育課程、活動,促進其個人知識的學習和人格的塑造。
最后,除了《刑法》第17條第四款規定的兩種非刑罰處遇措施外,應當在法律中規定其他種類的(完全開放式)處遇措施。例如建立專門學校用于重塑未成年犯,組織特定社會機構、非營利組織對未成年犯進行教育矯治等,讓矯治措施更加多樣化,應探索更加符合未成年犯最大利益的處遇措施。
三、制定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處理法
基于未成年人犯罪與成年人犯罪“本質”的差異,其處遇措施應當另成體系。當前我國應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實體和程序法律法規,散布于《刑法》、《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刑事訴訟法》(2012年修訂版)等法律以及一些行政法規,而其中規定如收容教養這樣的處遇措施的也僅僅是法規中,法律層級顯得不夠。盡管這些已制定的法律中有很多條文試圖來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利,促進其教育和矯正,但與國際上應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做法仍有一定差距,保護力度不夠,理念上仍未將未成年人犯罪問題的應對政策與成年人犯罪相區分。筆者建議,在未來有關于未成年犯的矯正和教育制度逐漸完善、時機成熟之時,制定一部單獨的應對未成年人違法與犯罪行為的單行法律,其中包括實體法和程序法的內容,將上述法律法規的合理成分收納進來,并且有機組合成一個完整的體系,讓違法和犯罪的未成年人得到特殊的教養與保護。這里我們尤其可以借鑒我國臺灣地區“少年事件處理法”制定的經驗,以及其當局司法機關實際處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事件的好的方法,理由在于,海峽兩岸骨肉相連,盡管經濟、政治、社會制度不同,但在風土、人文、歷史、環境等方面都具有相通之處,在刑事法律對話方面更因大陸法的傳統而有更多共同話語,因此借鑒其刑事立法和司法經驗最為合適。例如,制定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處理法時,可以參考臺灣地區《少年事件處理法》的結構,規定總則(立法目的、適用范圍、基本原則等)、審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司法機關、未成年人違法行為的調查和審理程序、保護處分措施的執行和監督、對不服司法處理的抗告和重新審理程序、未成年犯刑事案件的訴訟程序、附則等章節,并配套以明確的實施細則。
未成年人是祖國的未來,他們的最大利益與最大幸福是這個社會所應追求的重要目標。“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使當他們犯下錯誤時,我們也應以最大的寬容來教育和保護他們,刑罰手段“備而不用”、“最后使用”。
[1]皮藝軍.兒童權利的文化解釋[J].山東社會科學,2005(8):33.
[2]趙寶成.我國少年刑事政策現代化取向的實體法解讀[J].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2):17.
[3]Kevin Sidel.“Family Law and Juvenile Delinquency”[J]. Colorado Lawyer,2008(October).
[4]梁根林.當代中國少年犯罪的刑事政策總評[J].南京大學法律評論,2009(2):83-85.
[5]李自強.家庭暴力的代間傳遞:一位觸法少年的個案分享[J].亞洲家庭暴力與性侵害期刊,2013(2):123-128.
[6]冀祥德.最新刑事訴訟法釋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245.
[7]克勞斯·羅克辛.德國刑法總論教科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51.
[8]周雄.收容教養制度研究:刑法第十七條第四款之展開[J].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5(2):57.
[9]馬克昌.刑罰通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791-792.
[10]張蓉.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1:205.
(責任編輯:汪小珍)
DF393;DF612
A
1001-4225(2015)05-0018-08
2015-04-25
喻浩東(1992-),男,安徽寧國人,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專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