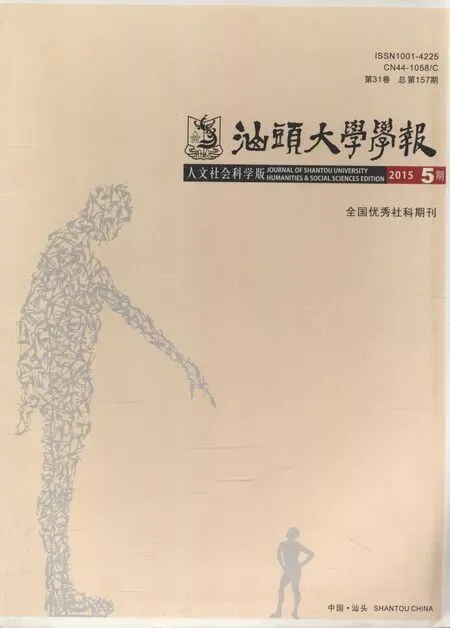關于“意義”的四種敘事——王安憶新時期小說創作的再解釋
王軍
(南京審計學院文學院,江蘇南京210029)
關于“意義”的四種敘事——王安憶新時期小說創作的再解釋
王軍
(南京審計學院文學院,江蘇南京210029)
新時期小說對于生存“意義”的探索非常豐富和個性化,而王安憶的“意義”自覺表現得尤其突出,在新時期的初期、中期和后期三個階段,通過對現實生活和時間意識的敏感把握,王安憶的小說建構出了四種關于“意義”的敘事:審視未來,反思傳統,追問性愛,探求純粹精神。從時間的視角來說,這四種“意義”敘事隱含了新時期小說的基本意義脈絡。
王安憶;新時期;意義敘事;時間意識
人類對自身生存意義的探究歷史由來已久,這一歷史在現代社會的推動下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人們逐漸認識到,“意義”不是一元的、絕對的,而是多元的、相對的,而且更具有現代意味的是,充滿困惑、迷失和自我否定的意義尋找過程,代替了尋找到某種意義這個結果,成為意義發現的典型符號。從這個角度說,新時期文學無疑很精彩地詮釋了這一現代特征,程文超曾經用“意義的誘惑”來總結這一時期文學批評的意義情結[1]。實際上,在整個新時期文學中,我們都看到了眾多作家在意義的誘惑下進行著多樣化的文學敘事,而王安憶的小說把個體的獨特性和時代的普遍性融合在了一起,給我們提供了一份發現新時期小說“意義”道路的范式樣本。
新時期的王安憶給人最深刻的印象,是其“視野開闊,能夠駕馭多種生活經驗和文學題材”,“多變的風格,并始終保持很強的創作活力”,[2]但是,王安憶對自己的“多變”卻另有一種表述:“評論家們說我是在求新求變。其實我覺得我的作品是隨著自己的成長而逐漸成熟。老老實實地一步一步往前走。如果說有變化那就是逐漸長大逐漸成熟,循序漸進。我并沒有像評論家說的那樣戲劇性地變化”。[3]局外人看到“求新求變”,自己卻只是“老老實實”,要對這個矛盾做出合理化的解釋,有必要追溯到一種現代性的現象和意識——在豐富的意義大世界中不斷尋找獨特的道路。正是因為這種意識的自覺存在,王安憶在新時期初、中、后三個階段,通過對現實生活和時間意識的敏感把握和執著探求,通過四種頗具代表性的“意義”敘事,完成了個體性和時代性的統一。
一、“向前看”及其自我審視
王安憶以“雯雯”系列小說在新時期初期的文壇獲得聲譽。與社會轉型狀態相呼應,新時期初期的文藝各領域都彌漫著一種“溫柔的感傷、憂郁和迷茫”情緒,并在文藝作品中“呈現為一條美麗的女性畫廊”,李澤厚把這一現象描述為“敏感主義”。[4]“雯雯”無疑也屬于這個女性家族里令人印象深刻的形象之一。《雨,沙沙沙》是個情節簡單的故事:在一個雨夜,紡織廠女工雯雯接受了一位男青年的幫助,他的溫暖治愈了雯雯在文革中經受的生活和愛情創傷,重新帶給了她生活的熱情,懷著對這個不再露面的男青年的期待,她放棄了和一個大學生組成家庭的可能。故事結尾寫的是雯雯在又一個雨夜中獨自前行:
她隱隱地但卻始終地相信,夢會實現。就像前面那橙黃色的燈。看上去,朦朦朧朧,不可捉摸,就好像是很遠很遠的一個幻影。然而它確實存在著,閃著亮,發著光,把黑沉沉的夜,照成美麗的橙黃色,等人走過去,就投下長長的影子。假如沒有它,世界會成什么樣?假如沒有那些對事業的追求,對愛情的夢想,對人與人友愛相幫的向往,生活又會成什么樣?①本文引用的小說作品,不單獨做注,都出自:王安憶《王安憶自選集》(五卷本).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小說是一個關于愛情的幻想,王安憶讓雯雯抒發情感時把“對事業的追求”、“對人與人友愛相幫的向往”堆積在一起,無疑有些溢出了小說的主題。但正是這些具有統一性的生活內容以及價值判斷構成了王安憶第一個小說階段的意義敘事:現實的煩惱沒有順理成章地帶來焦慮、痛苦或者沉重,無論有什么問題,都可以交給時間去解決,關鍵在于有“夢”,有了“夢”,人生就有了意義。
如果認同了“雯雯”對于意義的此種表達,那么我們就可以把“陳信”和“歐陽端麗”理解成“雯雯”在不同境遇下的化身。《本次列車終點》中的返鄉上海的男知青陳信,在愛情問題之外,還面臨著更加復雜的住房問題、家庭關系問題,后兩個問題的重要性實質上已經超過了愛情,所有的矛盾最后集中爆發了,故事也以陳信逃避式的出走而告終,但有意思的是,在此困境中陳信的精神卻突然出現了超越,他決心通過個人的思考來超脫這些眼前的煩惱,他樂觀地相信并等待一定會更加美好的未來:“他相信,只要到達,就不會惶惑,不會苦惱,不會惘然若失,而是真正找到了歸宿。”《流逝》的主人公歐陽端麗在身份上和雯雯、陳信完全不同,她是解放以前的大學生,嫁給了大資本家的大少爺,享盡榮華富貴,但是她和雯雯、陳信一樣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帶來的生活挫折和磨難,并在磨難中逐漸成長為一家人經濟和精神上的支撐。十年浩劫結束,公公落實了政策,房子回來了,錢多得用不完,孩子也長大了。但是對于歐陽端麗來說,重新回來的生活總是讓人覺得缺少一些什么東西。缺少什么呢?小說結束時,歐陽端麗決定保留自己在街道工廠的位置,伴隨這個決定的是文光的感慨:“有一個人,終生在尋求生活的意義,直到最后,他才明白,人生的真諦實質是十分簡單,就只是自食其力。……。這一路風風雨雨,坎坎坷坷,他嘗到的一切酸甜苦辣,便是人生的滋味。”
在這個階段,已經可以看出王安憶探索個人生存“意義”的自覺和執著,其“意義”敘事也是統一的,這幾篇小說都是寫經歷文革磨難并面對新生活時,人如何選擇并確定自己的價值。最值得注意的共同性是,小說最后都不約而同地讓主人公沉浸在關于人生意義的思考中,并選擇了一種朦朧的理想作為精神上的支撐。這種基于理想和信仰的意義闡釋,相當直接地呈現了新時期初期主流化的時間意識,在建國之后相當長時間里,“進化-革命”的觀念一直滲透在人們的思維和行為中,“社會向前發展,歷史不斷進步,挫折和困境只是螺旋式上升中的一支插曲”成為普遍性的潛意識,人們不需要思考,只需要接受這一切,并相信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對文革的否定也沒有從根本上動搖這種根深蒂固的慣性,“我們都想向前看,甚至來不及撫平身上的傷痕,就急著要把失去的時間追回來”[5]。在新意識形態“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召喚下,“進化論”的歷史思維方式繼續延續下來,引導了新時期初期文學,也包括王安憶小說的意義選擇。
把希望寄托于未來和“夢”,歷史性地構成了王安憶和新時期初期小說共同的意義基石,但是,這種意義敘事模式卻隱含著一種巨大的邏輯裂縫:在被否定的過去和蒼白的現實之后,如何能夠跨越性地到達一個完美的未來?在以往的革命小說中,這種邏輯鏈條是完整的,從過去(痛苦)到現在(斗爭和勝利)再到未來(美好)。而此時,物質的匱乏、精神的創傷、愛情、婚姻和人生的各種困境,構成了灰色的“現在”和“感傷、憂郁和迷茫”的敏感主義情緒,它們撕開和擴大著過去與未來之間的縫隙。要從這個環節起步到達“美好的未來”,不能依據邏輯,而只能依賴一種超自然的精神跨越,于是,我們看到了這種意義敘事的三個結果:首先,“未來”扮演的是現實替代物的角色,而不是現實的合理發展;其次,進化論歷史意識的延續也并非一種主體性的選擇,而更像是一種慣性,因為慣性,人們再一次把命運交給了未來,交給那個“夢”,這種剛從噩夢中出來又不得不走入一個新夢的歷史循環,使新時期初期小說中的“夢”意象失去了其在革命敘事中原有的強烈樂觀主義和英雄主義色彩,而帶有苦澀和虛幻的意味;最后,這個無法解決的邏輯裂縫也必然導致對“未來”的重新解釋。
在王安憶的小說中,關于未來的邏輯矛盾得到了細致的呈現,相對于《雨,沙沙沙》中雯雯對于“夢”的單純信奉,《本次列車終點》的陳信已經知道在“相信未來”時還“真該好好想一想”,《流逝》中的歐陽端麗也意識到了個人精神和未來選擇之間的矛盾,她決定繼續去街道工廠,然而“心里卻有點發虛”。阿格尼絲·赫勒曾經描述過“借助于未來而對現代性進行的合法化已經破產了”的過程[6],當陳信和歐陽端麗心中那種理想的堅定性正在悄悄潰散,那種可信賴、可托付的未來正在失去光芒時,我們也意識到了,未來所能承載的人生意義是脆弱的。王安憶在以“夢想”或“未來”設定意義道路的同時,也發現了這條道路的迷失和中斷,從“雯雯”到“歐陽端麗”,展現出王安憶對于信仰、理想、未來的思考開始復雜化,這意味著王安憶“意義”敘事第一階段的結束,也是她重新尋找新意義的起點。
二、“仁義”反諷和“傳統”失效
這個新起點來得很快,它就是寫于1984年的《小鮑莊》。評論家贊揚這篇小說突破了《流逝》之前的情感表達方式,顯示出了“在人生經驗與審美意識上的復雜化趨向”和“一種全面把握和駕馭生活的能力”。[7]小說也因為表現了對傳統文化的探討,被認為是“尋根文學”的力作。“尋根文學”是新時期文學中影響最為重大的一次文學思潮。它不僅提出了明確的文學主張,團結了一支非常重要的創作力量,而且“體現了與過去的文學傳統完全不一樣的審美經驗與美學境界”。[8]對于尋根文學核心特征的討論一直以來都非常激烈和豐富,而其中爭論的焦點是尋根文學與傳統文化的關系以及對傳統文化的價值判斷。相對而言,陳思和先生的觀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認為,尋根作家雖然寫作風格迥異,但是他們對傳統文化的肯定態度和理解,他們在“純潔祖國民族語言、恢復漢文化的意象思維,以及對完善傳統文學審美形式的追求上”[8]是同一的。
尋根文學對“意義”的敘事方式,帶有自覺的理論意識和把這種意識變成一種集體形態的強烈情感。不過,它和“進化-革命”敘事不同的地方是,它選擇的意義支點不是時間鏈條上“未來”那端,而是“過去”。這種反向的時間選擇呈現出與新時期初期大相徑庭的意義取向,讓人感覺到,“未來”所具有的寄托性意義在遭受懷疑的時候,具有強大生命力的“過去和傳統”就通過“意義倒逼”變成另一種精神源泉,線性時間在面對現實時使用了它自己的獨特邏輯。傳統文化在20世紀80年代人們心中展現出來的力量,既是現實的推動、呼喚,也是知識者的有意為之,韓少功的《文學的根》和阿城的《文化制約人類》這兩篇“尋根文學”的宣言都把文學乃至人類生存意義的指向明確在傳統或者民族文化上,但是無論是想通過“尋根”來擺脫當時的政治簡單化,還是試圖從西方獲得靈感,無論是僅僅要表達一種感情,還是設想一個理性現代的中國,最終這些意圖都落在“傳統”這一文化范疇上,使“傳統”這一文化范疇成為集體認同的“意義”焦點。
王安憶在“尋根文學”的高峰期寫出了《小鮑莊》,這篇小說的主題涉及到傳統文化中的“仁義”這一核心思想,正與尋根作家所呼吁的文學應該植根于傳統文化的土壤中相呼應,這也讓王安憶和《小鮑莊》極其自然地被納入到尋根文學的洪流中來。但是,僅憑這一點就認定王安憶和《小鮑莊》與尋根文學的同一化,并沒有真正把握住王安憶的獨特性。在王安憶的情感記憶中,知青生活、農村生活并不溫暖,而是帶有一種冰冷的個人感受,她在一封信件里寫道,文革之后將近十年的時間里,她一直不能認同其他知青作家對插隊生活的懷念:“我無法像很多人那樣,懷著親切的眷戀去寫插隊生活,把農村寫成伊甸園。”[9]至于原因,王安憶信里提到自己1983年在美國停留的幾個月時間:
或許也還因為去了美國數月,有了絕然不同的生活作為參照。總之,靜靜地、安全地看那不甚陌生又不甚熟悉的地方,忽而看懂了許多。[9]
后來王安憶多次提到1983年去美國參加“愛荷華寫作計劃”以及在美國游歷的經歷,但是她卻一直沒有清晰地闡釋出這段經歷給予她的巨大影響。那么,美國之行讓她看懂了什么?在將近20年后與張新穎的一次對談中,我們看到王安憶高頻度地使用一個詞來試圖說出自己那一個時期的文學思索,這個詞就是“意義”。那一年的王安憶似乎陷入了一個精神困境,她不停地問自己:寫作有什么意義,怎么讓自己寫的東西有意義?[10]有理由相信:意義問題,正是此時王安憶自覺地思考并看懂的中心問題之一。機緣巧合,尋根文學的出現填上了王安憶前期創作結束時的“意義空白”,把王安憶“意義”之路和“文化”一下子聯系在了一起。但是,這個意義的取向不是像大部分知青作家一樣把感情寄托在對那個“青春期”的懷念,也不是像很多尋根作家那樣重新用傳統的民族的文化來建立自己的精神認同,而是在一個東西方文化差異和對比中看到了中國傳統文化所具有的現代性缺失。
所以,王安憶在《小鮑莊》里試圖展現的不是“傳統”的魅力,而是通過對“仁義”模型及其死亡的描述,揭示了以儒家思想為正統的傳統文化的虛偽性。王安憶說,“撈渣是一個為大家贖罪的形象,或者說,這小孩的死,正是宣布了仁義的最后崩潰!許多人從撈渣的死獲得了好處,這本身就是非仁義”[11]。因此,《小鮑莊》雖然設計了一個“仁義榜樣”撈渣,但是撈渣周圍的一系列人物,包括鮑仁文、拾來、小翠、鮑秉德媳婦等的故事,卻建構起一個與“仁義小鮑莊”相對立的文化語境,這些包圍了主敘事的小敘事,不是在襯托和呈現主敘事的莊嚴,而是在消解主敘事的“仁義”道貌,其批判性撕裂了很多尋根小說追求的“古典歌謠式”的美學想象。王安憶傾注于《小鮑莊》中的意義取向,與被誤讀的《小鮑莊》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小鮑莊》被誤讀的原因各種各樣,很多人看到了“仁義撈渣”,而沒有看到“反仁義的小鮑莊”,看到了“仁義”的文字性表現,而沒有看到王安憶的“反諷”意圖,而也許更重要的是,很多人在認同乃至迷戀傳統的時候,忘記了“傳統”是一個復雜的宏大敘事,對于中國的現代性心理轉型來說,它也許難以承受其重。
《小鮑莊》代表了王安憶對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的基本立場,也展現出她對于尋根文學歷史觀和時間觀的另一種認知:傳統,尤其是儒家傳統,是否具有支持現代精神新生的能力?王安憶表現出了懷疑。在這一點上,王安憶和當時的很多尋根作家是可以區別開來的,她既沒有像阿城一樣對傳統拯救精神抱有幻想,也沒有像李杭育、賈平凹一樣對傳統的沒落唱出一曲挽歌,當尋根作家返身向后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精神資源、尋求生存意義的時候,王安憶卻毫不遲疑地拒絕了這種意義選擇。與第一階段不同,王安憶新時期中期的“意義”敘事集中于“傳統作為意義”的可能,而與第一階段相似的是,王安憶再次通過自己的獨特思考給出了否定的答案。
二、“性”和“純粹精神”:上下的兩難
時間作為一種線性的維度,其結構一般被分類為過去、現在、未來三個部分,這種帶有自然客觀狀態的時間意識在面對復雜的人類歷史社會和心靈世界時,顯現出了一定的蒼白性和扁平性,人類繁復的情感和意識創造出了簡單線性時間無法全面包容和有效描述的時間感。易水寒曾經總結了人類對于自身生存困境進行“突圍”的歷史,提出人類大致經過了宗教、理性、本能、傳統這四種途徑尋求意義,它們分別代表了向上、向前、向下、向后的時間方式。[9]這些時間意識的細致區分,豐富著時間的層次性,讓人類的感受得到更加精細的呈現。新時期文學以及王安憶的意義敘事,正是通過意義選擇的不懈探索,展現出了同樣豐富的時間意識。從這樣一個視閾,我們看到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王安憶從簡單線性時間中超越出來,她以非常熟悉和擅長的“愛情”主題自覺性走出了另一條意義道路,從而擴展了意義的可能性。她在一篇帶有回顧性的文章中寫出了她的思索:
我嘗試將愛情分成精神和物質兩部分:寫情書、打電話、言語都是精神方面的,而物質部分就是指性了。大概說來,我一九八九年寫的《神圣祭壇》《弟兄們》《崗上的世紀》就是想分別走精神或物質的路。《弟兄們》和《神圣祭壇》嘗試光憑精神會支撐多遠;《崗上的世紀》可以和《小城之戀》一塊看,它顯示了性力量的強大:可以將精神撲滅掉,光剩下性也能維持男女之愛。[11]
《小城之戀》寫得最早,也是王安憶較為滿意的一篇作品。王安憶對于愛情兩個部分的探討,可以從《小城之戀》算起。這部小說寫的是兩個無名的青年男女“她”和“他”的性愛故事。“這是兩個人的故事。我就想設計一個純兩人化的行為,那就是性了。”[10]小說的故事設計可以看成是王安憶所追求的“故事的邏輯性”的體現,在一連串的描述中,“她”和“他”逐漸成為兩個被排斥在整個群體之外的“異類”,他們因為練功方法錯誤而練壞了的體形,他們與其他人之間的割裂狀態,都在把他們推向一個只有他們兩人的封閉世界。劇團排演《艱苦歲月》最終拒絕了“他”,斬斷了他們進入正常世界的最后一條途徑,也使他們曾經朦朧的感情得到了一個契機結合并確定下來,他們只能就此進入這個被“性”所主宰的世界。然而,與其說他們被“性”所控制,不如說他們被一種“性的意義”所控制,他們有著與其身份不太適應的豐富的內心世界,使“性”成為他們的靈魂巨大動蕩的場所。他們相互體驗著“性”帶來的幸福和崇高,但是轉眼之間,他們又恐懼地感覺到了“性”的疲乏和骯臟,為自己不再純潔而悲哀和悔恨。他們之間的親近和搏斗,其實是他們心里無法認定“性的意義”所帶來的靈魂親近和搏斗。
小說不厭其繁地鋪敘了主人公游魂飄蕩、居無定所的狀態,也展現了作家心靈的深度介入,這一過程不僅屬于主人公,更屬于王安憶,那是一種把問題逼到絕路式的追問:對于個體而言,“性”的意義何在?“性”真的“可以將精神撲滅掉,光剩下性也能維持男女之愛”嗎?《小城之戀》似乎給出了相反的結論,小說的結尾描寫“她”生下一對雙胞胎之后,毅然斷絕了與他的關系,并且最后在“母愛”的肅穆與莊嚴中走向了純凈。《小城之戀》的“性”被母愛所否定,“性”曾經“近乎瘋狂地宣泄和放縱”,曾經容納了幸福和崇高,但此時卻構成了對性意義的自我消解,作為存在和意義支撐的力量也就此宣告失敗。王安憶對于“性”的探索,更加接近于一種“正名”,她否定了視“性”為羞恥的意義扭曲,也否定了以“性”獲取存在意義的可能。
如果說作為物質性因素的“性”代表了形而下生活的一種方向,那么,和性相分離的異性或同性之愛,則是王安憶設想的形而上精神最具現實意義的表現。在這相反的兩端,王安憶都走出了探索性的道路。但是,在把這兩種生活方向和意義追尋相聯結的過程中,和“性”這一本能因素相比較,沒有物質基礎的“精神”既顯示出了極端的純潔性,同時也顯示出由這種純潔性帶來的極端脆弱性。《弟兄們》寫了三個住在學生寢室里的女人,在許多徹夜不眠的夜晚,互相敞開心扉,通過一次又一次的討論,建立了一個精神同一體,對于她們來說,這種極端自由的狀態無疑屬于精神上的巔峰體驗,她們互相“喚醒”,這是“一生中最好的她們,最自由和最覺悟的她們”,她們也因此拋掉了一切性別負擔,轉換成了“三兄弟”。但是,對這個精神同一體不斷進行自我認同的過程中,讓它解體、消融的力量也如影隨形。老三首先在這個精神同一體上割開了巨大的裂縫,她回到了蘇北老家,回到了家庭,最重要的是她在精神上背棄了“三兄弟”的同一體,她對于男女關系的最后認識竟然是“自我”的不置可否狀態:“如果男女之間有愛情,那么自我被吞沒也是快樂和有價值的,而如果自我無法給人快樂,還會帶來破壞,那么要它有什么意義?”畢業之后,老二和老大分別在南京和上海生活,過了幾年她們才又一次相見,這是又一次精神結合的過程,她們又一次敞開心扉,共同推動她們之間純潔而高尚的友誼走向高潮,“這不像男女之間有情欲的推動,這全靠了理性。這是一個理性的、智慧的關系,這是人性的很高境界”。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她們的關系達到了極點的時候,老大的孩子從童車里摔了出來,眼角血流如注,老大的情誼綿綿剎那間卻轉化成對老二的仇恨,因為老二使她們陶醉在自己的友誼里而忽略了孩子,并造成了孩子的受傷,她下意識地對著老二喝道“別碰我的孩子”,這句極具傷害的話,結束了她們之間的精神結合。絕望的老二最終給我們提供了純粹精神的真諦:“有些東西,非常美好,可是非常脆弱,一旦破壞了,就再不能復原了。”
和《弟兄們》稍有差異,《神圣祭壇》討論的是異性之間的純粹精神,女教師戰卡佳找到了她在人世間唯一的對手,天才詩人項五一,他們倆在人間存在似乎就只有一個目的,一個是了解,一個是被了解,當他們耗盡了自己的智慧和熱情,在一個夜晚將了解和被了解的關系推向了頂峰之后,他們之間的故事就此結束。這兩篇小說對傳統的“知音”關系是一種深度解構,因為它們討論的主題不是生活的日常狀態,而是精神的極端可能,是擺脫物質因素影響的純粹精神如何在人的世界存活的終極性問題。這個問題的答案似乎已經明朗,在這種純粹精神中,人注定了無法獲得意義的完滿,而只能接受精神的煎熬。
純物質的“性”和純精神的“愛”,從時間形態上來說游離于線性結構之外,然而,從性質上來說,它們都呈現出強烈的“時間性”特征。倭鏗指出,人在神、理性、自然等外在性意義變得不可靠的時候,“為了保全我們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似乎僅剩唯一一條路可走:人轉向其自身。”[12]人建立起了屬于自身的內在意義生活,也建構起了內在心理時間的體系,在這個體系里,時間不是以線性的方式延伸,而是以強度的方式決定其存在的短暫或永恒。《小城之戀》中的“性”,是帶有強烈的物質消耗式的“瞬間性”時間,而《弟兄們》、《神圣祭壇》中的純粹精神則類似于宗教里的“永恒時間”,但與宗教中的“神的時間”相比,它是“人的時間”,它不是彼世的,而是現世的。在新時期后期,王安憶通過物質和精神這兩種“意義”敘事擺脫了未來和過去的意義模式,通過內在心理時間的開拓使線性時間轉化成三維的立體時間,和前兩個階段一樣,王安憶仍然沒有給我們提供一個“意義”的答案,但是這種“意義”拓展的探索,卻呈現出了一種和新時期精神非常契合的意義自覺和開放。
意義,是人對于現世的解釋和承諾,而意義后面的時間意識代表著一種普遍性的心理結構。新時期的小說創作出現了多樣化的意義方向和時間意識,雖然有很多的表達并不完滿和深刻,但是那種極具創造力的青春激情和亢奮,卻為當時的歷史做出了生動的記錄,也給后來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在新時期文學十余年的時間里,許多優秀作家都以個人化的方式參與到尋找意義的道路探索中,王安憶從新時期初期的審視未來,中期的反思傳統,再到后期探索純粹性愛和純粹精神的可能性等四種“意義”敘事,編織出了未來、過去、瞬間、永恒等四種不同時間方向的網絡。“意義對既定現狀的超越性張力與意義的意象希望或憧憬未來情調內在相關。意義往往是有待于實現的前景。因此,可能性是意義本質性特征”[13],王安憶不僅自覺地走上了意義探索之路,而且把握住了“意義可能性”對于意義本身的本質性特征,雖然每一種意義方向在王安憶的小說中都沒有找到自己的棲居地,沒有帶來人的精神自足和最終支撐,但是這個尋找意義的故事,以及執著于“意義”尋找本身,不正揭示出一種屬于現代性特征的意義狀態嗎?
[1]程文超.意義的誘惑[M].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
[2]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360.
[3]王安憶.王安憶說[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3:156.
[4]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256-261.
[5]巴金.懷念曹禺[C]//吳福輝,朱珩青.百年文壇憶錄.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
[6]阿格尼絲·赫勒.現代性理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18.
[7]何志云.生活經驗與審美意識的蟬蛻——《小鮑莊》讀后致王安憶[N].光明日報,1985-08-15.
[8]陳思和.當代文學創作中的文化尋根意識[J].文學評論,1986(6).
[9]王安憶.我寫《小鮑莊》——復何志云[N].光明日報,1985-08-15.
[10]王安憶,張新穎.談話錄[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142-143.
[11]王安憶.從現實人生的體驗到敘述策略的轉型[J].當代作家評論,1991(6).
[12]倭鏗.人生的意義與價值[M].周新建,周潔,譯.南京: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譯林出版社,2013:22.
[13]尤西林.闡釋并守護世界意義的人[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6:84-85.
(責任編輯:李金龍)
I206.7
A
1001-4225(2015)05-0026-06
2014-12-08
王軍(1971-),男,江西寧都人,文學博士,南京審計學院文學院副教授。
江蘇省教育廳2012年度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新時期小說中的時間意識及其《意義》敘事”(2012SJD75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