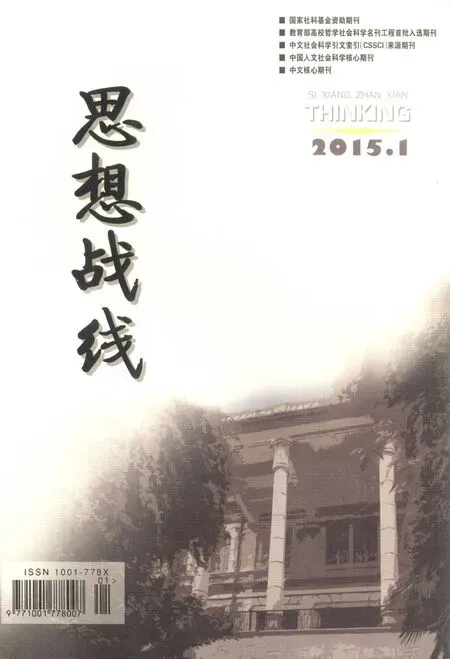必然的無知而必然的自由——淺論哈耶克知識認識論下的自由哲學
尚新力
哈耶克的知識觀或認識論構成其政治哲學的基礎,由這樣的基礎才建立了自由正義的價值理論和自由秩序的社會理論。哈耶克的知識論經歷了分立知識——默會知識——無知的演變過程。從分立知識的“知”到默會知識的“知又無知”再到無知的“必然無知”,是一種以“知識”為核心的方法論而形成其哲學意義上的認識論,且在此基礎上達致其政治哲學的價值觀及其社會理論。雖然這些基本概念的變化,不可視為一個同質的變化過程;但這樣的演變過程中的每一個知識觀都無疑可以引導出自由正義的價值觀念,并進一步在演變的過程中確立為自由秩序的社會理論。
一、我們何以必然的無知
哈耶克所言“必然的無知”是:“人對于文明運行所賴以為基礎的諸多因素,都處于不可避免的無知狀態”。顯然這表明,我們對形成和發展人類文明社會的諸多因素是我們所無知的,或者說,人類對于諸多有助于實現其目標的力量或因素往往處于“必然無知”的狀態;這里實際上包含著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我們對已知的因素中存在著無知;二是我們對不知的因素更是無知。在這里做這樣的表述,其意義在于:首先,正是因為已知中的無知,才使我們人類的理性有限之觀念具有真實意義,并使真實的社會行為規則得以獨立于我們對它們的辨識而存在;其次,正是因為引入了“無知”的知識觀,哈耶克才質變地深入到此前關于社會乃由行動者的觀念構成的“知”意義上的知識觀所無法理解的和不可能觸及的東西;最后,這一事實始終未引起人們的關注。科學家們很自然地傾向于強調我們確知的東西,而在社會領域往往是那些并不為我們所知的東西更具有重要意義,所以在研究社會的過程中采取科學家那種強調已知之物的取向就會導致極具誤導性的結果,諸如烏托邦式的建構方案之所以毫無實際價值,乃是因為它們都出自于那些預設我們擁有完全知識的理論家之手。
我們為何“必然的無知”而且永遠處于“必然的無知”狀態之中呢?
第一,我們人類的心智或理性并不是完美和完全的,如果我們承認這一點,就意味著我們對于人的心智或理性是無知的,由心智或理性得以形成的知識中也同樣存在著我們的無知。這是因為:一是人類要超越人的心智之外去思考心智是完全不可能的,由此人的心智是不能解釋其自身的,我們對心智的性質及其活動的方式是無知的。二是人的心智本身作為一種系統,也是努力使自己在適應外部環境的過程中不斷地發生著變化,這種變化也就意味著人的心智并不是那么完美和完全的,表明人的心智或理性存在著無知的區域。三是我們的心智是我們生活于其間的文明的產物,而且人的心智對于構成心智自身的大部分經驗并不意識——經驗通過將人的心智融合于文明之構成要素的習慣、習俗、語言和道德信念之中而對它發生影響。四是任何為個人心智有意識把握的知識,都是特定時間有助于其行動成功的知識的一小部分。當我們反思:他人擁有的知識在多大程度上構成我們成功實現個人目標的基本條件,我們就會發現我們對于我們行動的結果所賴以為基礎的環境極其無知。人的心智或理性面對著特殊的自然和社會環境更多地是顯示出其無知而無能。五是人的心智絕不能預見其自身的發展,由此我們的心智也就根本不可能有能力構設自此往后500年甚或50年的社會與自然狀態,我們對此是無知的。簡言之,我們的心智或理性是有限的,我們不可能將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形成為是理性的產物,即使是心智或理性的理解也同樣可能存在著誤解,所以我們是必然的無知。正是我們承認自己的必然無知,才能夠恰當地理解理性的力量和意義,防止理性濫用和唯理傾向造成的惡果。
第二,人類的科學知識下依然存在著無限的無知。哈耶克認為,科學知識是既不能窮盡那些為社會經常使用的明確的和有意識的知識,科學知識更不能完美而無遺地解釋那些為人類經常需要明確的和有意義的自然和社會的知識;這就是說,在科學知識外存在著無知,在科學知識內也隱含著無知。我們為什么無知呢?一是尋求知識的科學方法依然不能滿足社會對明確知識的全部需要;二是人們持續不斷使用的關于變動不局、千變萬化的特定事實的知識中,并不全都適宜于被系統解釋的知識或者說是邏輯而理性所解釋的知識;三是大多數知識是散存于無數個人手中的知識,業已形成的科學知識對于它們是知之甚少的;四是即使科學專家的知識,其間一些重要的知識并不是實質性的知識,而只是關于在何處以及如何去發現所需信息的知識。
第三,人類文明的進步并不意味著我們人類有意識和明確的知識的增長,我們依然處在無知之中;而且在知識增長和社會文明不斷地進步發展下我們可能面臨的是更大更多的無知。當我們把知識理解為有意識且明確的知識,也就是我們可以陳述某個事物為何的知識時,就以為文明的發展與知識的增長是同時并舉的,這顯然是一個嚴重的誤導;當我們往往對知識的增長感到自豪和得意時就以為無知的領域在知識的和文明的增長中不斷地縮減,因此我們能夠更為廣泛地和有意識地控制人的所有活動,并能夠依據這樣的活動指揮和主宰我們世界的一切,這顯然是我們人類一個嚴重的自負。哈耶克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陶醉于知識增長的人往往變成自由的敵人。
人類的自負在于我們往往對知識的增長感到自豪和得意。其實在知識增長的同時,“作為人自身創造的結果,對于人有意識的行動產生重要影響的人的有意識的知識的局限、從而也是人的無知范圍,亦會不斷地增加和擴大”。①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鄧正來譯,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第25頁。因為一是由于我們關于自然和社會的知識的增長會永遠地向我們展示新的無知領域,所以依據這種增長的知識所構建的文明亦會日呈復雜和紛繁,而這必然會對我們在智識上理解和領悟我們周邊的世界時造成新的障礙,形成更多的無知領域;二是在知識分工和分立的前提下,我們的知識愈多愈是增長,知識的分工也就愈是強烈,每個人的心智能夠從中所能汲取的知識份額也就愈小。我們的文明程度愈高,每個人對文明運行所依憑的事實就愈是知之甚少。
第四,在非理性的即不斷進化發展的“經驗知識”,我們對這樣的知識也同樣是必然的無知。我們承繼的知識中最為顯著的知識和最為主要的知識是理性的或科學的知識,但對于在現實意義上的“知識”而言,依舊只是一部分知識。因為除此之外的許多其他工具也就是存在于我們習慣所遵循的卻不明就里的大多數行為方式——諸如傳統、制度、習俗等等,乃是人類歷經悠久歲月逐漸發展形成的產物,且通過對它們的運用,我們才得以應對我們周邊的環境,而這些工具切切實實是世世代代相傳之經驗的產物,是人們累積性的進化發展的產物而非任何個人心智設計的產物。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認為在這方面我們人類依然表現出極大的無知——對于自己為何使用此種形式的工具而不使用他種形式的工具是無知的,對于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依賴于此種行動方式而不是他種行動方式是無知的,對于其努力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決定于其所遵循的他自己也沒有意識到的習慣是無知的。這不僅適用于未開化者也適用于文明者。所以說,我們每個人都是必然的無知,我們所無知的,不僅有理性知識方面的無知,也有經驗知識方面的無知;不僅有自然世界的物質性無知,也有人類社會的精神性無知。
二、必然的無知但絕不無為
就理性和經驗的知識而言,在我們的文明進程上表現為知識傳承和知識傳播這樣兩個方面。作為理性的或科學的知識之傳承和傳播是我們在社會文明進程中所熟知的,這種知識無疑在我們人類活動中具有重要的普遍性、基礎性和一般性質;然而,在我們人類文明的進程中每個人所面對的不斷變化的環境必定是一個特定的和非常的,我們試圖以理性或科學的知識來應對這種不同尋常和特定的環境變化而獲得成功和達致文明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為我們個人的成功和人類的文明更多的是來自于我們理性不及或心智不解的經驗所積累的知識。這里重要的是,在我們自知無知的理念下,對于那種哲學概念上的邏輯性或心智上的理性知識我們是不完全的,切不可自詡理性而濫用理性,更不可唯理主義地將它們絕對化;而對于那種世俗理解上的感性化或理智上的理性知識我們則是必須完備的,我們務必在我們所有的行為中都要具備這種克制、謹慎的理性。這就是說,無知不能無畏,無知只能敬畏。
正是在承認人類的必然無知的前提下,哈耶克才得以引導我們重新地認識理性,使我們在無知下而有所為。一方面是我們對唯理主義的否棄,對完全理性幻想的批判。人們對理性知識的完美化和絕對化,把理性知識視為具有絕對的全能、全知、全善,甚而頂禮膜拜到理性知識的無處不在、無所不能,進而使我們成為在任何現實中對理性的絕對服從和無條件的尊奉。顯然這一意識的謬誤在于:對人類理性不及的或經驗的知識的否定就是對人類實踐的否定,對理性命令的絕對服從就是對人類生命活力的棄絕。打破這種唯理觀的意識,我們唯一有所為的就是通過我們自己的實踐,使我們不抱幻想而自由地思考、行動、建立自己的現實,并在之中不斷地豐富、擴展理性,盡管理性知識在我們人類的生活中永遠不可能是惟一的和完全的但卻是普遍的和根本的。另一方面是我們對人類必然無知的否定必然導致我們從無所不知的假設出發想當然地重新去“理性的”設計社會制度的進程,哈耶克對此稱之為“建構的理性主義”,并指出這種幼稚的理性主義將給人類文明帶來毀滅性的打擊。哈耶克進而解釋道,“如果理性主義所企及的乃是盡可能有限的運用理性,那么我本人就是一個理性主義者,但如果理性主義這個術語意味著有意識的理性應當決定每項特定的行動,那么我就不是一個理性主義者。而且在我看來,這種理性主義恰恰是極不理性的。”①哈耶克:《法律、立法與自由》,鄧正來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年,第33頁。
由此可見,在我們關于人類文明進程中的知識傳承和傳播的論證中,最為重要和關鍵的是那些更廣泛更大量的由經驗積累的知識在時間上的傳承和現實中人們之間就其行動所賴以為基礎的信息的傳播。顯然,在依經驗形成的知識的傳承和傳播二者間具有相互作用和結合的一致性:當人們面臨的一些環境條件發生變化并造成在資源使用方面、在人們活動方向及種類方面以及在習慣和風俗方面的變化;這些變化要求人們在其他諸方面做出進一步的調適;調適會逐漸擴展或傳播至整個社會;每一個變化給社會或人們造成的“問題”在形成新的整體調試方式的過程中逐漸獲致“解決”。顯然,這個一致性就是我們人類社會進步文明的過程,雖然,我們對人類針對環境變化而將自己的經驗知識、技巧、個人態度與自己目的的各種組合或調適方式以及這種調適行動事實的傳播方式是無知的和無法預言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個人就不將傳承的經驗知識與自身的目標取向進行成功的組合或調適,也不意味著這種成功的組合或調試的事實不會產生擴展或傳播的效應;這只是意味著這些組合或調適,既不是出自人們經由共同的審慎考慮而做出的選擇,也不是出自人們通過共同努力尋求解決問題的方式而做出的選擇。
無知中的我們并不意味著無為——在人們自己將知識與技巧的各種組合形式付諸實施以后,人們即可以發現那些恰當的或更為合宜的做法或手段,進而為人們普遍接受。在這樣的實施即在人們面臨變化不定的環境來處理自己日常事務的過程中采取的無數微不足道的且平實一般的小措施,實在是產生了種種為人們所普遍接受的范例,其重要性絕不亞于得到明確公認并以明確方式傳播于社會的重大的智識創新。簡言之,社會中的每個人面對變化不定的環境或條件所做的成功組合或調試就是個人運用其他人之經驗的成功的結果,也是我們對自己無知的有意識地調適的結果。依照辯證的思路和實踐的體會,在我們面對無知的環境和條件的變化中,我們人類的文明進步和改變就是通過上述的路徑克服一系列原有條件而發生的,而這些條件自身也是克服此前的系列條件的產物,如此以至無窮。我們正是沿著這樣一條路徑:無知—知—更多的無知—更多的知,從而漸進的走向文明,這里的“知”既包括理性的知也包括理性不及的知或者說是實踐的經驗的知。我們可以斷定人類的無知絕不意味著他的無所作為,人類作為一種類存在物,就是通過相互之間的模仿、學習、借鑒等方式克服環境和條件的不斷變化所帶來的“問題”而不斷進步的產物,通過這種克服過程才使得我們人類有可能走向文明。
我們的必然無知絕不是一種不可知論的認識觀。哈耶克的這一必然無知的知識論的認識論,更加深刻地寓意著:我們面臨的所有問題都是可以得到答案的,如果我們就某一個問題現在無法解答,將來必能解答,如果永遠不能解答就必然不是一個問題。這就是說,我們不知的知識,可能是他人知道的知識;我們現時不知的知識,可能是我們未來知道的知識。所有的知識都是可知的,我們可以通過世上存在的各種途徑獲得我們無知的知識,不論這些知識是傳統的知識還是理性的知識。正是在這種可知論的認識論下,我們才可以在必然無知的自知中不斷的求知,使自己達致為一個真實的自己。
三、因為無知而必需自由
我們之所以主張個人自由,其依據在于承認所有的個人對于實現其有益于自身的目的所賴以為基礎的眾多因素,都存在著必然的無知。
為什么無知必然要求個人自由呢?
哈耶克認為,如果存在無所不知的人,如果我們知道當下所有影響我們希望的因素,如果我們知道所有影響未來需求和欲望的因素,自由就沒有什么意義了。雖然個人自由可能會使完全的預見成為不可能,但我們仍然需要自由,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只有自由,才可以給不可預見的和不可預測的事物提供發展空間,才可以使我們在千變萬化的境遇中自主地采取個人的有針對性的適時性行動,才可以使我們從中期望獲得實現我們諸多目標的機會,才可以經由獨立和競爭的努力促使那些我們見到便會需要的東西的出現,才可以為獲致和領悟無論是理性的知識還是理性不及的知識并且將它們適應性的加以運用開放出無限的可能性。
然而,對個人自由所帶來的結果我們依然也是無知的,因為我們并不知道個人將如何使用其自由,進而我們就不知道個人在運用自由于特定境遇中所造成的結果。正是因為如此,在無知下的必然自由就顯得極為關鍵——如果我們知曉自由如何被運用并預知其結果,那么我們還有什么必要和依據主張自由呢?更廣泛地說,我們是否能為未知之事物 (或偶然之事物)的發展提供最多的空間和機會也就是最大的自由決定了我們人類社會文明的發展和維系。我們能做的就是一增加機遇:促使個人的天賦和環境形成某種特別的組合并創造出新的工具或改進舊工具;二增進成功:促使諸如此類的創新能夠迅速地傳播至那些能夠利用它們的人并為他們所用。而要做到這二者,就必然需要自由。所以哈耶克認為在我們無知下的自由的全部問題乃在于以盡可能快的速度不斷地犯錯誤但不是犯罪。可見,我們對他人如何使用自由及其產生之結果的無知,對或然事物之發生和機遇能否出現的無知,恰恰是對自由的追加和必需。
所以說,既然個人在社會生活和實踐中之所以獲得益處,大多是基于我們每個人能從其所未認識到的其他人的知識中獲益這樣的事實;既然我們的文明來自于個人在追求其目標時能夠使用較其本人所擁有的更多知識,始于個人能夠從其本人并不擁有的知識中獲益并超越其無知的限度;既然在我們人類歷史的現實中顯現出愈是發達社會其社會生活和實踐的作用就愈是明顯。那么,就應該賦予處在必然無知狀態中的我們更多的實踐和行動的空間和機會,這就是自由。正是由于每個人在相互彼此調適的實踐和行動中具有更大空間和更多機會,才使得人們使用的知識比個人擁有的知識為多,比在智識上可能加以綜合的知識為多,由此人們獲得的成就也就比一個人心智所能預見的為大。從另一個角度講,這一自由意味著對直接強迫和控制個人實踐和行動之措施的否棄,因而一個自由社會所能使用的知識和他們獲得的成功才會比最明智的統治者的心智所能想象者為多。
我們如何理解我們主張的自由呢?
第一,自由首先是一個信念,我們堅信自由將釋放出更多的力量,我們堅信自由所達致的結果一定是利大于弊;這個堅信絕不是以我們可預見的自由之結果為依據的。哈耶克批判到,如果僅以事先知道自由的效用會產生助益的情況下而授予的自由,這實際上不是自由;如果我們已然知道自由會被如何使用而主張自由,這也不是真正的自由;如果對一些人使用自由的結果似乎不盡人意的條件下不予以自由,就更是對自由的愚見,因為由此我們就絕不會獲得自由的裨益,也絕不會達致只有在自由提供機會的情況下才能取得那些不可預見的新發展。自由可能被濫用,但自由被濫用的現象絕不是作為反對自由的論據。自由告訴我們一個道理:許多事情雖為我們不喜歡,他人仍可以為之。
第二,自由是每一個個人的自由,與我們或我們中的大多數人是否有可能利用某個空間或機會的問題無關。我們往往對自由產生這樣的根本誤解:我們賦予的自由應該是那種可以為所有人都能運用的自由而不是只有少數人能夠運用的自由。然而,自由的力量在于:百萬人中僅有一人所能使用的自由對社會的重要性以及對大多數人的助益,可能要超過人人都可以使用的自由。這就是說,平等的自由權利并不意味著會帶來平等的自由結果。正是由于這種結果上的不平等,導致我們對自由采取的兩種傾向:一種是對于大多數人來講既不可能,也不可欲的自由不是我們應該予以的自由;另一種是把只有少數人有能力運用自由的人的自由強制地予以給多數人。這兩種錯誤的傾向或做法實質上是對自由的背離,所不予以的自由和強行予以的自由根本就不是自由,它是對我們每個人對自由地運用自由的剝奪。所以,對于我們引以為重的是,不為大多數人愿意或有能力行使的那種自由,卻恰恰可能就是他人可以做有益于社會的事情所需要的那種自由;然而,有能力行使特定自由的少數人如何確定呢?對此我們依然無知。唯有通過將此種自由賦予所有人,才能確使不確定的任何個人都能獲致此種自由。因而,自由是每個個人的自由,是每個個人運用自由的自由,而不論是否有能力運用這個自由。這一點的重要性在于每個人是自由的,每個人運用自由的選擇也是自由的,這就是自由的平等,由此我們的社會文明才具有相當的多樣性和創新性。這是一個不爭的重要原則。
第三,自由是有秩序的自由。人類社會為了最佳地使用我們已擁有的各類知識,我們必須遵循那些為經驗所表明在總體上產出最佳結果的基本規則,盡管我們不知道在特定情勢下遵循這些規則會產生何種后果。“只要人不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那么,能夠給人以自由的惟一途徑,就是用這樣的一般性規則,來界定個人得以在其間進行決策的領域。”①哈耶克:《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鄧正來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第26頁。這就是說,在必然無知下的必然自由仍然要有一個遵循基本規則的即有秩序的自由或法治下的自由。
還應看到,在我們自由地追求個人目標時,我們要想成功,確實需要為我們的自由行動確立一些一般性規則或理性的規則,顯然這些規則是指不需在每一特定情形中對其正當性再進行考慮便會加以遵循的。諸如在并不合自己心意而又必須做的工作時,受到刺激而又必須控制自己情緒時,壓制自己某種沖動時。我們之所以常常認為有必要將這些理性下的做法變成一種不需思考的習慣,在于我們知道如果沒有這樣的習慣,那么,使我們這類行動成為可欲行動的理性根據,就不足以有效平衡各種各樣的即時性欲望,也不足以有效促使我們去做從長遠觀點來看我們也會希望自己去做的事情。為了理性地自由行動,我們往往認為有必要使我們的自由行動受習慣而非理性的指導;而為了避免自己做出錯誤的決策,我們又必須經過審慎思考而有理性地縮小我們的選擇范圍。在這里,特別是我們欲求實現自己的長期目標,理性和習慣具有不同的作用,并存而不矛盾,這是我們眾所周知的。這就是說,在必然無知下的必然自由仍然要有一個遵循理性規則的即有理性的自由和有道德的自由。“如果我們仍希望是人,那么我們便只有一途可走,即走向開放社會。我們必須進入那個未知的、不確定的且不安全的領域,運用我們所可能具有的理性去規劃安全和自由”。②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鄭一明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195頁。因此,哈耶克依據自由的邏輯而主張有秩序的自由。
所以說,我們從必然的無知中發現了必然的自由,進一步建立了自由是我們人類社會最普遍、最基本、最高尚、最偉大的價值所在的世界觀。
[1][英]哈耶克:《哈耶克讀本》,鄧正來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2][英]哈耶克:《科學的反革命》,鄧正來譯,北京:譯林出版社,2012年。
[3] [英]哈耶克: 《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鄧正來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
[4]鄧正來:《自由主義社會理論》,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
[5][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鄧正來譯,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
[6][英]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陸衡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7][美]拉齊恩.薩麗等:《哈耶克與古典自由主義》,秋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