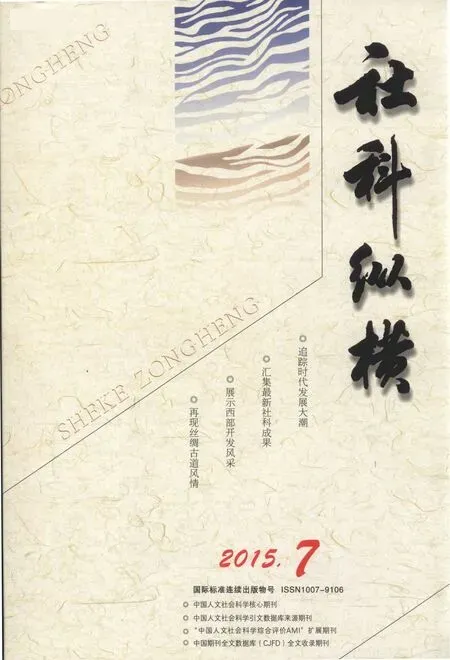從《馬可波羅游記》看元初泉州的商業經濟
申友良
(嶺南師范學院歷史系 廣東 湛江 524048)
泉州,在《馬可波羅游記》中稱為“刺桐城”,位于中國東南沿海,是現在福建省經濟文化中心和東亞文化之都,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的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歷史上的泉州港起于六朝,興于五代,宋元時期是其海外貿易的黃金時代,其中元朝則是其鼎盛時期。元初,泉州頭上光環無比炫目,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號稱“東方第一大港”,可與當時埃及亞歷山大港媲美。元初泉州的繁榮,可從意大利商人的《馬可波羅游記》窺見一二。
一、《馬可波羅游記》里元初泉州商業繁榮的表現
元朝重商,實行開明的經濟管理,對商人采取保護和鼓勵政策,還給予商賈一些特殊的優待。如給商賈以持璽書、佩虎符、乘驛馬的權利。楊軍琴認為:“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貧苦百姓,舍本農,趨商賈的風氣很盛,對此,時人深有感觸,馬祖常云:‘近年工商淫侈,游手眾多,驅壟畝之業,就市井之末。’經商致富已成為多數人追求的夢想。”[1](P121)
在這種濃厚的商業氣氛下,意大利商人馬可波羅來到了中國。馬可波羅初到泉州,對此城的印象是“城甚廣大”。此城不僅廣大,還很繁榮,是名副其實的商業之都。
馬可波羅曾多次來到泉州,對泉州甚為了解,見多識廣的他也驚嘆于泉州的繁華,記載了泉州國際大都市的風范。在他的《馬可波羅游記》中載:“船舶來往如織,轉載著各種貨物,使往蠻子省的各地出售。這里的胡椒出口量非常大……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貨物堆積如山,買賣的盛況令人難以想象。”[2](P217)從交通繁忙情況、紙幣的使用、商品種類、商業稅、商人數量和海外貿易的盛況可看出,元初泉州的商業經濟相當繁榮,可謂萬商朝華,是中國封建社會時期的一道亮麗風景。
第一,龐大的國際化商人隊伍。在泉州經商的,有元朝商人,還有可觀數量的回回海商,當然還有來自朝鮮、日本和東南亞等地的商人。這種狀況出現的原因有兩個:一是蒙元重商,二是蒙元賞識善于經商者。
首先,倪建中指出:“蒙古人是重商主義者,這也是其他少數民族的特點。因為,他們所居之處,往往不利于農耕,資源也相對缺乏,要想得到糧食、食鹽和工具,就必須發展貿易。”[3](P1033)經商與游牧民族熱衷于搶劫有異曲同工之妙,二者都是不用體力勞動就能獲得溫飽和財富,區別在于前者是文明的,后者是暴力的。元朝通過武力征服各國后,為了能細水長流,用錢生錢,于是,實行了一系列鼓勵和保護商業發展的措施,“這種保護和鼓勵,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保護財產安全,二是積極鼓勵通商,三是免除西域商賈雜泛差役,四是許多貴族和寺院僧侶經商有免稅特權。”[4](P70-71)帝國內出現一批逐利者。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儒家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輕商思想漸漸淡薄。其次,“由于蒙古貴族不善于經商和理財,‘只是撒花,無一人理會得賈販’,因此對那些善于斂財的商人特別信任和重用,許多人被吸收到蒙古帝國和元朝政府中擔任重要職務。”[1](P120)這種有意提高商人政治地位的做法,不僅吸引了國內商人,更是引得國外商人紛至沓來。馬可波羅自吹他頗受大汗忽必烈的喜愛和重視,大概與此政策有關。
泉州是當時國內最大世界第二的貿易港口,“是亦為一切蠻子商人常至之港”[5](P424),且“印度一切船舶運載香料及其他一切貴重貨物咸蒞此港”[5](P424)。可見,泉州不僅是國內商人常至之港,也是印度商人常至之地。兩者在此地交換商品,然后又從此港啟航,朝各自的目的地出發。關于泉州港崛起的原因,楊志娟認為,回回富商蒲家居功至偉。“元代回回海商集團的形成與蒲壽庚有直接的關系。”[6](P91)1276年,蒲壽庚降元后,被元政府授以官職,主持泉州的海外貿易,招徠大批善于經商的海外穆斯林商人來華,同時也經商,一時富甲泉州。“后來蒲師文繼任泉州市舶提舉司,兼海外諸蕃宣慰使,仍然專事招徠外商來華貿易。元朝時蒲氏家族在泉州聲勢十分顯赫,泉州在其家族的經營下,也揚名海外。”[6](P91)泉州港的繁華,得益于精于經商穆斯林人,尤其是世代經商的蒲家在泉州的長期經營。元統治者重用善于經商的人管理商業,是明智之舉。馬建春同樣相信泉州港的繁華離不開西域商人。馬建春在《元代西域人的商業活動》中堅持:“由西域商人主要負責開展的國際貿易,也給元朝商業的繁榮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7](P172)他寫道:“泉州的鎮南門外是西域商人聚居之地,‘四海舶商諸番琛 貢皆于是乎集’,‘番貨、遠物、異寶、奇貨之所淵蔽,殊方別域富商巨賈之所窟宅,號為天下最。’”[7](P175)當社會以開放的姿態接納外來者,外來者將對你有所回饋。泉州以開放的姿態接受外商來華——西域商人或者說回回海商在泉州實力雄厚,地位重要,泉州的繁榮跟他們的到來有直接關系。
第二,紙幣在泉州的流通。具有購買力的紙幣最早出現于北宋,稱“交子”,僅流通于四川。經濟越是發達的地區,紙幣的流通便越廣泛,因為經濟發達地區,商品交換活動頻繁時,金銅銀的數量可能無法滿足需求。而紙幣的流通,又能促進商業經濟的發展。元初,政府發行“中統元寶交鈔”,規定一切交易、支付全部用鈔。馬可波羅在《馬可波羅游記》中說到:“商人皆樂受之,蓋償價甚優,可立時得價,且得用此紙幣在所至之地易取所欲之物,加之此種紙幣最輕便可以攜帶也。”[5](P262)紙幣使用方便,且便于攜帶,商人都喜歡。張寧在《<馬克波羅游記>中的大都文明》認為:“由于其時紙幣初行,印數限量,鈔庫銀根充實,幣值穩定,處于紙幣信譽的黃金時代,因此贏得了馬可波羅的贊許。”[8](P103)并且,大概是因為經商需要,每到一地,他總是格外留心此地使用何種貨幣。游至泉州,他發現“居民使用紙幣而為偶像教徒。”[5](P424)泉州有數量龐大的外國商人和元朝商人,彼此間的商品交換活動通過紙幣的流通完成。而紙幣的流通,又大大方便了商品交換活動,彌補現錢不足的缺點,掙脫阻礙經濟發展的束縛,為泉州的經濟發展提供更廣闊的空間。
然而,雖然紙幣是法定的流通貨幣,但在元朝統治范圍內,因商業經濟不夠發達,處于自然經濟狀態下,很多地方用貝殼甚至鹽塊充當支付手段。如在金齒州,“其貨幣用金,然亦用海貝”[5](P323)紙幣的流通多是在原南宋統治地,即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僅次于世界第一大港亞歷山大港的泉州港自然是使用紙幣的。
第三,海外貿易繁盛。重視發展海外貿易是元朝的一大特色,更是中國封建社會最為光輝的一頁。中國歷代漢族封建統治者都不大重視海洋建設,始終堅信“工商皆末”。難得一次由政府組織的出海行動一般是平叛,或者出錢出力遣使耀國威,掙面子,比如明朝鄭和下西洋。楊志娟認為:“元代是中國歷史上積極經營海洋的朝代,尤其是忽必烈時代,蒙古統治者的開闊世界觀,積極的海上活動以及重商政策構建起了廣闊的海上貿易網絡。”[6](P93)元朝重視海外貿易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為控制海上商道,馬上得天下的元統治者不惜對東南亞、南亞國家用兵,并欲征服日本。在其努力下,海上絲綢之路得以暢通無阻。二是元政府積極推行官本船制政策,《元史》中的《食貨志》載:“官自具船給本,選人入番,貿易諸貨,其所獲之息,以十分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9](P94)這種政策實為雙贏,政府與商人合作,前者出錢,后者出力,最后各取所需。元政府的做法扶持了一批與政府合作經商的海商。
泉州港如此重要,除了海洋建設,暢通海上絲路之外,元政府也十分關注國內的交通建設。梁凌霄等人認為:“元朝疏浚了在宋金對峙時期已多處堵塞的京杭大運河。1291年,在京郊開鑿通惠河,引大都西北諸泉水東至通州,全長164里經重新疏鑿,河道大多取直,航程大為縮短,運糧船可以駛入大都積水潭(今北京什剎海一帶)停泊運河的鑿通加強了南北之間的經濟聯系和交往,‘使得江淮、湖廣、四川、海外諸番土貢、糧運、商旅懋遷,畢達京師’。”[10](P48)元初京杭大運河航路暢通,且元朝統治者重視陸路的建設,故商品能從泉州順利地運往國內各地,促進了泉州與內陸各地的經濟交流和泉州商業經濟的發展。交通的便利,還擴大了元初泉州港對外貿易的范圍,中國的商品擁有廣大的國際市場。如此,便促進了元初泉州商業經濟的興盛,也使得泉州成為當時中國最具國際范的城市。此外,元朝建立了嚴密的站赤制度,商人的流動因此更快速。
泉州位于中國東南沿海,是元朝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國內外商品進出口必經之地,是重要的國際貨物中轉站和集散地,更是出海官商的聚居之地。馬可波羅看到“其港有大海舶百艘,小者無數。”《馬可波羅游記》又載:“印度一切船舶運載香料及其他一切貴重貨物咸蒞此港。是亦為一切蠻子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貨寶石珍珠輸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議,然后由此港轉販蠻子境內。我敢言亞歷山大或他港運載胡椒一船赴諸基督教國,乃至刺桐港者,則有船舶百余,所以大汗在此港征收稅課,為額甚巨。”[5](P424)無數往來不斷的大小商船,堆積如山的貨物,人頭涌動的中外貿易場,無不讓馬可波羅折服。在馬可波羅眼中,這種繁華的盛況,甚至可媲美亞歷山大港,超越家鄉威尼斯。
申友良在《<馬可波羅游記>的困惑》中認為:“隨著泉州港的海外貿易盛況空前,來此貿易的蕃商也大大超過前代,外僑的人數之多、民族成分之雜和所屬地區之廣,是泉州前所未有的,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僑民社會,恐怕連當時的廣州也難與之相比。”[11](P155)海外貿易繁盛為泉州港帶來大量外來人口,儼然一個微型聯合國,也使泉州更為開放和更具活力。泉州海外貿易的發展,“促進了商品經濟生產及流通領域的擴大,帶動了當地造船業、制瓷業、紡織業的發展是泉州形成為當時各國商人和商品最集中的地方,成為中國的造船中心、絲織業中心、陶瓷生產與外銷的重要基地。而且還成了中世紀聯結歐亞大陸海上絲綢之路的東方第一大港。”[11](P155)元初的泉州,因海外貿易的興盛,名揚海內外。
第四,商品種類繁多,應有盡有,泉州港是國內外首屈一指的貨物集散地。對此,申友良提到“我國的絲綢、瓷器等商品,由此向東運銷朝鮮、日本;向南遠銷東南亞、南亞;向西遠銷西亞乃至歐洲、非洲各國,而這些國家的藥材、沙金、黃銅、香料、珠寶、象牙、犀角等也運至中國泉州等海港。”[11](P140)可見,泉州港是相當國際化的,商品種類亦是繁多。馬可波羅多次停留在泉州港,甚為熟悉之,《馬可波羅游記》載:“印度一切船舶運載香料及其他一切貴重貨物咸蒞此港。是亦為一切蠻子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貨寶石珍珠輸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議……則有船舶百余……此處一切生活必需之食糧皆甚豐饒……制造碗及磁器,既多且美。”[5](P424)他提到運載貨物、往來不斷的商船,還有印度香料、商貨寶石珍珠、糧食、瓷器等商品,熱情洋溢地歌頌了泉州的繁華和富庶。再詳細系統一點考察商品的名目,則可引用莊景輝的《論元代泉州的繁榮及其原因》一章中:“其記元代泉州外銷商品有九十多種,比宋代增加了不少。總的來看,輸出品系以衣料為最多,日用品和食用品等次之。衣料有錦、緞、絹……棉、苧、葛、麻……日用品有盤、瓷瓶……銀、鉛、錫、銅、鐵等各類金屬器,以及鹽、酒等食用品與漆器、黃油傘等雜貨。”[12](P105)聚集在泉州的商品各色各樣,大到昂貴的奢侈品,小到吃飯的鍋碗瓢盆,應有盡有,滿足了市場的需求。其中,運往泉州的銷往海內外的商品中,我們的絲織品“刺桐緞”便是馳譽海內外的名牌產品,深受歡迎。元朝著名文人吳澄:“泉,七閩之都會也,番貨遠物異寶奇玩之所淵蔽藪,殊方別域富巨賈之所窟也,號為天下最。”泉州商品種類齊全,經濟發達,不愧為“東方第一大港”。
二、《馬可波羅游記》里元初泉州商業經濟繁榮的原因
《馬可波羅游記》里元初泉州的商業經濟是相當繁榮的,除了忽必烈采取的重商政策以外,還有兩個最重要的原因。
第一,元初泉州的經濟基礎好。《馬可波羅游記》載:“居民使用紙幣而為偶像教徒”[5](P424),“此處一切生活必需之食糧皆甚豐饒”[5](P424)。元初,泉州是使用紙幣的,這里的一切生活必需的糧食足夠多,能養活除泉州居民外的更多人。紙幣的流通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元初,由于經濟較為落后,疆域內的大多數地方是用貝殼或鹽塊等物品充當貨幣的,比如吐番州“境內無紙幣,而以鹽為貨幣”[5](P305),再如哈剌章州,“所用貨幣則以海中所出之白貝而用作狗頸圈者為之”[5](P314)。少數經濟發展較好的地區,尤其是南宋故地,皆使用紙幣,泉州亦是如此。此外,泉州“一切生活必需之食糧皆甚豐饒”,有能力養活眾多外來人口。
第二,泉州港海內外交通繁忙。泉州港的地理位置優越,位于元朝疆域內的東南沿海,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是發展海外貿易的絕佳之地。《馬可波羅游記》載:“印度一切船舶運載香料及其他一切貴重貨物咸蒞此港。是亦為一切蠻子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貨寶石珍珠輸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議,然后由此港轉販蠻子境內……乃至此刺桐港者,則有船舶百余”[5](P424)。印度一切運載香料和其他貴重貨物的船舶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都到泉州港,南宋故地的商人和貨物通過河運到達和離開泉州,他們攜帶來的貨物多得不可思議,然后又攜帶多至不可思議的貨物離港。從海內外商船到港之多和多至不可思議的貨物可知,當時的泉州,無論是國際海運,還是國內河運,都相當繁忙。
三、《馬可波羅游記》里元初泉州商業經濟繁榮的影響
第一,泉州商業繁榮,為元初統治者提供穩定且數額龐大的商業稅。稅收是維持政府正常運行和皇家奢侈生活的必備品。泉州港是當時一個國際商業港口,一切停靠于泉州港的商船和中外商人的貿易活動,均須繳稅。關于泉州的商業活動和商業稅,《馬可波羅游記》載:“印度一切船舶運載香料及其他一切貴重貨物咸蒞此港。是亦為一切蠻子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貨寶石珍珠輸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議,然后由此港轉販蠻子境內。我敢言亞歷山大或他港運載胡椒一船赴諸基督教國,乃至刺桐港者,則有船舶百余,所以大汗在此港征收稅課,為額甚巨。凡輸入之商貨,包括寶石、珍珠及細貨在內,大汗課額十分取一,胡椒值百取四十四,沉香、檀香及其他粗貨值百取五十。”[5](P424)在馬可波羅看來,泉州是大型的國際貿易活動的場所。一是,中外商人云集于此港,既有渡海而來的印度人,有“一切蠻子商人”,還有像馬可波羅一樣的色目商人。二是,商品眾多,“商貨寶石珍珠輸入之多凈值不可思議”。三是,商船眾多,“印度一切船舶運載香料及其他一切貴重貨物咸蒞此港”,還有“一切蠻子商人”商船。四是,商業稅甚巨。由前面三點可知,泉州的商人商船商貨的規模是極為龐大的。再者,元政府在此港的收稅政策,“凡輸入之商貨,……,大汗課額十分取一,胡椒值百取四十四,沉香、檀香及其他粗貨值百取五十。”因此,所收各種名目的商業稅“為額甚巨”。商業稅成為泉州政府主要財政收入之一。此外,元初實行的包稅制度,目的在于減少稅收,鼓勵商業發展,對象主要是蒙古人、色目人,政府在北方的商業稅較少,故對南方城市的商業稅較為倚重。并且,在北方的蒙古族和少數民族主要是游牧民族,多從事畜牧業,居無定所,常常遷徙,牛羊馬生長期較為漫長,牲畜死亡率也高,造成牧民收入少且不穩定,不能為政府提供大量且穩定的稅收。農業本是可以為政府稅收做貢獻,但是元統治者命令許多中原及中原以北的從事農業的地區轉為從事畜牧業,大片農田草原化,元政府的稅收來源就更少了,商業經濟相對發達的南方城市的稅收就顯得更為重要了。陳高華在《元代商稅初探》中通過列數據和論證分析說明“商稅在財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商稅收入在財政收入的錢鈔部分中占有重要地位,其重要性僅次于鹽課。”[13](P14-15)作為商業經濟最為發達的南方城市之一,泉州港的商業稅甚巨,難怪政府如此重視泉州及其他沿海港口、海上交通的管理,甚至派兵駐守泉州,為泉州商業經濟的發展提供穩定的環境。泉州商業經濟的繁榮,在某種程度上為維持元朝的統治做了不少貢獻。
第二,大量外商來華和元朝商人出海,密切和促進了中外經濟文化交流和發展。《馬可波羅游記》中載:“印度一切船舶運載香料及其他一切貴重貨物咸蒞此港。是亦為一切蠻子商人常至之港。”[5](P424)可見,中外商人云集于泉州港,從事商業貿易。既然印度等地的商船停泊在泉州港,那必然還會從泉州港出發,返回印度等地。如此,以泉州港為終點和出發點,外國商人往返兩地,促進了中外的經濟交流,帶動了泉州當地經濟的發展。與此同時,元朝商人也在泉州港乘船出海經商。元初,中國泉州商人的足跡遍布海外,促進了泉州商業經濟的發展,也傳播了中國文化。聶德寧在《元代泉州港海外貿易商品初探》中寫道:“元代泉州港對外貿易的范圍極為廣泛。汪大淵的《夷島志略》記載了當時海外有99個國家和地區和泉州有貿易往來。”[14](P80)
這些國家和地區包括東南亞、南亞、西亞、東非等。其中,印度與泉州的經濟往來最密切。《馬可波羅游記》載:“印度一切船舶運載香料及其他一切貴重貨物咸蒞此港。”[5](P424)又有“在此城中見有來自印度之旅客甚眾”[5](P424)。近年來,在這些地區出土了許多中國瓷器、絲綢等物品,充分證實了其與中國商業往來之密切。元初,中國的瓷器、絲綢等是海外貴族才能享受的高檔奢侈品。中國對外貿易處于出超狀態,大大促進泉州商業經濟的發展。此外,中國制造的碗傳至海外,一定程度改變了外國人的生活方式。為保證足夠的商品供應海外市場,泉州手工業和其他制造業相當發達,“元代泉州港在出口到海外各國和地區的外銷商品中,采取了以本地、本省產品為主、外省名牌產品為輔的方針策略。”[14](P80)這極大帶動泉州商業經濟的發展。
泉州是元初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從《馬可波羅游記》中可知,它是海內外商人常至之地。海內外商人的經濟往來無意中導致了不同文化的碰撞,尤其是與當地文化的交融,促進當地文化的發展。莊景輝在《泉州港考古和海外交通史》中指出:“論及元代泉州的繁榮,特別值得述及的是各種宗教在這座城市的傳播和發展。由于蒙古統治者對各種宗教均采取寬容的政策,因此隨著各色人等的僑居泉州,這里也成為世界多種宗教在東方的重要據點,形成了一種多教并存、教寺林立、競相發展的駁雜局面。……在各種外來宗教中,伊斯蘭的勢力最大,其影響于泉州者亦最深。那時居于泉州的伊斯蘭教徒數以萬計,他們有自己的伊斯蘭公會組織,并有禮拜寺六七座。……元代各種外來宗教在泉州的傳播,眾多阿拉伯式、波斯式、印度式、意大利式和中國式的教堂的興修,曾把這個‘東方第一大港’點綴得光怪陸離,更洋溢著濃厚的國際氣氛。”[12](P109-110)因此,泉州文化,包括風俗、文學、藝術、宗教等,與當時內地文化頗為不同,它更為開放和包容,是當時一座重要的國際移民城市,可與當今香港媲美。
四、結語
馬可波羅是一名色目商人,《馬可波羅游記》關于泉州的記載,基本上是宗教和商業方面的內容,介紹了泉州的紙幣、商品、商業稅收、交通等商業信息,贊美了泉州商業的繁榮,可與亞歷山大港媲美;元政府在此港課稅為額甚巨,中外商人的活躍的貿易活動促進了中外經濟文化交流。
[1]楊軍琴.元代商人社會地位的變化[J].齊齊哈爾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8(1).
[2]可·波羅.梁生智譯.馬可波羅游記[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
[3]倪健中.風暴帝國[M].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公司出版社,1997.
[4]陳賢春.試論元代商人的社會地位和歷史作用[J].湖北大學學報,1993(3).
[5]馬可·波羅.馬可波羅行紀[M].馮承鈞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
[6]楊志娟.回回海商集團與元代海洋政策[J].煙臺大學學報,2013,26(3).
[7]馬建春.元代西域人的商業活動[J].暨南學報,2006(3).
[8]陸國俊.中西文化交流先驅——馬可·波羅[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9]宋濂.元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6.
[10]梁凌霄,魏楠,李文文.試論元朝商業繁榮的原因[J].隴東學院學報,2014,25(2).
[11]申友良.馬可波羅游記的困惑[M].臺灣:花木蘭出版社,2012.
[12]莊景輝.泉州港考古與海外交通史研究[M].長沙:岳麓出版社,2005.
[13]陳高華.元代商品初探[J].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7(1).
[14]聶德寧.元代泉州港海外貿易商品初探[J].南洋問題研究,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