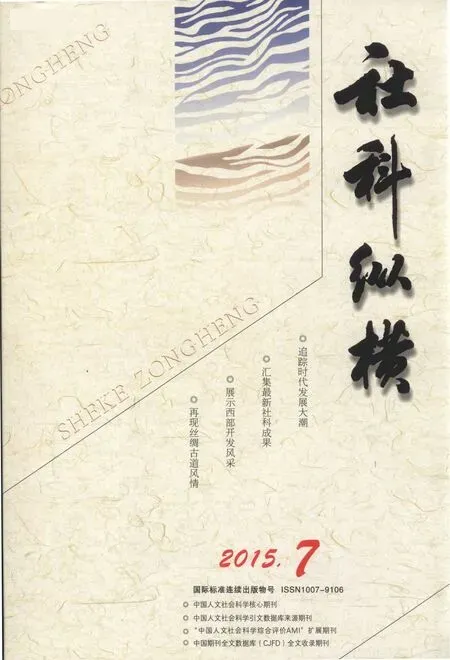徽商與揚州城市發展的互動關系研究
謝超峰
(安徽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 安徽 蕪湖 241002)
揚州于1982年被國家首批公布是歷史文化名城之一。揚州的建成史可上溯至春秋末年魯哀公九年(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修邛城、筑邛溝,由此開始了揚州的歷史。隋開皇九年(589年)設揚州,轄江都,揚州由此得名。縱觀揚州2500年的建成發展史,多呈繁盛景象,從吳王劉濞“即山鑄錢,煮海為鹽”,隋煬帝開鑿大運河,到唐時“揚一益二”的美稱,揚州歷來都是富庶之地,直至清中期,揚州的繁盛勢頭仍未消減。
揚州得天獨厚的地理區位優勢和政府的政策傾向等,使揚州成為歷朝歷代商人趨之若鶩之地。有明一代,《新修江都縣志》有云:“揚州多寓公,久而占籍,遂為士人。而以徽人之來最早,考其時代當在明中葉。揚州之盛,實徽商開之。”《五石脂》中也稱:“徽人在揚州最早,考其年代,當在明中葉,故揚州之盛,實徽商開之。”以上兩則史籍所述中“徽商”指的是徽州府商人,時至明中葉,尚未有安徽省之稱,此地仍處江南省管轄,另所謂“徽商開之”應主要是在康乾時期,徽商對揚州的發展做出過巨大的貢獻。
清后期,揚州的繁盛景象漸顯頹勢。地理區位優勢的失去、政府政策和資本模式的變化、運輸方式的變革、戰爭的干擾等使得揚州在發展的道路上舉步維艱。揚州的衰落,將在揚州投入大量資本,造就過昔日繁華揚州的徽商拖進了歷史的泥潭,造就了徽商的破敗。
一、揚州為徽商的發展搭建了舞臺
在明代,徽州人迫于生計,不得已外出經商,他們本著徽州人特有的堅韌和誠實的秉性,闖出了一片天下。揚州,歷來是商人“藏鏹百萬”、“富比素封”聚集之地,這里自然也成為了徽商足跡的探尋之地。乾嘉時,揚州徽商富甲天下,資本在萬元以下只算是小商,“海內三分寶,徽商藏九分”。大多數徽商將揚州作為安身立命之地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一)揚州成為兩淮鹽政中心
明清時期,“天下鹽課兩淮最多”[1](P406),揚州成為兩淮鹽業的中心。因此,揚州吸引了大量商人麇集,其中徽州商人居多。徽商是“以鄉族關系為紐帶所結成的徽州商人群體”[1](P1),到明萬歷年間,徽商開始與晉商齊名稱雄全國商界,財力雄厚。而支撐徽商事業躍升、富可敵國的產業就是經營兩淮鹽業。
明清兩朝鹽政大體因襲,全國分長蘆、奉天、山東、兩淮、浙江、福建、廣東、四川、云南、河東、陜甘11個鹽區。揚州是兩淮鹽業中心。從明代開始,即在揚州設立管理兩淮鹽業的鹽政衙門,官商結合的鹽業壟斷貿易,揚州從而便以鹽業營運中心的地位而空前繁盛起來。因此揚州吸引了大量商人麇集,其中徽州商人居多。從明代中期到清代乾、嘉,兩淮鹽商以徽商為主體。[1](P189)
揚州作為兩淮鹽政的中心,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其明顯的區位優勢。揚州最早是邗城,春秋末期吳王夫差開邗溝時所建,西漢又稱廣陵。隋稱江都,隋煬帝開大運河后,曾三次南游江都,可謂盛極一時。唐初稱維揚,后改為揚州。古代陸運遠不及水運便捷,揚州地處京杭大運河的南北交通要津,連通水路,因此日益成為重要的通商口岸。明末清初的戰亂,以及清軍揚州十屠之禍,數十萬人喪生,昔日繁華的揚州幾成廢墟。迄至清康乾時期,特別是乾隆帝南游數次巡幸揚州,使得揚州的城市發展進入了一個頂峰。
(二)揚州手工業發展興盛
明清時期揚州手工業也很發達,基本上包括三大類:一類是特種手工業,如:漆器、玉器、鏤金器、刺繡等滿足了揚州城內和關廂達官貴人、大商人、文化名人的需求。另一類是平民百姓的日用品,如農副產品、飲食服務、銅器、紡織、木器等。再一類就是文化發展的需要,如制筆、印刷。總體來講,揚州城市經濟發展與當時全國商品經濟的發展是一致的。眾多的商業行鋪,自早至晚進行繁忙的交易活動,構成一幅揚州城市興旺發達的景象。
清代揚州的雕版印刷業發展程度不容小覷。唐代刊刻《全唐詩》,多達900卷,收錄2200多人共計48000多首詩。除了雕版印刷業,漆器業也是揚州的主打手工業。有明一代,揚州的漆器制造業就已經名噪一時時人稱贊日:“形神俱美真通太,假寐仍期到夢鄉。”到了清代,揚州的漆器制造業達到了巔峰,出現了“漆砂硯”的時代精品。《揚州畫舫錄》云:“夏漆工善古漆器,有別紅、填漆兩種,以金、銀、鐵、木為胎,朱漆三十六次,縷議細錦。”
(三)揚州的造船業和漕運發達
揚州的造船業十分發達。揚州地理位置優越,漕運貨運發達,船廠所造船大多為滿足漕運海運,此外,還制造大量具有日常生活功用和供人消遣游樂的船只,以滿足城市居民伴隨城市發展而不斷產生的生活娛樂需求。
揚州地處京杭大運河與長江的交匯點,商人云集,商業繁盛,過往船只數量大,漕運業發達。僅在清后期,來自江蘇蘇松道、浙江、江西、湖南、湖北通過揚州漕船,就有2659只,運送人丁多達26590人。眾多的船只和人員往來,帶動了運河沿岸提供生活所需的服務行業的發展,同時漕運航船也給揚州帶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豐富物產。清時,漕運航船出行時,除了裝運正耗糧米以外,還可以附帶規定數量的免稅土特產,史稱“土宜”。“土宜”的攜帶數量每朝皆有變更,總量有相當幅度增加:順康年間為60石,清雍正年間為100石,清乾隆年間增至126石,而至清嘉慶年間則為150石,按嘉慶年間通過揚州的漕運航船數量的峰值6000只來計算,由漕運帶給沿岸城市的商品總量就高達90萬石之巨,這還不加上漕運航船上水手舵手私自攜帶商品的數量。揚州是漕運航線沿途的重要城市之一,可以說漕運對揚州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四)揚州城市高度商業化
揚州“地兼三江之利”,“其視江南北他郡尤雄”,“為東南第一都會”。史載“以地利言之,則襟帶淮泅,鎮鑰吳越,自荊襄而東下,屹為巨鎮,潛艘貢能歲至京師者,必于此焉。是達鹽策之利,邦賦枚賴”[2]。揚州如此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自然吸引商人聚集。清康乾時期,“四方豪商大賈鱗集糜至,僑寄戶居者不下數十萬”[3]揚州是一個商業城市,人來客往十分頻繁,服務性行業也就十分發達。如茶社、酒館、客棧、浴室十分普遍。此外,有專供富商大賈以及過往官紳享樂之類街巷,如富春巷、寶和元巷、春巷(茶社)、醉仙居巷、吃吃看巷、長慶巷等。同時揚州又發展成為東南沿海的重要糧食集散市場。糧食交易稅收占揚州整個關稅的三分之一。[3]
在徽商進駐之前,揚州已經高度商業化。不斷增長的居住人口和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帶來了無限商機,同時完備的城市功能服務區和日益增長的商業需求也為徽商提供了發展契機。
二、徽商對揚州城市發展的影響
(一)徽商在揚州的發展概況
明弘治五年,朝廷實行“折色開中”的辦法規定商人可以直接用銀子到鹽運使領取鹽引,徽商直接用銀子兌換鹽引進行貿易,他們依“茂林修竹之盛”,借“新安水利之便”,東出江浙,長期把持揚州鹽業。徽商人數眾多,資本雄厚,固有“揚州之盛實徽商開之”的說法。
揚州最大的商業是鹽業和南北貨,其中鹽業對徽商極具吸引力,也是徽商聚集揚州的主要目的。徽商大規模外出經商既是一種商業活動,也產生了大量的移民。徽商在揚州人數之多、時間之長十分突出。“據統計,由明嘉靖到清乾隆時移居揚州的客籍商人共80名,其中徽人占60名,山、陜各占10名。”[4](P124)“徽商成為揚州鹽商中主要代表,自明中葉以來,由于鹽業的興盛,外地流寓揚州的人口增多,土著與游寓之比為l:19,在游寓居民中,徽人居多,其中徽商又占多數,從人口數量而言,已占重要地位。”[5](P138)在眾多“蜂擁”而至的徽商及其家屬、親友中,有的一代寓居,二代定居,三代以后逐漸成為揚州人;有的“世居揚而系本籍”。徽州呈坎羅家“自灌宗起竟祖孫五代數十人在揚州經商”[1](P218)。因此,近代人陳去病在《五石脂》中說:“揚,蓋徽商殖民地也,故徽郡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鄭、黃、許,揚州莫不有之,大略皆流寓而著籍者也。而徽揚學派,亦因以大通。”[6](P311)這個群體攜帶著巨大的力量不僅在經濟上給揚州帶了巨大的影響,同時在社會生活、文化藝術、風俗習慣等方面都讓揚州城產生深刻、深遠的變化。可以說,徽商的因素深入了揚州社會骨髓之中。鹽商的商業活動已經脫離早期的“客商”的身份,而變成了“坐賈”。
明人宋應星估計,萬歷時揚州鹽業資本為三千萬兩。入清后,汪喜孫估計為七八千萬兩。乾隆三十七年戶部所存庫銀也不過七千八百余萬兩。巨額鹽業資本對揚州城市經濟的繁榮興盛。是一種極大的推動力。揚州繁華以鹽盛,鹽業的興盛帶動了商業、手工業的發展,促使城市面貌的改變,揚州富庶甲天下。[5](P138)
徽商保持執揚州鹽業之牛耳外,還從事其他行業,有的就是徽人開設的:如在乾隆初年,徽州人于河下開飲食店,賣松毛包子,名徽包店;又如藥材業,江藩家族在多子街開設的天瑞堂藥肆,黃履退開設的青芝堂藥鋪;金融行業,揚州的典當業完全為徽商壟斷,城內有名的典當主人為吳老典,以質庫名其家,家有十典,江北之富,未有出其右者。[5](P139)
(二)徽商對揚州發展的貢獻
明清時期,揚州達到鼎盛時期,“揚州之盛,實徽商開之。”徽商為揚州發展作出過巨大貢獻,具體表現如下:
1.推動揚州商品貿易發展
徽商對揚州經濟社會的促進作用,除了長期進行鹽業貿易,還在于徽商兼營其他貿易,拓展揚州市場。包括糧食經營,腌切干貨類交易,典當業以及餐飲業。對豐富揚州市場、豐富百姓生活有很大作用[7](P6),居處飲食服飾之盛甲天下。
明清時期,兩淮鹽業有很大發展。揚州系淮鹽集散地,每年有大宗食鹽由此轉運到湖北、湖南、河南六省。這種轉運經營,利潤巨大。清人汪喜孫估計:匯聚到兩淮鹽商的資本約有白銀七八千萬兩。這個數量,與乾隆時期的國庫存銀大致相等。這些資本主要由秦商(陜西商人)和徽商所有,其中徽州商人占了大部分,李澄說:乾隆時,在揚州業鹽的山西、徽州富商共有一百數十家,這些富商大部分為徽商。[7](P6)
揚州不是商品糧產地,兩淮鹽業人口的口糧歷來都是依靠外運。清初,鹽商兼營大宗糧食貿易情況極少。到雍正年間,隨著捐輸制的實行,開始有鹽商營米糧和設立“鹽義倉”。如雍正八年,“兩淮商人黃光德等具呈,情愿出資將湖南積谷三十余萬石照依原買之價交納湖南藩庫領運,隨地隨時售賣”[8](P155)。這是淮商合法經營糧食業的開端。
淮鹽行銷以湖廣市場最大,湖廣一帶水澤湖泊是漁產盛地,所以行鹽的徽商借機腌切加工業。“楚地素為魚米之鄉,湖魚旺產,亦號豐收,商得資其腌切,藉以完課”。腌制海貨貿易與淮鹽同為鹽商經營的主要項目,如揚州黃巾霸魚市以及沿海其他地區的海貨貿易市場。
鹽典合一也是徽商的一個特色,也是徽商從事鹽業資本得以周轉的中樞性行業。徽商中從事典當業的很多,幾近“全國金融幾可操作”的程度。揚州最為著名的典當商數徽人吳老典,“吳老典初為富室,居舊城,以質庫名其家。家有十典,江北之富,未出其右者,故謂之為老典。”[9](P296)至于鹽商兼營飲食者,也大有人在。如揚州面館,徽州特色沒骨魚面即是徽州“任以煮鹽事”的鹺商徐履安所兼營,“善烹飪,巖鎮街沒骨魚面,自履安始”[10](P228)。
2.推動揚州城市的發展
揚州城幾毀幾建,隨著清政權奠定,揚州城戰后重建也提上了日程。商業的發展更加速了城市的擴建,揚州拓展古城,沿運河沿岸建起了新城;人口不斷增加,“據統計,洪武九年(1376),揚州府有114782戶、丁口574419,到萬歷六年(1578)有147216戶、達到817856,增長了近30萬人。”[11](P262)當然,人口增長也有較大的波動。由于鹽商大量投資鹽業之外的行業,故而也促進了江蘇一帶市鎮經濟的發展。鹽業的發展,促進和加強了揚州與其它地區之間的經濟交往。徽商大批鹽艘載鹽至湖廣等地區,回頭時又載運米及其它貨物。[5](P139)
徽商對揚州城必要設施的修復與拓建也傾注了心力。如“江南范公堤,為沿海之藩籬,揚場之保障,原系商人捐修工程”[12](P468)。此外,徽商出資挖竣運鹽河道,修橋補路等更是屢見不鮮。
(1)大興園林建設。徽商在揚州大建園林,乾隆南巡是直接導致揚州城市大建設的原因。為了接駕,地方政府和揚州官紳,大事張羅,揚州大興園林,從御碼頭到平山堂,真可謂“一路樓臺直到山”,江、程、洪、張、汪、周,王諸園。這些園林除了主人宴會之外,文人墨客以常聚會。園林之外,不僅造景、建筑巧妙,展現藝術。還珍藏字畫,古籍之類,專供觀摩欣賞。有的長期供養文人。“直到解放前,仍有一些商店老板經常款待文人墨客,文人來來往往,老板便邀請到家里款座,以酒食招待,請文人留下墨寶。”[13](P11、12)
徽商江應庚興復平山堂、棲靈寺,建五烈祠、萬松嶺。為迎接乾隆南巡。鹽商在北郊建有虹橋攬勝、長堤春柳、荷蒲燕風、四橋煙雨等二十景,以后又增添綠楊城郭等四景,共二十四景。其中荷蒲薰風屬江園,為徽商江春家園。乾隆賜名為凈香園;四橋煙雨屬黃園,為徽商黃履退別業,乾隆賜名為趣園;長提春柳為徽商黃履昂子黃為蒲修筑。小玲瓏山館為馬日難兄弟所筑,有十二景。[5](P139)
(2)發展公共事業。傳統的中國社會是官紳在社區中發揮著主導的作用。然而,揚州徽商在其城市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亞于當地的官紳。這集中體現在徽商在城市公共事業中的擔當。揚州的育嬰堂、普濟堂等慈善機構,除少數部分是由當地官府撥款建設外,其余大多是由徽州商人捐建。揚州育嬰堂,順治時,由閔世璋等出資建設,康熙十五年,“運使李陳常允閔世璋之子寬及余士觀、汪光元、吳國士、陳蓮等請,定月給銀一百兩”[14](P264)。徽商利用購買的房地產,以其租金、租谷等收入供應福利機構的日常開支。
兩淮鹽政也開始復蘇,徽商資本得以增長。同時朝廷也把商人、士紳的捐輸作為安靖地方的重要手段。康熙十年,兩淮巡卸史席特納奏疏:“淮揚為商鹽根本重地,商民相互依倚,必災民得所,然后地方安靖,商課無虞”[15](P68)。由此開啟的“勸諭捐賑”帶動了大批商人。其中徽商陳恒升等“情愿樂輸,于揚州城外設立四廠煮粥,每月約賑男婦四萬五千余名。”[15](P68)
揚州新舊兩城地勢卑濕,排水溝易堵塞,乾隆二年,徽商公議修浚。徽商馬日琯獨力修浚自廣儲門至便益門街道,其余十四段由他商公修。同時疏浚的還有新舊兩城之官井。徽商鮑志道鑒于南河下自康山西至鈔關,北抵小東門地勢洼下,街衡易積水。他為之易磚為石。[5](P139)
揚州水運還設有救生江船。根據乾隆年間所撰《兩淮鹽法志》統計,兩淮商人從雍正9年到乾隆4年間在瓜洲等地所設或重修的救生船共13只,歲給工銀1025多兩,基本上都由徽商認給。此外,還有義塚和祠堂廟宇的修建。清代兩淮義塚大約出現在雍正年間。徽商黃仁德等“捐資于四郊買地十六處”,“在東關適中之地筑庵居之”[15](P70)。其目的在于掩埋受海潮黃淮水害或者無力葬埋者。此后,徽商在兩淮地區及揚州設立義塚便是常事。《兩淮鹽法志》的記載,徽商捐助的祠廟建筑就有十六處之多。在城市排水方面,徽商往往非常主動,“淮揚新舊兩城,人口稠密,地勢卑濕”,故而“道易淤,一逢淫雨,行路咨嗟,居民墊隘”[15](P71)。乾隆二年淮南總商創議修理,徽屬祁門商人馬曰琯“請于居宅相近之地,自廣儲門起至便益門止,獨捐二千四百兩浚治。其余分十四段,眾商出資公修。”[15](P71)當然了,徽商也往往通過捐輸錢兩得以議敘素封,躋身仕宦之列。
3.推動揚州文化教育的發展
徽商都“賈而好儒”:因為徽州社會兼有“十戶之村,不廢誦讀”[16](P161)的醉心儒學和“十三四歲,往外一丟”[17](P74)的熱衷商業,給了徽州人兩條出路—外出經商和讀書入仕。因而,徽商都樂于投資于教育,更致力培養子弟入仕為官。
(1)捐資修書院。明清揚州很多書院名為官修,實則為商修。如安定書院,“在府治東北三元坊。”康熙元年巡鹽御使胡文學建,雍正十三年,商人“捐資建造,計工費銀七千四百兩有奇”。又如梅花書院,該書院“在新城廣儲門外”,雍正十二年“揚州府同知劉重選與紳商馬曰琯獨立興建,更名梅花書院”[15](P71)。
汪應庚在揚州郡邑學宮傾圮后,捐五萬金重修,雍正年間,淮商又出資七千四百兩重建安定書院。梅花書院為馬曰琯修繕而成。書院學生膏火銀為鹽商供給。居揚徽商對于一些寒士,在經擠上給予支持,生活上予以照顧。
(2)刻書藏書豐富。如黃履最兄弟四人,徽商也,以鹽策起家。履最家住揚州康山南,筑有易園,刻《太平廣記》、《三才圖會》二書;黃履退排行第二,家住山南,有十間房花園,考訂藥性,刻有醫藥著作:《圣濟總錄》、《葉氏指南》,又刻有《四橋煙雨》、《水云勝概》二段。揚州刻書業十分發達,這僅僅是其中個別事例而已。刻書業發達對傳播文化、普及文化起了積極作用,同時也使一些著作保存下來,對后世文化事業發展作出貢獻。[3](P7)
鹽商自刻或為文士刻書。馬氏兄弟、江春、黃最、黃履退等都是這樣。馬曰琯刻《說文》、《玉篇》、《廣韻》、《字鑒》等書,謂之“馬板”。徽商中不少人富有藏書。清代揚州徽商中藏書數量最多的要數程晉芳、馬氏兄弟和汪揖。程晉芳購書五六萬卷,當時被人認為首屈一指。馬氏兄弟在小玲瓏山館筑一叢書樓。前后二樓,藏書十余萬卷,共百櫥。[5](P140)
袁同禮《清代私家藏書概略》說:“有清一代藏書,幾為江浙獨占,考證之學盛于江南,蓋以此也。”[18](P63)揚州是江浙交通重鎮,其藏書刻書在全國名列前茅,具有雄厚經濟實力和推崇儒學的徽商也充當了重要角色。祁門籍鹽商馬曰琯、馬曰璐兄弟的刻書在徽商中更是獨領風騷,其雕刻因精審而被譽為“馬版”。馬氏“小玲瓏山館”為當時學人借閱之所。《清史稿》“鶚搜奇嗜博,揚州馬曰琯小玲瓏山館富藏書,鶚久客其所,多見宋人集”,“皆博洽詳贍”[18](P65)。徽商藏書以饗士人,接濟讀書人,可以說是古代養士遺風。
與刻書先比,徽商的藏書也絲毫不差。其時,揚州規模較大的藏書家多數徽州籍商人。如:程晉芳,歙縣人。《清稗類鈔》有:“時兩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多蓄聲伎狗馬。魚門獨愔愔好學,服行儒業,罄其資以購書,庋閣之富,至五六萬卷,論一時藏書者莫不首屈一指”[18](P295)。藏書刻書本身也是搜書、鑒別的過程。沒有一定的基礎和學識是很難的。在這個過程有興趣于學的徽商,不斷汲取學養,卓然成為一代學者的不乏其人。嘉慶十六年江藩撰成《國朝漢學師承記》,意圖以師生或師友的關系為主線構建清代漢學譜系,這是公開對清代漢學家的一次門戶檢閱,其著作以傳記的形式記錄漢學家的生平資料和主要學術觀點,被視為帶有學術史性質的傳記集成。而程晉芳赫然在編輯者之列,此亦從另一個側面凸顯出程晉芳的樸學地位與影響。
(3)帶動樸學的發展。清代,揚州地域一些名人雅士將名物訓詁和考實求真的方法運用在了古籍整理和經史研究工作上面,引領學術潮流,形成中國學術發展史上的清代樸學[19]。清代樸學大家王念孫、王引之、汪中、焦循、阮元等人皆是揚州人士,他們學術思想建樹超群,獨具特色,將乾嘉漢學發展到一個高峰,由于這些大家的地緣因素和引領主流學術的特點,當今學術界習慣將以他們為代表的學術流派成為“揚州學派”。“揚州學派”地域界限為二州六縣,時間橫跨乾隆之民國初年,研究內容為樸學。“揚州學派”學者思想淵源可追尋至戴震學術思想,身為揚州后學的劉師培在《南北學派不同論》中指出:“戴氏弟子舍金壇段氏外,以揚州為最盛。高郵王氏傳其形聲訓故之學。王氏作《廣雅疏證》,其子引之申其義,作《經傳釋辭》、《經義述聞》,發明詞語之學”。
“揚州學派”的蓬勃發展,引起寓居于此的徽商的注意。徽商兼具雄厚的財力和“賈而好儒”人格特點,大力發展針對樸學的刻書和藏書業績,為清代樸學的發揚提供了支持。就刻書而言,徽商捐資幫助清朝政府雕版印刻《全唐詩》、《欽定佩文齋詠物詩選》、《御選歷代詩余》、《佩文齋書畫譜》、《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淵鑒類函》、《佩文韻府》、《欽定全金詩》等。除了援助官方雕版印刻以外,徽商私自雕版刻書的想象也很普遍。如祁門籍徽商馬氏出資私刻的《宋本韓柳二先生年譜》、《干祿字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等,因其雕琢精良,作品質量上乘而被世人稱為“馬版”。除卻刻書,徽商的藏書業也很發達,《清稗類鈔·義俠類》有云:“時兩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多蓄聲伎狗馬,服行儒業,罄其資以購書,庋閣之富,至五六萬卷,論一時藏書者莫不首屈一指。”書中所言程氏,就是歙縣籍程晉芳。祁門籍徽商馬氏藏書頗豐,史料記載,“兩淮馬裕家藏書”在《四庫全書》整理期間,共獻書372種,包括經部56種、史部121種、子部43種、集部152種。徽商陳登原所言:“吾人敢為一言,即吾人欲明清學之勝者,雖知其由多端,更不能與藏書之盛莫無關系”[20](P64)。調班刻書和藏書業是互為依托,互相促進的,兩者不可分割,而將這兩者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正是揚州徽商。
徽商對刻書藏書的熱情,促進了“揚州學派”和清代樸學的發展,也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流傳和繼承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4.推動揚州城市社會風俗的變革
鹽商為了家庭娛樂與欣賞,以及招待官員、士紳的需要,備有家庭戲班和樂隊。如江春有德音、春臺兩班。四川魏長生投江春,演戲一出,贈以千金。有的家庭戲班有二三百人之多,單戲箱就值二三十萬兩。鹽商排演一出《桃花扇》,費銀十六萬兩之多。在鹽商財力支持下,揚州成為全國戲曲中心之一。它對于提高揚州知名度,推動揚州地方文化事業的發展,使揚州歷史文化在原有基礎上得以提高,都有著不容忽視的重大作用。極大地推動了揚州地方文化的發展與繁華。清代揚州成為全國文化交流重要中心。南北文化中的不同流派在此碰擊相撞,產生出一批兼具南北文化優點的學人,從而推動全國文化的發展。[20](P140)
徽商致富之后,由儉入奢,漸染揚州繁華的都市生活,消費觀發生了重大變化,在飲食和服飾上表現的最為明顯。揚州的徽商大建園林,以園林為場所而開展的詩文會和戲劇表演也成為徽商生活的一部分。園林之內收藏大量書籍、字畫,刺激了揚州文化市場,雖然存在一定的畸形消費,不過客觀上來講對學術的繁榮有著促進意義,一時揚州博物之學大興。
(三)徽商在揚州的負面影響
兩淮鹽商與鹽官相率為偽,通同舞弊,參與干涉地方政事,影響鹽業政策的實施。種種情弊,敗壞了地方政事,影響極壞。[5](P141)其間徽商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徽商“善行媚權勢”[21]。鹽商中的總商,“凡鹽事之消長贏縮,以逮公私百役巨細,無所不當問。”[22]他們中的大部分為徽商,如江春“身系兩淮盛衰垂五十年”,擔任總商四十余年,“百萬之費,指顧立辦”[23]。
奢靡之風莫盛于商人。衣服屋宇窮極華靡,飲食器具備求工巧,徘優伎樂恒舞酣歌,宴會戲游殆無虛日,金錢珠貝視為泥沙,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越禮犯分,閣知自檢,驕奢淫佚相習成風。各地鹽商皆然,而淮揚為尤甚。”這種“奢靡性消費阻礙了揚州城市生產的發展,助長了社會上奢靡之風的盛行。”[24](P141)雍正曾在一道上諭中說:“奢靡之風莫盛于商人。聞各省鹽商內實空虛而外事奢靡,衣服屋宇窮極華靡,飲食器具備求工巧,俳優伎樂恒舞酣歌,宴會戲游殆無虛日,金錢珠貝視為泥沙,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越禮犯分,罔知自檢,驕奢淫佚相習成風。各地鹽商皆然,而淮揚為尤甚。”[25]這個鹽商派,歌舞童女,衣服肴撰,日費以數萬計。他們夸富斗靡,如以萬金買金箔,攜至金山塔上,向風飏之,頃刻而散。這種奢靡性消費阻礙了揚州城市生產的發展,助長了社會上奢靡之風的盛行。當時人孫枝蔚說:“廣陵不可居,風俗重鹽商。”[26]在鹽商的帶動下。城內“誰家年少好兒郎,岸上青駱水上航。猶恐千金揮不盡,又抬飛轎學鹽商。”[27]鄧之誠在論述此奢風時說:‘傳之京師及四方,成為風俗。奢風流行,以致世亂。揚州鹽商與有責焉。”
三、徽商的式微與揚州城市的衰落
清中期,揚州依然是清后期,揚州的繁盛景象漸顯頹勢。地理區位優勢的失去、政府政策和資本模式的變化、運輸方式的變革、戰爭的干擾等使得揚州在發展的道路上舉步維艱。揚州的衰落,將在揚州投入大量資本,造就過昔日繁華揚州的徽商拖進了歷史的泥潭,造就了徽商的破敗。
(一)揚州地理環境的變化
揚州地處長江與京杭運河“T”字型交匯處,溝通南北的運河和連接東西的長江,兩條水道是其生長發展的命脈所在。嘉慶《揚州府志》序中記載:“東南三大政,曰漕,曰鹽,曰河。廣陵本鹽莢要區,北距河、淮,乃轉輸之咽吭,實兼三者之難。”水運因其省時、省力,運輸成本低等優點,一直是短途運輸的主要方式。京杭大運河是明清時期揚州興旺的大動脈。然而,正是由于揚州等城市對大運河的依賴,一旦大運河出現交通運輸阻礙問題,就會帶來致命的影響。大運河向來水源不豐,常年從黃河引水,因黃河泥沙過多,對大運河造成淤塞。近代以來,常年的運河治理由于諸多原因無法進行,導致漕運體系趨于瓦解,同時鐵路的興起與運輸功能的喪失,導致揚州等城市的傳統商業地位的逐步下降。京杭大運河交通運輸便利的失去,對揚州手工業的打擊是巨大的,由于京杭大運河淤塞斷行,使得揚州傳統手工紡織產品失去市場,民國《月浦里志》有云,該鎮在同治后,“商鋪以酒、米、南貨為最,并有兼營小熟豆餅、洋紗者,花行、布行不過一二,率皆客商開設,土人鮮有投資者”。那些投資在手工紡織業的徽商也因此衰敗。
由于京杭大運河失去了運輸的功能,大宗商品,尤其是鹽的運輸方式從以往的水路改成陸路,后雖然改為海運,但短時期內還是使得徽商的商業運營成本提高,加劇徽商的衰敗。
(二)“票鹽制”改革對其影響
作為徽商主體的鹽商,搭乘明清政府“綱鹽制”的順風船,壟斷兩淮鹽引,實力不斷壯大。隨著兩淮鹽業壟斷市場的形成,兩淮鹽政腐化的現象暴露出來。官商勾結,政府打著“官督商銷、官運官銷、官運商銷,并據以變通之”的旗號為商人提供服務,商人從政府那里獲得鹽引和鹽業專營權利,政府借商人之手和經營才干,從而獲得穩鹽利收入,同時專商憑借專賣的經營特權也賺取了豐厚的壟斷鹽利。在封建政府的庇護下,鹽商肆無忌憚地高抬鹽價,坑害百姓。鹽價在官商“雙簧”作用下越抬越高,百姓苦不堪言。同時官商勾結也助長官場腐敗和貪污邪氣現象的滋生。
乾隆三十三年,新任兩淮鹽政發現此前的二十年里,官吏們私自扣下的引銀竟達一千多萬兩。上奏之后,乾隆帝震怒,許多官吏和徽州鹽商被逮入京。這是徽商遭受的第一個重大打擊。另一個致命打擊是道光十二年兩江總督兼兩淮鹽政陶澍首先在淮北“廢引改票”,實行票法。陶澍親赴海州調查研究,廣泛聽取綱商、灶戶、鹽官、鹽民等各方面的意見,決定實施“改道不改捆,歸局不歸商”的改革原則,并制定“只論鹽課之有無,不問商賈之南北”為核心內容的章程十條。陶澎的“票鹽制”改革取得成功,道光三十年,兩江總督陸建瀛將“票鹽制”在淮南進一步推廣。
改革的結果是徽商們失去了對鹽業的壟斷權。加之嘉道年間,長期的農民起義使清朝財政日益窘困,兩淮鹽商承受的攤派因此不斷加重,阻礙了正常的商業活動。鹽商的衰落,徽商主體受損,他們在揚州的投資和經營活動日漸稀少,影響了揚州的發展。
(三)徽商資本運作模式的落后
徽商的資本運營方式從本質上來說是封建小農經濟。徽商在攫取巨額商業利益以后,不是將資本用于擴大再生產,而是用于奢靡生活享受上面。大多數徽商“致富”后,原來吃苦耐勞、不畏艱險的優良品質蕩然無存,蛻變成了貪圖享樂、驕奢淫逸,他們開始大肆鋪張、修建房產、買田置地,將獲取的商業利益用于土地投資和生活享樂,由此導致了商業資本的進一步萎縮。清咸豐年間,徽商汪定貴花金百兩、白銀八十萬兩在家鄉修建豪宅承志堂。全宅有七個樓層、九個天井,房屋60間,占地2100平方米,建筑面積3000平方米;正廳前后三開間結構、兩進回廊,前有天井、外院、內院,后有書廳、花園、魚塘,還有娛樂廳、麻將廳、鴉片廳、小姐樓閣和保鏢、女傭住室等等,整幢建筑裝飾考究,磚、木、石三雕俱全,其徽商巨富的鋪排遺風可見一斑。徽商追逐功名利祿和氣勢排場,是大量社會財富消失,影響商業的擴大再生產,造成商業資本嚴重匱乏,徽商難以適應市場的激烈競爭而走向衰落。
徽商專注于物質享受,將大量金錢投入到奢侈生活享受上面,徽商的優良品質失去和商業資本的流失帶來徽商衰敗的后果,也因此影響揚州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加速了揚州的衰落。
(四)長三角經濟區的崛起
近代上海開埠以后,逐漸發展成為區域的工業、商業、貿易和金融中心,揚州等傳統工商業城市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經濟區域中,經濟地位下降,居于從屬地位。隨著鹽商消費集團的破產,揚州城市商業技能幾乎喪失,原先的服務行業也大幅萎縮,人口外流,城市社會生活失去活力,城市建設也因資金缺乏而無法開展,文化更是萎靡不振。上海作為長三角經濟中心也拉不動揚州的經濟,揚州既沒有作為經濟支柱的手工業,也沒有發達的農業經濟作為支撐。從而在中國經濟、社會大變動、大沖擊的背景下,它無法實現內部經濟結構的調整。也就是說,近代隨著徽商的破敗,揚州也百業凋零,江河日下了。
(五)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大肆入侵
鴉片戰爭之前,西方經濟入侵勢頭稍弱,西方商品輸入根本動搖不了中國上千年形成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根基。但是在鴉片戰爭之后,中國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經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西方列強除了在中國傾銷鴉片以外,還通過協定關稅和商品專營等手段,大量出售本國商品,同時西方列強還大量地搜括中國的廉價的農產品。西方列強侵略后形成的五口通商口岸及東南沿海,開始成為西方商品市場和原料供應地。他們強迫中國納人資本主義市場。“茶的出口,1843年大致是1300多萬斤,1855年,是5800萬斤。十二年間增加了5倍多。絲的出口,1843年是2000包,1845年超過5600多包。十二年間增加20多倍。”[28]
西方經濟入侵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破壞了城市的手工業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使得包括揚州在內中國沿海貿易城市的剛成雛形的商業運營模式不復存在,大量的手工業者破產,徽商資本受損嚴重,影響了揚州的發展壯大。
(六)中國近代內外戰亂的影響
戰爭作為一種特殊的超大規模的暴力行為,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破壞是十分巨大的,而戰爭往往以城市為主要攻擊目標,成為戰爭主戰場的城市,一般都難逃衰敗的命運。清兵入關,清王朝定鼎燕京后,揚州連接兩次遭受浩劫。先是清兵南下前,南明福王部將劉澤清、高杰縱兵焚燒;后是順治二年(1645年)4月,多鐸率領清軍大舉南下,圍攻揚州,破城后大師屠殺居民,死亡數高達八十萬,明兵部尚書史可法寧死不降,最后兵敗被俘,不屈犧牲,史稱“揚州十日”。
太平天國運動可以說是揚州衰落的轉折點。1851年太平天國運動爆發,揚州受戰爭影響,長江一線交通堵塞,淮鹽引地喪失;太平軍三次攻占揚州城,這場戰爭的直接后果是人口的劇減和城鎮的毀滅。據光緒《兩淮鹽法志》記載:“商人居鎮、揚二郡者,十有八九亦遭荼毒”。有學者估計,至1893年,揚州城市人口可能只剩下10萬人。太平天國運動,持續十幾年的戰亂波及長江南北,由廣西而湖南,由湖北而江西,牽連安徽,江蘇,浙江,最遠達山東、直隸。天京變亂之后,太平軍由功而守,與清軍進入了長期的相持,安徽成為主要的戰場。不間斷的拉鋸戰給徽州帶來深重的災難,不論官軍還是叛軍,“縱兵大掠,而全郡窖藏一空”[24](P479)。《徽難哀音》中記載了一位從漢口返徽最終在逃難過程中餓死在山中的“巨富”汪登載[29](P479)。在太平軍、湘軍和團練武裝的反復搜刮下,徽州的財富遭到巨大損失,很多徽商經過長期經營積累下來的財富和資本喪失殆盡。戰亂又使徽商大量死亡,徽商從業人員大為減少。這既導致了徽商的衰落,也對依賴徽商資本的揚州打擊很大。原本苦力支撐的貿易局面,逐漸走向尾聲。太平天國運動對揚州衰落的影響是巨大的,它使得揚州依托運河的交通優勢徹底喪失,漕運大受影響。作為揚州重要經濟支撐的兩淮鹽業遭受重大打擊,揚州的其它商業部門也因長江航路受阻而大受影響。作為揚州商人中資本最為雄厚的徽商在戰爭中喪失了大量資本,從業人員也大量死傷,使得揚州商業后繼無人加劇了揚州的衰落。
[1]張海鵬,王廷元.徽商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
[2]張世浣,嵩年.揚州府志[M].1810.
[3]江太新,蘇金玉.明清揚州繁華之探討[J].鹽業史研究,2006.
[4]薛宗正:明代鹽商的歷史演變[J],中國史研究,1980.
[5]朱宗宙:徽商與揚州[J].杭州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
[6]黃山市徽州區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徽州區文史資料[M].2007.
[7]江太新,蘇金玉.明清揚州繁華之探討[J],鹽業史研究:2006.
[8]蔣建平.清代前期米谷貿易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9]李斗.揚州畫舫錄[M].北京:中華書局,1960.
[10]尹秀芝,趙宗乙.中國古代民俗(第三冊)[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7.
[11]朱福烓.揚州的歷史和文化[M].揚州文物局印制,1982.
[12]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江蘇省通志稿·都水志[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13]張南.老揚州遺事[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
[14]劉建民.法治與社會論叢(第1卷)[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
[15]劉淼.清代前期徽州鹽商和揚州城市經濟的發展[J].安徽史學,1987.
[16]卞利.明清徽州社會研究[M].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
[17]方靜.魅力績溪[M].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06.
[18]方盛良.揚州徽商與清代樸學述略[J].文藝研究,2006.
[19]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前言[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20]昭梿.嘯亭雜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0.
[21]李維禎.大泌山房集卷[M].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中心,1993.
[22]鮑琮.棠椒鮑氏宣忠堂支譜卷[M].1805.
[23]王定安.兩淮鹽法志卷[M].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7.
[24]王廷元,王世華.徽商[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25]楊選,陳暹修.兩淮鹽法志[M].1551.
[26]孫枝蔚.溉堂前集[M].山東:齊魯書社,1997.
[27]董偉業.揚州竹枝詞[M].1874.
[28]陳旭麓.近代代中國近代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29]李明.明清蘇州、揚州、徽州三地風俗的互動互融——兼談“蘇意”、“揚氣”、“徽派”[J].史林,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