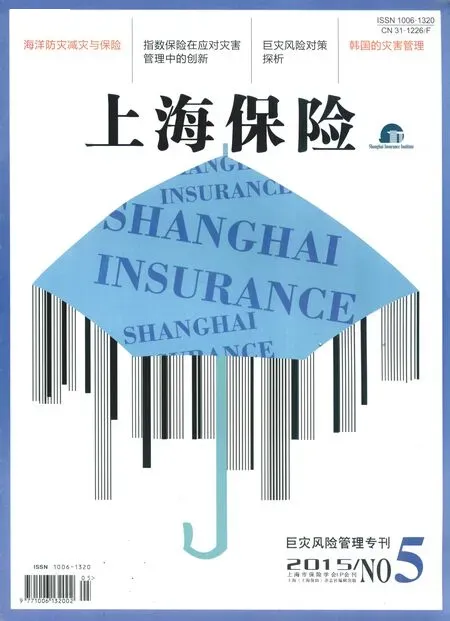恐怖主義災害風險管理與保險應對機制
薛思帆
復旦發展研究院中國保險與社會安全研究中心
?
恐怖主義災害風險管理與保險應對機制
薛思帆
復旦發展研究院中國保險與社會安全研究中心
一、恐怖主義災害現狀與特殊性
(一)恐怖主義災害的現狀
恐怖主義災害是全球共同面臨的重大安全威脅與挑戰。美國國務院發布的《2013年度全球恐怖主義報告》顯示,2013年全球共遭遇9707次暴力恐怖襲擊,超過1.78萬人因此喪生。我國恐怖事件在近年來也有數量增加、損失增重的跡象。根據經濟與和平組織(The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發布的全球恐怖主義指數(Global Terrorism Index),在被測算的158個國家中,中國的恐怖主義指數排名在2002年到2007年間基本維持在第40至第50位左右,而在2008年上升到第33位,2009年的新疆烏魯木齊“7·5事件”使得該排名上升到第15位的峰值,并且始終處于高位(2013年中國排名第25位)。
(二)恐怖主義災害的特殊性
恐怖主義襲擊的目標通常是普通的民眾或政府機構(如警察局等),通過暴力傷害非直接目標以制造恐怖氣氛,從而達到其特殊的政治、經濟、宗教目的。因此,恐怖主義災害往往會造成嚴重的經濟、社會影響,是一種十分特殊的人為巨災。人為巨災的損失通常可能由“加害人或受害人自己承擔損失、政府賠償和商業保險”幾種補償方式。對于恐怖主義災害而言,恐怖分子不可能有意愿承擔任何損失;由于恐怖事件惡劣的社會影響,往往會由政府出面成為賠償損失的主要承擔者。但這種方式往往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政府往往難以制定合理的標準且效率低下;如果將恐怖主義災害完全排除在商業保險以外,也不利于保險業發揮其應有的規避風險的作用,因而商業保險對恐怖主義災害的風險保障顯得十分必要。而另一方面,由于恐怖事件的特殊性,導致保險難以發揮其作用。尤其是重大恐怖事件,基本不符合傳統的可保條件,因此必須要設計特殊的保險應對機制才能應對此類風險。
本文首先通過研究文獻論述恐怖主義災害的各方面風險特征、風險管理目標和手段,然后主要討論應如何設計重大恐怖事件的保險應對機制。
二、恐怖主義災害的風險特征
(一)恐怖主義災害的社會特征
糟糕的社會經濟情況(低投資、消費和經濟開放程度)會對恐怖主義更有“吸引力”(Andreas Freytag, Jens J. Kru?ger,2011)。但恐怖襲擊與貧困之間成很明顯的非線性關系。當國民收入達到一定水平之后,再增加國民收入對恐怖主義幾乎沒有影響(Enders, Walter; Hoover, Gary A.,2012)。
21世紀以來,經濟不平等與對現狀的不滿,以及世界視角下在全球化過程中取得的不利地位成為恐怖主義的原因之一(Graham Bird, S. Brock Blomberg and Gregory D. Hess,2008)。甚至富裕的國家更可能成為恐怖分子襲擊的對象(Krueger, Alan B. and Laitin, David D.),比如美國就深受恐怖襲擊困擾,近年來歐洲也再度發生多起影響巨大的恐怖襲擊。
所以,恐怖主義災害的社會特征,首先表現為恐怖主義的全球化發展和轉移。如今,由于科技和媒體的發達,我們很難找到一個地方能夠完全和其他地區的恐怖主義隔離開來,當地的恐怖組織也很容易就能找到外界的資源和支持,找到外界的“同盟軍”,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伊斯蘭極端勢力對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的恐怖襲擊。
這使今天的反恐怖主義斗爭不僅僅與一個國家本身有關,更是一個復雜的國際問題,需要各國互相之間的合作與平衡。我國也存在這方面的隱患。
(二)恐怖主義災害的經濟特征
恐怖主義災害的發生顯然會帶來經濟損失。這種損失一方面可以是直接的損失,比如恐怖事件造成的財產損失、人身傷亡導致的人力資本損失等。例如發生在2014年7月28日新疆喀什地區莎車縣的一起恐怖事件,造成37人死亡,13人受傷,關于財產損失報道為“31輛車被打砸,其中6輛被燒”,這些可以認為是該事件帶來的直接損失。又如9·11事件中,其造成的直接損失占美國當年GDP的0.06%(Becker and Murphy,2001)。
另一方面,恐怖襲擊帶來的間接損失要大得多(Abadie and Gardeazabal, 2003),具有很長的“尾部”或持續期。比如在前述的新疆恐怖事件中,我們還需要考慮警察、安全等方面的成本。同樣,9·11事件之后,有研究估算其間接影響(長期影響)是美國GDP的0.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1)。
恐怖襲擊會通過影響社會的安全成本、不確定性(Alberto Abadie, Javier Gardeazabal,2008),通過各個行業之間的交互作用和乘數效應,以及通過引起人們情緒的恐慌和社會的不安寧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Blomberg, Hess & Orphanides(2004)指出,恐怖主義可以通過破壞生產投入,將資源從經濟生產轉向提高國土安全,并通過擾亂個人和公司的消費計劃以干擾經濟活動來減緩經濟增長。Abadie & Gardeazabal(2003)估計,恐怖主義帶來的經濟增長減緩可達10%。還有研究認為,恐怖主義通過影響一國的資本、基礎設施、安全、不確定性來影響經濟(Khusrav Gaibulloev & Todd Sandler,2011)。恐怖事件還會帶來人們精神的壓力和恐慌,嚴重的恐怖主義災害會對社會政治決策、體系造成影響,這種間接影響更難以測算。
雖然恐怖主義災害保險本身難以賠償更為龐大的間接損失,但其對于穩定社會生產力和民眾情緒,從而減少間接損失的發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假如沒有恐怖主義災害保險保證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遭遇恐怖襲擊時能獲得經濟上的保障,面對潛在的風險,企業就會對繼續運營持觀望態度,影響社會經濟發展。而對于醫院、學校等公共部門更是如此。
(三)恐怖主義災害的風險特征
恐怖事件具有發生時間與地點不確定的風險特征。筆者收集了2001年到2014年底發生在中國境內的105條恐怖事件記錄,其中發生在新疆的有55次。襲擊目標含普通市民、財產的有43次,警察、軍事機構27次,機場、公交等交通系統15次,政府機構7次,其他23次。恐怖事件的發生次數、傷亡人數在各年度差異非常大,往往與社會政治與重大事件相關,沒有統計規律可循。恐怖事件發生的地點分散在我國大多數省份,雖然發生頻率有一定規律,但由于每一次恐怖事件都可能給當地或更大范圍造成惡劣的影響,故發生次數少的省份也不無例外地加強反恐防范。發生的具體地點固然與其犯案的難度和目的有關(比如普通市民較多、實施起來較為容易、能夠引起恐慌等等),但仍然呈現出目標廣、難以確定的風險特征。
與地震、臺風等自然災害相比,恐怖事件的發生更加缺少規律性。恐怖分子可能只制造一些較小的襲擊,甚至沒有傷亡人數,但也可能經過預謀、策劃,制造如烏魯木齊“7·5事件”那樣極端嚴重的恐怖事件。由于恐怖事件是經過設計的,所以此類事件的風險防控難度比較大。恐怖事件所呈現的風險不確定性主要是由于恐怖事件的屬性使然。因為恐怖分子必須要不斷地在不同時間和地點制造恐怖事件,才能引起更大關注、制造更多恐怖氣氛;同時,恐怖組織和反恐部門處于博弈的狀態,一個地方的戒備加強可能導致另一個地方恐怖事件的發生;再加上報復社會性質的恐怖事件極具個體因素,加大了恐怖事件風險防控的難度。
三、恐怖主義災害的風險管理
(一)恐怖主義災害的風險管理目標
恐怖事件的社會、文化與經濟特征決定了對恐怖事件進行有效的風險管理,主要是為了減少恐怖事件對社會穩定、文化沖擊和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由此而采取的一切風險檢測、預警、預防、準備、應對、恢復、總結等風險管理活動。
恐怖事件的風險管理是為了實現以下目標:恐怖主義的可監測、可控制、可評價;減少由于恐怖事件的不確定性而造成的社會恐慌和不安;減少恐怖事件發生時和發生后的人身、財產直接損失和社會恐慌造成的間接損失;加強和重視對恐怖主義的研究,引導民眾反恐意識和提高對恐怖事件的風險管理能力,促進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培育抑制恐怖主義生存的土壤。
(二)恐怖主義災害的風險控制手段
對恐怖事件進行風險管理可以采用風險控制和風險轉移兩種傳統的風險管理手段。風險控制是指在恐怖事件具有充分不確定性和無法回避的基礎上,通過制定計劃和采取措施降低發生的可能性或者減少實際損失和影響。
在風險控制方面,為了降低恐怖襲擊發生的概率,首先應該建立健全恐怖事件風險的預警機制、處理機制和善后機制。第一,應以“國家安全委員會”為龍頭,統籌國家反恐工作。反恐涉及多個系統、多個部門職能。建議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統一部署下,設立省級機構,指揮協調軍隊、安全、公安、武警、交通、衛生、民族、宗教、民政、新聞等職能部門行動,形成反恐合力。第二,要建立健全相關立法,明確恐怖事件的處理辦法、賠償機制,讓人們能夠對損失有所準備,不至于由于害怕而影響投資。例如2015年2月,我國《反恐怖主義法》草案二審稿對恐怖主義等定義進行了更清晰的界定,對反恐怖主義的制度措施進行了完善。第三,加強對特殊作戰力量的培養。特殊作戰力量裝備精良、技能全面、反應快速,在恐怖事件發生時,或解救人質,或迅速平息事件,適應全天候作戰要求。第四,應該協調新聞、民政、衛生等諸多部門,對受傷害人群給予合理的補償,努力將社會不良影響降至最低。第五,培養民眾的反恐意識和反恐教育,提高民眾應對恐怖襲擊的應急能力。民眾首先要克服對恐怖襲擊的恐慌心理,避免因恐慌帶來的秩序紊亂加大反恐的難度。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政府建立一套完備的預警和應急機制,并且做到信息發布及時和公開透明。事實證明,如果不對恐怖事件進行及時和充分的披露,會加大民眾的恐慌心理,擴大恐怖事件的負面影響。第六,通過適當的媒體引導,讓民眾和外國商人、旅客能夠切實地看到,中國能夠保護所有公民和友人的人身和財產安全。
四、恐怖主義災害的保險應對機制
除了對恐怖主義災害進行風險控制以外,風險轉移也是重要的風險管理手段。其中,保險是最為重要和被國際上廣泛接受的風險轉移手段。比如美國9·11事件共造成損失約800億美元,保險業所承受的損失接近50%。然而,保險業在恐怖事件風險中發揮的作用仍有待提高。以美國為例,在9·11事件以前,雖然美國遭受的恐怖襲擊較多,但由于年均恐怖事件導致的死亡人數和直接損失與其他如自然災害或交通事故相比較小,在保險市場上,直接保險商以很低的保險費率承擔了恐怖風險,甚至有的保險商以零費率在合同中加入了承擔恐怖事件風險損失的條款,相應地,再保險商也以這樣的費率承擔了恐怖風險。9·11事件成為了有史以來保險損失最為慘重的災禍,導致美國保險業有市場記錄數據以來的第一次凈虧損。9·11事件使得保險業對待恐怖事件風險的態度發生了根本的轉變,美國絕大多數保險公司都迅速撤離了恐怖風險承保市場,或者將恐怖風險的承保費率提高到投保人難以承受的程度,國際再保商也作出了類似的反應。
(一)恐怖主義災害的可保性
根據Kunreuther(2003)對恐怖事件保險的探究,可保性必須具備兩個首要條件:第一,能夠測算出或估計出該事件可能發生的概率和可能的損失程度;第二,能夠為每一個階層潛在的客戶制定保險費率。對于第一個條件,保險精算需要運用過去該種事件發生的統計資料和數據進行分析。其中能否刻畫出承保損失的超概率曲線是判斷是否能估計其發生概率的一種方法(許閑、張涵博,2013)。就巨災而言,恐怖事件往往比自然災害和核基地事故更難以進行損失超概率曲線的度量,因為某一地區所能發生的恐怖事件往往非常少。而且,政府對反恐的投入、國際環境的變化等等都會影響恐怖事件發生的概率和后果,增加了測算的難度。簡而言之,恐怖事件相對于自然災害而言干擾因素更多,使得保險公司在費率厘定上存在一定的難度和不確定性。實際上,由于恐怖事件的風險發生和損失存在不確定性、可能產生保險的逆選擇問題、投保人的道德風險和恐怖事件具有關聯損失多等特點,使得恐怖事件的可保性存在一定的疑問。
恐怖事件的數據相比于自然災害更難以準確地收集。第一,對恐怖事件的定義本身還沒有統一;第二,政府往往出于機密、安全等因素,會刻意地不公布具體的恐怖事件數據,這也為保險產品設計制造了困難。正是由于以上的問題,完全由商業保險公司來承擔恐怖事件的風險往往難以形成有效的市場,正如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它們往往采取政府與私營公司合作的形式開展恐怖事件的保險。
(二)恐怖主義災害保險的國際經驗
在9·11事件發生以后,美國保險和再保險市場對于恐怖事件的資金投入驟減,保險公司要么完全不提供恐怖事件風險保障,要么把費率提高到投保人難以承受的高度。面對這樣的局面,美國政府很快發現,缺乏保險保障使得一些大型工程停滯或延期,經濟恢復遇到困難。由此,2002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恐怖風險保險法案(TRIA, Terrorism Risk Insurance Act),旨在通過避免市場崩潰,保證保險廣泛的可獲得性和可支付性,以保護消費者的利益。同時為私人保險市場提供一個過渡時期,使其從9·11的混亂中穩定下來,恢復對恐怖風險保險的定價,并建立足夠的準備金來面對未來的損失。其他國家,如德國、英國、法國、新加坡等都建立起了自己的恐怖事件風險保險體系,并且與美國一樣,主要是通過政府與私人保險業合作的方式提供恐怖事件風險保險。
美國《恐怖風險保險法案》自2002年出臺以來,分別在2005年、2007年和2015年獲得了三次延期。在最后一次延期獲得批準前,該法案引起了各方的激烈爭論,主要聚焦于“政府是否在用納稅人的錢來彌補商業保險公司在恐怖主義保險上的虧空”的問題。經過討論,該法案終于在2015年1月通過延期,從2016年開始再延期6年,但對于具體內容做了幾方面的修訂,例如提高了保險人自行承擔損失的份額。
(三)我國恐怖主義災害保險應對機制的若干建議
要實現恐怖事件風險保險的順利運行,關鍵在于建立合適的恐怖事件模型。恐怖事件的模型相比于傳統的保險精算模型要復雜得多。我國首先應該建立政府、保險公司和學界聯合的恐怖事件研究機構,建立相關數據庫,收集分析準確的數據,進行科學的分析。在這一方面做得比較好的有美國蘭德公司(RAND)和美國馬里蘭大學的全球恐怖主義數據庫(GTD)。考慮到恐怖事件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應該對恐怖事件風險進行謹慎和科學的評估,力求客觀真實地度量恐怖事件風險。
由于恐怖事件這一巨災事件的特殊性,政府和保險公司的關系顯得尤為重要。政府與保險公司建立公私合作機制(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是當前國際上通用的解決重大災害和社會安全事故的常用方法,此類安排在應對恐怖事件風險管理上也同樣適用。政府通過公權力可以彌補保險公司在數據收集等問題上的不足之處,同時通過政府的補貼、政策或者再保險等形式提高保險公司承保恐怖事件風險的動力和能力。保險公司通過發揮自己專業管理風險的能力,實現保險機制服務社會管理功能,運用商業手段解決恐怖事件可能對我國經濟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
此外,我國應該積極通過金融手段和創新拓寬保險公司承保恐怖事件風險的能力。一個國際做法就是引入金融衍生產品。此類金融衍生品,如投資銀行簽發的巨災證券,可以作為一種投資品讓投資者購買,其回報率可以由市場上的投資者對恐怖事件的發生概率的判斷來決定。巨災保險衍生品有四種主要形式:巨災債券、巨災掉期產品、巨災期貨和巨災期權。1992年12月保險衍生產品正式開始交易,交易地點是美國的CBOT (Chicago Board of Trade)。最早的產品交易形式是巨災期貨,接著,1993 年開始進行巨災期權交易,1994年1月發行了第一只巨災債券, 1996年10月紐約的CATEX(CatastrophicRisk Exchange)開始發行巨災掉期產品。保險衍生產品的出現和發展為保險業與資本市場之間建立了一個新的橋梁,使保險公司在風險管理上有了更多可以選擇的工具。然而,即便在9·11事件以后,美國的金融市場也沒有出現大量的恐怖事件巨災金融衍生品。恐怖主義巨災保險衍生品該如何發展,還是一個有待多方探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