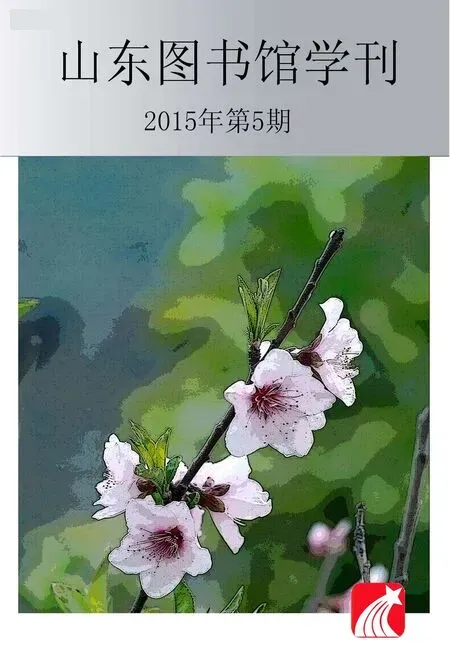商務印書館“大學叢書”研究綜述
王友富
(全國高等學校教學研究中心“愛課程”中心,北京100120)
商務印書館“大學叢書”研究綜述
王友富
(全國高等學校教學研究中心“愛課程”中心,北京100120)
概述研究文獻基本情況,從出版背景與原因、出版概況與過程、出版價值與社會影響、成功經驗與文化精神四個專題做了評述,總結了已有研究的特點,并對存在的問題與不足提出自己的看法。
商務印書館 大學叢書 出版史 教材 教科書
20世紀三四十年代,商務印書館[1]、中華書局[2]、世界書局[3]、上海黎明書局、上海珠算學社、上海啟智書局、南京正中書局、貴陽文通書局、上海生活書店(“新中國大學叢書”)、大學用書編輯委員會[4]等紛紛出版大學用書,多以“大學叢書”“大學用書”“大學文庫”“大學叢刊”等冠名。其中,商務印書館“大學叢書”是規模最大、門類最齊、影響最廣的一套大學用書,它開啟我國系統編譯國化大學教科書的先河,并達到集大成的地步。綜述商務印書館“大學叢書”的研究,分析現有研究已取得的成果和不足,對于研究者進一步深入挖掘“大學叢書”出版“寶藏”,構建完整的“大學叢書”研究理論體系,把握我國大學教材出版的發生發展史,并為高等教育研究與教育出版研究提供借鑒意義重大。
1 研究文獻概況
總體而言,學者對“大學叢書”的研究起步晚,研究成果尚不豐富。
1.1 研究論文
直接相關的文獻有6篇:東華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專業喬秀云的碩士論文[5],洪港[6]、范軍[7]、卓永[8]、楊琳和肖東發[9]、肖朗和吳濤[10]所撰期刊論文。比較相關的文獻有16篇:四川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專業宋軍令的碩士論文[11],北京大學圖書館學專業王波[12]、蘇州大學高等教育學專業李金航[13]、南開大學教育學專業金鑫[14]的博士論文,王余光[15]、汪家熔[16][17][18][19][20]、李輝[21]、房鑫亮[22]、王涵[23]、洪港[24]、肖朗和張秀坤[25][26]、肖東發[27]、范軍[28]、李瑞山[29]、李金航與周川[30]所撰的期刊論文。
1.2 著作方面
目前尚無以“大學叢書”為題的著作。提到“大學叢書”出版情況的有:(1)出版類著作,如王余光的《中國新圖書出版業初探》(1998年)、汪家熔的《商務印書館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1998年)、《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張元濟、陸費逵、王云五文化貢獻》(2002年)和《民族魂——教科書變遷》(2008年)等。其中,北京商務印書館館史研究室的汪家熔先生從1980年即開始出版史的研究,他主張出版史研究“接觸出版史的任何層面,落筆都必須見書”。(2)出版史、教育史和出版史料,如王余光、吳永貴的《中國出版通史》(民國卷),李華興的《民國教育史》,張靜廬輯注的《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等。其中,李華興主編的《民國教育史》對“大學叢書”給予較高評價。(3)研究商務印書館和王云五的著作,如法國學者戴仁《上海商務印書館1912—1949》、郭太風的《王云五評傳》(1999年)、楊揚《商務印書館:民間出版業的興衰》、吳相的《從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鎮》、王建輝著《文化的商務——王云五專題研究》、史春風的《商務印書館與中國近代文化》(2006年)、李家駒的《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林靜《商務印書館與近代教科書的出版》、臺灣學者王壽南主編的《王云五先生年譜初稿》、楊亮功等《我所認識的王云五先生》、蔣復璁的《王云五先生與近代中國》等。其中,郭太風著《王云五評傳》介紹了“大學叢書”的出版背景、經過和影響。郭太風是喬秀云論文的兩位指導教師之一,從喬文的“致謝”可以見到他對喬文選題的影響。(4)商務印書館的紀念文集,如《商務印書館九十年》《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商務印書館一百年》《商務印書館百年大事記(1897—1997)》。收錄當事人或與商務印書館有淵源的人的回憶性文章,其中有幾篇涉及“大學叢書”的文章。(5)王云五的回憶錄和年譜,如《舊學新探》《談往事》《兩年的苦斗》《八年的苦斗》《七十年與二十七年》《旅渝心聲》《岫廬八十自述》《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等。王云五是“大學叢書”的主持者,他的論著中多有涉及“大學叢書”,從不同角度反映了“大學叢書”的背景、特點、價值和出版情況。同時,臺灣學者有關王云五的研究成果較豐碩,其中不乏提到“大學叢書”者,且普遍持贊揚態度。
2 出版背景與原因
2.1“大學叢書”出版的時代背景
喬秀云從20世紀30年代國民政府有關高等教育的政策和近代中國大學教材的使用狀況兩個方面分析了“大學叢書”出版的時代背景。范軍[7]歸納了商務策劃出版“大學叢書”的三大背景:高等教育的穩步發展、大學教學改革的逐步深入、現代圖書館的勃興與發展。其中,該文對晚清以來大學教學改革的逐步推進和新圖書館運動所形成的教材市場的分析是其他研究者所未談到的。洪港[24]將編印講義、引進國外原版教材和出版本土化教材作為彼此相連的三個發展階段,從發展演變的角度勾勒了“大學叢書”出版的時代背景。
2.2“大學叢書”出版的輿論背景
一般認為,1931年4月27日,蔡元培關于《國化教科書問題》的演講是“大學叢書”出版的輿論準備。[31]喬秀云、王建輝[32]、宋軍令注意到,對于要不要出版中國文字的大學教材,當時是有不同看法的。但是,蔡元培的觀點代表了中國當時大多數人對編輯新的中文大學教材的心聲。支持者最終占了上風。這為“大學叢書”的出版造了很好的輿論。
2.3 蔡元培的倡議與商務印書館編寫大學課本的計劃孰先孰后及其關系
喬秀云、洪港[6]指出,王云五進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后,便有“編印以本國文寫作之大學教本”[33]的提議。洪港[6]還認為,商務印書館“大學叢書”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視為對蔡元培“國化教科書”主張的直接響應。宋軍令、楊琳和肖東發則指出,1930年前后,商務印書館就曾提議有系統地出版大學教科書,并受到蔡元培的重視與支持。蔡元培發表《國化教科書問題》的演講之后,王云五也敏銳地覺察到這是組織編輯大學教科書的重要契機,并于1931 年9月撰文表明有意組織編寫大學教科書。據筆者調查,王云五最早提議出版大學教科書是他第一次進商務時,應不晚于1921年11月,但當時時機并未成熟。以蔡元培與張元濟和王云五的私交,且王云五“對于商務印書館編譯出版方面有所創作,事前輒向蔡先生請教”[34],蔡元培是極有可能知道商務的計劃并持肯定意見的。商務印書館的計劃與蔡元培的演講應是相互激發、相互影響的關系。
2.4“大學叢書”出版的原因
宋軍令、洪港[6]等認為,商務印書館是出于國化教科書和促進學術獨立兩個方面的考量,從而投身近代大學教材出版事業的。范軍[7]則持不同意見,在他看來,所謂學術獨立主要是指學術獨立于政治意識形態。學術獨立是和大學獨立等相關聯的,這種獨立除了現代的思想觀念以外,最重要的是制度設計。而幾本書乃至一套叢書無論規模多大,影響都是十分有限的。但從商務與王云五的記載來看,他們確實以“學術獨立”的名義來運作的。據商務《四十年大事記》載,“本館遭難后,復業之始,鑒于民族復興端賴學術獨立,毅然開始編印本叢書。”[35]王云五在1931年9月為商務印書館35周年紀念集《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國教育》所撰寫的導言中稱,“‘教育普及’四字,為民十五年以后本館出版方針之一”,“‘學術獨立’四字又為民十五年后本館出版方針之一。”[36]此外,在考察“大學叢書”出版的原因時,研究者們都忽略了“大學叢書”出版的經濟動機,以及商務處理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做法,而揭示這一層內在原因對當今的出版企業借鑒“大學叢書”的成功經驗至關重要。
3 出版概況與過程
3.1 商務印書館是否首創“大學叢書”
王余光[15]、洪港[6]、范軍[7]、肖朗和吳濤概述了20世紀30年代前后各書局出版的“大學叢書”“大學用書”的情況。王余光[15]和洪港[6]提到其他書局的“大學叢書”或“大學用書”在商務“大學叢書”出版的前或后,肖朗和吳濤傾向于認為其他書局的“大學叢書”或“大學用書”在商務“大學叢書”出版之后,范軍[7]則據《中國近代現代叢書目錄》所載叢書細目認為,“大學叢書”既非商務印書館首創,也非其專利。筆者以為,商務“大學叢書”有泛指和專指兩種,其他書局為泛指,則商務應以“北京大學叢書”出版時間為準相比。
3.2 商務印書館“大學叢書”出版起訖時間
郭太風、喬秀云、楊琳和肖東發、范軍[7]、肖朗和吳濤提到“大學叢書”出版起訖時間,《中國近代現代叢書目錄》在收錄“大學叢書”標題下標明了出版起訖時間。歸納起來,商務印書館“大學叢書”開始出版的時間有1932年、1933年和1929年之說,截止的時間有1942和1954年之說。有待進一步考證。
3.3 商務印書館“大學叢書”出版的種數
此問題眾說紛紜,至今還沒有定論。商務的記載和王云五的記載自相矛盾,商務各處記載之間和王云五不同文獻之間說法均不一致。后來研究者的說法也不統一,歸納起來有:300余(多)種說、317種說、325種說、350種說、369種說和370種說。有必要梳理現存書、結合相關書目和館藏記錄考證。
3.4 商務印書館“大學叢書”的課程調研
商務印書館實施“大學叢書”出版計劃,是從征集國內外各大學一覽及課程表著手的。洪港[6]提及1935年版《大學叢書目錄》學院和科目數。肖朗和吳濤文詳細敘述了從《大學科目草案》到《大學叢書目錄》的擬定過程。除兩文外,沒有其他研究提及課程調研的事。而事實上,選題調研對于出版社選題策劃至關重要,有必要進一步考證。
3.5 商務印書館“大學叢書”的組稿與策劃
洪港[6]認為,商務印書館“大學叢書”組稿的方式有三種:從商務已出版之書中甄選、依據《大學叢書目錄》征集稿本、各委員介紹由商務訂約編輯。范軍[7]認為,“大學叢書”的編撰出版體現出了很強的選題策劃意識與制度規約意識。其策劃的周全和嚴密充分表現在出自王云五手筆的《商務印書館印行大學叢書章程》和《商務印書館大學叢書委員會章程》中。
3.6 專家審稿
喬秀云認為,大學叢書委員會集全國英才于一爐的編委陣容是商務由倚重館內力量轉變為依靠社會力量這一重大轉變的最好體現。范軍[7]羅列了55人大學叢書委員會名單,并認為,這些委員不只是掛名的虛銜,根據章程,他們對于叢書書目的擬訂、書稿的介紹征集、圖書質量的審核把關,是負有切實責任的。肖朗和吳濤文用較大篇幅論述“大學叢書”稿本審查情況,不僅列有部分“大學叢書”稿本與審查人的對照表,還歸納了“大學叢書”審查的特征及問題,并認為,大學叢書委員會委員及國內許多審稿專家的嚴格把關的確對叢書質量的保證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此外,范軍[7]、《中國民國通史》(民國卷)等注意到了55人組成的大學叢書委員會名單的變化情況。肖朗和吳濤則較為詳細地說明了委員會名單從51人到55人的變化情況。
3.7 編輯體例
楊揚[37]、洪港[6]認為,“大學叢書”倡導并踐行多元化的編輯體例①楊揚、洪港所言的“編輯體例”實際上指的還是組稿策略,編輯體例在出版業另有所指。,即同一學科采用幾種不同風格的著作作為教材。例如,中國學術史的論著采選了錢穆和梁啟超兩種不同的論著,中國哲學史也采選了馮友蘭和胡適二人的論著,教育哲學則采用了二譯一著。這種強化個性而不以所謂的定論來要求著者的“大學叢書”體例,在教科書編撰格式上是一種創新。
3.8 宣傳推廣
一般認為,商務印書館聘請社會名流擔任大學叢書委員會委員,不僅有利于擴大“大學叢書”的影響力,也有利于“大學叢書”被廣泛地采用。宋軍令還引用了商務印書館印行的《出版月刊》為“大學叢書”所做的廣告。喬秀云、洪港[6]、楊琳和肖東發、肖朗和吳濤提到,商務印書館為推廣“大學叢書”,在它所辦的函授學校設大學部,下設15個學系,60個學程,分別對應60種“大學叢書”教材。此外,在私立商務印書館函授學校聘請的校長、副校長及大學部各學系顧問32名專家學者中,有16名是大學叢書委員會委員,占總人數的50%。由此可見,商務印書館為推廣“大學叢書”可謂妙招盡出。商務印書館有雄厚的資金,又有印行雜志等天然優勢,因此,“大學叢書”的宣傳推廣方式應是多樣且豐富的。但就目前資料所看,這方面的研究還很不夠。
4 出版價值與社會影響
4.1 意義
此問題研究者探究的較多。歸納起來,有以下方面:(1)教育意義。喬秀云、宋軍令、洪港[6]、范軍[7]、楊琳和肖東發認為,“大學叢書”開辟了我國成功出版本土大學教材的先河,改變了大學授課完全依賴外文課本的狀況,解決了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語言障礙和國情差異問題,有力地推進了大學教材建設和課程設置的標準化和科學化,為現代學校學科設立和課程整理提供了借鑒,促進了我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發展。肖朗和吳濤認為,“大學叢書”的出版有助于近代中國大學的課程建設,從而為大學教學工作正常而有序的開展提供了重要支撐。(2)學術文化意義。喬秀云、宋軍令、楊揚、洪港[6]、楊琳和肖東發認為,“大學叢書”遴選全國范圍內的優秀著作予以出版,提高了國內學術著作的水平;為當時的中國學者提供發表學術成果的陣地,促進了近代中國學術的發展;其低廉的價格既減輕了學生的經濟負擔,又擴大了讀者范圍,進而促進了學術的普及。肖朗和吳濤還認為,“大學叢書”的出版提升了近代中國大學教材的學術質量。(3)出版意義。洪港[6]、范軍[7]、楊琳和肖東發認為,“大學叢書”的出版,開創了大學教材的出版模式,確立了大學教科書成為圖書出版專門類別的地位,促進了近代其他出版機構參與大學教材的編輯出版。“大學叢書”的策劃與運作體現出自覺而強烈的學術名家意識與精品戰略意識,對我們今天的出版工作仍不乏啟示。肖朗和吳濤認為,商務出版“大學叢書”,首創大學教材聯合編審的方式及機制,這一模式、方式和機制為中華書局、正中書局等紛紛效仿,并為“部定大學用書”所繼承。(4)現實意義。喬秀云認為,“大學叢書”出版為當今的高教改革和教材體系建設提供了借鑒,為當今出版事業積累了豐富的成功經驗。關于這個話題,值得進一步探討。
4.2 總體評價
鐘魯齋[38]、周谷城[39]、王鐵崖[40]、楊揚、郭太風、李華興[41]、王建輝、喬秀云、洪港[6]等從不同方面對“大學叢書”做了較高的評價,一般研究者均提肯定的評價,僅肖朗和吳濤提到,當時學者如梁鋆立和梁實秋曾于《圖書評論》發文,對“大學叢書”提出過“質疑”與批評。除此之外,研究者均未分析“大學叢書”的不足。
4.3 采用情況
“大學叢書”出版后受到國內高校的普遍歡迎。據喬秀云、洪港[6]、肖朗和吳濤介紹,“大學叢書”出版后,國立北京大學、國立南開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武漢大學、國立四川大學、國立浙江大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省立安徽大學、省立云南大學、私立廈門大學、私立之江文理學院等知名院校紛紛采用。采用的方式主要有三:(1)替代商務印行之“××大學叢書”。(2)替代原著。(3)替代講義。
4.4 具體書的流傳與影響
宋軍令、洪港[6]、肖朗和吳濤均舉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為例。楊琳和肖東發則介紹了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的流傳情況,認為該書是中國本土教材被譯為外文向海外傳播中國文化的典范。王延鋒[42]、范軍[7]、汪家熔[43]則列舉薩本棟《普通物理學》的流傳情況,稱其為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物理學教材的范本。該教材還被譯成英文,影響波及海外,獲得國際學者的好評。此外,喬秀云、宋軍令、肖朗和吳濤還介紹了十余種有“定評”的著作。
5 成功經驗與文化精神
5.1 成功經驗
一般認為,“大學叢書”的成功,與商務印書館依靠社會力量,注重網羅各類人才,重視人才和利用人才等不無關系。喬秀云還提到了商務印書館振興民族文化事業的高度責任心和主人翁意識、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分子群體之間的密切關系等。值得注意的是,從經濟效益的角度來分析和判斷“大學叢書”出版的成功經驗還有待更深入的挖掘。
5.2 文化精神
喬秀云認為,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大學叢書”蘊涵著不屈不撓、振興中華的文化精神。這種奮斗精神和民族正氣是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的。
6 已有研究的特點與不足
6.1 已有研究的特點
從現有文獻來看,關于“大學叢書”的研究有以下幾個特點:首先,它是一個交叉的話題,有從中國近現代史方面入手研究的,也有從教育學方面入手的,還有從出版史方面進行研究。其次,主體研究人數雖少,發表文章也不算多,但因為這個話題本身就比較專深,研究的質量較高,研究者在不同側面取得了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再次,研究者不乏像汪家熔、范軍等單兵作戰卻成果豐碩的例子,但更多地表現出較為明顯的師緣群體研究性質,如王余光及其弟子吳永貴等民國出版史研究群體,肖朗及其弟子洪港等教育學史研究群體,郭太風及其弟子喬秀云的近現代史研究群體,肖東發及其弟子楊琳的編輯出版學群體等。
6.2 已有研究的不足
已有研究從多個方面做了十分有價值的探索,取得了頗為可觀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喬秀云、洪港、范軍、肖朗和吳濤文對于“大學叢書”研究較為深入。這些研究為后來者的研究或提供了觀點啟發,或提供了文獻線索,或提供存疑的問題入口。但相對來說,這些研究宏觀層面的討論居多,如對出版背景、過程和意義等討論較多,對微觀細節討論不夠充分,如出版編、印、發等細節,經濟效益,出版形制,出版物的版本與流傳,“大學叢書”的不足等問題。同時,仍有不少尚未解決的問題或疑點,如出版種數問題、時間起訖問題等;一些問題還有系統深入討論的必要等,如出版過程的階段性特征與狀況等。
綜上,多角度且質量較高的研究為從出版的角度系統考察“大學叢書”奠定了堅實基礎。
〔1〕王余光.中國新圖書出版業初探[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151
〔2〕吳永貴.中華書局與中國近代教育:1912-1949[D].武漢:武漢大學,185-186
〔3〕世界書局.世界書局圖書目錄[G].上海:世界書局,1935:20-27
〔4〕國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鑒編纂委員會.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G].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1484
〔5〕喬秀云.大學叢書譯著研究初探[D].上海:東華大學,2006
〔6〕洪港.試論中國近代大學教材的發展——以商務版“大學叢書”為中心[J].煤炭高等教育,2008,26(3):23-27
〔7〕范軍.20世紀30年代商務版“大學叢書”的策劃與運作[J].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2):23-27
〔8〕卓永.姜立夫與《大學叢書》[J].籀園,2011(2):58-59
〔9〕楊琳,肖東發.商務印書館《大學叢書》的出版及歷史意義[J].出版科學,2012(2):22-25
〔10〕肖朗,吳濤.商務印書館“大學叢書”與近代中國大學教材建設[J].高等教育研究,2013,34(12):72-80
〔11〕宋軍令.近代商務印書館教科書出版研究[D].成都:四川大學,2004
〔12〕王波.晚清和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與北京大學的互助合作研究[D].北京:北京大學,2014
〔13〕李金航.中國近代大學教科書發展歷程研究[D].蘇州:蘇州大學,2013
〔14〕金鑫.民國大學中文學科講義研究[D].天津:南開大學,2014
〔15〕王余光.教科書與近代教育[J].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0(3):108-114
〔16〕汪家熔.抗日戰爭時期的商務印書館[J].編輯學刊,1995(3):85-90
〔17〕汪家熔.抗日戰爭時期的商務印書館(二)[J].編輯學刊,1995 (4):90-94
〔18〕汪家熔.抗日戰爭時期的商務印書館(三)[J].編輯學刊,1995 (5):84-90
〔19〕汪家熔.抗日戰爭時期的商務印書館(四)[J].編輯學刊,1995 (6):88-92
〔20〕汪家熔.抗日戰爭時期的商務印書館(五)[J].編輯學刊,1996 (1):72-77
〔21〕李輝.王云五與蔡元培的交往[J].文史月刊,2005(8):35-38
〔22〕房鑫亮.國難后商務印書館的復興[J].檔案與探索,2005(8):49-53
〔23〕王涵.“北京大學叢書”:中國最早的“大學叢書”[N].中國教育報,2007-12-27(5)
〔24〕洪港.中國近代大學教材建設述論[J].現代大學教育,2010 (3):81-85
〔25〕肖朗,張秀坤.民國教育界與出版界的互動及其影響——以王云五的人際交游為考察中心[J].教育學報,2011(3):120-128
〔26〕肖朗,張秀坤.王云五與近代教育出版家的主體意識——以《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為考察中心[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4):120-128
〔27〕肖東發.大學與出版在中國[J].現代出版,2012(3):8-11
〔28〕范軍.略論民國時期的大學出版[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2):136-144
〔29〕李瑞山.民國大學講義出版生態掃描[J].中國圖書評論,2014 (2):108-112
〔30〕李金航,周川.中國近代大學教科書本土化及啟示[J].現代教育管理,2015(5):113-117
〔31〕蔡元培.國化教科書[N].申報,1931-04-27
〔32〕王建輝.文化的商務:王云五專題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0:115
〔33〕王云五.岫廬八十自述[M].臺北:商務印書館,1967:84
〔34〕王云五.談往事[M].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8:180
〔35〕本館四十年大事記[G]//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702
〔36〕王云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328
〔37〕楊揚.商務印書館:民間出版業的興衰[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135
〔38〕鐘魯齋.改進我國教育幾個當前的問題[J].教育雜志,1937 (1):9-14
〔39〕周谷城.商務印書館與中國的現代化[G]//商務印書館九十年.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415
〔40〕王鐵崖.商務印書館對中國文化教育的貢獻[G]//商務印書館九十年.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420-421
〔41〕李華興主編.民國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491
〔42〕王延鋒.我國早期大學對物理教材的編譯概況[J].大學物理, 2003,22(10):34-37
〔43〕汪家熔.民族魂——教科書的變遷[M].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8:225
Research Review of“University Textbook Series”by the Commercial Press
Wang Youfu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situation of available literature,and makes comments on publishing background and reasons,publishing situation and process,publishing value and social influence,successful experience and cultural spirit.Then,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isting research and puts forward personal views on existing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The Commercial Press;“University Textbook Series”;Publishing history;Textbooks
G239.29
A
王友富(1976-),男,漢族,副編審,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文獻目錄學、編輯規范與實務、出版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