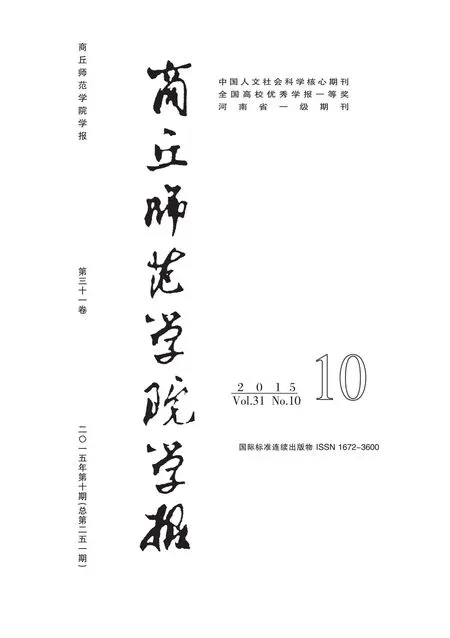中國古代經典解釋中的思想對話與觀念變遷
——以《老子》第五章“多聞”與“多言”的詮釋為例
劉 世 宇
(北京大學 哲學系 ,北京100871)
中國古代經典解釋中的思想對話與觀念變遷
——以《老子》第五章“多聞”與“多言”的詮釋為例
劉 世 宇
(北京大學 哲學系 ,北京100871)
中國古代思想詮釋往往在一字一句的改動之中別有天地。通行本《老子》第5章中的“多言數(shù)窮”,在馬王堆帛書本《老子》中作“多聞數(shù)窮”。以往研究多著眼于版本研究,聚訟于兩個版本孰優(yōu)孰劣,難免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應立足于文本變遷背后更廣闊的思想對話與觀念變遷,多角度探尋這一文本變遷背后的思想蘊含:從《老子》本身的思想體系出發(fā),“多聞”批評了“學”,而“多言”直接針對有為的政治;從儒家的思想角度出發(fā),本章對“仁—多聞”或“仁—多言”的批評主旨是否定政治教化的可能性,是對儒家以“仁—智”治國思想的徹底否定。《莊子》的外篇和雜篇、《文子》、《淮南子》等對此章的引用和解釋著眼于批判儒家的經典之學不足應對事變時移,嚴遵和王弼則借詮釋此章以批判政教言令的煩苛。道家后學解釋的差異提示我們應該注意到中國古代經典詮釋的學術活動背后的時代影響。
《老子》;第五章;多聞數(shù)窮;多言數(shù)窮
中國古代的哲學創(chuàng)作很多是通過“寓作于編”的方式進行的。思想家們往往通過改編或者闡釋經典來闡明自己的思想。這些文本的改作和闡釋往往十分微妙,很多只是一個字或者一句話的細微差別,因此很容易被誤以為版本傳抄的問題而被輕輕放過。然而,細微的差別背后卻可能蘊含著不同學派和不同時代的思想家們的思想碰撞。《老子》“天地不仁”章中通行本“多言數(shù)窮”和帛書本“多聞數(shù)窮”之間的差異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本文擬以此為例,對中國古代經典解釋中的思想對話與觀念變遷問題進行粗略探討。
一
《老子》“天地不仁”章通行本中的內容是: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龠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shù)窮,不如守中。
這一章的內容在馬王堆帛書《老子》中作: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尤橐龠與?虛而不 屈,動而俞出。多聞數(shù)窮,不若守于中。
對比可知,兩個版本意義之間的最大差別即在“多言”與“多聞”的差異。這一差異在傳世諸本之間早已存在,如王弼本、傅奕本、河上公本、景龍本都做“言”;想爾本、遂州本、倫敦所藏敦煌本以及新近公布的北大竹簡本則做“聞”。“言”“聞”雖然看似僅一字之差,但由于其中意義差別很大,孰是孰非一直為學者聚訟。在帛書出土后引發(fā)的《老子》研究的熱潮影響下,使得這一文本上的差異再次引起學者注意。但由于現(xiàn)階段幾乎不可能找到“最早”的《老子》祖本作為佐證(郭店楚簡本僅有“天地之間,其猶橐龠與?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學者們只能采用“從老子思想體系著眼,最符合老子思想的便是最值得肯定的”[1]態(tài)度和方法作出自己的判定。然而,由于無論是“多言”抑或是“多聞”,二者在意蘊豐富的《老子》思想體系之中都能夠找到自洽的文本依據(jù),最終使得答案在相當程度上只能取決于學者們各自對《老子》的認識和理解。
以“言”為論,“天地不仁”章對“多言”的否定顯然和《老子》對“言”的態(tài)度是一致的。從文本本身看,“言”在王弼本中較常見,共19處,其中少部分用法(共8處,如第22章“豈虛言哉”、 第35章“言以喪禮居之”、 第41章“故建言有之”、 第66章“必以言下之”、 第69章“用兵有言”、第70章“吾言甚亦知”以及“言有宗”、 第76章“正言若反”)似乎并無深意。而在其余的11處中,《老子》對“言”特別是過多的“言”始終持懷疑和否定的態(tài)度,這其中“不言”出現(xiàn)了4次(分別為第2、43、56、73章),強調“言”少一些的“貴言”(第17章)與“希言”(第23章)各出現(xiàn)1次,直接反對“多言”的1處即第5章“多言數(shù)窮”。這里需要略作辨析的是“信言”與“美言”(共出現(xiàn)4次)。從“美言可以市”( 第62章)、“美言不信”( 第81章)的論述可以清晰地看出,王弼本《老子》對“美言”的否定是十分明顯的。“言善信”( 第8章)說法則似乎表明王弼本《老子》對“信言”有所肯定,但在肯定的同時,《老子》也強調“信言”的特征是素樸或者“不美”。這實際上仍是強調“信言”應當“少”而當,避免多而華。換而言之,在這11處中,《老子》除了反對“多言”和“美言”外,都是在直接或間接地主張“不言”或“少言”。
從思想邏輯的角度看,反對君主施政的造作有為,主張用虛靜無為治國是《老子》政治哲學的基本主張,“天地不仁”章反對“多言”與《老子》這一思想是高度一致的。在《老子》中,“言”往往是和“教”聯(lián)系在一起的(如明確主張“行不言之教”),因此學者多將此章中的“言”訓解為“聲教法令”,其正與《老子》主張的“不言之教”、“希言”等相對,“多言數(shù)窮”也就意味著“政令煩苛,加速敗亡。”[2]76照此理解,《老子》“天地不仁”章正好按照“推天道以明人事”的論證模式構建了一個層級推進的論述整體:首先由“天地不仁”這一天道規(guī)則推導出人事中“圣人不仁”;其次則以橐龠比喻天地“不仁”,即是以“虛”的態(tài)度對待萬物、包容萬物而無所偏私,讓萬物能夠自然而然,生生不息,即第16章所謂“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之意;隨即由此而推導出治國有為容易速敗,不如保持虛靜,反而能夠讓百姓自然造就、自我成就。對此,陳鼓應指出:“‘天地不仁’和天地虛空都是老子‘無為’思想的引申。天地‘無為’(順應自然),萬物反而能夠生化不息。‘無為’的反面是強作妄為,政令煩苛(‘多言’),將導致敗亡的后果。”[2]79
相較而言,從文本上看,“聞”似乎是《老子》不甚重視的一個概念,王弼本中“聞”僅現(xiàn)7處,帛書本為9處,多出的地方為對應《老子》“天地不仁”章的“多聞數(shù)窮”(王弼本寫作“多言數(shù)窮”)和第48章的“聞道者日損”(王弼本寫作“為道日損”)。從意義上看,“聞”在《老子》中大多數(shù)都僅僅指“聽”或聽覺,如王弼本第14章之“聽之不聞”、第35章“聽之不足聞”、 第41章“上(中、下)士聞道”、第50章“蓋聞善攝生者”、第80章“雞犬之聲相聞”等用法顯示的那樣,并無特別的含義。唯一的例外之處應為“天地不仁”章中的“多聞數(shù)窮”,其意義略微復雜曲折一些。但這種情況并不意味著“多言數(shù)窮”應當是“多聞數(shù)窮”,畢竟“數(shù)量上的優(yōu)勢并不能決定版本的優(yōu)劣”[1]。
反對“多聞”同樣十分符合《老子》的思想邏輯,即反對“學”和“用知”。有學者認為,“聞”在這里可以理解為學或掌握知識的一種方式,“多聞”即是多知識,意味著充實。《老子》第5章自身的論述邏輯,先是論述天地、圣人應順應自然,無所偏愛,再以橐龠比喻天地之道為“虛”,最后是告誡人們需要守中(即“守虛”)。“多聞”與天道的虛靜構成對比:“倘若接受了過多的仁義禮法之類的‘學’,心被 ‘充實’了,其必然難以再順應自然、應對自如。”[1]另一方面,在《老子》看來,學和智是緊密相關的,統(tǒng)治者提倡“學”,就是鼓勵臣民百姓用智。《老子》明確反對以智治國,主張“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其認為“多聞”會導致速敗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對此高明指出:“老子主張?zhí)撿o無為,無知無欲。他認為知識是一切紛爭的源泉。……‘多聞’即多學,如《論語·季氏》‘友多聞’,邢昺疏:‘多聞謂博學。’可見‘多聞’同老子主張的‘使民無知無欲’和‘學不學’相抵觸,故此經云‘多聞數(shù)窮’,前后思想、脈絡完全一致。”[3]172
綜上所述,對究竟應該是“多聞”還是“多言”這一問題,從版本勘定的角度看,目前恐怕仍難定論。因為從思想角度看,“多聞”與“多言”在《老子》的思想體系中并不是針鋒相對、非此即彼,二者實則相互區(qū)別而又互為補充,折射出《老子》思想內部豐富復雜的張力關系。《老子》主張政治上的無為而治,他既強烈反對政令苛煩的有為之治,也同樣反對以智治國。所以,無論是“多言數(shù)窮”還是“多聞數(shù)窮”,在《老子》的思想邏輯中都是能夠講得通的。
二
在“多聞數(shù)窮”和“多言數(shù)窮”版本優(yōu)劣的學術爭論中,作為《老子》“天地不仁”章重要思想對話者的儒家受到了某種程度的忽視。然而,《老子》“天地不仁”章對天道虛靜而圣人應效法天道“守中”這一思想的闡發(fā),是建立在直接批評否定儒家“仁—多聞”或“仁—多言”基礎之上的。這意味著如果僅僅只是從《老子》自身的思想體系入手,而不對儒家相關思想作一點必要的探討,將很難真正理解《老子》這章論述的內在思想邏輯。例如,第一句中的天地“不仁”與第二句中的“虛”存在什么樣的關聯(lián)?為什么只有“不仁”才能“虛”?如果沒有對“仁”的討論,僅從《老子》立場對上述問題進行回答將是很不充分的。此外,同樣需要探討的還有,從“不仁”或“虛”的角度看,為何“多聞”或“多言”將導致“數(shù)窮”這一問題。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同樣離不開對“仁”與“多聞”或“多言”之間的關系的探討。
首先看“仁”的觀念。“仁”顯然是儒家核心觀念之一,但對究竟什么是“仁”,先秦儒者們似乎并沒有給出一個統(tǒng)一的定義。據(jù)《論語》記載,孔子在世時,包括顏淵、仲弓、子貢、子張等諸賢弟子就曾多次向孔子“問仁”,孔子面對不同弟子時給出的答案各有不同,顯示出這是一個被儒者普遍關注但又頗有發(fā)散性的觀念。不過,不論“仁”的思想內涵有多復雜,其中都會包含著某些一以貫之的要素。其中愛的情感顯然是貫穿于“仁”的最基本的內涵之一。“從《論語》和儒學史共同構成的觀察視角來看,仁的最基本內涵就是愛,更確切地說是愛人。”[4]70概略來講,作為愛的“仁”在先秦儒家思想中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的特征:首先,它是一種內心充實的真情實感,一如仁之端發(fā)動于乍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反之,“心不在焉”必然會導致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這種不用心就是孔子斥宰我的“不仁”。其次,這種愛是與血緣的親親有關,所以它自然而然地存在著差等,也就意味著分別,意味著對不同對象的愛并不是等質等量,而是有所偏私、有一定差等的。如其對自己父母兄弟的愛和對路人的愛就絕對不可等量齊觀。再次,作為“愛”的同時,“仁”也包含“恨”的情感。“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里仁》)以及“君子有惡”(《陽貨》)等說法顯示出,儒家的“仁”天然地包含著對“非禮”等違背儒家倫理規(guī)范的人的厭惡。換句話說,仁之中內在地包含著某些道德標準,一個內心有仁的人,其內心是實而不是“虛”的,他對這個世界是存在著某種態(tài)度和選擇的,這在《老子》看來就意味著某種偏見,是無法周遍萬物的。
當然,作為愛,儒家的“仁”從來就不僅僅是個人道德層面的道德化教條,而是既有形上理論依據(jù),又在社會政治領域有其具體表現(xiàn)的。從形上的角度看,如“一陰一陽之為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信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易傳·系辭傳上》)以及“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易傳·說卦》)等說法所顯示的,仁是天道法則在人事中的體現(xiàn),是人對天道的效法。從具體的社會和政治領域角度看,愛的差等化原則本身就包含著秩序性的要素,使得其很容易外化為作為社會秩序的禮。“克己復禮為仁”的說法顯示仁和禮實際上是一體兩面。仁的好惡表現(xiàn)在政治領域,或是“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禮記·經解》)或是“有大罪而大誅之,簡;有小罪而赦之,匿也。……簡,義之方;匿,仁之方也。”(帛書《五行篇》)。這些說法都表明,儒家的“仁”不僅僅有溫情脈脈的“德政”的一面,同樣也有暗含著對違反儒家思想的異端進行禁非罰惡、強調刑殺的一面,只不過這一面被其溫情脈脈的一面所遮掩罷了。
如何實現(xiàn)“仁”?對儒家而言,“學”無疑是最重要的路徑之一。《論語》第一篇《學而》的主題即是圍繞“學”而展開,顯示出《論語》編撰者的獨特用心[5]305。孟子總結自己成長之路“乃所愿,則學孔子”,《荀子》以《勸學》為首篇,《禮記》亦有《大學》等專篇論“學”,這些現(xiàn)象至少在形式上可以說明儒家對“學”之于成人的重要性的強調。在儒家看來,“正是后天的學習與否以及學習的內容,決定了一個人生命成長的方向”[4]70。所以,《大學》開篇即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這也就意味著,在儒家看來,學是有著明確的方向和目標的,那就是明明德,即知曉仁義禮智這一類的儒家德性,并且將這些德性轉化為自己的德性,最終成就以儒家德性為根基的道德人格。而且,學的過程本身亦是王道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化民成俗的政治功能。《禮記·學記》即說:“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儒家的為學之道顯然是有次第的,重視聞見以求獲得廣博知識的積累是學的過程中十分重要的一個方面。所以《大學》的修學次第之中,以正心誠意、格物致知為起點。孔子亦自居于學知而非生知,“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其求學方法亦不過“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論語·述而》)。他認為,益者有三友,“友多聞”即居其一,其原因即在于朋友見識廣博能夠有益于自身的德行修養(yǎng)。另一方面,對儒家的“多聞”的理解還不能僅停留在知識與德行的增益層面,還應注意到“多聞”也是為政的一項基本素質,因為只有多聞才能避免偏聽偏信,利于明察事理。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后儒在注解《論語》“友多聞”一語時特言“多聞者能識政治之要”[6]658就并不一定完全是牽強附會的解釋。《論語》載子張問干祿為政之道時,孔子即告誡他:“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余,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論語·為政》)
“言”在儒家思想體系中和“聞”一樣具有多重含義。儒家對“言”十分重視,孔門四科之中,“言語”即居其一。對于“言”的功能,孔子曾經說:“《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仁者其言也讱” (《論語·顏淵》),“巧言令色鮮矣仁”( 《論語·學而》),“言談者,仁之文也”(《禮記·儒行》),亦顯示出仁與言之間存在著本然聯(lián)系。不過,“言”在這層意義上還只是與“行”對應的“言”,儒家以此強調德行修養(yǎng)上的言行一致。
而《老子》所批判的儒家的“言”,可能還不是上述內容,更大的可能是儒家提倡的“德”之言,即明王先圣的教化之言。孔子說:“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論語·憲問》)一個有德的君子,必定會承擔起他的社會責任,教化民眾,傳播德性知識。因此,他們的“言”在道德層面就成了德性真理的體現(xiàn)。作為先王先賢的圣言典籍,都是需要人們懷著敬畏的心去面對和學習的,君子“三畏”之一即是“圣人之言”。這些圣人之言,落實到政治層面,就是“政教言令”。所以,孔子特別強調政治領域的“名正言順”,他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論語·子路》)“言”在這里就顯然具有政教法令的意義。
從“言”和“聞”兩個概念的具體內涵來看,二者顯然有著很大的不同。其中“多聞”明顯是指向“學”,指向改變自己;而“言”則更多地強調“教”,是要改變別人。這種差別有似于儒家思想對“成己”與“成物”的區(qū)分。但“聞”與“言”這種區(qū)別可以相互轉化,施政時的“多聞”無疑是從屬于“教”,對圣人之“言”的敬畏最終也必然會走向“學”,這也正是儒家特別重視學習經典的原因所在。這種轉化之所以可能,當然是二者在內在精神上的高度一致。首先,“仁”的德性預設已經為儒家的“教”與“學”規(guī)定了具體的方向。對儒者自己而言,儒家把仁視做人之為人的標準,視做了人的生命存在的本質規(guī)定性,教和學顯然都是要圍繞如何讓人能夠成仁展開的,聞和言本身就密不可分;對他人而言,仁的德性的成立不能僅僅是成己,而是在成己的基礎之上成物,修己以安人,這也就意味著,一個真正的仁者,是肩負著用圣人之言教導百姓,肩負著以先覺覺后覺的責任的。他有義務和責任用承載著 “仁”等儒家德性的圣人之言去引導和改變百姓。這也就意味著,一個儒者的生命之中充盈著仁的德性的時候,他就必然內在的會要求自己“多聞”,以不斷的增益自己的德性,同時又會采用“多言”的方式孜孜不倦的將“仁”擴展出去。從政治的角度看,“學”與“教”只不過是“教化”的一體之兩面,兩者實際上都在政治層面預設了人性的可以改變,認為有教化的可能和必要,因此,主張“多聞”和“多言”都必然導致教化,導致有為的政治。具體地說,鼓勵為政的“多聞”無疑是在鼓勵一種“昭昭”和“察察”的政治,儒家希望通過“多聞”的方式使得自己不被蒙蔽,在《老子》看來無疑是用智力與民眾爭競,其實質就是以智治國;而鼓勵為政時“多言”,試圖通過政教言令去干涉百姓生活,去改變百姓的生活方式甚至生命本身,毫無疑問是在鼓勵政令煩苛,這是和《老子》主張的“以百姓心為心”,君主無為以任百姓自然的“不干涉”的政治主張完全不同的。
也因為儒家的這些思想和《老子》思想明顯存在著巨大的差距,其被《老子》“天地不仁”章針鋒相對地進行批評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因為在《老子》看來,天地對萬物從來就沒有什么特殊的感情,“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老子》第51章),這種“不仁”并不是殘暴不仁或天性涼薄,而是面對萬物時的無心,無所謂偏愛,更無所謂好惡,萬物或生或殺,或成或毀,不過是萬物自己的自然造化,即如莊子說的“天地殛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物而不為仁”(《莊子·大宗師》)。換而言之,這種不仁更多地是“無心”和“無意”,以及由這種無心帶來的無所偏愛,是面對萬物的虛懷若谷和包容,是一種主張寬容的政治。正是這種“虛而不屈”,才能在面對萬物時做到無所偏私和不干涉,才能“曲成萬物”而不是存一部分而毀棄其余。萬物也由此得以自然自化,生生不息,永不衰竭。這種天道觀推衍到政治領域,就是主張圣人效法天道,之于百姓亦應無心無為,守虛或“守中”。因此,在《老子》看來,儒家主張治國的時候懷仁行義,無論從何種角度看,都是帶著某種“好”或者“惡”的偏見去面對百姓。因為有著這樣的成心,所以儒家會試圖教化和改變百姓,必然導致崇尚“多聞”或“多言”,導致有為的政治;同時,因為這種仁義之中有差等,所以會導致任人唯親,因為有好惡,所以容易導致黨同伐異——因為不能周遍萬物,最終只能導致“數(shù)窮”的惡果。
三
對照儒家思想的主張來看,“天地不仁”一章顯然是對儒家思想的某種回應。不過,無論從《老子》自身的思想邏輯,還是以儒家思想作為參照,實際上都很難確定《老子》“天地不仁”章究竟在哪一層意思上反對“多聞”或“多言”。從《老子》反對“學”,主張“絕學無憂”、“常使民無知無欲”的立場出發(fā),《老子》似乎更明顯地反對與“學”聯(lián)系緊密的“多聞”;但必須看到,儒家主張的德言或者圣人之言,或者說經典之學,也同樣與儒家的“學”緊密相關,這同樣是道家所反對的,《老子》的后學之中亦不乏持此立場來解此章的人。而若從《老子》主張無為治國、反對政令煩苛的角度看,選擇“言”似乎更明白曉暢;但這同樣無法否定“聞”的合理性,因為“多聞”正是治國上的“昭昭”和“察察”。此外,目前我們能見到的最早的《老子》版本為郭店楚簡本《老子》,對應此章僅有中間“天地之間,其猶橐龠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四句,而“帛書本和諸傳世本前后的文句是竹簡本抄寫時有而未錄,還是后人增添的,單就這一章來說,似乎很難斷定”[7]131。因此,對《老子》這一極富思想包容性的文本而言,在選擇“聞”或“言”這一問題上,其實不妨持兩可的態(tài)度。這種兩可的態(tài)度提醒我們,更有意義的問題可能不在于最初的《老子》中究竟是“多聞”還是“多言”這一問題的是是非非,而是在思想史的變遷中把握相關概念的嬗變過程所呈現(xiàn)的意義。當我們跳出非此即彼的版本判定的思考方式,而關注到文本和思想是在歷史闡釋中形成的這一事實,將對文獻問題的關注轉向思想史,“多聞”和“多言”的問題就會變得有趣得多。
這里首先進入人們視野的應當是對“天地不仁”章直接進行過闡釋的《文子》。關于《文子》,以前學者多認定其為偽書。但是,1973年定州竹簡本《文子》的出土庶幾可證,即使通行本《文子》有后人篡改的部分內容,其來源仍可能相當古老,將其斷代在漢初之前當無問題。由于該書的文獻和思想問題相當復雜,本文不擬詳細討論,而僅關注其與《老子》“天地不仁”章相關的思想內容。
首先是“仁”的問題,與儒家如出一轍,《文子》將仁定義為“愛人”。《微明》說:“仁莫大于愛人,智莫大于知人。”這一說法幾乎是在重復孔子就樊遲問“仁”和“智”而給出的答案。仁愛存在的最大問題即在于其不能周遍萬物,因此《文子·自然》在引《老子》“天地不仁”等一語之后,即批評說:“夫慈愛仁義者,近狹之道也。”而在其看來,真正的天地之道乃是“道為之命,物以自正”,因此“道立而不教,明照而不察”。圣人則法天道,“立法以導民之心,各使自然”,最終是“不奪人能”、“不害其事”。在這里值得注意的是天地不仁與“不教”和“不察”的關系:君主懷仁行義,顯然是要立教施察;“不教”顯然和“言”相關,而“不察”則似乎反對的是“多聞”。
僅據(jù)上述說法斷定《文子》對“聞”和“言”均持否定態(tài)度似略顯武斷。不過,有直接證據(jù)顯示《文子》是將“聞”和“言”等而視之甚至混為一談的。《道原》說:“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于時,故知時者無常之行……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于智,智者不知,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多聞數(shù)窮,不如守中’,‘ 絕學無憂’,‘絕圣棄智,民利百倍’。”這里的“書”和“言”似乎都在指向儒家。對此,默希子注之為:“書者,《詩》、《書》、《禮》、《樂》也;言者,謂先王賢智之言也。皆以陳之芻狗,非常道也。”[8]25這種注釋是符合《文子》本身的思想邏輯的。《上義》即云:“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故名可名,非常名也。”在先秦強調誦先王之書的學派,最著名的顯然是儒家,故由此可知《文子》此處所批評者是誰。“多聞數(shù)窮”、“絕學無憂”以及“絕圣棄智”等說法在這里并列,似乎暗示《老子》對“多聞”的否定,實質上是否定的儒家強調“教化”、強調“教”“學”代政的政治哲學以及在此背后的“智”德。這顯然和上文提及《文子》反對“仁”的思想邏輯一致。
當然,將“誦先王之書”和“言”聯(lián)系起來并加以否定的并不止《文子》。莊子后學的作品,如《莊子·天運》直接指出六經亦不過是“先王之陳跡”,其更借師金之口譏孔子是以“以陳芻狗聚弟子游居寢臥其下”,所追求的最終不過是黃粱一夢。《天運》多次強調:“仁義,先王之遽廬也,只可以一宿而不可以多處。”“仁義慘然乃憒吾心,亂莫大焉。”《莊子·天道》作者亦借斲輪扁之口表達書不過是圣王之言的陳跡糟粕,并認為當世之人貴言傳書其實并不足貴,“視而可見者,形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而這些是不足以傳達書言背后的真意的。在《天道》篇作者看來,“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其所運行,“殛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物而不為仁”,因此圣王應“以虛靜推于天地,通于萬物”。這些說法,除了沒有直接引用《老子》“天地不仁”章的原文,其思想內容幾乎就是對《老子》“天地不仁”一章思想含而不引的解讀和發(fā)揮。
很難確定《文子》和《莊子》外篇將“書”與“言”聯(lián)系在一起的做法孰先孰后,但二者一定對《淮南子·道應訓》的作者有著直接的影響,因為《道應訓》的作者幾乎完全重述了《莊子·天道》中斲輪扁的寓言解釋《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隨后又借王壽焚書的寓言,重復了《文子·道原》“事者,應變而動。變生于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于知者,知者藏書”的觀點,以此解釋《老子》“多言數(shù)窮”一語。《淮南子》在這里將兩組材料結合起來討論,可以看到黃老道家和莊子后學在某些地方互相合流所留下的雪泥鴻爪。
《淮南子》作“多言數(shù)窮”而不是“多聞數(shù)窮”應當非《道應訓》作者引文有誤,而極可能是《道應訓》的作者根據(jù)的是其他版本的《老子》,或者是其寓作于編的故意改動。從《道應訓》的論述邏輯看,其認為“多言”導致“數(shù)窮”的原因,乃是“書”中所載的圣人之“言”是過時無用的陳跡,依附先王之言而進行教化不足以應付事動時變,因此致力于先王之言,誦學詩書,只會導致“博學多聞,而不免于惑”。在這里,“書”和“言”已經產生直接聯(lián)系,而與《文子》對“聞”這種學習行為的反對所持理由不一樣。這種思想差別也反映在《道應訓》與《韓非子·喻老》之中:《道應訓》和《韓非子·喻老》共享了王壽焚書的寓言,但是,《道應訓》在某種意義上忽略了“焚書”行為上的象征意義,而是以“多言數(shù)窮”的說法,突出施政應對時事變化上先王之言的不足為恃。這就與《韓非子·喻老》所載王壽焚書的寓言用意略有區(qū)別。《韓非子·喻老》在用同樣的寓言表達“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篋”的觀點的同時,更強調了王壽焚書的行為本身體現(xiàn)了《老子》“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的精神,這就使得二者強調的重點顯示出一定差別。因此,以韓非引“學不學”來證明《道應訓》中“多聞”之是和“多言”之非的理由是不充分的,但我們可以通過二者引用同一個寓言管窺到《韓非子》對《老子》的理解和漢初黃老道家之間某種微妙的互動。
與《文子》《淮南子》等將“言”解釋為載之典籍的圣王之言不同,西漢末年的嚴君平在《老子指歸》中則將“言”闡釋為“政教法令”,其解釋“天地不仁”曰:“天地非傾心移意,勞精神,務有事,凄凄惻惻,流愛加利,布恩施厚,成遂萬物而有以為也……天地釋虛無而事愛利,則變化不通,物不盡生。圣人釋虛無而事愛利,則德澤不普,海內不并,恩不下究,事不盡成。……天地不言,以其虛無,得物之中,生物不窮。圣人不言,法令虛而合物則。”[9]127—128他認為,“仁愛之為術也分”,因此,明王圣主應與道同儀,以效法天地泊然無為,任萬物自化。“圣人不言,法令虛而合物則”則暗示,“多言”之“言”,即在于君主懷仁愛之心而造作施為的各種政教法令。這一思想與王弼的看法頗為類似。王弼在注解“天地不仁”時亦認為:“天地任自然,無為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為。造立施化,則物失其真。有恩有為,則物不具存。”而在注釋“多言數(shù)窮”時則指出:“愈為之則愈失之矣。物樹其惠,事措其言,不惠不濟,不言不理,必窮之數(shù)也。”[10]13-14同樣認為“多言”的政治實質是“有為”的政治,政治干涉越多,政治敗亡得也就越快。
綜上,將“言”或“聞”與“書”并談,通過強調典籍所記載的先圣之言不合事變時移之宜,以解釋“多聞數(shù)窮”或“多言數(shù)窮”,這顯然是黃老之學對《老子》“天地不仁”章進行的較為獨特的詮釋。“言”被直接的“法令化”或“政治化”,實際上是對漢代大一統(tǒng)之后法令滋彰社會現(xiàn)實的折射,“政教法令”當然比明王先圣載之典籍的德化之言更具政治意味,盡管二者可能在現(xiàn)實政治之中相互轉化。仔細玩味,強調“多言”導致速敗的原因在于先王之言的不合時宜,進而反對典籍的“教”和“學”,這之中大致還殘存著某些學術思想爭論的意味,但將“多言”直接與有為的政治聯(lián)系起來,批評現(xiàn)實政治的意味更明確。從文獻的成書而論,前者思想成形于罷黜百家之前,后者則是在思想獨尊儒術之后。由此也可見,思想的轉變總是和其時代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的。
四
上述內容只是大致對《老子》“天地不仁”章中“多聞數(shù)窮”和“多言數(shù)窮”的可能解釋進行的掛一漏萬的回顧和介紹,關注于文本在歷史詮釋之中的差異反映出來的思想差異,旨在揭示在中國的經典解釋傳統(tǒng)中可能的思想對話和觀念變遷的豐富性和復雜性。中國古代文本的形成相當復雜。后世學者所見的某一個文本或觀念的形成,往往是在相當長的時間中與其他學派思想激蕩而成。這也導致最初的文本或思想,在傳抄中經過無意或有意的改動,或者在某些特定的時代話題或思潮的影響下朝著某個方向被詮釋,最終變得面目全非,以致無從溯源以復其初。從思想理解的角度看,這也使我們認識到,在理解某一個文本時,實際上需要面對的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文本和思想群。例如,僅僅從《老子》的文本和自身的思想邏輯出發(fā),而不注意到儒家的思想背景,就很難在“多聞”和政治之間產生直接聯(lián)想;同理,如果沒有《文子》等文獻詮釋“言”與儒家經典之學之間存在的關聯(lián),我們也很難發(fā)現(xiàn)《老子》對“多言”的批評中包含著對“學”的否定。這些都意味著,在處理某一個文本或思想史問題時,開放與包容的心態(tài)和視野是十分必要的。
對《老子》“天地不仁”章早期的思想解釋史的回溯還顯示,不同學派思想的互相滲透和影響在思想史上相當普遍。《文子》和《莊子》在批評儒家時,都在“言”和其經典之學之間建立關聯(lián),這很難將之視作巧合。而《韓非子》《文子》以及《淮南子》在批評“言”時所使用的寓言與思想幾乎一致,都強調儒家的經典之學不足以應付事變時移,其區(qū)別僅在于《文子》沒有使用王壽焚書的寓言,而《淮南子》在沿襲《文子》思想史時卻援引了《韓非子》的寓言故事,三者之間存在著某種關系是顯而易見的。
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思想主題和現(xiàn)實背景,這些都難免會對解釋者的思想闡釋方向產生影響。處于西漢末年的嚴遵和生活在東漢曹魏之交的王弼,都將《老子》“天地不仁”章的版本定為“多言”而不是“多聞”,并且都將“多言”解釋為政令的煩苛,這會與他們分享了某些類似的時代背景毫無關聯(lián)嗎?對思想必須要能夠適應時代的變革進行特別強調,這樣的看法顯然更可能形成于一個大變革的時代之中,并且存在著某種思想上的市場競爭。分析某一個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有助于理解這樣一種思想為什么是這樣而不是那樣。
囿于學力的有限,本文的疏漏之處在所難免。例如,“聞”在先秦思想史中顯然具有更多意義。如出土的儒家文獻《五行》篇即將“聞”的作用抬得極高:“見而知之,知也;聞而知之,圣也。”“聞”成為與“圣”緊密相關的概念,這與《老子》否定“多聞”、主張“絕圣棄智”之間是否有關聯(lián)?又如《呂氏春秋》中對統(tǒng)治者“多聞”的嚴厲批評,認為治國“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這種批評和《老子》對“多聞”的批評之間有無思想淵源?這些問題本文都沒有展開討論。又例如,本文沒有討論《老子》河上公注從“養(yǎng)身”的角度對“多言數(shù)窮”的解釋(“多事害神,多言害身,口開舌舉,必有禍患”[11]13-14)的思想意義,也沒有探討王弼之后《老子》注釋者對此章的闡釋。毫無疑問,這些闡釋在思想史上也是極富意義的——但這些問題都只能有待于感興趣的方家給出更好的解答。
[1]張晶晶.“多聞數(shù)窮”與“多言數(shù)窮”——淺析《老子》第五章帛書本和通行本的不同[J].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6).
[2]陳鼓應.老子注譯及評介[M].北京:中華書局,2010.
[3]高明.帛書老子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1996.
[4]王博.中國儒學史(先秦卷) [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5]王博.簡帛思想文獻論集[M].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
[6]劉寶楠.論語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1990.
[7]劉笑敢.老子古今:五種對勘與析評引論(上冊)[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8]王利器.文子疏義 [M].北京:中華書局,2000.
[9]老子指歸[M].嚴遵,注.王德有,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4.
[10]王弼集校釋[M].樓宇烈,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
[11]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M].北京:中華書局,1993.
【責任編輯:高建立】
2015-08-16
劉世宇(1980—),男,湖北恩施人,博士生,主要從事中國先秦哲學研究。
B223.1
A
1672-3600(2015)10-00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