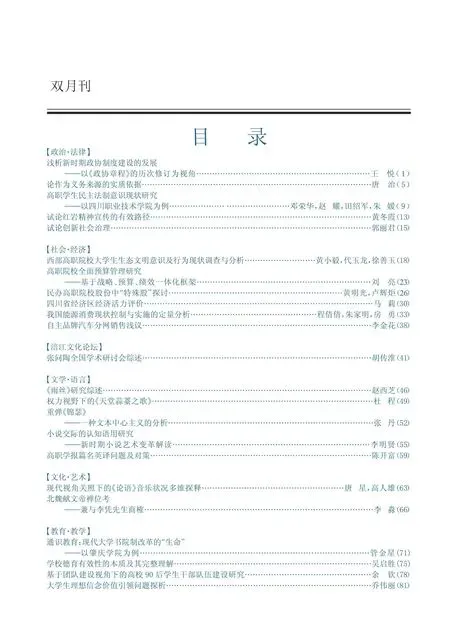權力視野下的《天堂蒜薹之歌》
杜程
(蘇州大學中文系,江蘇 蘇州 215123)
權力視野下的《天堂蒜薹之歌》
杜程
(蘇州大學中文系,江蘇 蘇州215123)
摘要:《天堂蒜薹之歌》敘寫了“天堂縣”蒜農們因為蒜薹滯銷而沖擊縣政府這一政治性事件的前前后后。本文試圖采用福柯的權力理論對“天堂縣”中權力的運行,權力對個人的懲戒,以及民眾對權力的反抗做出一定的歸納。從而得出:不受制約和監督的權力會對社會造成巨大危害的結論,并從中反思權力的制約和平衡對于社會的積極意義。
關鍵詞:天堂蒜薹之歌;權力;話語;運行;懲戒;反抗
《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以發生于中國山東的“蒜薹事件”為原型創作的長篇小說。1987年山東蒼山縣數千農民響應縣政府的號召大量種植蒜薹,結果蒜薹全部滯銷,縣政府官員反映遲緩,憂心如焚的農民自發聚集起來,釀成了震驚一時的“蒜薹事件”。得知這一消息之后,莫言擱置了正在寫作的《紅高粱》續集,用短短35天時間創作了《天堂蒜薹之歌》這部為農民“鳴不平的急就章”。莫言在《自序》中坦言:“長期以來,社會主義陣營里的文學,總是在政治的旋渦里掙扎。”①《天堂蒜薹之歌》正是這樣一部具有強烈政治和現實關切的作品。它反映了不受制約的權力在封閉的環境中給農民帶來的傷害,在習總書記大力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的時代背景下,《天堂蒜薹之歌》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本文試圖用福柯的權力理論,分析《天堂蒜薹之歌》中權力的運行、權力對人的規訓懲罰,并對權力的制約進行思索。
1 權力的運行
福柯筆下的權力有兩種含義:“行為的能力”和“支配他人的能力”。本文所分析的權力運行主要針對其后一種,它表述的是不同個體之間的一種關系,在兩個人中,如果一個處于支配地位而另一個處于服從地位,那么我們就可以說前者相對于后者具有權力。這種支配力在范戴克筆下意味著控制力,即一個群體對另外一些群體的控制。這種控制涉及行為和認知:一個權力群體不僅會限制其他群體的行為自由,也會影響他們的思想。
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們可以發現一種絕對權威的統治性權力編織著整個“天堂縣”。人與人之間處在支配與被支配,控制與被控制的關系之中。這種支配與控制的權力既體現在天堂縣政府與農民之間,也體現在每一個家庭內部;既體現在對肉體的管束上,又體現在對精神,知識和話語的統治上。
首先在家庭內部,我們發現“父權”在“天堂縣”農村中具有極端重要的位置。父親對子女的日常行為,婚姻愛情有著絕對控制權,在家庭事務的決策中具有無可辯駁的絕對權威。《天堂蒜薹之歌》中的方四叔一家正是作者有意塑造的典型。方四叔在家中向來說一不二,老婆、子女從來都不敢違逆。為了給身有殘疾的大兒子娶一房媳婦,方四叔和曹家,劉家簽訂了三家“換婚協議”,要將女兒金菊嫁給曹家半癱的幼子,從而換來楊家的女兒嫁給方家老大。兒女的終身大事就這樣在他們起初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被父親武斷的決定了。金菊在得知這一消息后,整日以淚洗面,面容憔悴卻不敢反對方四叔。金菊和高馬的愛情在情急之下被捅破,憤怒的方四叔將金菊狠揍一頓,關在家中。如果不是金高二人最后成功私奔而去,金菊必然會在父親的高壓之下,嫁給半癱的曹家幼子,從而斷送一生的幸福。由此可見父權在家庭內部的獨斷專行和最高權威。但是這種剛性的統治力,在父親一旦過世就會立即消失。方四叔在家中之時,兩個兒子雖然不和,但是不敢表現出來,等到四叔一死,兩人之間立馬鬧著分家,為了爭奪財產甚至大打出手。方四叔的權威隨著他的去世一起蕩然無存。
在整個社會中,“天堂縣”政府對于普通民眾同樣是絕對權威的。在沖擊政府之前,“天堂縣”的蒜農承擔著各個機關的各種不合理稅費,卻敢怒不敢言。在“天堂縣”這樣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中,政府以一種無制約的高壓性的強制力支配著民眾,保持著社會穩定。這種剛性的穩定將絕大多數矛盾壓服了下去,但是矛盾并沒有消失而是積累了下來,終于當矛盾積累到極限時,當農民賣不出辛苦種出的蒜薹時,所有的不滿爆發了,于是發生了沖擊政府事件。在事件發生后,暴力機關迅速反應,用更加高壓的手段將帶頭肇事者緝拿歸案。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政府的公權力就這樣被大大的濫用了。
《天堂蒜薹之歌》中“天堂縣”的各個機關并不是各自獨立的,它們彼此交連,相互關照,形成了一張復雜的權力網。福柯最早提出了“權力網”的概念。他認為“權力的合理性在于它的明確的戰術合理性。這些戰術環環相扣、彼此呼應、傳播蔓延。在權力關系之外尋找支點和條件,最終勾畫出整體機制。”②在蒜農進城賣蒜的途中,要經過工商局,衛生局,稅務局,城管所等等各個機關的設定的關卡,它們彼此參照,向蒜農們收取大量費用。本地機關還相互聯合,共同擠走外地收購公司,以實現本地壟斷經營,毫不顧及蒜農利益。在“天堂縣”的權力網中,各個機關同聲共氣,共同的利益將他們編織到了一起,成為權力網上的各個支點。
2 權力的懲戒
權力的懲戒包括訓誡和懲罰兩個部分。權力的訓誡告訴我們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權力的懲罰則告訴我們如果做了不該做的會導致什么樣的結果。在正常社會環境下,訓誡可以引導社會秩序的正常平穩發展,而懲罰則對訓誡起著保證作用。然而《天堂蒜薹之歌》中的“天堂縣”整個社會環境被扭曲了,權力的訓誡中處處體現著等級意識,而權力的懲罰則遠超過了法律規定的限度,甚至成為了單方面的施虐。
“天堂縣”的蒜農終沖擊政府機關后,暴力機關迅速行動,將高羊,高馬,張扣等人羈押歸案。正常的權力懲罰在這里變得暴力,野蠻而又血腥。警察在抓捕過程中對高羊百般虐待。“他扭動著身體,一根堅硬尖利的槐針扎進了肚皮,仿佛連腸子都扎著了,因為他感到腸子猛烈地抽動一下。為了讓槐針從肚皮上拔出來,他不得不把雙臂死勁往后拉——忍受著彈簧鐐銬咬進手脖的痛苦。他弓著背,垂著頭,看到黑紅色的槐針已從肚皮上拔出來,針尖上掛著一縷白色的纖維。肚皮上的孔里慢慢地滲出了一滴血,也是黑紅色,跟槐樹針的顏色一樣。”在審問張扣的過程中,張扣唱著自編自創的“天堂蒜薹之歌”,諷刺著當地的警察和政府官員,于是對瞎子張扣的審問顯得無比野蠻。“一位虎背熊腰的警察忍無可忍地跳起來,罵道:瞎種,你是天堂蒜薹案的頭號罪犯。老子不信制服不了你!他跳起來,一腳踢中了張扣的嘴巴。張扣的歌聲戛然而止。一股血水噴出來,幾顆雪白的牙齒落在了審訊室的地板上。張扣摸索著坐起來,警察又是一腳,將他放平在地。他的嘴里依然嗚嚕著,那是一些雖然模糊不清但令警察們膽戰心驚的話。警察抬腳還要踢時,被一位政府官員止住了。一個戴眼鏡的警察蹲在張扣身邊,用透明的膠紙牢牢地封住了他嘴巴。”在張扣被釋放之后,仍然堅持傳唱“天堂蒜薹之歌”,引發了“天堂縣”政府個別人士的強烈不滿,在多次警告未果之后,對張扣的肉體懲罰終于達到了最高峰:“‘你不閉住嘴巴,俺給你封住嘴巴!’一位白衣警察怒氣沖沖地說著,把手中二尺長的電警棍舉起來。電警棍頭上喇喇地噴著綠色的火花。‘俺用電封住你的嘴巴!’警察把電警棍戳在張扣嘴上。”最后張扣終于慘死于這種毫無人道的暴力執法之上。權力的懲罰在缺乏制約和監督的情況下從保護人民的手段變成了滿足一己私欲的工具。
3 權力的反抗
《天堂蒜薹之歌》中的蕓蕓眾生,直接或間接地,全都被籠罩在權力的陰影下。懦弱的高羊,勇敢的高馬,追求愛情的金菊,狡猾的方四嬸,他們都是權力的受害者,最后也都成為反抗權力的“暴民”。
天堂縣的蒜農們因為蒜薹擠壓,集中到政府門口,要求縣政府解決問題。由于多次要求縣長出面無果,蒜農們的情緒無法控制,開始沖擊縣政府,打砸政府辦公室。
蒜農們的行為絕非是偶然的、突發的,沖擊政府辦公室是矛盾激化的結果。天堂縣鼓勵農民種蒜薹,但是最后卻沒有力量全部收購,反而阻撓外地供銷社在天堂縣收購蒜薹,斷絕了蒜農自由出售的可能。再加上長期以來各個部門對蒜農的一些不合理政策,以及方四叔被鄉黨委書記的公車撞死等事件的刺激,矛盾爆發是必然結果。在“天堂縣”中我們可以發現政府行為幾乎沒有監督和制約力量,這同我黨我國的依法治國,依法執政原則是完全背離的。“天堂縣”的例子告訴我們權力缺乏制約會給社會帶來多大的危害,這種危害不僅是對民眾的,同時也是對政府自身的。民眾在切身利益受到嚴重侵害而又求告無門的情況下,會自發的保衛自己的權益,政府的公權力在這其中不免受到傷害。
但是,簡單的沖擊政府機構并沒有實際意義,除了表達不滿,發泄情緒之外,并不能解決“天堂縣”蒜農的實際問題。“天堂縣”需要的是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只有建立了一個完整的監督機制,積極推進依法治國建設,政府才能高效廉潔,民眾的利益才能得到保證。類似于“天堂蒜薹事件”的故事才不會繼續發生。
同時對于民眾我們需要提高法律意識,這不僅是為了防止類似于沖擊政府事件的重演,更為了更好地維護自身權益。在“天堂縣”民眾身上我們看到了中國農村固有的宗法制度的殘余和濃厚的等級意識。只有真正地有了公民精神,有了法律意識,農民才能同政府平等對話,才能監督政府的行為,才能真正維護自身權益,如同楊助理一般狐假虎威,為害鄉里的人物才能從此消失。家庭內部同樣需要平等意識,女子并不是父母斂財的工具,最后可以“一萬元賣掉”。戀愛自由,婚姻自由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就是文學作品普遍反映的問題,其中不乏《小二黑結婚》一般的佳作。可是直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同樣的問題仍然在中國農村出現,其中的問題就在于“父權”的權威在農村并沒有被打破。宗法制度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仍然在農村有所殘留,父親在家中獨掌大權,財產分配沒有女子的份額,這就必然使得農村女子的戀愛婚姻自由很難真正實現。只有平等意識普及,法制觀念健全,類似于金菊和高馬之間的悲慘愛情故事才能從此避免。
福柯認為對于權力的反抗和權利本身是一體兩面的,“反抗與權力是共生的、同時存在的。只要存在著權力關系,就會存在反抗的可能性。我們不能落入權力的圈套:我們總是能夠通過明確的策略來改變它的控制。”
任何社會,任何時候我們都需要保持對權力的高度警惕,這樣可以保持人格獨立和清醒意識。同時整個社會才能保持適度的緊張感,政府機關才會有活力,有動力,才能始終保持高效廉潔。“天堂縣”正是由于長期以來從上到下對權力毫無反抗,逆來順受,才使得權力愈發膨脹,最后積重難返,醞釀出了“蒜薹事件”,民眾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爆發了過于激烈的反抗,整個社會都為這次事件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需要時刻保持對權力一定的反抗意識的不止是民眾,同樣包括“天堂縣”縣委書記紀南城,縣長仲為民,乃至楊助理員在內的所有黨政機關工作人員。應該時刻警惕不要落入“權力的圈套”,自覺抵御權力的腐蝕,才能真正做到為人民服務。
注釋:
①莫言.天堂蒜薹之歌[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1:3
②福柯.杜小真(選編).福柯集[M].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3.
參考文獻:
[1]莫言.天堂蒜薹之歌[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1.
[2]福柯.權力的眼睛[M].嚴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福柯.福柯思想肖像[M].劉北成,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4]福柯.規訓與懲罰[M].劉北成,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
[5]福柯.福柯集[M].杜小真,譯.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
[6]張清華.敘述的極限——論莫言[J].當代作家評論,2003.
責任編輯:周哲良
中圖分類號:I20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094(2015)02-0049-03
收稿日期:2015-02-04
作者簡介:杜程(1989-),男,安徽宣城人,蘇州大學中文系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現當代文學。
On The Garlic Balla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DU Cheng
(Chinese Department of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123)
Abstract:The Garlic Ballads describes the events that people in Tiantang County attack the government because the garlic sprouts is unmarketable.Based on the Foucault's theory of discourse and power,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operation of the power and the individual discipline in Tiantang County.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power without restriction and supervision will cause great harm to the society. So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power restriction and balance in the society should be thought about.
Keywords:The Garlic Ballads; Power; Discourse; Operation; Punishment; Resis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