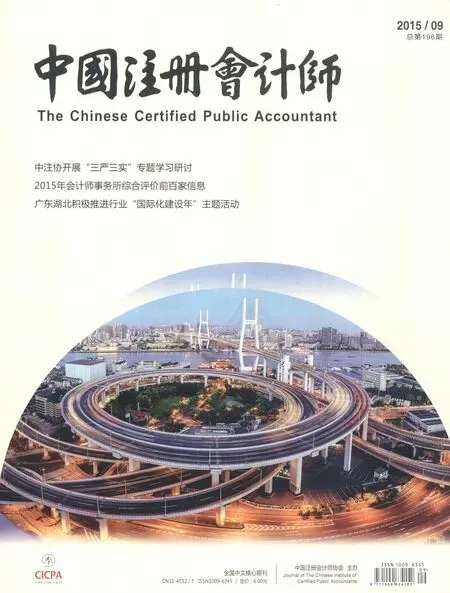上市公司財務(wù)欺詐行為的識別模型構(gòu)建與防范
張銀華
一、引言
2002年7月,中國注冊會計師協(xié)會發(fā)布了《審計技術(shù)提示第1號——財務(wù)欺詐風險》(以下簡稱《提示》),詳細列示了各種可能導(dǎo)致公司進行財務(wù)欺詐的因素,以及表明公司存在財務(wù)欺詐風險的“紅旗”,以提醒注冊會計師在執(zhí)行會計報表審計時對此予以充分關(guān)注,保持應(yīng)有的職業(yè)謹慎。遺憾的是,應(yīng)當選取哪些財務(wù)指標、該財務(wù)指標達到何種臨界值時財務(wù)欺詐可能性最大,對于這些具體操作性問題,《提示》并沒有提供直接的指導(dǎo)。
目前,上市公司財務(wù)欺詐行為不斷新穎化、復(fù)雜化及隱蔽化,如何建構(gòu)科學的財務(wù)欺詐行為識別模型,透過紛繁復(fù)雜的會計信息,避開財務(wù)報告中的陷阱,最大限度地降低與避免企業(yè)財務(wù)欺詐行為給投資者造成的風險,已經(jīng)成為日前學術(shù)界與實務(wù)界亟需解決的熱點話題之一。自國內(nèi)證券市場開市之后,許多上市企業(yè)因財務(wù)欺詐行為而收到證監(jiān)會的行政處罰,比如,銀廣夏股份公司以及被稱為“老牌績優(yōu)”的藍田股份公司等,這些僅僅是上市公司財務(wù)欺詐的一個縮影。近些年來,國內(nèi)證券市場中上市企業(yè)的財務(wù)欺詐行為已經(jīng)是“遍地開花”,上市企業(yè)財務(wù)欺詐行為不但誤導(dǎo)投資人與債權(quán)人,致使他們在失真的財務(wù)報告下做出錯誤的決策和判斷,同時還可以瞞過政府監(jiān)管部門的“眼睛”,致使監(jiān)管部門不能及時識別與發(fā)現(xiàn)上市公司的欺詐行為,不能很好地降低證券市場上的信貸風險。此外,上市公司的財務(wù)欺詐行為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影響到上市公司財務(wù)報告的審計監(jiān)督方的信譽,為注冊會計師的審計工作帶來信任危機。故而,信貸風險下財務(wù)欺詐行為不僅關(guān)乎到投資人與債權(quán)人的利益,還關(guān)乎著證監(jiān)部門以及會計師事務(wù)所工作的正常開展。
鑒于國內(nèi)在信貸風險下財務(wù)欺詐行為識別建模方面的研究空缺,本文循著《提示》思路,在綜合分析已有文獻各種欺詐因素的基礎(chǔ)上,研究哪些財務(wù)指標能夠有效顯示財務(wù)欺詐的存在,并選取其中最為有效的財務(wù)指標建立財務(wù)欺詐鑒別模型。并進一步進行了實證檢驗,證實了模型的可行性。
本文所提及的財務(wù)欺詐行為主要是指上市公司的財務(wù)報告舞弊行為,具體為管理當局在違反有關(guān)法律法規(guī)的前提下,故意臆造與公布虛假的財會信息報告,并借助于各種手段去歪曲企業(yè)自身某一特定會計期間內(nèi)的財務(wù)狀況、經(jīng)營成果以及現(xiàn)金流量等狀況,為投資者傳遞虛假信息,致使其做出錯誤的判斷與決策,進而實現(xiàn)企業(y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種違法行為。
二、理論回顧
國內(nèi)外對財務(wù)欺詐行為的研究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分別為財務(wù)欺詐行為存在的原因、發(fā)生的預(yù)兆以及識別與防范措施。本文主要從信貸風險下財務(wù)欺詐行為的識別與防范方面梳理國內(nèi)外理論研究成果。早在20世紀30年代,國外就已經(jīng)開始對企業(yè)財務(wù)欺詐行為進行研究,所以國外相應(yīng)的理論研究成果比較豐富。盡管國內(nèi)會計界對財務(wù)欺詐行為的研究還比較淺,但是自“銀廣夏事件”后,國內(nèi)學術(shù)界也逐漸開始關(guān)注企業(yè)財務(wù)欺詐行為,并獲得了一定的研究進展,對實踐工作帶來了很大的幫助。
在實證分析過程中,需要選取具有信貸業(yè)務(wù)的上市公司作為實證分析的總樣本,并且在這些上市公司中有一部分企業(yè)存在有財務(wù)欺詐行為,另一部分沒有財務(wù)欺詐行為。并將其分為評估樣本和檢驗樣本,其中評估樣本主要用于信貸風險下建立財務(wù)欺詐行為的識別模型,檢驗樣本主要用于驗證信貸風險下建立財務(wù)欺詐行為識別模型的可行性。
Bell and Carcello(2000)借助于來自 KPMG 審計實務(wù)中的 77家實施財務(wù)欺詐的企業(yè)與305家沒有財務(wù)欺詐行為的企業(yè)的數(shù)據(jù),構(gòu)建出財務(wù)欺詐行為的logistic 回歸識別模型,對該模型進行了實證檢驗,并指出企業(yè)外部審計人員可以利用此模型預(yù)測財務(wù)欺詐行為出現(xiàn)的概率,同時提出了信貸風險下企業(yè)財務(wù)欺詐行為出現(xiàn)的原因在于:企業(yè)內(nèi)部控制體系不健全、管理當局利益訴求、以及銀行業(yè)自身的原因等。Ch.Spathi(2002)在多變量統(tǒng)計技術(shù)與多標準分析能力的幫助下,實證分析了企業(yè)財務(wù)欺詐行為的識別問題,通過研究發(fā)現(xiàn),多標準分析判別技術(shù)優(yōu)于傳統(tǒng)的識別技術(shù),有利于財務(wù)欺詐行為的識別,同時還指出了企業(yè)財務(wù)比值在財務(wù)欺詐行為識別過程中的重要性。
王建瓊、王懷東(2009)以1998-2005年國內(nèi)因欺詐行為被處罰的33家上市公司為實證樣本,基于上市公司公開披露的財務(wù)信息報告構(gòu)建出上市公司財務(wù)欺詐行為判別的Logistic回歸模型,并通過了實證檢驗。馬天壤(2012)分析了國內(nèi)財務(wù)欺詐的現(xiàn)狀與對策,并對財務(wù)欺詐行為進行了界定,將財務(wù)欺詐行為界定為“在企業(yè)對外披露財務(wù)報表時,有意的錯報或者是漏報,達到欺騙財務(wù)報表運用者的目的”。李月梅(2012)指出國內(nèi)各地大量涌現(xiàn)財務(wù)欺詐事件,給經(jīng)濟發(fā)展帶來了巨大的創(chuàng)傷,并從財務(wù)欺詐的含義、財務(wù)欺詐行為目的、財務(wù)欺詐行為特征以及財務(wù)欺詐行為的外在表現(xiàn)等入手,對全面防范企業(yè)財務(wù)欺詐行為的對策進行了研究。趙自強與陳曦(2013)結(jié)合國內(nèi)上市公司現(xiàn)有的財務(wù)信息數(shù)據(jù),分析潛在的財務(wù)欺詐行為影響要素,對財務(wù)欺詐行為預(yù)測模型進行了實證分析,并利用這些欺詐風險要素構(gòu)建出企業(yè)財務(wù)欺詐行為的識別模型,以便更好地預(yù)測國內(nèi)上市公司財務(wù)報告欺詐行為。

表1 樣本T 檢驗

表2 變量回歸檢驗結(jié)果

表3 P 值
從總體上來講,經(jīng)由實證檢驗技術(shù)確立的識別模型是一種科學有效的模型,并具有一定的實踐運用價值,通過上述理論梳理發(fā)現(xiàn),借助于Logistic技術(shù)建立的回歸模型應(yīng)用頻率較高。所以,本文在全面綜合各種欺詐因素的前提下,借助于Logistic技術(shù)建立多元回歸模型,進而提出財務(wù)欺詐行為的識別模型與防范策略。
三、分析方法
(一)樣本選取
在實證分析過程中,需要選取具有信貸業(yè)務(wù)的上市公司作為實證分析的總樣本,并且在這些上市公司中有一部分企業(yè)存在有財務(wù)欺詐行為,另一部分沒有財務(wù)欺詐行為。并將其分為評估樣本和檢驗樣本,其中評估樣本主要用于信貸風險下建立財務(wù)欺詐行為的識別模型,檢驗樣本主要用于驗證信貸風險下建立財務(wù)欺詐行為識別模型的可行性。
(二)邏輯回歸分析
為了確保樣本的科學性和可靠性,需要對評估樣本進行邏輯回歸分析,而邏輯回歸分析具體是統(tǒng)計與識別研究對象,在進行邏輯回歸分析之前需要確定出觀測變量的類別和觀測變量的具體值。邏輯回歸分析從本質(zhì)上來講就是將眾多的變量信息進行歸集和分配,并據(jù)此構(gòu)建出相應(yīng)的識別模型,同時還需要確保識別模型在分類樣本時正確率達到最大。本文通過對“財務(wù)欺詐行為”與“非財務(wù)欺詐行為”的上市公司進行歸類分析,并以此為基礎(chǔ)探討出反映這兩種上市公司相關(guān)性較高的特征變量,并建立起財務(wù)欺詐行為識別模型。通常情況下邏輯回歸識別模型為:


表4 驗證p 值
其中,p是上市公司財務(wù)欺詐行為存在的概率,1-p是不存在財務(wù)欺詐行為的概率;a是截距;β 是回歸系數(shù),x為實證樣本的特征變量。
(三)評估樣本判別概率
將評估樣本上市公司進行標準化處理,接著將其相應(yīng)的財務(wù)數(shù)據(jù)指標代入(1)式,求得這些企業(yè)財務(wù)欺詐行為的判別概率。判別概率越高,就意味著企業(yè)的財務(wù)信息質(zhì)量越好,反之企業(yè)的財務(wù)質(zhì)量就越低,最后確定出財務(wù)欺詐與非財務(wù)欺詐上市公司的分割點。
(四)檢驗樣本驗證模型
用檢驗樣本進一步驗證財務(wù)欺詐行為識別模型的科學性與可行性,對上述利用評估樣本求出的分割點,運用檢驗樣本企業(yè)財務(wù)信息數(shù)據(jù)進行驗證,得出檢驗樣本企業(yè)的正確檢驗率,進而評價出上市公司財務(wù)欺詐行為識別模型的鑒別力。
四、實證分析
(一)樣本選取
本文實證分析的樣本主要來自于巨潮資訊以及兩大交易所網(wǎng)站披露出來的滬深兩市上市企業(yè)的財務(wù)信息報告。樣本選擇的具體標準為2009-2013年持續(xù)經(jīng)營、沒有被取消上市資格的企業(yè)。
1.財務(wù)欺詐樣本的選取。由于國內(nèi)證券市場發(fā)展較慢,被查處存在有財務(wù)欺詐行為的上市公司比較少,再加上一些財務(wù)欺詐的上市企業(yè)年份較早,因而,為鑒于國內(nèi)上市公司財務(wù)欺詐行為存在的普遍性,本文將年報審計意見為“否定意見”亦或是“拒絕表示意見”的企業(yè)界定為存在財務(wù)欺詐行為的樣本。在此基礎(chǔ)上,本文參照2009-2013年的年報審計告意見,選取了130家上市公司作為財務(wù)欺詐樣本進行實證分析。
2.配對樣本的選取。本文通過相應(yīng)的判定來確定配對樣本,即為滿足設(shè)定的條件,就可以界定為配對樣本。具體滿足的條件為:2009-2013年年報審計意見為 “標準無保留意見”、財務(wù)信息數(shù)據(jù)齊全、利潤與現(xiàn)金流量的乘積大于零。本文選出評估樣本中存在財務(wù)欺詐行為的上市公司為45家;與之相對應(yīng)的配對樣本45家主要依據(jù)會計期間相同、行業(yè)相似或相近以及企業(yè)規(guī)模相當?shù)臈l件選出。檢驗樣本為20家上市公司,其配對樣本同上選取方法。
(二)財務(wù)指標選取
有研究指出上市公司的負債組合會提升其管理層推行財務(wù)欺詐行為的概率,當財務(wù)杠桿提升時,財富就會從債權(quán)人轉(zhuǎn)向管理層,在既定債務(wù)契約既定情形中,管理者與所有者的信貸風險固化,也可以說一些風險已經(jīng)轉(zhuǎn)移到銀行。此類指標可以選用負債率(DR)與產(chǎn)權(quán)比率(ER)來反映。
權(quán)責發(fā)生制為上市公司財務(wù)欺詐行為提供了技術(shù)支持,具體包含有企業(yè)的銷售收入、應(yīng)收賬款、壞賬準備以及存貨,這些指標的主觀判斷性使得它們具有更大的審計難度,而應(yīng)收賬款是欺詐的核心。這類指標需要用應(yīng)收賬款存貨比率(AIR)、存貨比率(IR)與賒銷比率(CR)來反映。
盈利能力是企業(yè)盈余管理的重點,為了獲取更多的銀行貸款,業(yè)績相對較差的企業(yè)的欺詐可能性更大,此類指標可以選取毛利率(GPR)、銷售利潤率(SPR)以及資金周轉(zhuǎn)率(CTR)、營運資產(chǎn)率(OAR)來反映。
實證樣本數(shù)據(jù)收集之后,首先需要進行篩選和處理:剔除因行業(yè)因素而影響指標的樣本數(shù)據(jù),接著再對數(shù)據(jù)進行標準化處理。本文對樣本數(shù)據(jù)進行T檢驗,具體結(jié)果見表1所示。
通過T檢驗結(jié)果可以得出以下結(jié)論,從均值上來看,在信貸過程中存在財務(wù)欺詐行為的上市公司與不存在財務(wù)欺詐行為的上市公司的DR、AIR、GPR、CTR、OAR具有比較明顯的差異性,并且這些變量的雙尾T檢驗顯著性都在0.05之下,所以上市公司的DR、AIR、GPR、CTR、OAR具有顯著差異;在信貸過程中存在財務(wù)欺詐行為的上市公司與不存在財務(wù)欺詐行為的上市公司ER、IR、CR、SPR的差別較小,且雙尾T檢驗顯著性都在0.05之上,說明變量ER、IR、CR、SPR不能很好地區(qū)分出存在財務(wù)欺詐行為和不存在財務(wù)欺詐行為的上市公司。
通過上述分析,最終選取DR、AIR、GPR、CTR、OAR作為信貸風險下上市公司財務(wù)欺詐行為的識別模型變量。
(三)信貸風險下財務(wù)欺詐識別模型的構(gòu)建
對選取的90家評估樣本財務(wù)信息數(shù)據(jù),借助于統(tǒng)計分析軟件SPSS 17.0 進行邏輯回歸分析。邏輯回歸分析的具體流程是,依據(jù)已有觀測變量存在財務(wù)欺詐上市公司(y=0)與非財務(wù)欺詐上市公司(y≠0)的分類以及用以表示財務(wù)比率的變量,進而推導(dǎo)出相應(yīng)的邏輯回歸模型,并把相應(yīng)自變量的值回代到回歸模型中去。在構(gòu)建模型之前需要對所選財務(wù)比率變量進行邏輯分析,發(fā)現(xiàn)應(yīng)收賬款存貨比率變量未通過檢驗,故而需要將其剔除出去。接著再對所剩的財務(wù)比率變量與Y進行分析,結(jié)果顯示出模型具有一定的顯著性。
回歸檢驗結(jié)果見表2,在Wald統(tǒng)計檢驗結(jié)果中顯示,除X4在0.1水平上顯著,X1、X2、X3在0.05水平上顯著,進一步證實了兩種上市公司的特征變量之間具有顯著的差別性。
依據(jù)表2中回歸結(jié)果可以得到信貸風險下財務(wù)欺詐識別模型:

其中,X1、X2、X3、X4分別為DR、GPR、CTR、OAR。
接著需要將評估樣本上市公司各項財務(wù)比率值標準化之后的數(shù)據(jù)代入式(2),進而可以求得各評估樣本的p值,結(jié)果見表3。
用構(gòu)建好的模型對 90家原始樣本進行歸類,依據(jù)最小錯誤歸類原則,在p=0.5時,財務(wù)欺詐行為的上市公司<0.5的個數(shù)為43家,占到95.6%;配對樣本的上市公司>0.5的個數(shù)為42,占到93.3%。所以有94.4%的判斷正確率,原始樣本的預(yù)測結(jié)果相對比較滿意,故而,可以得出0.5即是這兩種上市公司的分界點。
(四)識別模型檢驗
為了進一步驗證構(gòu)建模型的可行性,本文將40家檢驗樣本的x1、x2、x3、x4四個變量值代入模型中,求出相應(yīng)的概率值p,并將p與0.5比較,比較結(jié)果見表4。
從表4中可以看出,小于0.5的財務(wù)欺詐上市公司為18家,大于0.5的配對樣本上市公司為18家,所以有90%的判斷正確率,由此可以看出本文構(gòu)建的信貸風險下財務(wù)欺詐行為識別模型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五、信貸風險下財務(wù)欺詐行為的防范
通過實證分析,毛利率(GPR)、銷售利潤率(SPR)以及資金周轉(zhuǎn)率(CTR)、營運資產(chǎn)率(OAR)界定為信貸風險下財務(wù)欺詐行為識別標準。較之于同行業(yè)來講,倘若上市公司在這些指標上存有異常狀況,就可以斷定該上市公司存有欺詐嫌疑,因此,需要采取相應(yīng)的措施來防范。比如,可以營造健康的信貸環(huán)境,規(guī)范政府部門對信貸市場以及上市公司的行政干預(yù)力度、健全注冊會計師審計體系、強化誠信體系建設(shè)、加強上市公司的內(nèi)部控制工作、完善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的管理系統(tǒng),建立相應(yīng)的會計準則等等。
與此同時,本文所選取的財務(wù)指標變量是縱向數(shù)據(jù),故而,在運用財務(wù)杠桿以及盈利能力等相關(guān)財務(wù)指標去辨識財務(wù)欺詐行為的同時,既能夠?qū)⑸鲜泄緮?shù)據(jù)與同行業(yè)進行比較,又能夠?qū)⑸鲜泄咀陨淼呢攧?wù)報告數(shù)據(jù)進行縱向化的比較。
1.Bell, Timothy B., Carcello, Joseph,Spring 2000,A decision aid for accessing the likelihood of fraudulent financial reporting,Auditing, 19:169-184.
2.Ch.Spathis, M.Doumpos and C.Zopounidis,2002,Detecting falsified financial statements:a comparative study using multicriteria analysis and multivariates statistical techniques,The 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 11::509-535.
3.王建瓊,王懷東.財務(wù)欺詐手段識別:來自中國上市公司的實證分析.軟科學.2009(12)
4.馬天壤.我國財務(wù)欺詐的現(xiàn)狀與對策.人口與經(jīng)濟.2012
5.李月梅.論財務(wù)欺詐的防范.山西財經(jīng)大學學報.2012
6.趙自強,陳曦.我國上市公司風險因素與財務(wù)報表舞弊預(yù)測.商業(yè)研究.20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