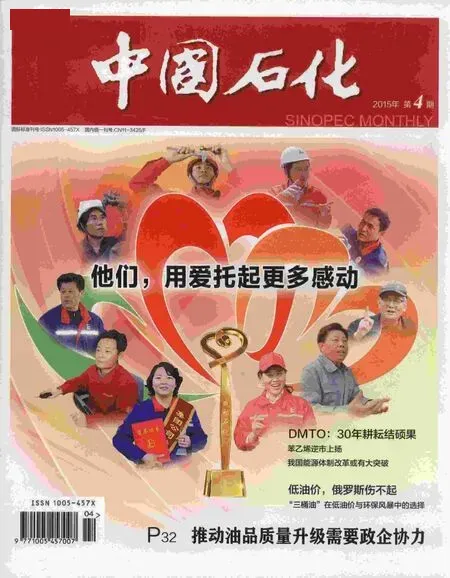DMTO:30年耕耘結碩果
□ 本刊記者 許帆婷 李建永 田 源
編者按:1月9日,在2014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中國石化煉化工程集團(SEG)洛陽工程有限公司與中科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新興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聯合研發的甲醇制取低碳烯烴(DMTO)技術摘得國家技術發明獎(通用類)一等獎。從中科院大連化物所開始基礎研究攻關開始,DMTO技術研發經歷了30余年的歷程。洛陽工程公司攻關團隊承擔了DMTO的工藝設計和工程放大的任務,為DMTO技術從實驗室走向工業化付出了不懈努力。本期《關注》欄目的一組文章將為讀者展現DMTO技術誕生、發展的基本歷程,并對該技術的未來發展前景進行客觀分析。
“有大連化物所扎實的研究,有三方精誠合作的團隊,再有兩次放大一百倍的工程開發。”陳俊武院士這樣總結DMTO的成功之道。
2015年4月初,殘冬的余寒尚未完全褪去。滕州這個魯南小城的郊外,聯想控股聯泓集團神達/昊達DMTO裝置簇新锃亮的表面在陽光下熠熠生輝。這套去年12月剛剛投產的甲醇制烯烴裝置,是連接聯想集團煤化工產業鏈上下游的關鍵一環。
“整套裝置包括DMTO和烯烴分離都是洛陽工程公司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沒想到開車這么順利。” 聯泓集團副總裁兼神達昊達公司總經理陳德燁的言談中充滿了對洛陽工程公司項目團隊的佩服,“他們樹立了MTO工程的標桿。”
就在今年1月9日,在2014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中石化煉化工程集團(SEG)洛陽工程公司與中科院大連化物所、新興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聯合研發的甲醇制取低碳烯烴(DMTO)技術,摘得國家技術發明獎(通用類)唯一的一等獎。
艱難的開始

1997年的一天,中國科學院院士、時任洛陽工程公司技術委員會主任的陳俊武,在辦公室里接待了來自中國科學院大連化物所的幾位客人。其中,有一位是從事了十幾年DMTO研究開發的王公慰研究員,還有一位年輕人則是目前的DMTO技術負責人劉中民研究員。
“甲醇制烯烴,我們已經選定了催化劑,想接著往下進行工程技術開發和設計。”劉中民向陳院士表達了合作意愿。
20世紀70、80年代的石油危機使醇醚制烯烴的技術路線在世界上形成研究熱潮。與石化行業有千絲萬縷聯系的中科院大連化物所瞄準了這項技術。
由于DMTO工藝專用催化劑反應后快速失活,想要推進甲醇制烯烴的工業化,必須借鑒催化裂化幾十年的工業經驗,使用流態化工程技術。國內首屈一指的權威單位就是中石化洛陽工程有限公司。
陳俊武院士經過仔細思考,認為這件事在戰術上有把握,戰略上也有廣闊的應用前景。雙方一拍即合,開始了20年的合作之路。
“雖然現在石油價格低,但長期趨勢是上漲的。中國缺石油,但煤多,便宜,用煤制甲醇生產烯烴的路線是可行的。”陳俊武做出了這樣的戰略決定,他的眼光很準。
然而,似乎是時勢弄人,1997年以后國際油價一路下行,當時已經為中石油西南石油局做好的MTO可研方案擱淺了。隨后數年,雙方一起找過幾家業主,也因種種緣由沒有了下文。
寶劍封匣,十年蟄隱。研究者的心卻始終系在MTO發展的脈絡上。“當時我們盡管沒有用戶,仍然一直跟蹤國外技術進展,用紅字標注相關專利要點,復印給陳院士。” 洛陽工程公司資深專家陳香生說,“埃克森美孚和UOP的專利包括了各種設計方案,但真正的核心數據卻沒有。”2000年前后,陳香生無意中查找到歐洲一個研究機構發表的專利,其中談到催化劑積炭與選擇性的數據。
“我不是搞工程設計的,沒有引起太大注意,但陳院士看完后說很重要。他與大連提供的實驗室數據進行對比,認可了這一結論。認定這是MTO與催化裂化一系列工程技術差別的核心,也是MTO工藝工程技術開發的出發點。”陳香生回憶。
2004年,在時任陜西省省長賈治邦組織的專家學者研討經濟發展思路會議上,省政府經濟顧問李毓強教授推薦了DMTO技術,希望可以借此開發陜北的優質煤資源。陜西省政府當即決策,由陜西國有企業出資幫助大化所完成工業化試驗,然后在陜西建大型工業裝置。試驗的風險投資由陜西方面承擔。通過李毓強教授牽線,三方于2004年8月2日達成了具有歷史意義的DMTO技術開發合作協議。
2006年,DMTO技術又一次遇到了重大轉機。神華包頭煤化工項目決定要上MTO裝置,當時與美國UOP公司談技術轉讓已經談得很深了。時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長的張國寶得知DMTO技術正在進行萬噸級工業試驗,要求神華再等半年,如果試驗成功,就采用國產技術。“所以神華項目只有MTO這一段采用的是國產技術,其他所有裝置都是引進的,包括烯烴分離。”洛陽工程公司副總工程師劉昱說。
回想起十余年DMTO攻關經歷,陳俊武不無感慨:“30多歲參與了催化裂化的設計開發,70多歲又遇到了MTO。我這輩子沒白過。”
六年間,兩次跨躍
“2004年8月8日,在陜西榆林啟動工業性試驗裝置動工儀式;2010年8月8日,神華包頭DMTO裝置投產,正巧是同一個日子。”對劉中民來說,這是個永遠不會忘記的日子。6年間,DMTO技術從實驗室走向工業化,實現了兩個“一百倍”工程放大的跨越。

□ 陳俊武院士(左二)、劉中民研究員(右二)、劉昱副總工程師(左)與陜西新興煤化工有限公司總經理袁知中(右)在神華包頭MTO裝置指導開車。陳香生 攝
洛陽工程公司和中科院大連化物所剛開展合作的時候,美國UOP公司已經做了1.5噸/天規模的試驗,對外宣稱可以直接建進料百萬噸級的裝置。劉中民問陳院士能做多大,得到的答復是最好先做萬噸級的工業試驗。“這不還是趕不過人家嗎?陳院士讓我眼光放長遠一些,認為一步放大一萬倍到工業裝置風險太大了。事實證明陳院士判斷很對。必須老老實實走這一步,先做一個每天進料50噸甲醇的工業性試驗,分兩步走。”劉中民說。
華縣工業化實驗裝置主要目的是發現實驗室條件與工業條件的規律和差別,為百萬噸級商業化裝置提供設計基礎數據。
神華包頭180萬噸/年DMTO裝置規模是再次放大“一百倍”的結果。“第一套工業裝置的規模是經過嚴格論證的。180萬噸DMTO裝置的反再系統和350萬噸催化裂化的裝置規模大致相當,在我們工程經驗范圍內,把握最大。”洛陽工程公司資深專家梁龍虎介紹。
然而,各種意料之中與意料之外的困難紛至沓來。
“當時主要擔心的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安全、環保等能把你‘一票否決’的因素。”華縣的試驗裝置周圍都是農村,人員狀況復雜,劉中民的心一直懸著。
DMTO裝置是神華包頭項目工業鏈條中唯一采用國產技術的,而且是首次工業化的技術,受到了普遍的質疑。“包頭項目從前端的煤氣化、凈化,到后端的聚乙烯、聚丙烯,都是國外成熟的技術。如果把整個項目比喻成一個啞鈴,那么DMTO就是中間的把兒。假如把兒斷了,一百五十多億的投資該怎么辦?”洛陽工程公司神華DMTO項目經理楊杰覺得大家的擔心可以理解,“當時很多人并不看好DMTO首次工業化嘗試,神華集團甚至做好了開車不成功的預案。”
楊杰感受的壓力還來自于神華項目的工期。“按合同我們要在2010年5月25日前中交,建設周期19個月,跨越兩個冬季。”包頭的冬天,極端溫度零下30多度,采暖季從每年10月15日至次年4月15日,長達半年。按照事先規劃,反再系統要在2009年4月份達到吊裝條件。因此,必須在2008年冬季把反應器基礎建設封頂。
“反應器高24米,相當于8層樓的高度,在零下25度的條件下,用腳手架搭棚子整個包圍起來,在里面燒爐子,保證內部溫度滿足混凝土的澆筑要求。”楊杰說,“現場施工經理半夜冒著嚴寒,拿著測溫計一個帳篷一個帳篷鉆,檢查溫度和環境有沒有問題。2008年的冬天,我們就是這么度過的。”
2010年8月,神華180萬噸/年DMTO工業示范裝置開車成功,成為世界首套、全球規模最大的甲醇制烯烴裝置。成功的背后,是洛陽工程公司開發團隊十幾個專業組、幾十名研究者上百次大小討論、無數個不眠的夜晚。
“有大連化物所扎實的研究,有三方精誠合作的團隊,再有兩次放大一百倍的工程開發。”陳俊武院士這樣總結DMTO的成功之道。
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碰撞
“像DMTO這樣的大項目,需要多兵種大兵團作戰,我們與洛陽工程公司的合作是優勢互補。”談起合作,中國科學院院士、中科院大連化物所所長張濤對洛陽工程公司在催化裂化方面的功底十分佩服。事實上,這也不是雙方的第一次合作。
為了促進科研成果轉化,洛陽工程公司和大連化物所的“握手”堪稱企業與科研院所強強聯合的典范。可以想見,這種合作并不是一開始就一帆風順。
“我是做研究的,他們是搞工程的。做研究的人多少都有點理想主義,看到什么都不滿意。他們就比較實際。”劉中民笑稱,技術問題難免有分歧,觀點不一致,越討論就越清楚。“但當時那個環境,就不是個心平氣和的場合,壓力很大,大家還‘吵’過幾次。”
陳香生還清楚地記得,在華縣做試驗的時候一件“紅過臉”的事。現場的選擇性始終達不到實驗室80%以上這一水平。為此,80歲高齡的陳院士還兩次赴大連化物所調研實驗數據,分析差異的原因。最終發現,這是由于工業化放大的裝置,在加熱方式、輸送方式、物料分配等方面與實驗室裝置不太相同。
“實驗室往往不考慮工程放大的特點,有時候他們的要求在工程上確實難以滿足。實驗室很容易達到的選擇性,工業上往往就不行。”劉昱解釋,比如實驗室要求催化劑很快分離,但實際上從密相到稀相有個分離空間。這是一個不斷磨合、不斷溝通的艱苦過程。“前提是相互信任。”
“還有一次試驗,在開工的時候催化劑活性突然往下掉。我就懷疑他們的催化劑有問題。”陳香生回憶,為了防止反應溫度過高,反應器頂部設計有一個噴水霧化的激冷設施,一般不會啟用,為試驗激冷效果曾試驗過一次。大連認為催化劑沒問題,是噴水激冷噴壞了催化劑。雙方產生了爭議。陳香生建議,在噴水前先取個樣。實驗的結果表明,分子篩晶體沒問題,是催化劑強度問題致使破損。后來大連化物所將催化劑帶回實驗室驗證,制備工藝調整后再沒出現活性下降的問題。
“大連化物所有一個合作的優點,他做他的理論,不干涉你的工程。他只提要求,至于怎么實現,對你完全信任。”在劉昱的眼中,大連化物所的團隊已經成了最好的朋友。回想起那段經歷,變得愉快起來。
“大連化物所是原始創新的發起者,我們圍繞DMTO工藝技術工程化、大型化和工業化做了大量的開發工作,既有協同創新和集成創新,又參與了其中的原始創新,起到了橋梁和紐帶作用。”全程參與了DMTO項目攻關的洛陽工程公司黨委書記王國良這樣評價雙方的合作。
對洛陽工程公司本身來說,DMTO項目創出了一個新的業務天地。“當時三方簽協議,約定一起對外許可技術,洛陽工程公司除了占有一定比例的技術許可的份額外,還約定了開展相關工程設計的條款。”洛陽工程公司市場部相關人員介紹,“使用DMTO技術,業主要跟洛陽工程公司談設計合同,至于是否選擇EPC(項目總承包)模式就看業主的情況了。”目前洛陽工程公司EPC項目中,DMTO項目占了相當大的比例。
前路漫漫修且遠
神華DMTO項目的成功形成良好的示范作用。一時間,擁躉者眾。
到目前為止,DMTO技術一共許可了20套,已經開車成功7套,其中大多數是洛陽工程公司做EPC的項目。“上DMTO項目的多是新業主,對他們而言做EPC的好處是不需要投入太多管理力量,減少中間環節、縮短工期。”洛陽工程公司市場部負責人介紹。
雖然技術已經相對成熟,但對洛陽工程公司來說,開拓市場的過程遠非風平浪靜。每個業主都有個性化的需求。青海鹽湖項目,地處高原,空氣稀薄,地基遇淡水即沉,電氣設備遇鹽霧易腐,給施工帶來不小考驗;山東神達項目,地下都是堅硬的巖石,鋪設管線必須一炮一炮地把地崩開;延長靖邊項目,煤油共煉,是煤化工與傳統煉油化工的結合,需要在設計上單獨考慮。
“到去年年底,煤制烯烴的總產能大概在700萬噸/年左右,等我們所有的裝置都開起來,到2016年總產能估計在1800萬噸/年左右。”梁龍虎說。根據陳俊武院士估算,甲醇制烯烴對傳統石腦油制烯烴的產能替代率在百分之二十左右為宜。市場空間有限,DMTO技術想要走得更遠,必須不斷進步。

□ 世界首套全球規模最大的180萬噸年煤基甲醇制烯烴MTO工業示范裝置在內蒙古建成投產。 陳香生 攝
隨著新裝置的不斷投產,技術也越來越成熟。“由于催化劑是采用不完全再生工藝,如果對生焦和燒焦兩個步驟處理不好會引起超溫的問題。”劉昱介紹,在寧波禾元裝置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控制新鮮催化劑生焦的問題,在后面的裝置上都得到很好解決。“業主給我們反饋,我們認真研究后就會在下一套裝置上改進。”
與此同時,大連化物所與洛陽工程公司聯合研發的DMTO二代技術,在陜西蒲城開車成功。二代技術加了一個C4+回煉裝置,丙烯收率可以提高7~8個百分點。“二代裝置要做大量設計工作,同一個催化劑要滿足兩個不同條件,形式更復雜。”劉昱說。
“為了支撐工業發展,理論研究一直在改進。我們花了很多功夫做基礎研究,目的就是把原理弄得更明白。”劉中民說。這不是DMTO獨有的,整個化工界仍處在對原理的不斷探索中。催化裂化的反應機理至今仍在不斷探索和提升中,DMTO的甲醇根本沒有碳-碳鍵,但反應產物有碳-碳鍵,這是怎么產生的?“我們對原理比以往更明白了一些,但依然任重道遠。”
DMTO技術要走向國際市場,還面臨著標準化問題。“沒有規范的MTO技術標準,要推廣到國外就很難。現在DMTO的實際操作中,很多都用的是催化裂化的技術標準,但它究竟合適不合適還有待考量。”陳香生建議,“希望行業協會能牽頭去做這項工作。”
對于DMTO技術的前景,聯泓集團副總裁陳德燁十分看好:“它增加了國內化工的多樣性。一個行業需要有激烈競爭才會進步,否則永遠都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