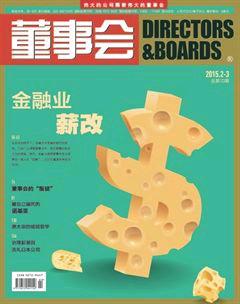別讓董事不懂事

董事會并沒有發生效用
美國在安然事件后展開第一波監管改革以來,已經超過十年。盡管監管機構提出許多指導方針,但大多數董事會并沒有核心使命:提供有力的監督,同時策略性地支持管理層努力創造長期價值。這不只是片面看法,很多董事也認為,董事會的表現不理想。
麥肯錫針對772名董事進行問卷調查,其中只有34%的受訪者認為,他們任職的董事會充分了解公司策略;只有22%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董事會十分明白自己的企業如何創造價值;只有16%的受訪者說,他們的董事會非常了解公司所處產業的動態。
麥肯錫與加拿大退休金計劃投資委員會(CPPIB),早前詢問世界各地604位高管與董事,哪一種壓力來源,是導致他們任職的組織過分強調短期財務成績、忽視長期價值創造的最重要因素。出現最多次的答復,竟然認為最大壓力來源是董事會——47%的受訪者選擇這個答案。甚至有47 位受訪者表明自己是上市公司董事,其中有74%的人把矛頭指向自己。
這樣的調查結果很令人震驚。顯然,答案不在于強制要求董事進行另一回合的良好公司治理項目勾選,以及種種配合動作,那種做法不足以改善情況。企業如何加強董事會的認知,并且協助董事建立、維持、改善長期的心態?
選擇對的人
根據Activist Insight 公司為全球化律師事務所年利達(Linklaters)所做的研究,從2010年1月到2013 年9 月,行動派股東干預的數目增加了88%,令人驚訝。據悉,這類干預包括挑戰公司以爭取董事席次、股票回購、撤換CEO等。美國主要的私募股權公司CCMP Capital 總裁兼CEO史帝文·莫瑞(Stephen Murray)宣稱,“行動派股東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一般認為上市公司董事會的能力不夠,無法滿足股東的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麥肯錫公司在2014年9月調查了692 位董事及C級高管,其中只有14%勾選了“有獨立思考的美譽”,而這本該是上市公司董事會任命新董事時考慮的主要標準之一。
此外,上市公司董事會往往沒有充分考慮到,要吸引合適的企業專長人才,這種情況不同于私募界在尋求普通合伙人或成功的家族企業的做法。除了深厚的領域知識之外,擁有多元化的觀點、在建立相關事業方面擁有豐富的經歷,都是極為重要的。但目前的情況是,太多董事是通才。正如加拿大大型礦業公司泰克資源(Teck Resources)的CEO唐·林賽(Don Lindsay)所言,“對這一行原本沒有太大興趣的通才型董事有個大問題,那就是我們可能需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說服他們做出重要的決定。”
展開優質的談話
巴克萊的董事會主席大衛·沃克爵士就直言不諱地指出,“我首先問董事會的問題就是,他們是否花了足夠的時間和精力來評估公司的長期戰略,如果他們誠實,答案肯定是‘沒有’。”
大多數治理專家都認為,上市公司的董事需要花更多的時間來理解并制定策略。其中有些人的建議來得很具體。MFS投資管理公司的前主席兼哈佛商學院前高級講師羅伯特·波正(Robert Pozen)說,超大型公司的董事除參加定期的董事會會議,每月至少要花兩天時間,或者每年花24天的時間來履行職責。根據麥肯錫在英國的一項調查,私人企業的董事每年應花費多達54天的時間。
雖然董事每年至少有35天的時間扎在董事會工作上,但具體是多長時間并不是最關鍵的。既然目標是培養長遠而正確的眼光,那么最關鍵的就是進行高質量和有深度的戰略對話。在實際操作中,并不是非要建立戰略委員會,因為審計委員會或風險委員會的職責已經包括了這一項。正如沃克所說,對公司來講,戰略才是根本挑戰,所以整個董事會都要參與其中。而為了確保長遠的對話和正確的戰略決策,集體努力才是至關重要的。
接觸機構投資者
盡管很多人將高管追求短期業績的行為歸罪于董事會,但這種壓力背后的真正根源是資本市場。所以,董事會應當用長遠眼光來看待資本,并極力說服機構投資者也這么做,因為機構投資者獨特的所有權地位使其成為遏制短線炒作的強大力量。
董事會可以并且應該更積極地與長期股東進行對話,相信許多投資者對此都會欣然接受。黑巖集團(Blackrock)是世界上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坐擁4.5萬億美元巨額資產,已經在爭取與管理層和董事會接觸,正如CEO拉里·芬克所說的“有力的、持續的溝通”。“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要對公司的經營指手畫腳。”芬克強調,“我們只是想確保有一個高質量的董事會和管理團隊,以服務于公司的長遠利益和客戶的長期利益”。
更多的公司應該采用這種方法。其實,有50%的受訪董事認為,與長期股東就公司的長遠戰略和業績進行交流有利無害,能最有效地緩解追求短期回報和高位股價的壓力。前提只有一個:這種交流必須是雙向對話,而不是單一告白。
放長線釣大魚
優秀的資本家都信仰金錢激勵。道理很簡單,既然我們要人家做很多事情,比如只擔任少數幾家公司的董事,更深入、更公開地參與公司事務,花更多的時間來探討和交流長期戰略,承擔極大的名譽風險,那么就應該付給他們更高的報酬。這無疑值得舉雙手贊成,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安排薪資結構。許多公司已經由混合型激勵轉向長期回報。
幾年前,強生建立了最低所有權原則,旨在使非執行董事的利益更多地與股東回報掛鉤。強生要求每個董事持股量約等于其年度現金分紅的五倍。可口可樂也規定:董事的股票獎勵要在其離開董事會之后才可兌現。通用電氣也采用了類似的辦法。
雖然以上這些舉措來得相對簡單清晰,但絕非易事,因為所有的措施必須符合公司實情和行業背景。提出并堅決執行這些辦法需要董事會主席和各成員的靈活處理,更需要與CEO展開精誠合作。最終,公司文化、行為、治理結構都會發生深刻的轉變。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優質公司將創造股東以及大眾都期望的長期價值。
源于哈佛商業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