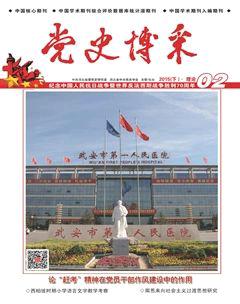西柏坡時(shí)期小學(xué)語言文字教學(xué)考察
李霞
西柏坡時(shí)期的教育是新中國教育事業(yè)的重要奠基時(shí)期,這一時(shí)期的探索,為新中國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寶貴經(jīng)驗(yàn)。本文試從西柏坡時(shí)期初小教學(xué)過程漢字書寫的教與學(xué)、作業(yè)與練習(xí)、錯(cuò)別字的改正、造句與作文等對(duì)語言文字教學(xué)進(jìn)行考察,分析西柏坡時(shí)期語言文字教學(xué)的時(shí)代特色。
一、注重讀音與書寫
西柏坡時(shí)期初級(jí)小學(xué)設(shè)國語課程,該課程教學(xué)目的在于提高學(xué)生的語言文字認(rèn)知和運(yùn)用能力。
晉察冀解放區(qū)初級(jí)小學(xué)《國語》教材共8冊(cè),1-4冊(cè)每冊(cè)45篇課文,5-8冊(cè)每冊(cè)50篇課文。一般小學(xué)每課教學(xué)時(shí)間80分鐘至120分鐘(兩節(jié)或三節(jié))。教師通過課堂講解課文,使學(xué)生學(xué)習(xí)、掌握該篇課文中的生字詞。教授漢字讀音時(shí),一般是先由教師領(lǐng)讀幾遍,后由學(xué)生讀,如此記住生字詞的發(fā)音。對(duì)于生字的識(shí)記,課本編纂者有明確要求:“新學(xué)生字,必須強(qiáng)調(diào)多寫,并分析字的偏旁結(jié)構(gòu),區(qū)別類似字的不同點(diǎn),以便兒童記憶”。[1]部分教員還采取了識(shí)字牌方法。如唐縣南唐梅小學(xué)教員馬振山,利用硬紙夾等制作識(shí)字牌,將生字寫上,“教國語時(shí)可利用它教生字用,把國語上的生字寫上教學(xué)生念或?qū)懀貏e是利用小先生教小的同學(xué)最好。學(xué)生去生產(chǎn)時(shí),可帶到地里去學(xué)習(xí),帶著又輕便,學(xué)習(xí)又便利”。[2]實(shí)際上,戰(zhàn)爭(zhēng)年代的教學(xué)往往是在作戰(zhàn)的間隙展開的。據(jù)原石門地下工作者邢燕先生回憶,在抗日根據(jù)地和解放區(qū)學(xué)文化時(shí),教寫字的老師往往不是專職的,尋找部隊(duì)有文化的人擔(dān)任。以墻壁為黑板,石灰、土坷垃(土塊)等為粉筆。“學(xué)生席地而坐,用一塊石板、甚至在地上練習(xí)寫字,就這樣我從文盲學(xué)到了可以寫文章。”[3]
對(duì)于生字的書寫,教員要求不可亂寫亂畫,要字整行齊。部分教員自寫仿影,讓學(xué)生照著仿影寫。《冀中教育》1949年第2卷第2期中報(bào)道:“李峙周是深縣清輝頭完小的教師……他的辦法是自己只寫樣子,叫高年級(jí)寫字較好的照著寫;寫完后,再挑好的給低年級(jí)做仿影,這樣又引起了高年級(jí)學(xué)生仿影的比賽。他在復(fù)式教學(xué)中,督促正在寫字的班次時(shí),要學(xué)生每寫一句,心里要念幾個(gè)過,并想一想怎么講,寫完后即能默讀。這以寫代讀的辦法,經(jīng)他試驗(yàn),有三分之二的人能做到。”[4]利用復(fù)式教學(xué)的便利與寫仿影的方式,不僅幫助學(xué)生寫好字,并且激發(fā)了學(xué)生們的上進(jìn)心。
對(duì)于生字詞的釋義,教員們則采取生動(dòng)形象的舉例子,模仿等形式。如阜平石灘頭小學(xué)教員耿明倫的教學(xué)方法是:“(一)讀字音:遇到難發(fā)的音,易錯(cuò)的字,要多范讀,令學(xué)生隨讀,逐一矯正的。發(fā)字音時(shí),教師的口腔,要表演各種形狀,使兒童容易模仿。凡兩個(gè)字以上的詞,要連在一起,使音域有自然變化,才能讀出正確的音調(diào)。(二)解字義:字義的解釋,要用各種方式,使學(xué)生能夠明了,如教‘坐、跑、笑等字可用表演法,如教‘黑、白等字可用實(shí)物比較,如教‘什么、就造一句子說明,如‘這是什么東西,‘吃了飯就上學(xué)”。[5]教員的范讀能使學(xué)生更為直觀地學(xué)習(xí)字詞的發(fā)音,避免個(gè)人領(lǐng)會(huì)錯(cuò)誤;而教員采取靈活多樣的方式解釋字詞意思,更讓學(xué)生在生動(dòng)活潑的氛圍中記憶,激發(fā)了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熱情與學(xué)習(xí)主動(dòng)性。
二、加強(qiáng)課后作業(yè)與練習(xí)
西柏坡時(shí)期初小課本在每組課文后有相應(yīng)練習(xí)題,以檢查鞏固學(xué)生所學(xué)的知識(shí)。如華北新華書店1948年10月出版的《國語》初小第四冊(cè),全書分為8個(gè)單元,每個(gè)單元一套練習(xí)題,共有八套。每套練習(xí)有3-4道題,最常出現(xiàn)的題型主要是讀讀講講,將本組課文中學(xué)到的生字組成多個(gè)詞語與短句,讓學(xué)生多方面了解該字詞的用法。在該冊(cè)第一單元練習(xí)一中的讀讀講講就有:“午,上午,下午,中午,睡午覺,現(xiàn)在已到正午了;戰(zhàn),參戰(zhàn),戰(zhàn)士,挑戰(zhàn),歡送新戰(zhàn)士;拉,拉過來,拉著走,拉斷了,請(qǐng)你拉拉這輛小車”等。另外有填詞,形近字辨析,兩字合一字,填寫近、反義字等。練習(xí)由淺入深,并注意加強(qiáng)“詞”與“術(shù)語”的記憶與運(yùn)用,然后連詞成句或造句。例如第三單元練習(xí)三中的造句題:“用‘缺少、‘能夠、‘忘記、‘強(qiáng)壯各造一句話”。另有問答或討論題來檢測(cè)學(xué)生知識(shí)掌握程度與語言表達(dá)能力。如第七單元練習(xí)七中討論題“(一)咱們同學(xué)中有鬧不團(tuán)結(jié)的嗎?(二)過去有人說地主的福氣大,這話對(duì)不對(duì)?”而課后“做一做” 練習(xí),則是將學(xué)生所學(xué)的字、詞、句、文應(yīng)用到實(shí)際生活中。如練習(xí)六中的做一做:“廣安村政府,把小米三千斤送到七區(qū)區(qū)公所,請(qǐng)你幫助他們開一張送條”。實(shí)際上是對(duì)第六單元第33課《便條與收據(jù)》這篇課文知識(shí)點(diǎn)的應(yīng)用。用生活中的常見事例,提升學(xué)生聯(lián)系實(shí)際運(yùn)用所學(xué)語言文字的能力,這正是西柏坡時(shí)期語言文字教學(xué)突出的特點(diǎn)。
造句是鍛煉學(xué)生語言能力的基本方式,初小課本中便有較多該類練習(xí)。如1948年10月華北新華書店出版《國語》初小第四冊(cè)中練習(xí)四第2題,用“哦” “咦”“啊”各造一句話,如:“咦!怎么我的書找不到了?哦!原來在這!啊!怎么他這樣不聽話呀!”[6]。練習(xí)八第1題,“用下面的詞,各造一句話:紀(jì)律,克服,軍鞋,損失,醒了,開心,相信”[7]。以上這些詞語中有名詞、動(dòng)詞、語氣詞等,對(duì)不同詞性的詞語進(jìn)行句子創(chuàng)造,不僅使學(xué)生更深刻理解、運(yùn)用字詞,更能提高學(xué)生的思考聯(lián)想能力。除造句外,接寫句子也能提高學(xué)生語句運(yùn)用能力。該冊(cè)練習(xí)五中第1題,“接寫下面的句子:一、秋涼了我……二、妹妹把一只家雀……三、北風(fēng)刮得很大,氣候……”[8]。接句練習(xí)中,學(xué)生須分析出所缺成分,繼而連接下去。此類練習(xí)可提高學(xué)生造句、作文的能力。
除課內(nèi)練習(xí)外,課外語句練習(xí)也在教學(xué)中得以提倡,如唐縣南唐梅小學(xué)教員馬振山制作的識(shí)字牌,能幫助三四年級(jí)的學(xué)生聯(lián)詞成句[9]。
鞏固新知識(shí)的最佳方式便是運(yùn)用,因此,作業(yè)與練習(xí)在西柏坡時(shí)期語言文字讀寫的教學(xué)中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
三、認(rèn)真糾正錯(cuò)別字
為規(guī)范解放區(qū)語言文字的應(yīng)用,西柏坡時(shí)期語言文字教學(xué)中,非常注重錯(cuò)別字的糾正。
(一)對(duì)學(xué)生錯(cuò)別字的改正。較為常見的是教師標(biāo)出錯(cuò)別字,引導(dǎo)學(xué)生自行修改;定期溫習(xí),檢查錯(cuò)別字的改正情況;進(jìn)行漢字測(cè)驗(yàn),在校園內(nèi)張貼標(biāo)語口號(hào),引起學(xué)生注意等,部分教員還采取其他方法。如教師對(duì)學(xué)生錯(cuò)字情況進(jìn)行統(tǒng)計(jì)備注,制定針對(duì)性措施。“教師改文時(shí),備差白字一本,以學(xué)生為單位把寫錯(cuò)的字登記,如該生一字寫錯(cuò)兩次即予批評(píng)。”[10]“在檢查學(xué)生筆記和批閱作文時(shí),都要注意到里面所發(fā)生的錯(cuò)別字,除于字旁注差錯(cuò)符號(hào)外,并隨時(shí)把發(fā)現(xiàn)的字分別列表記載下來,以備統(tǒng)計(jì)各種字、詞弄錯(cuò)的人來。”[11]將錯(cuò)字進(jìn)行系統(tǒng)性登記備注,有助于教師針對(duì)每位學(xué)生進(jìn)行輔導(dǎo),幫助學(xué)生對(duì)錯(cuò)別字的改正。
(二)對(duì)教材中錯(cuò)別字的修改與更正。1946年6月,晉察冀邊委會(huì)教育處編寫的《國語》初小課本中出現(xiàn)不少錯(cuò)別字,解放區(qū)教育雜志《教育陣地》1947年第2期予以更正。如將初小國語第1冊(cè)第42頁“一斗碾米七斤半”中“斤”改為“升”,第7冊(cè)第5頁,“付新華書店新兒童邊幣參百元”中“參”改為“叁”。如安國中陽由北豐在《冀中教育》1949年第2卷第4期來信指出“初小國語第七冊(cè)第十二課‘二十四節(jié)的‘殼雨和二十課‘自大的蛀蟲的‘蛙蟲笑著說,這個(gè)‘殼和‘蛙是否錯(cuò)字?”編輯部回答:都是錯(cuò)字,“請(qǐng)改為‘穀雨和‘蛀蟲笑著說”。[12]教材是教學(xué)的最基本工具,隨時(shí)糾正其中存在的錯(cuò)字,體現(xiàn)了解放區(qū)教育工作者嚴(yán)謹(jǐn)、科學(xué)的治學(xué)態(tài)度。
四、精心訓(xùn)練小學(xué)作文
作文是考驗(yàn)學(xué)生詞句語法綜合運(yùn)用能力的主要方式之一。學(xué)生要寫好一篇作文須經(jīng)過多階段學(xué)習(xí)。首先教師要選文讓學(xué)生多讀,選文的詞句盡量簡(jiǎn)單,內(nèi)容較易理解,方便兒童借鑒與吸收,如此來提高學(xué)生的語感與語言連貫性。其次,題目的選定是關(guān)鍵。對(duì)于寫作能力不高的學(xué)生,教員需要命題;而具有一定寫作能力的學(xué)生,最好讓其自主命題。行唐三完教員孫眉?jí)劭偨Y(jié)教作文課經(jīng)驗(yàn)時(shí)講到,“學(xué)生程度低的時(shí)候,不妨由教師出題目,同時(shí)也不要多出。但教師一定要注意到題目的范圍,與兒童實(shí)際生活的聯(lián)系,不要出超過了兒童的思想范圍以外的題目,程度高的學(xué)生,他自己有了命題的能力,最好是由他自己來命題”[13]。
批改作文時(shí),教員們也注意到不能只批寫“簡(jiǎn)單明了”,“不通”,“順暢”等簡(jiǎn)單批語,要詳細(xì)具體給予批改。孫眉?jí)墼凇督逃嚨亍?947年第2期發(fā)表教研文章認(rèn)為:“應(yīng)該首先找出他這篇文章中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在這個(gè)毛病上,應(yīng)該特別嚴(yán)格的進(jìn)行修改,比如說他詞句中,可有可無的字太多,這時(shí)教師要逐句一一的替他勾掉,使學(xué)生一看便可知道這次最大的毛病是什么,下次便會(huì)注意克服的。”[14]教員利用宏觀、微觀兩種視角進(jìn)行作文批改,對(duì)癥下藥,杜絕敷衍草率,有效地幫助學(xué)生解決作文問題。
五、西柏坡時(shí)期語言文字教學(xué)的思考
(一)在中共歷史上學(xué)校教育語言文字中的地位
西柏坡時(shí)期初小語言文字教學(xué)是中共教育史上重要的里程碑。相比抗戰(zhàn)時(shí)期的語言文字教育,政治化稍稍減弱,實(shí)用性更為強(qiáng)化。與華北人民政府后期和建國初期的教育相比,稍顯片面與不足,理論教育欠缺。
西柏坡時(shí)期的小學(xué)國語教育,借鑒了抗戰(zhàn)時(shí)期教育的優(yōu)點(diǎn)。如1948年1月晉察冀新華書店出版的《國語》初小第二冊(cè)第35課《霸王鞭》:“小竹竿,栓銅錢,手里拿起霸王鞭。打幾打,轉(zhuǎn)幾轉(zhuǎn),紅紅綠綠真好看。又打鼓,又打鑼,停了鑼鼓就唱歌。唱個(gè)勝利歌,大家真快樂”。“霸王鞭”起源于山西榆社,課文用簡(jiǎn)單的詞匯描繪出民間藝術(shù)“霸王鞭”的活潑歡快場(chǎng)景,便于兒童理解與接受,激發(fā)其熱愛家鄉(xiāng)的情懷。由此可以看出,西柏坡時(shí)期解放區(qū)小學(xué)課本的編纂上,注重把地方化、兒童化的語言素材吸納為課堂教學(xué)內(nèi)容。
西柏坡時(shí)期的小學(xué)國語教育,為新中國的教育事業(yè)的恢復(fù)、改造與發(fā)展奠定了基礎(chǔ)。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后,即著手恢復(fù)發(fā)展教育,并重新編寫了部分課本。如1948年下半年編寫的課本,在晉察冀版課本基礎(chǔ)上進(jìn)行了些許改動(dòng),保留了原課本通俗易懂,實(shí)用性強(qiáng)等特點(diǎn)。該時(shí)期對(duì)教學(xué)方法的探索,也為新中國建立后的教育教學(xué)改革提供了寶貴經(jīng)驗(yàn)。
(二)西柏坡時(shí)期語言文字教學(xué)的特點(diǎn)
1.語言文字教學(xué)具有較強(qiáng)實(shí)用性。冀晉行政公署于1947年5月2日作出《關(guān)于進(jìn)一步貫徹教育與生產(chǎn)結(jié)合實(shí)行以工養(yǎng)學(xué)方針的決定》,以通過教育與生產(chǎn)的合作互助,實(shí)現(xiàn)雙收。例如1948年1月晉察冀新華書店出版的《國語》初小第二冊(cè),全書共45課,在內(nèi)容上與生產(chǎn)勞作相關(guān)的有12篇,其中第36課《砍柴拾糞》,第38課《紡棉花》等,都是提倡學(xué)生進(jìn)行實(shí)踐勞作,帶動(dòng)學(xué)生課余時(shí)間的生產(chǎn)。另有《眼的衛(wèi)生》《身體怎樣才會(huì)好》《衛(wèi)生模范》《感冒》等,課文內(nèi)容均是與生活息息相關(guān)。每課的生字,如算、分、工、谷、玉、糧等,都是生活生產(chǎn)中的常用字,充分體現(xiàn)出漢字的實(shí)用性。又如《國語》初小第四冊(cè),其中有關(guān)勞動(dòng)生產(chǎn)、衛(wèi)生常識(shí)等單元,都是從實(shí)際入手編寫課文,便于學(xué)生課堂學(xué)習(xí)的內(nèi)容與生產(chǎn)生活相結(jié)合。政治教育單元?jiǎng)t在土改與解放戰(zhàn)爭(zhēng)環(huán)境下對(duì)學(xué)生進(jìn)行時(shí)事教育。該部分生字如痢、疾、拉、瀉、炸、雷、裁等,在日常生活中有較高的使用頻率。
2.教學(xué)方法靈活多樣。該時(shí)期學(xué)校教學(xué)條件較差,多為復(fù)式教學(xué)。教員在十分艱苦的環(huán)境中,采用多樣教學(xué)方法保證教學(xué)質(zhì)量。比如,課外文字學(xué)習(xí)方法頗為豐富。涉縣前寬漳小學(xué)教員在放假摘花椒時(shí)給每個(gè)學(xué)生制作識(shí)字牌,早上叫兒童領(lǐng)牌識(shí)字,黃昏時(shí)到校匯報(bào)成績。由于教育方針及教學(xué)方式的革新,適齡兒童入學(xué)率普遍提高。“群眾對(duì)學(xué)校和自己子弟的學(xué)習(xí)也非常開心。”[15]較為新穎的還有阜平四板峪店小學(xué)教員段繡三組織學(xué)生到山坡、草地上,見到婦孺、動(dòng)物,學(xué)生便會(huì)爭(zhēng)先恐后寫起字來。“在山上有不少小學(xué)生寫到四五十個(gè)字,真是興趣高而收效大。”[16]
3.語法教學(xué)較為欠缺。“在語文知識(shí)方面,沒有注意更有計(jì)劃有步驟地培養(yǎng)兒童運(yùn)用語言文字的基本能力,而是大量采用了‘路條和‘收據(jù)之類的零星材料”。[17]雖然1948年1月和10月出版的小學(xué)國語課本,語言簡(jiǎn)單,結(jié)構(gòu)明了,但缺乏對(duì)學(xué)生進(jìn)行系統(tǒng)地語言、語法教育,授之以“魚”而未授之以“漁”。
(三)西柏坡時(shí)期語言文字教學(xué)的影響
西柏坡時(shí)期語言文字教育具有實(shí)用性、通俗化、豐富性的特點(diǎn),學(xué)生學(xué)到的開收條、算賬目等內(nèi)容以及秋耕、上糞等具體勞動(dòng)常識(shí),在實(shí)際生活中得到了應(yīng)用,極大地方便了群眾的生產(chǎn)和生活,改變了群眾中存在的教育對(duì)實(shí)際生活無用的思想觀念,吸引了更多的適齡學(xué)生入校學(xué)習(xí),使解放區(qū)廣大人民接受了新民主主義文化教育,提高了文化水平和思想認(rèn)識(shí)水平。然而,課堂教學(xué)中過分側(cè)重語言文字的實(shí)用性、通俗化,以致出現(xiàn)了過于口語化、甚至庸俗化傾向。這種傾向的存在和發(fā)展,勢(shì)必影響到學(xué)生對(duì)書面語體的理解和掌握,不利于對(duì)語言背后的思維方式的傳承。
注釋:
[1] 德頫、劉松濤、黃雁星、項(xiàng)若愚:《國語》初小第四冊(cè),華北新華書店,1948年10月,第1頁。
[2]馬振山:《識(shí)字牌》,《教育陣地》1947年第2期,第32頁。
[3]邢燕,河北安平縣人,1927年3月生。1944年開始從事地下抗日工作,1947年11月隨軍參加解放石家莊戰(zhàn)役。1947年石家莊解放后,被分配到石家莊市政府秘書處工作。1952年7月調(diào)任石家莊市衛(wèi)生局秘書干事。1962年任石家莊郊區(qū)防疫站任站長。1977年到石家莊市防疫站任職。1988年離休。引文據(jù)2014年11月采訪錄音整理。
[4]宋砥剛:《李峙周是怎樣教低年級(jí)學(xué)生》,《冀中教育》1949年第2期,第22頁。
[5]耿明倫:《讀音與解義》,《教育陣地》1947年第2期,第32頁。
[6]德頫、劉松濤、黃雁星、項(xiàng)若愚:《國語》初小第四冊(cè),華北新華書店,1948年10月,第32頁。
[7]德頫、劉松濤、黃雁星、項(xiàng)若愚:《國語》初小第四冊(cè),第61頁。
[8]德頫、劉松濤、黃雁星、項(xiàng)若愚:《國語》初小第四冊(cè),第39頁。
[9]馬振山:《識(shí)字牌》,《教育陣地》1947年第2期,第32頁。
[10]趙有福:《糾正差白字》,《教育陣地》1947年第2期,第22頁。
[11]《怎樣改正學(xué)生的錯(cuò)別字》,《冀中教育》1949年第2期,第21頁。
[12]《問答·國語》,《冀中教育》,1949年第4期,第47頁。
[13]《潞城等縣糾正偏差后小學(xué)教育大有轉(zhuǎn)機(jī)》,《人民日?qǐng)?bào)》1948年9月13日,第2版。
[14] 段繡三:《看見什么就寫什么》,《教育陣地》1947年第2期,第32頁。
[15]人民教育社編:《老解放區(qū)教育工作經(jīng)驗(yàn)片段》,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年,第290頁。
[16]孫眉?jí)郏骸度绾胃淖魑摹罚督逃嚨亍?947年第2期,第21頁。
[17]孫眉?jí)郏骸度绾胃淖魑摹罚督逃嚨亍?947年第2期,第21頁。
本文系教育部語言文字應(yīng)用管理司2014年度調(diào)研項(xiàng)目 “西柏坡時(shí)期語言文字工作調(diào)查與研究”成果。項(xiàng)目批準(zhǔn)號(hào):YY201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