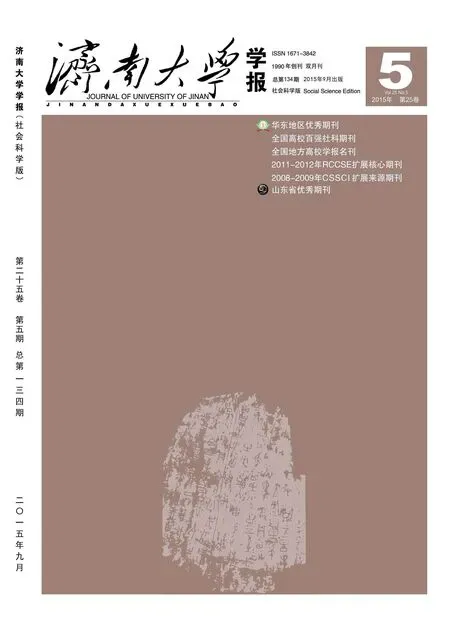鴛鴦蝴蝶派的編輯策略與清末民初女性小說創(chuàng)作
魯 毅
(濟南大學 文學院,山東濟南250022)
一、緣起:清末民初女性小說研究中的問題
進入20世紀,隨著中國社會的急劇變動,中國文學也進入了前所未有的轉型時期,現代性成為前進的方向與目標,其中女性小說家成規(guī)模的涌現便是重要的表征之一。她們的涌現,首先,是在晚清改良主義思潮下,伴隨著聲勢浩大的“廢纏足,興女學”的女性解放運動,使其突破了宮闈羅帳,獲得了廣泛的知識閱讀面,開始了表達自我的漫長旅程。其次,近現代傳媒業(yè)與文學消費市場的迅猛發(fā)展,讓這些女性“智識者”有了言說自身的媒介與場域,傳播的進程得以實現并延伸,她們漸為大眾認識并接受,最終在清末民初呈現為“前五四”時代一個富有意味的文學現象。
對于清末民初女性小說家群體及其創(chuàng)作的介紹與研究,已出現了相關的碩士論文(沈燕《20世紀初中國女性小說作家研究》)、博士論文(薛海燕《近代女性文學研究》),以及郭延禮先生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女性文學轉型期(1900—1919)的文學創(chuàng)作及其文學史意義研究”,他們對近代女性小說家群體及其文學史地位做了探討,認為“20世紀第一個二十年女性作家開闊的視野和新的價值觀,……開創(chuàng)了女性文學的新時代”[1]。具體而言,則指涉內容方面的題材擴大、關注民間疾苦、描寫愛情婚姻悲劇、關注底層女性命運等,以及藝術層面上的小說體制、敘事模式變革等。但這種表述是否存在著遮蔽呢?實際上,與同期鴛蝴派①男性作家的創(chuàng)作相比,這些方面并非獨特,只可看作是男性文本的擴張與延伸,那么女性寫作之所以為“女性”的基點何在?從這一維度出發(fā),又應當做怎樣的價值重估呢?
本人認為,還應當進入女性主義批評及性別話語研究層面觀照清末民初女性小說家群體及其創(chuàng)作,也誠如郭延禮先生所言:“我這篇文章只是初步勾勒了20世紀初女性小說發(fā)展的一個輪廓,……至于對這一時段女性小說從思想意蘊到藝術變革的論述,……只有留待研究女性文學的專家了。”[1]以這種思路與相關的研究方法審視她們,會發(fā)現,清末民初女性小說家群體的涌現并非簡單地順應時代發(fā)展的自然呈現,其歷史細節(jié)處,更有著諸多外在因素的推動,其間執(zhí)掌印刷文化資本的鴛蝴派對這一群體的出現起到了關鍵作用。因此,對清末民初鴛蝴派報刊編輯策略的考察提供了切入同期女性小說家群體及其創(chuàng)作的獨特視角。那么在由編輯、作家、讀者構建的“現代”文學場域中,編輯是如何塑形并規(guī)約女性小說家生成的?女性小說家又是如何在由印刷資本象征的男權話語主導下言說的?其間女性小說家有無逸出規(guī)約之外的現代女性話語及敘事模式?以此最終探討本時期女性小說家的創(chuàng)作在近現代女性文學發(fā)展的整體鏈條中應當占據怎樣的位置。
二、想象女性:被“包裝”的女性小說家及其創(chuàng)作
縱觀清末民初的印刷媒體,尤其是上海的文藝報刊,鴛蝴派涉足其中甚重,并充當著主編、主筆、發(fā)行人、撰稿人等多重身份,可以說鴛蝴派及其創(chuàng)作在民初的繁榮是與近代報刊業(yè)的發(fā)達及其報人身份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經過晚清少數文人的辦報實踐,民初鴛蝴派報人已經積累了豐厚的經驗,并促使眾多文藝刊物及報紙副刊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力,尤其在贏得受眾方面,為后世的文學實踐提供了諸多借鑒。然而這種經驗并非天然習得,他們多出于生計考慮,作為江浙籍移民涌入“十里洋場”并加入這一行業(yè),在初來乍到時,需要轉變的第一重思維,即緩釋報人與文人之間的身份“誤差”。版權之爭似乎成為他們的夢魘,如徐枕亞曾義憤填膺地登報啟事:“《玉梨魂》登載該報,純屬義務,未嘗賣于該報,有關系之個人完全版權,應歸著作人所有,毫無疑義,嗣假陳馬兩君出版兩年,以還行銷達兩萬以上,鄙人未沾利益,至前日始有收回版權之議,幾費唇舌,才就解決,一方面交涉甫了,一方面翻印又來,視耽欲逐,竟欲飲盡鄙人之心血而甘心”[2],而眾多作家在文末標記的“不受酬”則遮羞了“賣文為生”的職業(yè)尷尬。其轉變的第二重思維,即認識到作為大眾傳播媒介的報刊。當他們嫻熟地設計著報刊上的文藝欄目,百感交集地闡發(fā)著刊物的文化定位時,表明他們已經能夠游刃有余地駕馭其所掌控的印刷文化資本,并將其作為一個文化產業(yè)進行經營,形成了“作者—編輯—文本(小說)—媒介(報刊)—讀者”這樣較為成熟的產業(yè)鏈條。在以往的研究中,訊息傳播過程中的“編輯”一環(huán)往往被忽視,實際上,他在其中充當了制定規(guī)則、協(xié)調秩序、“把關人”的角色,這對于作家的文學道路乃至成名起到了關鍵作用,如惲鐵樵之于張恨水,包天笑之于周瘦鵑等,不勝枚舉。清末民初女性小說家群體的涌現顯然經過了鴛蝴派編輯的“把關”,并且在她們的藝術水準之外,還覆蓋了一層濃郁的“包裝”痕跡,這主要表現為:
其一,影像推介,即鴛蝴派編輯創(chuàng)意性地將諸多女性小說家的影像刊載在報刊的插畫中,圖文并茂地向大眾進行傳播,如《女子世界》(第1期)與《游戲雜志》(第4期)中的溫倩華;《女子世界》(第3期)、《小說叢報》(第10期)、《香艷雜志》(第4期)中的呂韻清;《女子世界》(第2期)中的汪詠霞;《婦女雜志》(3卷9號)、《香艷雜志》(第10期)、《中華婦女界》(1卷10期)、《小說叢報》(第10期)中的徐張蕙如;《女子世界》(第1期)中的陳翠娜;《香艷雜志》(第8期)、《女子世界》(第4期)、《中華婦女界》(2卷6期)中的吳懺情;《小說叢報》(第18期)中的姚琴媜;《小說叢報》(第19期)中的朱畹九等。那么他們?yōu)槭裁匆平檫@些女性小說家的影像呢?
首先,這契合了晚清以來盛行的女性解放思潮。隨著1895年甲午戰(zhàn)爭的慘敗,“自強”成為整個社會認同的核心語匯[3](P534),而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途徑便是“啟蒙”,于是“女性”作為一個弱勢群體“被發(fā)現”了,并整合進思想啟蒙與民族國家認同的時代主旋律中,但深隱其中的是象征著社會支配者的男權話語對女性的俯視與規(guī)約。一旦女性被啟蒙,便獲得了進入男性立法的社會秩序,不但可以發(fā)出自己的聲音,甚至可以啟蒙大眾,如小說中的黃繡球(《黃繡球》),在通曉世界大義后,便四處發(fā)表演說,在現實中,也如《婦女雜志》中借助“公共空間”發(fā)表言論的女校學生。這便是男權社會的“立法”,從開始就預設了理想女性的成長之路。而鴛蝴派報刊上的女性作家影像即在晚清以來的啟蒙主潮下,作為被立法與被規(guī)約的社會范型推出的,她們?yōu)榇蟊姡貏e是“被啟蒙”的女性受眾做了標榜。
其次,在社會啟蒙思潮之外,還隱含著時尚文化的訴求。在清末民初鴛蝴派編輯的刊物封面及插畫中,女性影像占有極大的比重,卻呈現為兩種極端:一類是女作家或文藝家的影像,以《小說叢報》等為代表;一類是妓女的影像,以《小說新報》等為代表。研究者往往將其誤讀為鴛蝴派內部的張力,即主編徐枕亞與李定夷編輯理念的差異,但實際上,報刊中所傳播的妓女影像并非新文藝家所詬病的媚俗文化,而是與女性作家的影像一道并置為“新型都市女性的樣板”[4](P87),成為清末民初社會文化潮流中的時尚因素,既“為現代人提供了整合與確認自我身份的途徑”[5](P256),同時也不遺余力地建構著自身的“鴛蝴氣息”及其社會角色,使其成為“洋場”中一個具有身份識別性的文學(文化)流派。
再次,名家效應的營造。處在現代市場語境中的鴛蝴派編輯已充分意識到名家之于媒介生存的重要意義,而與名家約名稿又并非易事,于是女性作家再一次被觀照,她們需要被“包裝”成名家,以擴大其所附屬媒介的文化資本,這與“五四”時期《晨報》副刊之于冰心的“包裝”如出一轍。于是在鴛蝴派的編輯策略下,女性小說家逐漸浮出水面,并獲得了轟動效應,從反復被提及的顧明道曾化名為“梅倩女史”為《眉語》撰稿的經歷便可見一斑:“不料登徒子某,竟認梅倩為掃眉才子,寫信以通情慷,明道用女子口吻致復,直使某大大的風魔,遙向梅倩求婚。”[6](P280)
那么鴛蝴派編輯為女性小說家塑造了怎樣的媒介形象呢?在橫、縱向維度上,他們對女性作家的影像范型做了提升。晚清“小說界革命”中,梁啟超對大眾女性的期待僅僅是能對小說“手之口之”[7](P37)即可。清末民初流行的“賢妻良母”主義則強調“家庭教育,為我女界唯一之天職”[8],在承認男性主導的前提下,將女性的角色設定為“賢內助”,這仍是在踐行傳統(tǒng)儒教中男性、文學、政治權利所屬公共領域,女性、生育、勞務所屬家庭領域的規(guī)范。而鴛蝴派編輯對女性作家的視覺傳達則提升到了精英標準,即“近日女學界中之鳳毛麟角”[9],要求其對傳統(tǒng)、現代各種文類均要涉獵。此外,從影像者的身份來看,社會名流、編輯妻友占主要分量,如瑤卿女史為吳雙熱夫人,曾蘭為吳虞之妻,高劍華為許嘯天的夫人,徐畹蘭為趙苕狂母親等。通過女性影像傳達出的精英意識源自鴛蝴派這一特殊的文化群體,他們將獨特的傳統(tǒng)文化記憶添加進現代語境中,加之啟蒙文化主潮,三者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呈現為鴛蝴派所規(guī)約的女性范型。
其二,名家評論,即借助于報刊這個“公共空間”,主編將刊發(fā)作品的意圖及對作品的闡釋附識于文末或為序向讀者進行推介。清末民初鴛蝴派報刊的編輯理念直接決定著文人作家、投稿者的準入,如《小說月報》主編惲鐵樵,在執(zhí)掌該報之際,主張以高雅的古文入小說,因此魯迅的文言小說《懷舊》得以編發(fā),為了突顯作品的價值和編輯的良苦用心,惲鐵樵還以其名家身份在文后附志:“曾見青年才解握管,便講辭章,卒致滿紙饾饤,無有是處,亟宜以此等文字藥之”[10],以增加作品的分量,擴大小說的受眾影響。這一編輯策略也出現于女性小說的編發(fā)中,如幻影女士在《禮拜六》上共發(fā)表12篇小說,其中主編王鈍根就寫了3篇評語。從鴛蝴派編輯所作的附識或序的內容來看,重點突出的是:
第一,女性作者形象的文學描繪,如“黃翠凝女士者,余友毅漢之母夫人也。余之識夫人在十年前,苦志撫孤,以賣文自給”[11],“遭逢拂逆而不自失望,犧牲富貴而服事貧賤,惟基督徒能之,幻影女士當是基督徒”[12],在此之余,編輯還加入自身的閱讀體驗:“(黃翠凝)善作家庭小說,情文并茂。今自粵郵我《離雛記》一篇,不及卒讀,淚浪浪下矣”,“敬告世之有母之兒,當知無母之慘凄,有若此者”[12],從而為女性作家建立起影像之外更加鮮明的媒介形象。
第二,作品的現實意義。“勸世”與“救世”是鴛蝴派作品及其發(fā)刊詞中出現頻率較高的詞匯,盡管就其實際創(chuàng)作、辦刊方針及編輯理念來看,作為轉型時期的文人,他們游走于“壽世”與“售世”之間,甚至倒向了后者,但是晚清以來的救亡主潮、“新小說”的啟蒙范式、民初的“共和”語境,以及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意識,使得他們時時提及文學的社會功用,因此女性小說家作品中的“勸世”題旨與話語獲得了他們的認同,即“有功世道之文”[12]。他們不但自己按照這樣的理念解讀女性作家的作品,還導引著讀者的思路:“作者意存勸世,不僅為游戲小說而已。”[13]甚至對諸多女性小說的評論存在過度闡釋的傾向,乃至抬升到教科書的高度。他們期待通過這樣的“包裝”手段,女性文本的價值功用可以發(fā)揮到極致:“深望女士此文,普及中華婦女界,漸知濟人為天職,失意者竭其力,得意者助以資,使震旦前途,不致為怨霧所阻塞,國家進步之曙光,庶幾可睹矣。”[12]
總之,無論是通過視覺文化傳達的影像推介,還是由傳統(tǒng)文學中的私人評點模式轉變而來的公共話語空間的名家評論,鴛蝴派編輯按照自身的構想“剪輯”著待傳播的女性小說家形象,規(guī)范、約束著女性小說的大眾傳播軌道,最終為讀者“包裝”出了清末民初女性小說家的群像。那么女性小說家在這種由印刷資本象征的男性話語場中又是如何言說自身的呢?
三、女性想象:男性話語的文本實踐及“越軌”書寫
如前文所言,諸多鴛蝴派作家兼具報人及編輯身份,因此其小說的創(chuàng)作范式與美學樣態(tài)基本上可以囊括進鴛蝴派刊發(fā)作品的編輯理念與策略中。從清末民初女性小說家的實際創(chuàng)作來看,在整體上可以認為是這種編輯策略與理念的話語實踐,具體表現為:
第一,言情模式的承襲。鴛蝴派以言情小說聞名,并揭起了民初哀感頑艷的唯情主義小說浪潮,其模式大致可概括為“開篇之始,以生花筆描寫艷情,令讀者愛慕不忍釋手,既而一波再折,轉入離恨之天,或忽聚而忽散,或乍合乍離,抉其要旨,無非為婚姻不自由,發(fā)揮一篇文章而已”[14]。這種模式在同期女性小說中也被嫻熟地運用起來,如《一聲去也》(許毓華)中儂與陸郎的愛情止步于“父母之命”,《我之新年》(呂韻清)中的琴姑與芹哥、《他生未卜此生休》(謝幼韞)中的婉仙與陸生,其婚戀悲劇皆受阻于小人、惡紳、強盜等鴛蝴派小說人物原型;以及由這種模式延展出的女子受難模式,如《蕭郎》(柳佩瑜)中的吳紉秋在舊式婚姻中的隱忍與犧牲,《聲聲淚》(幻影女士)中孤兒寡母的殞命與美好人倫關系的毀滅等。種種敘事連同頻繁出現的疾病、哭泣、死亡等病態(tài)意象[15],使女性小說文本沿襲著男性話語,并生成了一股濃重的悲涼、陰郁之氣,甚至延展至歷史、域外等類型的小說中。然而這種敘事氛圍在鴛蝴派的大本營《民權素》及其刊載的小說中卻早已做了“立法”:“曇花一現,泡影幻成,徒留茲《民權素》一編,以供世之傷心人憑吊。”[16]總之,清末民初的大部分女性小說仍舊囿于鴛蝴派的言情模式和敘事氛圍,缺少新的悲情模式的開拓,以至束縛了女性意識的獨立表達,她們尚不能建構女性自身的精神屬地,這有待新的文學、文化質素的出現為其提供契機。
第二,民族國家敘事話語的延續(xù)。鴛蝴派小說中頻繁出現的國族敘事話語可以追溯到晚清“新小說”,其內容不僅包含反復出現的國族獨立話語:“哀我支那,生乃與猶太為伍,不知這部書出來,能夠千年睡獅一旦夢醒否?”[17](P117)社會現實批判話語:“廣州城里沒清官,上要金錢下要錢,有錢就可無王法,海底沉埋九命冤。”[18](P417)還包括社會諸方面革新、開智識的啟蒙話語等。盡管這種話語的架構因民初“共和”語境的出現發(fā)生了新變,除了添加革命敘事及其悼亡話語外,其基本內涵大體一致。同期諸多女性小說文本將這種具有啟蒙特色的國族敘事話語片段式地添加進來,如小說《債臺物語》開篇即大發(fā)感慨:“新年消遣,何事不可?必要拿錢混賭,有何趣味?況且民生窮蹙,國勢愈危,從前我國雖弱,各國為了均勢,還戴上這維持東亞和平的假面,現因歐戰(zhàn)一開,日本趁各國不暇東顧,就作種種無理要求,允他呢,便是朝鮮之績,不允呢,又有許多為難,危機一發(fā),我們百姓多有責任的,豈可裝沒事人一般,推在政府身上?”[13]《郎歟盜歟》中的盜賊鯨剛將自己的“盜”義闡釋為:“誠憤于世界之不平等,公理人道,日就湮沒,奸詐者出其金錢勢力以欺虐忠厚,猶文過飾非,以上流君子自居,須知世界愈繁華,強權愈發(fā)達,而人心愈兇惡。”[19]其他還如對都會中金錢異化人心、道德墮落等的批判話語俯拾即是,甚至她們還塑造了諸多惡女人、新式女學生等形象去詮釋這種思想。需要注意,晚清以來的國族敘事話語具有強烈的性別統(tǒng)合色彩,亦或說滲透著一種“雄化”修辭策略,轉化為文學形象即如《女媧石》中的金瑤瑟、《瓜分慘禍預言記》中的夏震歐等性別缺失的“英雌”形象,這在一定程度上對微弱的女性意識及女性形象的生長構成了消解。
盡管清末民初女性小說家群體的創(chuàng)作在整體上可以看作鴛蝴派男性話語的文本實踐,但如《德國詩集》等個別文本已鮮明地呈現出對這種話語實踐的“越軌”,逸出了鴛蝴派編輯所設定的潛在敘事范本,這種“越軌”主要表現為女性作家對女性的想象有了全新的突破:
第一,女性形象的嬗變。清末民初鴛蝴派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往往被想象為具有堅忍品格、恪守傳統(tǒng)道德的女性,亦或賢妻良母,以表達對傳統(tǒng)倫理道德的認同與對本土文化的堅守,同期諸多女性小說文本實踐了這一話語范型,如《聲聲淚》中的孀婦“明大義,撫孤守節(jié),藉十指支茲殘局,且甚賢惠”[20]等。而《德國詩集》中的主人公婉姑與這些女性形象相比,盡管從屬于同一時空,但更像是現代與古典的分野,西方學識成為她們人生際遇中的判斷依據,或者說更強調現代知識構成對形象建構、敘事所起的作用,如婉姑“主張不嫁,靠著學問之力,卻是能夠獨立生活”[21],還有主人公反復提及的萊奈烏氏的詩透出的悲戚:“歡樂難持久,相親僅一時”所給予人生的隱喻等。此外,婉姑形象的呈現不再依托于男性敘事所慣常的受難、成長模式,及其規(guī)約的“孝女”“節(jié)女”“賢妻”“良母”等角色,而是將敘事時空更多地讓位于女性在日常家庭生活中的兩性思考與內心沖突,這種敘事新秩序提供了女性表達自身的依據。
此外,個別小說所提供的另類女性形象也對鴛蝴派男性話語模式構成了消解,如幻影女士在小說《回頭是岸》中提供了中國文學中較少見到的女基督徒形象,她將男性作家筆下理想女性所固守的傳統(tǒng)道德置換為異域宗教思想,于是小說模式開始逸出大眾軌道,即不再重復小人離亂、婚戀不自由的悲劇,轉為張揚博愛主義的宗教敘事,而由小說中女士珍藏的剪報:“星期六日下午二時半,天文家某君,與某女士結婚于圣約翰禮拜堂”[12]透出的象征著男性話語的言情因子卻已是“前塵如夢”,退出了主體敘事之外,這也是作者敘事的自覺:“惟近觀小說,凡失意者,皆以一死自了,絕不念父母邦家,誠恐涓涓不塞,將成江河也,不忖谫陋而作是篇。”幻影的另一部小說《墳場談話錄》可看作這種突破的前奏,盡管還是鴛蝴派的模式,但作為主人公知識構成的西方基督教文化資源,不僅使小說的敘事消解在了情節(jié)的演進上,更進一步建構起了宗教惡魔形象“撒旦”,將一切無常與美的消逝歸結為“撒旦所撥弄者也”[22],并誓言“吾愿借天帝偉力,滅絕撒旦,勿令蕓蕓眾生,為其顛倒也”。這種“反抗絕望”的抗爭話語在清末民初女性小說中實屬難能可貴,彰顯出女性形象的突破所帶來的女性意識的萌芽與覺醒。
第二,女性主體意識的突顯。在清末民初鴛蝴派及女性小說家的創(chuàng)作中,女性形象往往特別突出,但并不代表女性主體地位及主體意識的浮現。從話語修辭角度講,在她們的小說文本中,女性在兩性對照的修辭中是被動和從屬的,她們在戀愛中壓抑自己的情感,在舊式婚姻制度中犧牲自己的幸福,在家庭生活中隱忍著苦難。此外,男性與女性作家所描繪的女性形象,存在著一種“被看”“被欣賞”“把玩”的視角,甚至是物化(objectification)的,即“女性的身體或特征常被刻意地與物件(甚至動物)相提并論,共同展示,也有以物隱喻女性特質,從而達到將女性降為‘玩物’和‘性尤物’(sex object)的目的”[23](P97),如《玉梨魂》開篇,梨花之于主人公白梨影、辛夷之于小姑筠倩的象征,再如《墳場談話錄》中對謝韻薇的描述:“二九年華,榮花始茂,豈意蘭方挺秀,橫被霜摧,月正騰輝,遽遭云掩也。”[22]而在《德國詩集》中,這種“被看”的潛在寫作已然消失,置換為女性怎樣“看”男性,怎樣主動地運用智慧與學識,理性地觀察世界,看待兩性關系,深刻地思考著由婚姻危機帶來的焦慮:
丈夫雖向我懺悔,向我謝罪,我聽了這一番話,心中究竟舒服不舒服,我丈夫竟忘了家中有妻有女咧,想到這種地方,卻是心中生一種說不出來的難過,再想他是個大文學家,無論遇見的是怎樣的美人,是怎樣的薄命女子,他竟把心移到一個鄉(xiāng)間旅店中的一個女子身上去,未免太覺淺陋了,我胸中不禁熱如烈火,又想到那少女在春雨連綿之日,離鄉(xiāng)背井,連安慰她的人也沒有一個,我又悲傷不堪。[21]
這種敘事“越軌”的發(fā)生,究其原因,一是近現代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中女性知識譜系的更替;二是小說敘事的轉型,即由傳統(tǒng)的全知敘事轉換為第一人稱主觀敘事,這不包括設置超敘事層的第一人稱敘事,即“我”聽某人講述主人公的故事,《德國詩集》采用的則是“我”講述自己的故事,這種敘事新秩序不僅使小說由情結模式過渡為情緒模式,也為女性言說自身提供了豐富的空間;三是敘事空間的轉換,在鴛蝴派內部由古典言情向日常家庭生活書寫的開拓中,女性作家逐漸擺脫了固有的言情模式及人物原型的負累,在瑣碎的生活中不斷開掘著女性的角色定位及人生意義。盡管清末民初女性小說中的“越軌”書寫數量不多,卻已經彰顯,它所指向的是與“五四”同聲部的“人”的發(fā)現,是一種現代性的呈現。更重要的是,與借助于西方文化資源生長的“五四”女性小說不同,它的根基卻是以本土資源為給養(yǎng)的鴛蝴派小說,正是在對它的模仿與超越中將近代女性小說涌向了現代門檻。
四、結語
清末民初女性小說家群體及其創(chuàng)作處于一個較為尷尬的境地,晚清以來啟蒙與救亡的時代主潮,鴛蝴派男性作家所掌控的文化資本及其創(chuàng)作,乃至“五四”女性小說的文學史地位等都在不斷地將她們消解。此外,她們還面臨著另一重困境,即小說《燈前瑣語》中的姐妹對話所隱喻的:姐姐倡導的是賢妻良母主義:“予念不為人婦則已,即為人婦,即當盡婦職,不敢為一己之學問,放棄家庭之責任也。”[24]妹妹則致力于振國興邦的社會改革:“我國家庭,以貴族豪富之家為最紛亂,所謂家長主婦者,每以賭博為消遣,子女髫齡,即染惡習……哀哉中國!家庭如是,尚何望乎振興也?”但最終妹妹的社會理想不僅為姐姐的訓導所消解:“我國家庭,大抵如是,求其雍雍睦睦者,百不得一,長姊處境雖拂逆,然無負于人,無忝于職,問心無愧,自有真樂,且兒已長成,苦盡甘來之日不遠矣。”同時鑒于友人讀書為妾的經歷走向了幻滅。在這里,女性分明已經意識到主體的存在,卻夢醒了無路可走,轉型時期的社會尚不能提供給她們一種全新的人生經驗與思考,更遑論將這種體驗轉換為文學形象。
盡管如此,近代女性小說家群體的創(chuàng)作意義是不容忽視的,它不僅僅是作為被發(fā)現的史料,亦或填補了古代女性敘事文學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她們的“越軌”書寫構成了中國文學現代轉型中不可缺失的關鍵一環(huán),即本土資源的現代性開掘,它提供了“五四”范式不可能有的一種路徑。
[1]郭延禮.20世紀初中國女性小說家群體論[J].中山大學學報,2011,(2).
[2]徐枕亞.枕亞啟事[J].小說叢報,1916,(18).
[3]葛兆光.中國思想史(二卷)[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4][美]葉凱蒂.上海·愛:名妓、知識分子和娛樂文化(1850—1910)[M].楊可譯.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12.
[5]劉傳霞.中國當代文學身體政治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6]秋翁.二十年前之期刊[G]//芮和師,范伯群.鴛鴦蝴蝶派文學資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7]任公.譯印政治小說序[G]//陳平原,夏曉虹.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8]擷華女士.家庭教育簡談[J].婦女雜志,1915,(3).
[9]名畫家包胡振玉女士之影[J].小說叢報,1914,(6).
[10]周逴.懷舊[J].小說月報,1913,(4).
[11]黃翠凝.離雛記[J].小說畫報,1917,(7).
[12]幻影女士.回頭是岸[J].禮拜六,1915,(48).
[13]韻清女史.債臺物語[N].申報,1915-02-17.
[14]蔣箸超.白骨散[J].民權素,1914,(1).
[15]魯毅.民初鴛鴦蝴蝶派哀情小說背后的潛流與漩渦[J].東岳論叢,2014,(11).
[16]沈東訥.序三[J].民權素,1914,(1).
[17]猶太移民萬古恨.自由結婚[M]//章培恒.中國近代小說大系.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1.
[18]吳趼人.九命奇冤[M]//章培恒.中國近代小說大系.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1.
[19]姚淑孟.郎歟盜歟[J].眉語,1915,(3).
[20]幻影女士.聲聲淚[J].禮拜六,1914,(22).
[21]徐賦靈.德國詩集[J].小說畫報,1918,(16).
[22]幻影女士.墳場談話錄[J].禮拜六,1914,(19).
[23]陳順馨.女英雄形象與男性修辭[M]//陳慧芬,馬元曦.當代中國女性文學文化批評文選.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24]幻影女士.燈前瑣語[J].禮拜六,1915,(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