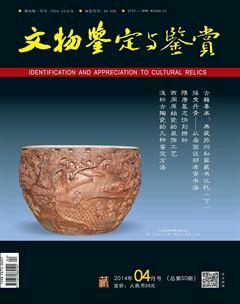阜陽出土西王母禽獸鏡考釋
楊玉彬



編者按:西王母神話是銅鏡常見的裝飾題材,阜陽博物館藏有兩枚該題材的銅鏡,保存完好、鑄工精整、紋飾華美。本刊前兩期刊登了本文上篇和中篇,記述了兩枚銅鏡的形制與紋飾,并通過分析各地所藏及見于著錄的22面西王母禽獸鏡的圖式物象構成,總結出西王母圖像系統的組合特征,并對西王母圖像的神話學內涵進行了闡述。本期將刊登本文下篇,分析西王母禽獸鏡興衰演變的年代與流播地域。
五、興衰演變的年代與流播地域
前文所見兩漢西王母禽獸鏡,形制、圖式、銘文各有變化,如表二所示。
上表22枚例鏡中,有17枚為禽獸博局紋鏡,占總量的77.3%,可知兩漢禽獸鏡中的西王母圖像系統,主要出現在禽獸博局紋鏡中,而禽獸博局紋鏡流行的年代在西漢晚期至東漢前期。22枚例鏡中,另有四乳四虺鏡1枚、四乳禽獸鏡(非博局紋)2枚、多乳禽獸鏡2枚,其中填襯有“四神”紋的四乳四虺鏡及四乳禽獸鏡,主要流行于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多乳禽獸鏡則主要流行于東漢中晚期。據此,可知西王母禽獸鏡應主要流行于西漢晚期至東漢中期,其中以新莽前后最為盛行,東漢中期以后漸趨式微。
上表例鏡,根據鏡圖構成的差異可大體分作三組。
Ⅰ組:典型例鏡4枚。
a、宜興私藏四乳四虺鏡(圖9)。主紋區四乳四分區組圖,每區置一組碩大虺紋,虺紋下或周圍間隙填襯“四神”紋及西王母、玉兔、九尾狐、三足烏、鳳鳥等紋飾。
b、儀征漢墓出土四乳禽獸博局紋鏡(圖24)。主紋區置四乳禽獸博局紋,禽獸紋主要有西王母、玉兔搗藥、九尾狐、三足烏、羽人持獻丹丸與仙草、蟾蜍等。
c、儀征漢墓出土四乳禽獸博局紋鏡(圖4)。主紋區置四乳禽獸博局紋,禽獸紋主要有西王母、玉兔搗藥、三足烏、羽人、鳳鳥、丹藥、仙果云氣等。
d、宜興私藏四乳禽獸鏡(圖10)。主紋區四乳四分區組圖,四區禽獸紋主要有西王母、玉兔搗藥、羽人持仙果(草)、白虎、蟾蜍、鳳鳥、九尾狐、熊、云氣紋等。
上述4枚例鏡,Ⅰa式鏡具有西漢晚期鏡特征,鏡圖中的西王母圖像系統僅作為“填襯物象”出現,形體小而簡約,表明此鏡構圖中雖融入了西王母神話內容,卻未能處于核心、主導地位,應系目前所見年代最早的西王母禽獸鏡標本;Ⅰb式鏡出土于西漢晚期墓葬,鏡圖中西王母及其物象系統不僅俱全,且形構大而清晰,已經位居主紋區成為“核心圖像”;Ⅰc式鏡同樣屬于出土器,年代及圖像組合特征與Ⅰb式鏡基本雷同;Ⅰd式鏡為宜興私藏,比較其形制與圖像組合特征,亦屬于典型的西漢晚期鏡,鏡圖中的西王母物象系統配組配位特征,與Ⅰb式、Ⅰc式鏡類似。據此,可看出西漢晚期西王母禽獸紋鏡典型的組圖特征:1.西王母多與玉兔搗藥、九尾狐、三足烏、羽人、鳳鳥、蟾蜍等共同組合成一個較為穩定的圖像系統。2.西王母均為頭部戴勝、著寬大袍服、側身跽坐圖式。3.西王母圖像系統內的物象,基本分布于整幅鏡圖中,除Ⅰa式鏡外,其余例鏡中的西王母在圖像系統中均處于“核心地位”。
Ⅱ組:典型例鏡4枚,形制與圖像組合特征如下。
a、宜興私藏四乳禽獸博局紋鏡(圖25)。主紋區四乳四分區組圖,四區分別配置禽獸博局紋,禽獸紋主要有西王母、白虎、羽人飼龍、瑞獸等。
b、宜興私藏八乳禽獸博局紋鏡(圖26)。主紋區內置八乳禽獸博局紋,禽獸紋主要有西王母飼九尾狐、羽人飼禽鳥等。
c、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始建國二年”銘四乳禽獸博局紋鏡(圖5)。主紋區置四乳禽獸簡化博局紋,四區禽獸紋分別為西王母配玉兔搗藥、兩羽人騎獨角獸、鳳鳥配獨角獸、神獸。主紋區外置一周“始建國二年……”銘文圈帶。
d、揚州蜀崗新莽墓出土博局禽獸鏡(圖3)。主紋區置四乳博局禽獸紋,四區禽獸主紋分別為西王母與玉兔獻藥、羽人戲鳳鳥、獨角羊與長尾獸、三足獸與長尾鼠,主紋間隙填襯云氣紋。
以上4枚例鏡中均缺少完整的西王母圖像系統,Ⅱa式鏡中僅有一區配置“西王母與白虎”圖式,其余三區圖像與西王母神話內涵無直接關聯;Ⅱb式鏡中僅有一區配置“西王母飼九尾狐”圖式,其余圖像區與西王母神話無關聯;Ⅱc、Ⅱd式鏡中,均僅有一區配置“西王母與玉兔搗藥”圖式,其余圖像區與西王母神話無關聯。據此,可看出新莽時期西王母禽獸紋鏡組圖的主要特征:1.鏡圖中完整的西王母圖像系統漸趨簡化,西王母與玉兔搗藥、九尾狐、三足烏、鳳鳥、白虎、蟾蜍等同配一幅鏡圖內的現象基本不存。2.西王母組圖僅占整幅鏡圖空間的四分之一,且多與傳統圖像系統內的一種神人或禽獸配組,在鏡圖內的“核心地位”趨于淡化。3.著寬大袍服、戴勝、側身跽坐仍是西王母圖式的典型特征。
Ⅲ組:典型例鏡6枚,形制與圖像組合特征如下。
a、阜陽郭韓莊漢墓出土四乳禽獸博局紋鏡,見前文介紹(圖1)。
b、阜陽趙王莊漢墓出土四乳禽獸博局紋鏡,見前文介紹(圖2)。
c、宜興私藏四乳禽獸博局紋鏡(圖8)。主紋區置四乳禽獸博局紋,四區禽獸紋分別為西王母與玉兔搗藥、兩組鳥銜魚、熊與鹿、羽人與瑞獸。
d、宜興私藏五乳禽獸紋鏡(圖27)。主紋區五乳五分區組圖,分別配組西王母與羽人、羽人飼龍、玄武與獨角長尾蟾蜍、白虎與長尾獸、鳳鳥與兩戲獸。主紋區外置一周“桼言之紀從鏡始……”銘文圈帶,畫紋帶緣。
e、壽縣漢墓出土七乳禽獸紋鏡(圖12)。主紋區七乳七分區組圖,七組禽獸紋分別為西王母與玉兔搗藥、熊與鹿、羽人飼獸、兩奔馬、蟾蜍飼雀鳥、羽人騎鹿、熊搏牛。
f、故宮博物院藏禽獸博局鏡(圖11)。主紋區四分區組圖,分別配置西王母圖像系統、羽人射虎、羽人乘玄武駕鶴出游、羽人駕魚出游。
以上例鏡,Ⅲa式鏡四分區組圖,缺少完整的西王母圖像系統,僅在四分之一圖像區配置“西王母與玉兔搗藥”圖式,西王母戴勝,體作“獸首人身”型;Ⅲb式鏡主紋區四分區組圖,僅有四分之一圖像區配置“西王母飼鳳鳥”圖式,但鏡緣畫紋帶中配置有九尾狐、三足烏圖像;Ⅲc式鏡四分區組圖,僅在四分之一圖像區配置“西王母與玉兔搗藥”圖式;Ⅲd式鏡五分區組圖,僅在其中一區配置“西王母與舞蹈侍神”圖式;Ⅲe式鏡七分區組圖,其中一區配置“西王母與玉兔搗藥”圖式,西王母不戴勝,為“人獸合體”形態;Ⅲf式鏡四分區組圖,其中一區配置西王母、玉兔搗藥、九尾狐、三足烏、神樹、鳳鳥等,構成一類較罕見的西王母圖像系統模式。西王母雖著寬袍側身跽坐,但頭部不戴勝。據此,可大體歸納出東漢之際西王母禽獸鏡圖像的主要特征:1.西王母形象有“戴勝”“不戴勝”兩類,既有“世俗貴婦型”的圖式、也有“獸首人身型”的例證。2.鏡圖中西王母圖像系統的配置活潑多變,其中以“簡化型”圖式最流行,亦見“完整型”和主紋區、鏡緣畫紋帶區“分散型”配置的例證。3.多乳禽獸鏡圖式中的西王母組圖更趨于簡約而“符號化”,西王母作為鏡圖“核心圖像”的地位消逝。
比較以上三組典型例鏡,可對兩漢時期此類鏡興衰演變特征總結如下:西王母禽獸紋鏡興起于西漢中期以后,主要流行于西漢晚期至東漢早中期,其中以新莽時期最盛,東漢中期以后漸趨式微。西漢晚期西王母禽獸鏡組圖,主神西王母均側身跽坐、著寬袍戴勝,與玉兔搗藥、九尾狐、三足烏、蟾蜍、鳳鳥、羽人、白虎、仙果、丹丸、藥尊等共同配組構成一個圖像系統,并在鏡圖中居于核心地位。新莽前后此類鏡圖式開始發生變化,主神西王母雖仍保持寬袍戴勝、側身跽坐的形象,但早期完整的神話圖像系統已開始簡化省隱、肢解離散,多以西王母配置一種神人侍者或禽獸的“簡化型”模式出現,所占據的鏡圖空間位置亦多限定在整幅鏡圖的四分之一范圍。東漢早、中期此類鏡西王母組圖則進一步簡約、異化,既流行“簡化型”西王母圖像系統模式,亦見少量的“完整型”圖像系統模式,同時西王母組圖在整幅鏡圖中所占的空間比例漸趨收縮。延至東漢中晚期的多乳禽獸鏡中,西王母組圖所占的空間不僅進一步被壓縮,其形象也開始向著頭部“不戴勝”、面部五官省隱模糊的趨勢嬗變,表明此期鏡圖中傳統意義上的西王母主神的“核心地位”已漸趨消逝。
兩漢時期西王母禽獸鏡的流播地域,從本文統計的20余枚標本看(表二),這些例鏡集中出現在江蘇揚州、宜興和安徽六安、阜陽地區,其中以宜興、儀征所見例鏡的年代最早。如果以上地域為此類鏡的發源地與流播中心,則這個區域恰好位于西漢諸侯王國所在的關東地區,其具體位置大致在西漢淮南國、吳國故地之臨近淮河流域范圍。漢代關東諸侯王國所在的淮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區,自先秦以來就神仙巫術發達,從目前所見畫像材料看,兩漢之際西王母神話傳說在這一地區空前流播。《漢書·哀帝紀》《漢書·五行志》所記西漢末曾發生過席卷全國的大規模祭祀西王母的流民運動,這個運動即肇始于關東地區,并遍行關東二十六個郡國后向西傳至京師地區。日本學者岡村秀典考證認為此次遍布西漢全國的祭拜西王母狂潮,即源出于淮河流域地區,如果這個結論無誤,考慮西王母禽獸鏡發源地、流播地區、興衰時段的具體情況,或可將西漢末至東漢初年的上述全國性民間祭拜西王母運動的發源地,推定在吳國與淮南王國故地區域內。
六、余論
1.西王母神話傳說在我國古代源遠流長,兩漢時期,神仙信仰與升仙不死說、陰陽五行說、讖緯思想、原始道教信仰等社會思想的影響改造,使西王母神話與西王母形象發生了復雜演變。西漢晚期以來,漢室衰微、宦官外戚專權、皇權角逐更易、自然災害頻發、土地劇烈兼并等社會現象,導致政局動蕩不安、社會信仰危機、人民流離失所,災難與死亡的恐慌時刻威脅著世人的安全,人們十分渴望得到西王母神的庇護與賜福,以求得在現實世界中或精神家園里解除災難與痛苦,由此推動了西王母信仰崇拜之風空前熾盛,并在同時代物質文化載體中留下烙印,禽獸鏡圖式中出現西王母神話內容,是上述社會背景下的產物。
2.漢代神人禽獸鏡中的西王母圖像雖遠不及神人神獸鏡、神人畫像鏡中的同類圖像出現頻度高,卻在兩漢人物鏡的形成與演變過程中有著特殊的重要意義,在此之前,漢鏡中也有人物圖像出現,如禽獸鏡中習見的“羽人”“人面獸”“人面鳥”等,但這些怪異“人物”的形態,多作尖首長耳的獸體型或禽鳥狀,有的不僅體被羽翼,還有卷曲的長尾,因而它們還不能視為完整意義上的“人”形,準確地描述應歸入“半人半獸(禽)”“人獸(禽)合體”型,屬于鏡圖物象中由“禽獸”向“人物”演變的一類過渡形態。而漢神人禽獸鏡中的西王母圖像,自一出現就是著寬袍、頭戴勝、側身跽坐的完整人物形態,與漢代世俗生活中貴婦的形構、發式、服飾完全相同,此前鏡圖中“人獸(禽)合體”式的人物造型特征完全消逝。此后,漢鏡圖式中無論是刻畫“仙人”、還是表現現實生活中的“俗人”,都延續了這種構圖特征,由此,可以認為神人禽獸鏡中的西王母造型,開啟了漢代人物鏡中人物圖像“世俗化”演變的先河,在兩漢人物鏡發展演變過程中有著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
3.就阜陽所處的淮河流域而言,東漢中晚期這一地域畫像鏡、神獸鏡中西王母神話題材十分流行,如著錄中常見的所謂北方地區西王母畫像鏡,多半源出或流播于淮河流域。阜陽地區出土的兩例西王母禽獸鏡,A式鏡的年代約在東漢早期,B式鏡的年代約在東漢中期,兩枚鏡鏡圖承載的神話題材,與稍晚之際出現的畫像鏡、神獸鏡中的同類題材在年代上顯然應有前承后續的關聯,兩者表現形式有異,神性內涵雷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