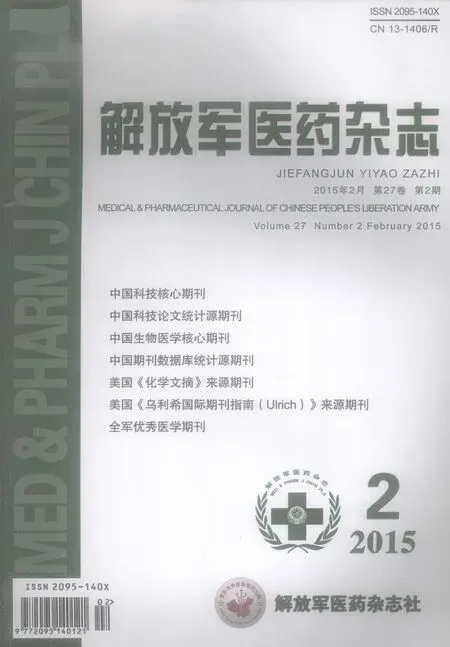牙周源性牙周牙髓聯合病變微生物感染臨床分析
鄧卓峰,周 崢
牙周牙髓聯合病變是牙周病或根尖周病晚期發生的導致廣泛牙周組織破壞及牙髓病變綜合征[1-4],其與口腔中的微生物共同作用是導致失牙的重要原因[5]。隨著分子生物學技術的不斷發展,PCR-DGGE等檢測微生物菌群方法的應用促進了口腔生物學的進步,牙周牙髓聯合病變依據病變來源分為牙周源性、牙髓源性和二者聯合作用導致的牙髓病變[6]。本文著重分析牙周源性牙周牙髓聯合病變的微生物感染種類,為臨床針對性治療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選擇2013年1—12月收治的牙周牙髓聯合病變38例,其中男21例,女17例;年齡23~38(25.26±2.92)歲。所有患者進行了病史、臨床口腔專科檢查和影像學檢查。38例選取78顆患牙,患牙均因存在炎癥致Ⅱ~Ⅲ度松動,其牙周袋深度≥5 mm[7],且至少存在1個牙位牙周袋探診深度至根尖,且均無齲、無隱裂等牙體疾病,3個月內未使用過抗生素。同時選取同期38例來我院進行正畸的78顆同樣牙位的拔除牙作為對照樣本,男20例,女18例;年齡22~40(26.12±2.88)歲。患者無其他口腔疾病,均知情同意,排除齲齒、非齲性疾病、隱裂,3個月內使用過抗生素者。兩組年齡、性別等一般資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標本采樣方法
1.2.1 牙周袋標本:兩組均采集牙周袋標本,在操作前以無菌刮匙清除齦上菌斑,防止齦上菌斑干擾,之后以生理鹽水漱口1 min,取樣牙采用棉卷隔離隔濕,探診患牙牙周袋至根尖的牙根牙周組織,隔濕吹干,以吸潮紙紙尖蘸取牙周袋牙冠2/3的齦溝液,之后迅速放入牙周袋底部,約20~30 s后取出,以無菌剪刀剪下其尖端5 mm放入含有PBS液的離心管;同時以無菌刮治器探入牙周袋底部刮取牙根的菌斑于滅菌的PBS液中。2種操作均重復1次,均于-20℃保存作為牙周袋標本。
1.2.2 根管采樣:在患牙拔出后,在根尖1/3處截斷,如無成形牙髓時,采用蘸有無菌生理鹽水的無菌銼反復銼根尖1/3處的根管后壁,之后將無菌吸潮紙插入,停留20~30 s取出,以無菌剪刀剪下其尖端5 mm作為根管標本。
1.3 標本檢測方法 將存于-20℃的樣本解凍,8000 r/min離心3 min,去上清后加入90μl緩沖液(主要為溶菌酶)37℃處理30 min,采用天根生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的細菌基因組DNA提取試劑盒提取2種標本DNA,并以其為模板,之后進行PCR擴增,采用細菌通用引物[8],上游引物為968f-GC(5'-CGCCCGGGGCGCGCCCCGGGCGGGGCGGGGGCACGGGGGGAACGCGAAGAACCTTAC-3'),下游為 1401r(5'-CGGTGTGTACAAGACCC-3 '),生 成 全 長 為 16S r DNA的V2-V3區[8-9]。模板DNA加熱至93℃ 4 min后,使其雙鏈或經PCR擴增形成雙鏈DNA解離成單鏈,以為其與引物結合進行下輪反應循環;之后,溫度降至55℃,引物與模板DNA單鏈互補序列配對結合,形成DNA模板-引物結合物,其在 Taq DNA聚合酶的作用下,以dNTP為反應原料,靶序列為模板,按堿基配對與半保留復制原理,合成新的與模板DNA鏈互補的半保留復制鏈,重復循環變性-退火-延伸過程,在其過程中根據不同的PCR引物序列,設置不同的退火溫度和時長[10](第一步:93℃變性 4 min、55℃退火 40 s、70℃延伸 1.5 min;第二步:93℃1 min、56℃30 s、72℃30 s;72℃優化7 min)。PCR反應體系為50μl(北京全式金生物科技公司),以1.5%瓊脂糖凝膠電泳檢測PCR產物。每個樣本取35μl,變性劑凝膠的濃度采用40% ~60%的6%聚丙烯酰胺凝膠,進行100%變性,之后采用1∶10 000的 SYBR GreenⅠ核酸燃料染色40 min,將染色的凝膠采用ImageLab成像系統分析拍照,觀察標本的電泳條帶,并將有代表性的條帶進行切膠至滅菌的蒸餾水中(4℃ 24 h)后,離心取上清為模板進行PCR循環,之后將反應產物進行克隆測序并使用GenBank的BLAST對測序結果進行序列分析和序列同源性比較[8,11]。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7.0統計軟件進行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檢驗;相關因素分析采用Spearman相關性分析,α=0.05為檢驗水準。
2 結果
2.1 微生物檢出情況 觀察組48顆患牙標本檢出微生物,檢出率為61.54%。48顆患牙牙周袋均檢出微生物,檢出率為100%;29顆患牙根管牙髓檢出微生物,檢出率為60.42%。牙周袋微生物檢出率高于根管(χ2=9.128,P<0.05)。對照組12顆檢出微生物,檢出率為15.38%,均為牙周袋檢出。觀察組患牙微生物檢出率高于對照組(χ2=14.927,P <0.05)。
2.2 菌屬情況 觀察組BLAST測序結果顯示,患牙標本中牙周袋菌屬為變形菌門的彎曲菌屬34顆、放線菌屬42顆、梭桿菌門的梭桿菌屬28顆、腸桿菌門的腸桿菌屬19顆和變形菌門的嗜血桿菌屬14顆;根管標本菌屬為放線菌門的棒狀桿菌屬25顆和放線菌屬4顆。對照組拔除牙齒中牙周袋菌屬為奈瑟菌屬8顆、放線菌屬6顆和彎曲菌屬3顆。兩組同一標本具有多重微生物感染。
2.3 菌種條帶 對觀察組牙周袋、根管牙髓標本和對照組標本菌種條帶做PCA發現,觀察組中牙周袋標本菌種條帶14.33%~57.85%在同顆牙根管牙髓標本中存在,但根管牙髓標本中菌種條帶有1.32%~67.55%在同顆牙牙周袋標本中不存在。觀察組中菌種條帶1.21%~4.38%在對照組同位牙標本中存在,但對照組標本中菌種條帶有0~0.57%在觀察組同位牙標本中不存在。
2.4 菌種與牙周源性牙周牙髓聯合病變相關性分析 將觀察組和對照組的棒狀桿菌屬、放線菌屬、彎曲菌屬、梭桿菌屬和嗜血桿菌屬進行賦值(陽性=1,陰性 =0),以牙周源性牙周牙髓聯合病變(陽性=1,陰性=0)為應變量Y,以上因素為自變量X進行回歸分析顯示,牙周源性牙周牙髓聯合病變與彎曲菌屬、放線菌屬、梭桿菌屬、腸桿菌屬、嗜血桿菌屬感染呈正相關(r=0.232,P<0.05)。
3 討論
牙髓和牙周組織解剖學結構互通,因此當發生牙周牙髓聯合病變時,二者微生物感染種類常交叉感染,致難區分牙周牙髓聯合病變的來源是牙周源性還是牙髓源性,或者是二者聯合作用。國內外文獻對可能引起牙周牙髓聯合病變微生物種類的系統研究較少,而著重單獨研究牙周源性導致的牙周牙髓聯合病變的報道更少[6-10]。為了增加此方面的臨床觀察數據,本研究采用了PCR-DGGE生物技術檢測了牙周牙髓聯合病變患牙中牙周袋和根管內微生物情況,初步探討了牙周源性牙周牙髓聯合病變的微生物種類。
傳統研究中將口腔微生物測定以細菌培養法為主,其認為限定了菌種的范圍[11-12],難以全面分析口腔微生物菌種情況,因此本文采用了PCR-DGGE法,其通過分析細菌菌落的基因多態性可直觀識別菌種而不受培養條件限制,其敏感度和特異度相對均較高[13],因此可全面分析微生物的種類。本研究結果發現牙周牙髓聯合病變的牙周袋微生物檢出率為100%,高于根管牙髓微生物檢出率的60.42%,對照組牙周袋微生物檢出率為100%,說明牙周源性牙周牙髓聯合病變與微生物感染相關。對其感染的菌種條帶分析發現,觀察組中牙周袋標本菌種條帶14.33%~57.85%在同顆牙根管的牙髓標本中存在,但根管牙髓標本中菌種條帶有1.32% ~67.55%在同顆牙牙周袋標本中不存在;觀察組中菌種條帶1.21%~4.38%在對照組同位牙標本中存在,但對照組標本中菌種條帶有0~0.57%在觀察組同位牙標本中不存在,說明牙周源性牙周牙髓聯合病變患牙牙周組織和牙髓組織中的菌群結構和組成具有相似性的同時還具有差異性,這可能與患牙局部內環境差異和其中原有微生物的存在相關,即局部微環境自然選擇的結果[14]。另外,國內外研究發現,牙周組織的菌群在牙周炎進展到一定程度時可通過根管、根尖等通道進入到牙髓中存活、繁殖,導致牙髓損傷,或影響到根管內牙髓的微環境,從而使牙髓內原有微生物復蘇[15-21]。
根據BLAST測序檢測微生物種類發現牙周源性牙周牙髓聯合病變牙周袋微生物感染以彎曲菌屬、放線菌屬、梭桿菌屬、腸桿菌屬、嗜血桿菌屬為主;牙髓主要以棒狀桿菌屬和放線菌屬感染為主;而正常人群口腔檢出菌屬以奈瑟菌屬、放線菌屬和彎曲菌屬為主,這與 Krmek 等[22]、Chaniotis等[23]、萬蕾和章錦才[24]的研究結果相似。對菌種與牙周源性牙周牙髓聯合病變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牙周源性牙周牙髓聯合病變與彎曲菌屬、放線菌屬、梭桿菌屬、腸桿菌屬、嗜血桿菌屬感染有關。
總之,牙周源性牙周牙髓聯合病變發生與微生物感染有關,且牙周源性與牙髓源性感染微生物種類既有相似又有不同,因此臨床可針對其微生物感染種類進行輔助治療[25-28],以提高治愈率。
[1] 張明珠,徐杰,彭藝,等.牙周牙髓聯合病變與常見牙周病原微生物感染的關系研究[J].上海交通大學學報:醫學版,2011,31(4):447-450.
[2] 劉玲.牙周牙髓聯合病變治療的臨床分析[J].中外醫療,2014,33(14):82-83.
[3] 王宏峰.牙周牙髓聯合病變與牙周感染的相關性分析[J].醫藥論壇雜志,2014,35(4):100-101.
[4] 何坤.牙周牙髓聯合病變的綜合治療的探討[J].吉林醫學,2014,35(5):1036.
[5] 嚴妍.牙周牙髓聯合病變的細菌學研究[D].北京:首都醫科大學,2010.
[6] 周康,季佩紅,俞立英,等.牙周牙髓聯合病變牙周袋內厭氧菌的培養檢測和藥敏試驗[J].上海口腔醫學,2013,22(1):72-76.
[7] 夏明慧.牙周牙髓聯合病變細菌的PCR-DGGE分析[D].濟南:山東大學,2012.
[8] 夏明慧,亓慶國.牙周牙髓聯合病變菌群的PCR-DGGE分析[J].中華微生物學和免疫學雜志,2012,32(10):866-870.
[9] Kabbach W,Zezell D M,Pereira T M,et al.A thermal investigation of dental bleaching in vitro[J].Photomed Laser Surg,2008,26(5):489-493.
[10] Uslu O,Akcam M O,Evirgen S,et al.Prevalence of dental anomalies in various malocclusions[J].Am JOrthod Dentofacial Orthop,2009,135(3):328-335.
[11]王暢,劉瑩,漆正楠,等.牙周健康者齦上菌斑與唾液微生物群落分析[J].牙體牙髓牙周病學雜志,2013,23(11):694-699.
[12]陳鐵樓,許兵,李曙光,等.艦員和地勤人員牙周細菌學酶學指標比較[J].解放軍預防醫學雜志,2011,29(1):40-41.
[13]束蓉,周彥玢,劉大力,等.DGGE法評價牙周袋深度的變化對齦下微生物群落的影響[J].上海交通大學學報:醫學版,2011,31(8):1140-1144.
[14]張成飛.牙體牙髓病臨床問題解析Ⅷ,牙根尖三分之一的生物學特點及臨床意義[J].中華口腔醫學雜志,2011,46(9):567-570.
[15] Martinho F C,Gomes B P.Quantification of endotoxins and cultivable bacteria in root canal infection before and after chemomechanical preparation with 2.5%sodium hypochlorite[J].JEndod,2008,34(3):268-272.
[16]黃鏡靜,武曦.牙齦卟啉單胞菌在牙周炎病理和防治中的研究進展[J].重慶醫學,2012,41(18):1869-1871.
[17]徐菁玲,李偉力.牙周微生物與心血管疾病相關性的研究進展[J].牙體牙髓牙周病學雜志,2009,19(3):175-178.
[18]肖建輝.淺談牙髓牙周聯合病變的治療[J].中華中西醫雜志,2009,7(4):23.
[19]扈祚文,鐘文,謝培增,等.熱帶海域長期巡邏官兵牙周病患病情況[J].解放軍預防醫學雜志,2012,30(4):282-283.
[20]吳海林,俞少杰,吳風華.牙周牙髓聯合病變與牙周感染的相關性分析[J].中華實用診斷與治療雜志,2013,27(10):1017-1019.
[21]杜莉.牙周牙髓聯合病變120例治療觀察[J].陜西醫學雜志,2012(10):1357-1359.
[22] Krmek SJ,Miletic I,Simeon P,et al.The temperature changes in the pulp chamber during cavity preparation with the Er:YAG laser using a very short pulse[J].Photomed Laser Surg,2009,27(2):351-355.
[23]Chaniotis A M,Tzanetakis G N,Kontakiotis E G,et al.Combined endodontic and surgical management of a mandibular lateral incisor with a rare type of dens invaginatus[J].JEndod,2008,34(10):1255-1260.
[24]萬蕾,章錦才.牙周牙髓聯合病變的研究進展[J].廣東牙病防治,2011,19(11):612-614.
[25]弓飛,崔廣慶,程濤,等.牙周牙髓聯合病變與常見牙周病原體感染的相關性分析[J].中華醫院感染學雜志,2014,24(14):3592-3593,3596.
[26]王妙妍,陳廣盛,莊海燕,等.鹽酸米諾環素緩釋抗菌軟膏修復牙周牙髓聯合病變[J].中國組織工程研究,2014(34):5525-5529.
[27]王紅.老年人牙周牙髓聯合病變的臨床治療體會[J].中國實用醫藥,2014(6):18-19.
[28]辛少華,伍瑞平,謝瑞春.牙周牙髓聯合病變的綜合治療的研究[J].藥物與人·學術版,2014,27(1S):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