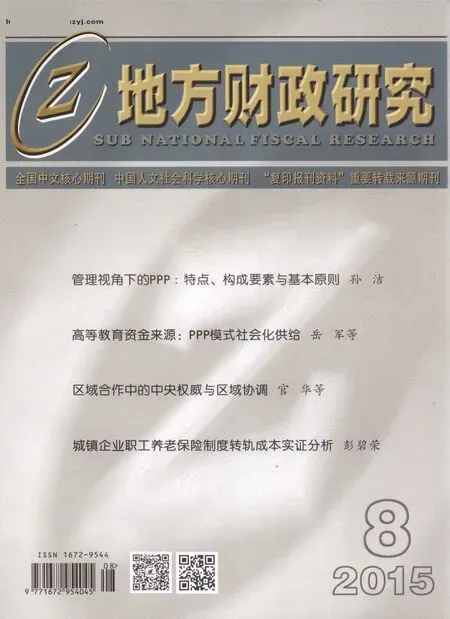PPP模式下財政承受能力研究——基于英國的實證分析
黃徐會
(暨南大學,廣州 510520)
一、引言
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此前被譯為“公私合作模式”,官方確定為“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指的是通過特許經營、購買服務、股權合作等模式,形成政府與社會資本相結合,共享利益、同擔風險的長期合作模式,旨在增強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及服務的能力,保證公共服務的質量,充分利用民間閑余資本的同時,確保政府債務規模的可控性。
在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態勢相對疲弱的新常態下,PPP模式因其能夠緩解地方財政支出壓力,減少債務規模而被寄予厚望。我國于2014年由財政部設立了統籌部門: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中心。由于該模式在英國等國已發展多年且較成熟,當前我國的整體PPP模式框架與操作指南極大程度參考了英國PFI模式。主要區別在于,英國強調開展PPP模式的首要考慮原則為物有所值,而我國則在此基礎上,依照國情增加了對財政承受力的考量。原因在于,盡管PPP模式被認為是一條具有效率且極可能解決當前政府債務擴大與政府支出需求擴大二者矛盾的途徑,但是,由于PPP項目針對的主要是具有非排他、非競爭性的公共物品或服務,審批通過PPP項目一方面意味著社會資本的引入,另一方面也增加政府的直接財政支出或隱性債務。故PPP模式只有被限定在一定規模內才能發揮其作用,我國應在開展初期,重視財政承受力的論證,將每年因PPP項目而引起的財政支出從總量上給予限制,防止PPP模式成為地方隱藏債務的炸彈。
對于財政承受力這一概念,學術界并未廣泛研究使用。高建初、馬巾英(1993)指出,所謂財政承受力就是財政對經濟和社會發展所提供的財力負擔。延伸至PPP模式,這一概念是指對于PPP項目,財政支出所需要承擔的多少。梁尚敏(1987)也認為量力而行就是考量財政的承受能力,使之不致突破“防線”,任何財政支出都必須把住財政承受力的計劃和關口。宗禾(2015)解讀稱,財政承受能力評估是根據PPP項目預算支出責任,評估PPP項目實施對當前和今后年度財政支出的影響。楊志勇(2015)更是指出,對財政承受力論證相當于為項目裝上“安全閥”,給民營資本吃了定心丸,又利于規范PPP項目財政支出管理。綜上所述,政府在安排PPP項目時需要考慮到每個項目將給政府自身帶來的財政支出責任,并按照量入為出的原則,充分考慮政府所能承受的最合理的財政支出責任,為PPP項目設置“天花板”。財政承受力的研究雖仍處于概念界定理解的階段,但有理由認為,政府所能承受的最合理財政支出責任這個“天花板”即為財政承受力。筆者以此出發,試圖對我國PPP模式是否有必要通過考量財政承受力來限制整體規模,又如何確定財政承受力等問題進行研究并做出解釋,為合理開展PPP模式提供思考。
鑒于中國PPP項目才剛起步,項目思路與相關數據并不清晰,無法直接研究我國對財政承受力的考量。而英國作為最早開展PPP模式且具有豐富經驗的國家,已設立了全國PPP項目統籌部門,且擁有健全完善的預算制度。故英國雖未明確指出對財政承受力的考量,但筆者假設其預算制度實質上已將財政承受力的考量包含在PPP項目的前期審批中,從而確保了PPP項目的規模被控制在財政承受力范圍內。基于該重要假設,結合英國PPP項目數據,證明其財政承受力即PPP項目所帶來的財政支出責任確實被限定在一定范圍。
而由于英國采用的是PFI模式,由私人企業進行設計-建設-融資-運營-維護基礎設施,期間政府按照合理資本回報率每年給予私人企業一定數額補貼,合同到期后,私人企業無償移交給政府。這意味著由PPP項目帶來的財政支出責任主要為給予私人企業的補貼,故在前文重要假設下,筆者將以英國歷年因PPP項目所實際產生的債務量反映PPP項目財政支出責任大小,延伸至代表PPP項目財政承受力的大小。通過對英國歷年PPP債務量變化,與相關影響要素進行回歸分析,旨在發現其中存在的線性回歸關系,確定“英國將考量財政承受力作為審批PPP項目潛在條件”的假設成立與否,并嘗試估算出適當的財政承受力,最終為我國PPP項目考量財政承受力,限制規模舉措提供借鑒經驗。
二、英國財政承受力與各項影響要素的回歸關系
本文論證思路是建立在一個重要假設上:英國在確定PPP項目時會考量財政承受力的大小,并依此判斷采用PPP模式的項目數量與總額。該假設成立時,政府每年在PPP項目的財政承受力將被限定在一定范圍內,而其變化與相關影響要素保持一定線性關系。全文使用三個模型:(1)根據英國PPP項目特點,以英國政府每年因PPP項目而承受的債務總額代表PPP項目財政承受力,通過因子分析法將組成債務總額的幾個指標整合成若干個因變量;(2)再次采用因子分析法確定財政承受力的影響因素;(3)通過對財政承受能力及影響因素進行回歸確定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而支持或否定假設。而具體各項變量的選擇在各個模型內將予以說明。
數據來源于對英國財政部基礎設施建設局(IUK)發布的全國PPP項目匯總數據進行整理而得,因英國PPP項目自1997年始才真正步入正軌,趨于成熟,因此筆者又以1997年到2012年為跨度整理,該跨度內各年數據完整、連續,能真實反映該國PPP項目情況。同時,文中若干個與PPP可能相關的宏觀數據指標,均從英國統計局(ONS)網站上獲取,保證了數據的客觀準確性。需說明的是,原始數據的貨幣單位均為百萬英鎊。
(一)模型一:財政承受能力的確定
如前文所述,筆者用英國政府每年因PPP項目而承受的債務總額來代表財政承受力的大小。本模型選擇以下3個指標用來全面反映PPP債務總額以說明英國財政承受力大小,原因在于對財政承受力的評估包含了PPP項目實施對當前和今后年度財政支出的影響的評估,選取指標用以反映PPP債務總額時,應考慮新增項目帶來的債務、歷史項目遺留的債務總額;而對于新增項目,又包含為引起當年直接債務及未來潛在債務。只有全面考慮方能描繪出因PPP項目而承受的債務總額。另,對于未來潛在債務,為使模型不至于太復雜,本文未考慮現值因素。
三個指標分別為:(1)第i年批準的PPP項目引起的當前及未來債務總額,包含政府在第i年及隨后年度支付給私人企業的款項;(2)第i年以前年度所有PPP項目遺留的債務總額,包括往年簽訂但仍需在未來支付給私人企業的款項。(3)第i年以前PPP項目帶來的第i年應支付給私人企業的債務總額。而這三個變量的數據均可通過整理英國財政部數據得到。通過spss對這三項指標進行因子分析,目的在于發現這幾個數據之間的聯系,進而歸類降維,將同一類變量整合成一個因子。
該因子分析中,KMO為0.56,略小于0.6,但Bartlett的球形度檢驗中,顯著性概率sig是0.000,表明該若干變量適合做因子分析。故筆者利用最大方差旋轉法進行因子旋轉,最終得到1個公共因子及其因子解釋的總方差(表1)。從表1可以看出,方差的累積貢獻率為68.225%,即成分1可解釋這三個變量68.225%的內容,因此我們有足夠理由認為這個公共因子能夠基本反映絕大部分信息。由于筆者選取的三個要素均與債務相關,代表著每年所面臨的PPP當期及未來債務大小,我們將這個整合出來的公共因子命名為債務因子(DEBT)。

表1 解釋的總方差
借助spss軟件,我們還可以得到債務因子(DEBT)的綜合得分(見圖 1),可見債務因子(DEBT)整體呈現上升的趨勢,一方面是由于每年簽訂新的PPP合同直接擴大債務規模,另一方面則是之前年度簽訂的PPP協議遺留的歷史累積債務。其中2006年綜合得分暴跌,就原始數據而言,該年PPP各項債務數值出現了大幅上漲導致得分降低,究其原因,2006年市場良好,利率等貸款條件非常寬松,吸引了大量銀行和資本參與PPP項目。但這一異動年度并不影響實證結果,故保留該得分。

圖1 模型1公共因子得分
在該因子分析下,筆者達到了預想目標,將整理的3個英國PPP債務相關變量歸類整合成為1個債務公共因子(DEBT),該因子涵括了英國每年因PPP項目而引發的債務增加及累計額,反映了英國某一年度因PPP項目而承受的債務情況,數值不斷增加,可見政府財政承受力并非靜態固定不變,而是按照一定模式逐年增加。因此在后續線性分析中,以債務因子(DEBT)代表財政承受力,作為因變量,分析影響其大小的因素,再有的放矢地提出將債務規模控制在政府財政可承受范圍內的建議。
(二)模型二:影響因素的確定
由模型一可見政府就PPP項目的財政承受力每年發生變化,筆者猜想該變化可能受到英國本身經濟發展的影響,也可能受到政府財政收支規模變化的影響,還可能在全部政府債務中占據一定比例,同時與政府PPP項目簽訂的資本額可能存在一定相關關系,故綜合考慮后,本模型選取了5個宏觀變量對英國各個年度宏觀背景進行考量,充分考慮政府的財政大環境。宏觀變量如下:(1)英國當年通過預算審核的財政總支出;(2)通過預算審核的財政總收入;(3)政府全年承擔的政府債務凈值;(4)國內生產總值;(5)當年英國政府與私人企業簽訂的新增PPP項目合同中注明的總資本價值,即全年所有新增PPP項目賬面資本價值量的總額。與之前類似,該部分同樣使用SPSS對這5個數據進行因子分析。
該因子分析中,KMO為0.73,大于0.6,而且Bartlett的球形度檢驗中,顯著性概率sig是0.000,表明該模型非常適合做因子分析。筆者依然利用最大方差旋轉法進行因子旋轉,最終得到2個公共因子及其因子解釋的總方差。從表2可以看出,兩個公共因子方差的累積貢獻率為97.938%,即成分1、2幾乎完全解釋所有因子。而根據表3的旋轉后成分矩陣圖,我們可將前四個宏觀變量歸為第1個公共因子,因其表達的是宏觀經濟環境,故命名為宏觀因子(MACRO);而最后一個變量歸入到第2個公共因子,命名為PPP資本因子(PPPCAP)。
我們通過軟件得到該部分兩個公共因子的得分曲線圖。由圖2可見,MACRO公共因子趨于穩健上升,這得益于全球經濟的不斷發展,英國各項宏觀數據指標逐年穩健上升。而PPPCAP公共因子整體趨勢上呈現的是先上升,并在2006年達到峰值后,持續下降。原因主要有兩點:(1)隨著PPP模式在英國不斷發展,已經由熱烈追逐降溫,逐漸形成新常態,政府無論是對審批程序還是模式本身均趨于理性,而私人企業也理性對待;(2)如前文所言,2006年后英國國內市場下滑,銀行利率下降,貸款條件苛刻等因素打擊了部分私人企業參與PPP項目熱情,08年經濟危機后更是雪上加霜。

表2 解釋的總方差

表3 旋轉成份矩陣a
該部分通過因子分析法將筆者選取的5個變量歸為2個公共因子,一個是宏觀因子(MACRO),代表每年宏觀經濟情況,另一個是PPP資本因子(PPPCAP),代表每年政府與私人企業簽訂的PPP項目合同標注的資本價值。這二者都是可能影響到英國財政承受力(即PPP項目債務總額的內容)的重要影響要素,因此均可作為自變量,用來分析了解二者分別對政府PPP項目債務總量造成何等影響,方便建立關系,為我國提供寶貴經驗。
(三)模型三:英國財政承受能力影響因素的回歸分析
假設英國政府每年因PPP項目而承受的債務總額與宏觀環境存在著回歸關系,即宏觀環境的好轉惡化與PPP項目資本價值量大小二者均對PPP債務總額有影響,從而建立回歸模型如下:

圖2 模型2公共因子得分

其中,α為自變量PPCAP的系數,表示PPP資本因子每增加一單位引起的債務因子變動數;β為自變量MACRO的系數,表示宏觀因子每增加一單位引起的債務因子變動數;ξ為誤差項
利用eviews6.0做線性回歸得到表4,因此線性回歸方程如下:

其中R2及修正R2分別為0.982和0.981,表明線性方程的擬合優度非常高,而且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P值也遠小于0.05,說明方程犯錯的概率很低,該線性回歸方程是有效的。D-W檢驗為1.287,位于dU與dL之間,屬于不能確定是否存在自相關,但進一步進行LM檢驗后,P值非常小,故并不存在自相關。

表4 財政承受力債務因子(DEBT)的回歸結果
據此可以得到相關結論。首先,PPP資本因子對債務因子的影響僅為0.121,這意味著在PPP模式框架下,政府與私人企業簽訂PPP項目合同時確定的項目的資本價值,對該PPP項目所帶來的債務總額的實際影響比較小,這提醒我們,政府在前期審核論證過程中,不能簡單地借助資本價值來判斷政府每年整體承受的債務,而應當以嚴謹科學的方式預計債務規模,方能掌控PPP模式。
其次,該線性回歸中PPP資本因子與債務因子呈反向變動,與筆者設想的不同。反向變動的原因在于,英國每年簽署的PPP項目資本價值總量整體在減少,處于下降趨勢,但PPP債務總額卻因以前年度PPP項目累計的債務而不斷攀升。二者呈現一定的反向關系,但不應一概而論,即這種反向變動關系并不意味著PPP項目資本價值升高時,PPP債務總額反而會減少。結合其對PPP債務總量影響小的結論,我們可以有所側重地接受這種反向變動關系,即認為簽署的PPP項目資本價值總量與債務總額同步增長,但債務總額并不會因資本價值總量下降而下降。
再者,回歸方程反映了英國財政支出、GDP等宏觀變量對PPP債務總額呈同比關系,且系數為0.9838,其影響更明顯更強烈,這表明筆者的“英國政府每年因PPP項目而所承受的債務總額與宏觀環境存在著回歸關系”原假設是可接受的。英國政府每年承受的PPP債務總額與宏觀指標呈正比,具體而言,財政支出等宏觀經濟指標與政府每年PPP債務總額呈同方向變動關系。
這就為我國政府考慮財政承受力的舉措提供了實證基礎。正如一開始筆者的設想,英國政府雖未提出我國類似的“財政承受力”原則,但實際上每年PPP項目帶來的總債務即財政承受力與經濟發展及財政能力同步,項目帶來的總財政支出責任被有意識地控制,表明實質上英國依靠本身出色的預算制度,在統籌安排PPP項目規模時充分考慮項目所帶來的財政支出責任,并將PPP債務規模控制其財政能力所能接受的安全范圍內。因此可以得出結論,以英國實踐為借鑒,我國在確定PPP項目時,一方面,應當考慮為PPP項目設置相應財政承受力,將財政支出責任限定在一定范圍;另一方面也應當使PPP項目發展與宏觀經濟發展同步,讓財政承受力的設定隨經濟發展不斷調整,從而PPP模式的發展不至于過快或過慢。
(四)估算英國財政承受力大小
究竟應當如何為PPP項目設定合理的財政承受力,這個問題值得深入研究,但并非本文重心,故筆者試圖仍以英國為經驗,粗略估計英國潛在考量的財政承受力大小,并希望借此為我國提供參考。結合我國財政部文件思路與本文結論,筆者將財政承受力設定為PPP帶來的財政支出責任占當年公共支出預算的比例,并簡單粗略估計英國每年新增PPP項目帶來的債務,由于屬于粗略估計,主要從預算角度考慮新增項目對預算的影響,該數值僅由兩部分組成,既包含了因往年PPP項目而引起本年支付的債務,又包含因本年新增PPP項目而引起的本年及未來的債務,兩者的和對當年英國財政支出預算的比例,得圖3。可以看到,在英國,該占比一般在4%—7%之間,最高不超過10%,且有不斷降低的趨勢。
三、對我國財政承受力考量的啟示
(一)與宏觀指標掛鉤,確保可控的債務總額
為防止PPP項目的實施加劇財政收支不平衡,我國應當充分考慮設置財政承受力,而不管其設置數額為多少,均意味著應當合理控制PPP項目財政支出責任,即限制每年的PPP債務規模。本文以PPP模式最完善的英國為實證,充分表明,財政承受力大小的設置與財政支出等宏觀指標呈同比變化趨勢。我國可從中借鑒:要達到PPP模式限制與推動發展并存,二者尋求平衡點的目的,應將之與財政支出等指標掛鉤,如將每年政府PPP支出義務預算總額與財政支出之間確定比例進行限制,一方面保證每年PPP項目審批總額自動隨著經濟發展狀況提高或降低,使之與經濟本身匹配,達到減輕政府財政支出壓力,緩解債務危機的目的;另一方面,以硬指標從制度上倒逼地方政府重視PPP項目的前期財政審批論證,迫使地方政府梳理出質量高、需求更迫切的公共項目,并避免與市場爭利,真正發揮PPP模式的作用。

圖3 英國每年PPP債務對財政支出占比
(二)合理設置財政承受力的大小
針對財政承受力的論證,我國財政部當前出臺文件提出:“每一年度全部與PPP項目需要從預算中安排的支出責任,占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比例應當不超過10%”,結合前文對英國財政承受力的粗略估計,并考慮到英國有較發達的政府舉債體系,我國將因PPP項目引起公共支出責任占當年公共預算支出比例適當提高到10%是符合國情,比較合理的。以此為PPP模式發展的天花板,待PPP模式在我國發展成熟,配合同步趨于完善的財政預算體系,在下一階段可考慮重新調整該比重,并在最后與英國一樣將其轉變為一種軟限制。
(三)PPP項目納入預算,落實財政承受力原則考量
英國預算制度已經深入人心,成為了PPP項目考量財政承受力的隱含前提條件。而我國財政預算制度仍在發展完善中,在制定PPP項目準則時提出考慮財政承受力,明確將PPP項目納入到公共支出預算中的舉措非常具有必要。只有將PPP項目納入預算中,方能確保PPP模式依照財政承受力原則進行的前期論證有效,對財政支出責任進行有效控制。這是PPP項目周期長、見效緩的特性結合我國當前強調的中長期預算制度的結果,是PPP模式中國化的關鍵一步。有了英國等第一梯隊國家的成功經驗,中國應更多的吸取經驗的同時,結合國情謹慎前行,逐步放開。筆者認為,我國初期展開PPP項目仍應重視項目的前期考證,以財政承受力為前提,再強調物有所值,雙管齊下方能達到預想效果。
(四)各地盡快成立PPP中心
英國本身國土面積小,行政劃分相對簡單,當前僅設立全國性的IUK負責統籌安排全國PPP項目。但我國地大物博,行政劃分復雜。除國家財政部設立了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中心外,各地也應加快設立省級、市級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中心。一般由各地財政部門牽頭組建中心,參照財政部公布的PPP指南充分學習領悟PPP精神,統一部署,各地方PPP中心在前期審批論證PPP項目時,應按照地方財政收支情況合理論證當地PPP項目的財政承受力大小,并以此為上限合理安排各地方PPP模式開展規模,使財政承受力原則得到自上而下的貫徹。這對各地解決當前普遍存在的“推進城鎮化建設與控制地方債務規模”二者矛盾至關重要,也更有利于從國家層面上把握規劃PPP項目。
(五)合理保持PPP模式與其他債務解決方式的結構
PPP模式確實能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一部分地方政府債務問題,但出于可控考慮,PPP總量需要限定在一定可控范圍內,因此其發揮的作用也是有限。再者,PPP模式主要解決的是增量債務,對于存量債務作用較小。當前地方政府債務普遍高企,土地財政已經被證明非可持續的解決財政方法,但地方政府籌措解決政府債務的合法渠道不多,因此才對PPP模式趨之若鶩,缺考思考理解。筆者認為可逐步推出其他緩解地方債務問題的舉措,如落實發展地方債務置換,理順匹配各級政府財權事權等,多方結合,方能切實解決問題。
〔1〕 劉旭輝,陳熹.PPP模式在新型城鎮化建設中的推廣運用研究——以江西省為例[J].金融與經濟,2015,02:85-88
〔2〕 王琦.推進PPP管理模式化解地方政府債務危機[J].中國管理信息化,2015,06:164-165.
〔3〕 亞行:PPP項目的財政效應分析 [J].中國財政,2014,09:20-21.
〔4〕 曾曉安.用PPP模式化解地方政府債務的路徑選擇[J].中國財政,2014,09:25-26.
〔5〕 白璐璠,王春成.PPP模式與地方公共財政負債管理[J].中國財政,2014,14:43-45.
〔6〕 廖新晨,趙釗.PPP視角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治理研究[J].現代經濟信息,2014,17:489.
〔7〕 楊志文.探索財政出資的PPP新模式 [J].西部財會,2013,08:7-11.
〔8〕 梁尚敏.論財政承受能力[J].財政研究,1987,01:12-16.
〔9〕 高建初,馬巾英.財政對改革承受能力的彈性初探[J].當代財經,1993,03:23-25.
〔10〕宗禾.財政部發布PPP項目財政承受能力論證指引[N].中國財經報,2015-04-16003.
〔11〕 H Ping,Tserng;Jeffrey S,Russell,Ching-Wen,Hsu,Chieh,Lin.Analyzing the Role of National PPP Units in Promoting PPPs:Using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a Case Study[J].JOURNALOF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MANAGEMENT,2012,(2):242-249.
〔12〕 Surya,Sudheer,Meduri,M,Tech;,and,Thillai,Rajan,Annamalai,Ph,D.Unit Costs of Public and PPP Road Projects:Evidence from India[J].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2013,(1):35-43.
〔13〕 Evis,Gjebrea,and,Oltjana,Zoto.Infrastructure Public Private Partnerhip Investmen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Western Balkan and Emerging Countries[J].EU Crisis and the Role of the Periphery,2014,(2):131-144.
〔14〕Furneaux,C,W,Brown,K,A,c,Tywoniak,S,and,Gudmundsson,A.Performance of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J].Proceedings of the 4th World Congress on Engineering Asset Management,2009,(9):326-334.
〔15〕 PETER,RAISBECK,COLIN,DUFFIELD,and,MING,XU.Comparative performance of PPPs and traditional procurement in Australia[J].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2010,(4):345-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