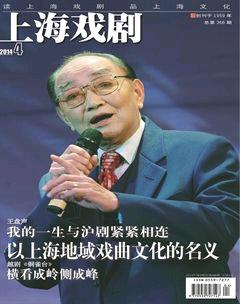這對你不好
押沙龍在1966
1
我經常覺得很多戲難看。制作粗糙、技巧拙劣、演技浮夸、缺乏操守、品位低下、想象力匱乏、態度隨便……而導致這一切的有一個源頭,我認為和從業者受到的教育有關。所以這一次,我想談一談我眼中的戲劇學院和戲劇學院的學生。
2
之所以認為戲的好看難看和戲劇學院的學生有著密切的關系,是因為和影視行業不同,現在市面上大部分舞臺劇作品的主創,依然是受過戲劇學院或者相關專業教育的,所謂“科班出身”的。我雖然沒有做過精確的統計,但只要你在每次看戲時拿過宣傳冊,讀過宣傳冊上的主創資料,就會發現這個基本情況。
3
寫這篇的時候正值藝考,我看到一個新聞,說今年也許會統一劃定一個藝術生的文化課分數線,而這個分數線將接近一本線——這真是少數我認為英明的決定,我希望這是真的。
4
因為大部分戲劇學院的學生做出來的戲難看、制作粗糙、技巧拙劣、演技浮夸、缺乏操守、品位低下、想象力匱乏、態度隨便……是因為他們高考文化成績實在太差了。
人們接受戲劇教育的門檻太低了——是的,每一年表演系“千里挑一”的新聞,美術考試密密麻麻的現場,都讓藝術類大學顯得很“高大上”,很“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但是,如果真去追究這報考的幾千幾萬人中,有多少是熱愛表演?有多少是熱愛出名?有多少是想做演員?有多少是想當明星?有多少是一心想接受專業訓練?又有多少是成績太差走投無路,半年前開始突擊學素描,學表演,學寫作,僅僅為了另辟蹊徑混張本科文憑的?專業課考試真的足夠嚴格,足夠合理到能將這些動機不純的學生統統過濾在外嗎?顯然不。相反,專業課考試有太多偶然的因素能讓這樣的人混進合格線,而文化課分數線也不能把好最后一道關。
“藝術家”三個字成為了絕佳的借口,完美的遮羞布,好像“藝術家”就是和“偏科”、“自由”、“隨性”、“與眾不同”、“天才”這些詞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甚至連戲劇學院的學生自己也這樣沾沾自喜地以為,于是當他們聽到文化課的分數線可能提高到一本的時候,回應竟然是:“完蛋了,要招進來一群書呆子了。”——可事實上,就算真的是書呆子,也比這一群不學無術,將懶惰當成隨性,將無知當成術業有專攻的偽藝術家強。
5
是的,高考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缺陷和弊端,無法全面考察一個人的能力。但是,它至少考察了一個人最基本的一些能力,包括邏輯、閱讀理解力、耐心和自律——而這些,是每一個準備進入高等學府繼續深造的學子必須擁有的、最基本的學習能力。憑什么藝術生就可以沒有?將藝術院校的文化課分數線降低,就是在暗示對于未來的“藝術家們”,這種基本能力可以沒有,可以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可以網開一面。
這種網開一面,就是導致藝術生一些基本能力缺失的罪魁禍首。
這種網開一面,并不是對做不出數學卷子最后一道大題網開一面,也不是對搞不清英語語法網開一面,而恰恰是在對邏輯、閱讀理解力、耐心、自律甚至治學精神和求知欲網開一面,將這些統統漏在網外,然后,剩下了什么?
就剩下了那么多看不懂劇本,將臺詞亂改一氣的演員;那么多不讀劇本不看新戲,滿足于小品式調度的導演;那么多眼界窄品位低,將寫作降格為接活的寫手,將舞臺設計降格為接活的熟練工。
而這些人,不僅缺乏基本能力,還因為僥幸被所謂“千里挑一”的藝術院校錄取,而多了一份“我是與眾不同的藝術家”的自以為是。
6
也許再一次,有人要拿李安或其他一些特例來反駁我,說什么李安考了兩次聯考都落榜了,現在還不是成為了大導演?可是,李安并不是因為聯考落榜才成為今天的李安的,李安是因為堅持不懈地寫作,是因為拍每一部電影前都做大量的背景功課,是因為腳踏實地,是因為清楚自己的目標、能力和界限在哪里才成為現在的李安的。每一個將李安的落榜,李安六年的“蟄伏”扯出來作為自己的保護傘的準演員,準導演和準編劇,請捫心自問,你們一年看幾本書?你們演戲和導戲前有沒有做足夠的功課?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功課?如果不為交作業,不為賺錢,你們自愿寫過幾個劇本?
7
我為了解文化課分數線對于藝術院校或者相關專業是不是一個問題,而采訪了南京大學的呂效平老師,他也非常坦率地回答了我這確實是一個問題,并且針對戲文專業,他們正在逐步調整:“先是50%的考生必須過一本。現在是,所有錄取學生必須過一本。”這確實是非常苛刻的要求,但是我認為非常必要,特別對于戲文專業來說。呂效平老師還介紹說,他們戲文專業的課程設置,是始于文學的:“外國文學部分的要求基本上同于漢語言文學專業,古典文學宋以前部分與漢語言文學專業一起上課,元明清部分才是戲劇學專業上。現當代文學也是這樣。”對此,呂效平老師做了一個很有趣的比喻:“戲文和理科的天文專業相似:數學部分同于數學系,物理部分同于物理系,然后才是天文專業。”
8
是的,就像戲劇學院的老師常常強調的,我們要教給學生基本功,可基本功是什么?對戲文專業的學生來說,基本功是了解什么叫三一律,如何做突轉和懸念,怎么寫鎖閉式結構嗎?不是。
戲劇影視文學,首先是文學。基本功應該是文學基礎,是社科人文,是通識教育。因為這些,是關乎格局和眼界的。戲劇學院的老師最該做的,是想盡辦法引導學生對藝術、對哲學、對這個世界的方方面面,有越充分越好的了解。而這種了解,會徹底改變一個人的思考方式。而一個人的思考方式,又會對他寫作上主題的選擇,敘述的方式產生重要的影響——而這,才是真正重要的。
三一律,突轉和懸念,鎖閉式結構,情境甚至劇本格式——這些要學嗎?要學!但技巧固然重要,格局和眼界才是定勝負的關鍵。沒有格局和眼界的技巧,只會淪為雕蟲小技,只能在春晚小品式的話劇和長舌的婆媳家庭劇里,為創作者掙點可憐巴巴的稿費。endprint
而如何獲得對藝術,對哲學,對這個世界的基本常識?只有通過閱讀,通過精讀。而精讀需要什么?需要邏輯、閱讀理解力、耐心和自律——你看,我們又繞回來了。
9
其他專業也是一樣的。導演系的基本功是什么?是元素小品的訓練?是學會找支點,建立畫面?表演系的基本功是什么?是通過呼吸發聲吐字把八百標兵奔北坡念順?是通過形體訓練學會怎樣好看地在舞臺上摔跤?不是。
這些是基礎,是技巧沒錯,但決定一個人能否成為好導演和好演員的,是想象力,是敏感度,是創新意識。
而獲得想象力和敏感度的方法,要么是拼命地生活,要么是拼命地閱讀。
我一再強調閱讀,是因為當我們聽說一個人在進行藝術創作的時候,總是會鼓勵他“多體驗生活”。可是,生活有無數種,你不可能統統體驗到,科恩兄弟也不是因為在現實生活里體驗過做殺手了,才拍出《老無所依》的——而閱讀,是讓人可以體驗到盡量多種生活,盡量多種情緒的捷徑,并且,拓展著你的想象力,提高著你對事物的敏銳度。
而關于創新意識,我常常驚訝于戲劇學院的學生,包括老師觀念上的陳舊和落后。信息的遲滯和閉塞簡直讓人難以相信。更可怕的是,我沒有看到他們對世界上最新的舞臺技術和舞臺美學趨勢的求知欲。在網絡如此發達的今天,如果有心,就可以查到你想知道的任何資料,只要拿出找“片子”的一半熱情和執著,就能找到美國、歐洲乃至日本韓國最近上演的劇目消息,最新的劇評和最有趣的舞臺設計——如果是因為在信息搜索的能力上,在英語的閱讀能力上有障礙的話——我真的不想再一次提醒,這是哪個環節上出了錯。
如果一個一心想做導演的學生,對這一季百老匯在演什么,去年的普利策戲劇獎的得主,最新的裝置藝術,最貴的當代畫家,最受關注的行為藝術家等等全部毫無概念,一無所知的話,那他不僅不可能在此基礎上有所創新,甚至是對自己從事工作的失職和怠慢。
10
我之所以一再強調眼界和格局的重要,甚至認為它排在技巧之前,是因為眼界和格局還涉及一個藝術創作中至關重要的品質:好奇。
眼界格局,和好奇心求知欲,是相輔相成,兩相助長的。看得越多越好奇,越好奇越看得多,然后,這些會變成對于一門藝術真正的,終生的熱愛。
這種熱愛,才是導演、演員、編劇和舞美設計師有資格被稱為“藝術家”的原因,因為對他們來說,這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事業,是理想。而沒有這份熱愛,只知道些突轉懸念,元素小品,聲音形體的,都只是“熟練工”。
11
也許有人會說,戲劇學院要教的就是技巧,眼界格局,好奇心求知欲,靠的是學生自覺,教是教不出來的。
是的,熱愛教不出來,但熱愛可以引導。
引導學生閱讀、看戲、觀摩電影和畫展,學習更多其他領域的知識,也是戲劇學院教育上的職責之一。但事實上,學院中雖不乏有好老師,但還有不少教師,一方面不停地在課堂上傳授陳詞濫調,另一方面對于國際戲劇舞臺最新潮流好像也只說得出《戰馬》。但僅用iPad下載IBDB的APP所獲的信息量,早已遠遠超越課堂上的收獲,當然,對于學術界的最新訊息,就更難從他們口中知曉。
有的時候我甚至懷疑,學院的老師們對戲劇的熱愛究竟有幾分?對學問的熱愛究竟有幾分?權當我是惡猜了。
在信息化和電子化的今天,資訊、學養和實踐構成了最完善的教學鏈,如果沒有這些,連iPad都能向學院教師發起挑戰,而戲劇學院和藍翔技校又有什么區別?
12
再補充一個眼界和格局的重要所在。眼界和格局決定了審美品位,而品位則直接決定了作品的質素。
我的觀察是,一個人只可能做出最多等于,往往低于自己審美品位的作品。
眼永遠會比手高,所以如果你真心喜歡湖南衛視的偶像劇,那說明你是做不出湖南衛視的偶像劇的,更別說其他的了。
13
考進戲劇學院或者相關專業的學生,在我看來大致分為兩類,渾渾噩噩混文憑的,以及高中時的文藝積極分子,文藝愛好者,也就是所謂的“文藝青年”。當然,后者還是居多的,并且,通過四年的熏陶,前者也在漸漸成為后者,畢竟,要喜歡上文藝,也不像要喜歡上數學那么困難。
而戲劇學院,就是將文藝愛好者漸漸變成文藝工作者的一條通道,一座橋梁。這兩者之間的區別在于,前者通常會欣賞、旁觀、全情投入和自我感動,而后者則需要分析、總結、自知和反省。
文藝愛好者可以在排練教室和朋友們嘮嗑吃外賣,在舞臺上忘記角色賣弄自己然后聽著此起彼伏捧場的“牛逼”淚光閃閃,在半夜吃串兒喝酒慶功,被一種波希米亞式的,“貧窮藝術家”的假象所感動。
文藝工作者則需要通過大量的觀摩和信息搜集,知道自己和他人,和世界的差距在哪里,然后經歷無數次痛苦的自我否定,再創作,再否定,再創作。
可惜的是,我看到太多文藝愛好者,太少文藝工作者。
這些文藝愛好者在經歷了戲劇學院的學習之后,并沒有學到自知自省,而只是多了一點表演上的油滑制式,寫作上的程式套路,導演上的……忽悠人的口才。
當他們真正進入這個行業以后,一方面,引以為豪的基本功慢慢忘光,另一方面,本來就少之又少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又變成了徹底的麻木和惰性。
而他們唯一擅長的,就是利用雙重標準進行永無止境的自我安慰——
當他們參與一部所謂的“商業話劇”時,就用“這是為了賺錢我得聽老板的”來為自己做出惡俗的東西開脫,并且掩飾了其中所有的能力問題(而很多商業話劇根本不是有沒有節操的問題,而是連一個有效的戲劇場面都不曾存在,這只和導演的基本功有關);當他們獲得一個機會做一些更加“藝術”的東西時,他們又以一副“觀眾太蠢我太前衛”的梵高姿態來作為作品不受歡迎的原因,而無視作品本身的空洞無聊,老土矯情。
至此,要基本功沒基本功,要格局眼界沒格局眼界,還剩下什么?什么也不剩了。
我們經常在看的,就是這些一無是處的,科班出身的戲劇工作者,帶給我們的粗糙草率的演出。
14
當然,我也一直非常奇怪,這群“偽藝術家”們在跨出校園之后,是如何一次又一次獲得工作機會,活躍在戲劇舞臺上的呢?后來我仔細想了想,覺得大家還是沾了時代、環境和體制的光,至少在目前的上海,新劇場越來越多,但填充物太少,劇目太少,演員太少,編劇太少,導演太少,不讓劇場開天窗已是不幸中的萬幸,沒有幾百個演員爭奪一個角色,沒有搞砸了一個戲就再也得不到投資人垂青的競爭,再不濟,還有各種名目的先鋒戲劇節、青年戲劇節的口徑可以走。
這種寬松,友好,缺乏競爭的戲劇環境,簡直就像懶散者的溫床,細菌的培養皿,讓編、導、演各部門產生“我真牛逼”的錯覺,繼而,成了一個得意又懶散的藝術工作者,他們不用去健身保持身材,不用多讀書看展,甚至不用每天保持三分鐘以上的思考,全部的精力都投身于怎樣用便宜招兒唬住觀眾,反正掌聲和鮮花一個都不能少。
15
最后我想說,無論是校內或校外,藝術生都受到了寬松政策的特殊對待,這也許是對天才的縱容,但更多時候,這讓戲劇學院淪為了藍翔技校、希望工程,讓商業演出淪為了慈善晚會,讓觀眾淪為了錢多人傻速來的活菩薩,而一批又一批連二本線都考不過的藝術工作者們,依然在沾沾自喜地生產著“藝術垃圾”。
這對你不好,學院領導,演出商,觀眾,從業人員,明白嗎?這對你不好。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