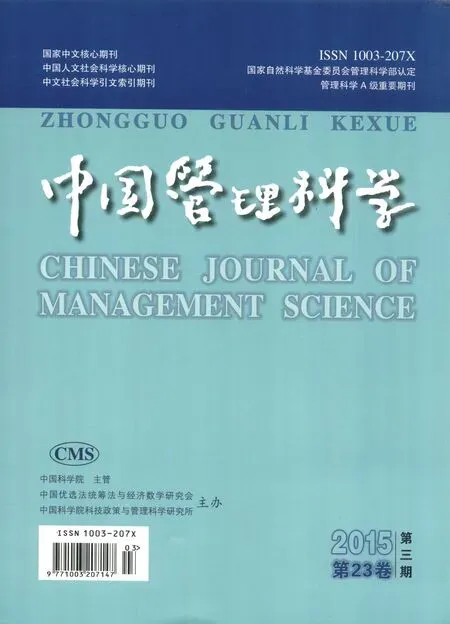重要股東市場行為引導下的利益趨同與壕溝防守效應
王建文,國艷玲,王麗娜,韓飛飛
(合肥工業大學管理學院,安徽 合肥 230000)
?
重要股東市場行為引導下的利益趨同與壕溝防守效應
王建文,國艷玲,王麗娜,韓飛飛
(合肥工業大學管理學院,安徽 合肥 230000)
重要股東的市場行為不僅會對股價造成直接影響,還因其影響公司成長、與其他投資者的利益相沖突而倍受證券理論與實務界的關注。本文以存在增減持行為的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按主成分分析法構建成長性指標,通過對重要股東增減持股票與公司成長性間的多元回歸分析,研究其市場行為在多因素綜合影響下對利益趨同與壕溝防守效應的催化作用。實證結論顯示:重要股東增持總會強化利益趨同、減持強化壕溝防守;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越多,壕溝防守效應越明顯,前十大股東持股比例越多,利益趨同效應越明顯,體現了股權制衡與股權控制的平衡關系。
重要股東;利益趨同;壕溝防守;市場行為;公司成長性
1 引言
重要股東是指在公司經營中起關鍵作用的股東,主要有兩類:一是以主要資金資本提供者——大股東為代表的控制權股東,二是以主要人力資本提供者——管理者持股為特征的經營權股東。股權分置改革后這兩類重要股東市場行為不僅左右著A股趨勢,還左右著公司經營業績與成長,因而倍受學者們的關注。重要股東的市場行為是強化了“利益趨同”還是強化了“壕溝防守”?這是未來市場能否持續健康發展的關鍵問題。利益趨同與壕溝防守主要是針對管理者持股而產生的命題,前者是指管理者持股增加會使管理者和股東的目標函數趨于一致,有助于管理者減少機會主義行為;后者是指管理者和外部股東的利益不一致,持股過多會使他們擁有更大的權利來控制企業,會使其犧牲股東利益換取自利目標。利益趨同與壕溝防守效應也應用于大股東與中小股東的利益關系上,兩者利益趨向一致則為利益趨同,反之為壕溝防守。上市公司的中小股東與大股東、股東與管理者之間存在“搭便車”與委托代理關系,兩層關系對應著兩個層次的利益趨同與壕溝防守。
單純從股權控制的角度分析,學者們普遍認為,股權結構是影響利益趨同與壕溝防守效應的關鍵因素,但觀點差別較大。Grossman和Hart[1]就認為:股權結構分散的環境下,因為監督收益小于監督成本,單個股東缺乏監督公司經營管理、積極參與公司治理和驅動公司成長的激勵,集中的股權使得監督管理者的收益大于成本,從而提供了制約管理者道德風險的有效機制;然而,Shleifer和Vishny[2]認為,大股東對小股東的掠奪是股權集中型公司業績低下、新興股票市場不發達的重要原因,集中的所有權雖然賦予了大股東監督管理者的激勵和能力,但也賦予了其掠奪小股東的激勵和能力,從而導致大股東道德風險的產生;Porta[3]認為,企業的代理沖突主要存在于控股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控股股東為了獲取私人收益,可能會通過一些渠道損害中小股東的利益,而世界大部分國家的公司所有權結構相對集中,并由控股股東控制,這是產生代理沖突的主要原因;Claessens[4]根據Porta的研究成果,對東亞9國的上市公司進行了系統的研究,認為大部分公司價值會隨控股股東擁有的現金流所有權而增長,而當控股股東的控制權超過其現金流所有權時公司價值會下降,有著壕溝防守效應;Hart[5]認為,大股東控制會導致屬于管理者個人的專用性投資減少,使投資和創新的動機減弱,進而使代理成本增加和公司價值下降,即出現壕溝防守效應。我國多數學者的研究表明,利益趨同效應和壕溝防守效應會隨著大股東持股比例的變化而變化,許永斌等[6]發現我國上市公司的控制權持有比例與公司績效之間呈現“侵害—協同—掘壕”的曲線型關系;但也有不少學者認為大股東持股均會表現出利益趨同效應,吳淑琨[7]、孔愛國[8]、徐莉萍等[9]實證研究發現,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對公司績效及價值影響總是正的;吳振信等[10]認為,中小股東可以通過第一大股東的減持比例來評價該公司的價值,同時發現質量越高的公司,第一大股東減持比例越小;劉銀國等[11]實證檢驗了股權結構與公司績效的關系,結果顯示股權集中度與公司績效呈現反向變動的冪函數關系,股權制衡度與公司績效成負相關關系;徐向藝等[12]的研究結論是:控股股東持股比例較低時,其侵占中小股東利益的動機隨持股比例的提高而增加,但當控股比例達到一定程度后,因在上市公司中占的利益很大,對中小股東利益侵占行為就會減弱。
從委托代理關系上分析,大多數學者們認為適當的管理者持股能有效解決股東與管理者之間利益沖突,降低代理成本,提升公司價值,但主要觀點分歧較大。最初Jensen和Meckling[13]提出正比例關系理論,即公司價值取決于內部股東持股,持股比例越高公司業績越好,有效降低代理成本的方法就是讓管理者持有更多股份;隨后Morck、Shleifer和Vishny[14]、Mcconnell和Servaes[15]提出雙重關系理論,即高管持股會同時產生利益趨同與壕溝防守效應,一方面隨著高管持股比例提高,對其激勵作用增強,高管追求的效用與股東越趨向于一致,從而可以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業價值,另一方面隨著高管持股比例提高,高管對企業的控制力不斷增強,來自外部的其他約束力越來越弱,使高管可以在更大范圍內追求個人利益,提高代理成本,降低企業價值;Mcconnell[16]研究內部股東增股消息發布前后六天內公司價值與內部持股比例的關系,研究認為公司價值與內部持股比例呈曲線關系,隨著內部持股比例的上升,公司價值先上升后下降;我國學者韓亮亮等[17]研究發現,高管持股與企業價值之間呈顯著的非線性關系,當高管持股比例在8%-25% 之間時,壕溝防守效應占主導,而小于8% 或大于25% 時,利益趨同效應占主導。
綜合以上研究,我們發現大多數學者將管理者持股與大股東持股產生的效應分立研究,且是單純研究靜態持股比例下的利益趨同與壕溝防守效應,其主要問題是:大股東與管理者持股均為影響公司成長的重要股東,他們之間有難以割舍的聯系,割裂的研究可能導致結論不完整;另外,不能區分重要股東增減持所產生的市場套利期待及存量持股所產生的持股期待,從套利期待上看,增持后期望股價上漲,與存量持股期待市值提升一致,但減持后重要股東的套利期待是股價下跌,與存量持股期待方向相反,由此使得利益趨同與壕溝防守效應發生改變。而本文正是以公司成長性為視角,將管理者與大股東均看成是影響公司成長的重要股東,并區分套利期待與持股期待,研究不同市場行為下的利益趨同與壕溝防守效應,以此重新審視重要股東與普通股東之間的利益關系。
2 研究設計
2.1 研究假設
是利益趨同還是壕溝防守,區分標準就是公司的成長性,成長性提升是利益趨同強化的結果,反之就是壕溝防守強化的結果。因此本文以成長性為被解釋變量設立多因素分析模型。
重要股東增持會影響投資者主要源自兩方面,一是增持作為股價被低估的信號,能提振市場信心;二是增持承擔一定的時間成本和風險,如果增持后公司盈利能力和成長性沒有提高,增持可能產生價值損失,因此增持可以看作未來盈利增長的信號。由此提出假設1:
假設1:重要股東、大股東凈增持與成長性正相關
基于朱茶芬等[18]的研究,大股東可憑借對公司估值和業績前景的優勢信息進行選擇性減持,高估值且業績前景差的公司更可能成為減持的對象。因此筆者傾向于認為:(1)重要股東作為知情者,對公司未來成長預期準確,其減持行為意味著公司成長性會變差;(2)IPO上市后,重要股東的創業激情會漸漸消退,一旦限售股解禁,就會拋售股票,導致公司成長性變差;(3)大股東或管理者減持后,其監督經營動力消退,會增加掏空行為,使公司成長性變差。由此提出假設2:
假設2:重要股東、大股東凈減持與成長性負相關
國內學者對我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與公司績效的研究結論存在較大差別。陳小悅等[19]認為,非保護性行業上市公司第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與企業業績顯著正相關;而白重恩等[20]則認為公司價值和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之間存在著U 形的關系,而按照Shleifer和Vishny[2]的觀點,過于集中的所有權賦予大股東監督管理者激勵和能力的同時,也賦予了其掠奪小股東的激勵和能力,從而導致道德風險的產生,在我國制度尚不健全的環境下,大股東對管理者的監督和約束更多依賴行政手段,而民營上市公司的大股東與管理者是完全的利益共同體,股權監督的作用均較小,由此提出假設3:
假設3: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與成長性負相關
股權監督取決于第一大股東以外的其它大股東對管理者及第一大股東的監督,從大股東合謀侵害中小股東利益的難度分析,大股東之間股權分布越均衡越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約束機制,雖然我國上市公司股權集中度對成長性影響尚無定論,但可歸納為兩方面:一是一股獨大不利于公司治理,尤其是進入穩定期以后的公司;二是股權集中對代理人的監督與約束增強,有利于一般投資者“搭便車”。這兩種矛盾的觀點使我們有興趣去驗證一個處于監督圈內的股權分散與制衡,而這一監督圈就是指前十大股東,是我們能尋找到的范圍最廣的大股東數據,并認為大股東相互制衡會減少對其他股東的侵害,因此提出假設4:
假設4:前十大股東持股比例與成長性正相關
2.2 變量選取與度量
2.2.1 被解釋變量(FA)
Mansfield[21]認為企業成長是個隨機過程,影響企業成長有諸多因素,難以對其準確預測。這說明成長是一個極其抽象復雜的過程。從兩個層次的利益趨同與壕溝防守效應分析,成長既是管理者努力與能力的結果,又是股權監督控制的結果,成長是一個復雜的指標綜合體。在實證應用方面,有些學者采用某個單一的指標代表成長性,也有些學者選用其中幾個指標。呂長江等[22]認為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與凈資產增長率這兩個指標可反映成長能力。本文借鑒該觀點并作一定補充,按公司成長邏輯構造三個層次指標:第一層次是市場與業務,公司成長的基礎是業務,失去業務擴展的成長不可持續,因此營業收入增長率是成長性指標的首選;第二層次是利潤,收入增加應帶來利潤增長,否則收入增長不可持續,第二層次選擇凈利潤增長率;第三層次是資產,利潤增加應使資產增加,這既體現積累,又體現規模升級,從公司成長的角度來看,總資產優于凈資產,凈資產易于表達資產歸屬問題,但不易表達資產運作問題,因此第三層次選用總資產增長率。通過營業收入增長率、凈利潤增長率、總資產增長率這三個指標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一個成長性因子FA,以此代表成長性指標,避免單一指標的片面性以及過多指標間的相互沖突。
2.2.2 解釋變量
設置4個解釋變量:重要股東凈增持比例(OP)、重要股東凈減持比例(RP)、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FR)、前十大股東持股比例(TR)。
2.2.3 控制變量
為增加模型擬合度,在分析影響成長的其它因素并進行一定的篩選后,最終確定公司規模、公司成立年數、資產負債率、總資產周轉率以及國內生產總值、行業變量等作為控制變量。相關變量定義見表1。
2.3 模型構建
為了區分重要股東增減持對成長性影響的差異,本文分別建立:(1)重要股東凈增持對公司成長性影響多元回歸分析模型;(2)重要股東凈減持對公司成長性影響多元回歸分析模型。回歸方程如下:

表1 重要股東市場行為對成長性影響回歸模型變量表
FA=C+β1OP+β2FR+β3TR+β4SIZE+β5AGE+β6DEBT+β7CI+β8GDP+β9ID+μ
(1)
FA=C+β1RP+β2FR+β3TR+β4SIZE+β5AGE+β6DEBT+β7CI+β8GDP+β9ID+μ
(2)
式中,C、β1、β2、β3、β4、β5、β6、β7、β8、β9為待估回歸系數,μ為隨機擾動項。
2.4 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
選取滬、深兩市2006年1月1日~2010年12月31日期間所有發生重要股東增減持行為的上市公司,為保證研究樣本的有效性,剔除了如下公司:(1)金融、保險類上市公司,因這類行業適用的會計準則和方法與其它上市公司有差異,其財務指標表達的內涵不同,同時金融類公司屬國有控股、享有較多的政策紅利,其成長性與高管努力及大股東監督在本質上的關聯較小,大股東增持往往僅是一種穩定市場的信號;(2)ST、*ST、**ST公司,其主要特點是業績不穩定,存在大股東變更等突變因素,會干擾實證結論的可信度;(3)同時有A、B股及境外上市股的公司,由于增減持可在不同市場進行,且股價又不統一,其增減持動機過于復雜。剔除后最終得到增減持樣本1070家,其中凈增持樣本342家,凈減持樣本728家,大股東和高管同時增減持的公司進行了合并處理。增減持數據來源于WIND數據庫,財務數據來自于財匯金融分析平臺客戶端。
3 實證結果分析
3.1 重要股東凈增持對成長性影響的回歸結果
表2為重要股東凈增持對成長性影響的回歸結果,其中第1列為全部重要股東凈增持下公司成長性回歸模型,第2列為大股東凈增持下公司成長性回歸模型。兩個模型中,OP的系數都顯著為正,說明全部重要股東、大股東凈增持對成長性均有顯著的正面影響,與假設1一致。重要股東增持的“套利期待”提升了公司成長性,并做出了實質性努力,增持導致的股權比例提高也提升了“持股期待”,強化了利益趨同。重要股東凈增持模型中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系數顯著為負,說明一股獨大極易形成大股東與高管之間的利益內部協同,進而損害中小股東利益,使公司成長性變差,與假設3一致。前十大股東持股比例系數顯著為正,與假設4一致。大股東之間的相互監督、制衡降低了對中小股東的侵害。大股東凈增持模型中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而前十大股東的持股比例與成長性出現弱負相關,與假設4不一致,其原因可能是:(1)大股東增持的成長性效應與持股效應相互干擾;(2)模型未區分不同大股東增持,而我們統計的所有樣本中,增持的大股東大多數為第一大股東,第二至第十大股東增持比例極少。因此,對不同大股東持股與成長性的關系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表2 重要股東凈增持的多元回歸分析結果
注:***,**和*分別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顯著;括號內為t值;對模型的異方差和自相關進行了檢驗,模型存在異方差,運用White Heteroskedasticity-Consistent Standard Errors & Covariance估計。
3.2 重要股東凈減持對成長性影響的回歸結果
表3為重要股東凈減持對成長性影響的回歸結果,其中第1列為全部重要股東凈減持下公司成長性回歸模型,第2列為大股東凈減持下公司成長性回歸模型。全部重要股東、大股東凈減持對成長性均有顯著的負面影響,與假設2一致。重要股東減持的“套利期待”降低了公司成長性,也降低對成長性努力的程度,減持導致的股權比例降低也削弱了“持股期待”,強化了壕溝防守。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與成長性都呈負相關關系,且都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與假設3一致。前十大股東持股比例與成長性均呈正相關關系,都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與假設4一致。

表3 重要股東凈減持的多元回歸分析結果
注:***,**和*分別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顯著;括號內為t值;對模型的異方差和自相關進行了檢驗,模型存在異方差,運用White Heteroskedasticity-Consistent Standard Errors & Covariance估計。
4 穩定性檢驗
為了證明研究結論的穩健性,運用Logistic回歸對模型進行測算,當FA為正時,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零。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列出了重要股東凈增持和凈減持的Logistic回歸結果,具體回歸結果見表4。從回歸結果看,兩個模型中的變量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結論與多元回歸分析結果一致。

表4 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表
注:***,**和*分別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顯著。
5 結語
由于對成長性研究的理論難度和增減持股份后成長性觀察的現實困難,大多數國內學者將研究增減持聚焦在市場效應上,然而,由于內地股市有效程度不高,股價效應與成長性效應難以統一,使得該統一研究的問題需分拆成兩個問題研究,筆者選擇了成長性效應進行研究,并結合股權控制效應,發現如下幾個重要關系:
(1)重要股東增持的確有利于成長性的提升,增持會強化利益趨同效應;而減持股票對成長性產生了消極影響,并強化了壕溝防守效應,市場行為修正了持股結構所產生的利益趨同與壕溝防守效應。
(2)高比例持股的第一大股東構成了公司成長的制約因素。這與部分學者如陳小悅等認為的控股股東股權比例越高越好的結論相反。從股權分置改革后的制度環境分析,大股東與中小股東的利益沖突不是消失了,而是形式改變了,在缺乏外部監督和股東之間多元制約的情況下,資本市場的套利動因會驅使控股股東通過各種手段侵害中小股東的市場利益,從而強化壕溝防守效應。當然,大股東增持股份可使壕溝防守效應短期變得不明顯,但并不意味著消失。
(3)股權制衡在公司治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公司的成長離不開有監督能力的其他大股東制衡。且前十大股東持股數量越多,股權制衡作用越明顯,利益趨同效應越顯著。
研究結論啟示:(1)利益趨同與壕溝防守效應會隨增減持行為發生變化,強化利益趨同需抑制減持鼓勵增持;(2)既要充分發揮大股東在有效監督高管、與中小股東利益兼容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又要防止大股東利用其絕對信息優勢,謀取超額收益,侵害中小股東利益的行為;(3)應該建立重要股東減持的法律制度,嚴格規范減持股份的信息披露制度,弱化重要股東信息壟斷,使其在減持中做到公開、透明,以減少重要股東有害于市場健康發展及公司成長的市場行為;(4)雖然有部分學者認為股權集中模式好于股權制衡模式[23]。但以股權分置改革后的實踐來看,股權制衡模式可能會成為更好的治理模式,這已在本研究結論中有所體現。防止一股獨大與鼓勵大股東增持雖是一個相悖的邏輯,但大股東增持會使壕溝防守弱化,這卻是一個有積極意義的結果。
本文作為完稿前能采集到成長性指標的全樣本分析,其時間跨度較大,除市場環境有部分變化外,其它基礎環境無大的變化,且大量數據發生在上證綜指6124下跌以來的熊市階段,如果市場環境發生重大改變,尤其當出現股價與公司成長性背離嚴重時,或是制度上出現重大變遷時,其研究結論或許會不適應,因誘發市場套利的新動因出現,增減持行為會受其影響,因此,需要不斷增加因素并持續跟蹤研究。而且,結合市場有效性、公司成長性、制度合理性、股權結構等方面因素,通過系統設計使市場行為推動股權結構優化,通過制度設計強化利益趨同、防范壕溝防守將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
[1] Grossman S J, Hart O D. One share-one vote and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8, 20:175-202.
[2] Shleifer A, Vishny R W. 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J]. Journal of Finance, 1997, 52(2): 737-783.
[3]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J]. Journal of Finance, 1999, 54(2): 471-517.
[4] Claessens S, Djankov S, Lang L H P. The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in east asian corporation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0, 58(1): 81-112.
[5] Hart O. Firms, contracts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M].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6] 許永斌,鄭金芳.中國民營上市公司家族控制權特征與公司績效實證研究[J].會計研究,2007,(11):50-57.
[7] 吳淑琨. 股權結構與公司績效的U型關系研究——1997~2000年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02,(1):80-87.
[8] 孔愛國,王淑慶.股權結構對公司業績的影響——基于中國上市公司的實證分析[J].復旦學報,2003,(5):26-33.
[9] 徐莉萍,辛宇.股權集中度和股權制衡及其對公司經營績效的影響[J].經濟研究,2006,(1):90-100.
[10] 吳振信,張雪峰,王書平,等.受限股解禁的信號傳遞模型[J].中國管理科學,2008,16(S1):353-357.
[11] 劉銀國,高瑩,白文周.股權結構與公司績效相關性研究[J].管理世界,2010,(9): 177-179.
[12] 徐向藝,張立達.上市公司股權結構與公司價值關系研究——一個分組檢驗的結果[J].中國工業經濟,2008,241(4):102-109.
[13] Jensen M C, Meckling W H. Theory of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Journal of Finacial Economics, 1976, 3(4): 305-360.
[14] Morck R, Shleifer A, Vishny R W. Management ownership and market valu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8, 20(1/2): 293-315.
[15] Mcconnell J J, Servaes H. Additional evidence on equity ownership and corporate valu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0, 27(2): 595-612.
[16] Mcconell J, Servaes H, Lins K. Changes in insider ownership and changes in the market value of the firm[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08,14(2):431-445.
[17] 韓亮亮,李凱,宋力.高管持股與企業價值——基于利益趨同效應與壕溝防守效應的經驗研究[J].南開管理評論,2006,9(4):35-41.
[18] 朱茶芬,陳超.信息優勢、波動風險與大股東的選擇性減持行為[J].浙江大學學報,2009,40(2):164-173.
[19] 陳小悅,徐曉東.股權結構、企業績效與投資者利益保護[J].經濟研究,2001,(11):3-11.
[20] 白重恩,劉俏.中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實證研究[J].經濟研究,2005,(2):81-91.
[21] Mansfield E. Entry, Gibran’s law, innovation and the growth of firms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2,52(2):1023-1030.
[22] 呂長江,金超,陳英.財務杠桿對公司成長性影響的實證研究[J].財經問題研究,2006,(2): 82-87.
[23] 黨文娟,張宗益,吳俊.基于博弈論的均衡股權結構治理模型研究[J].中國管理科學,2008,16(3):164-172.
The Alignment and the Entrenchment Effect Caused by Shareholders’ Market Behavior
WANG Jian-wen, GUO Yan-ling,WANG Li-na, HAN Fei-fei
(School of Management,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000, China)
Important shareholders’ market behavior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from securiti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because it has not only directly impact on stock prices, but also affect the company’s growth, and which is in conflict with the interests of other investor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which have buying or selling behavior as the sample are used in this paper, growth target is then created through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model of Shareholders’ buying or selling behavior and company’s growth is constructed. The empirical research the catalysis of the Alignment and the Entrenchment Effect under the multi-factors' combined influence. The empirical result shows that: important shareholders’ buying behavior will strengthen the alignment effect and their selling behavior will strengthen the entrenchment effect. What’s more, the entrenchment effect is more obvious when the largest shareholders have more shareholding proportion, and the alignment effect is more obvious when the top ten shareholders hold more stock, which reflects the equilibrium relation between equity balance and equity controlling.
important shareholder; alignment effect; entrenchment effect; market behavior; company’s growth
2012-04-18;
2013-04-07
王建文(1964-),男(漢族),湖南益陽人,合肥工業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公司治理、會計與資本市場.
1003-207(2015)03-0076-06
10.16381/j.cnki.issn1003-207x.2015.03.009
F830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