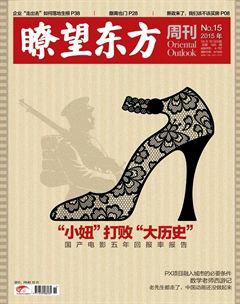歷史片潰敗,“小妞”登場
山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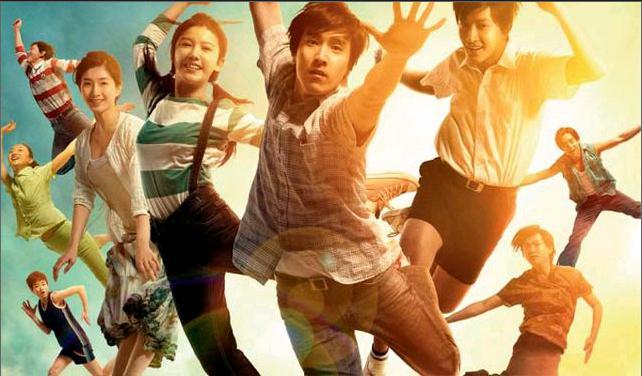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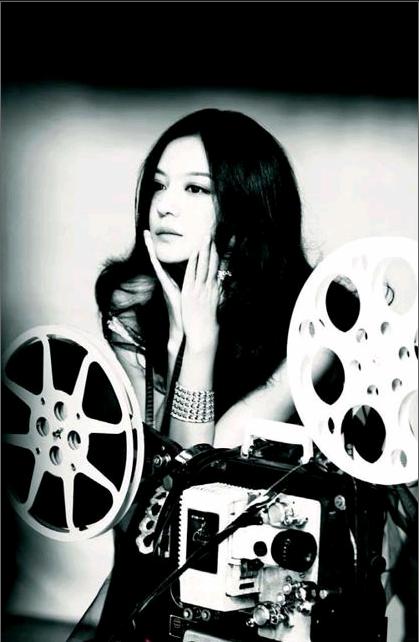
“小妞”打敗“大歷史”
資本的選擇從來都斬釘截鐵。所以,2014年的中國國產片前十名,處處閃現耿浩(電影《心花路放》主角)、陳尋(電影《匆匆那年》主角)們或搞笑溫情或青蔥懷舊的身影。
假如說2010年中國觀眾對國產片的興趣還集中在《唐山大地震》《狄仁杰》《葉問》《趙氏孤兒》這些疊加中國傳統與好萊塢色彩的大片型“巨制”之上,那么經過5年演進,特別是經過2012年、2013年有些戲劇性的博弈,以一連串“負號”作為回報率標簽的“中國式大片”,看起來已經退出了舞臺。
這幾部電影,恰巧串起了上至戰國、下到當代的中國歷史。如果說其中還有一個斷代,那么2012年的《一九四二》無疑可作彌補。而其回報率亦是負值:-20%。
在這一年《非誠勿擾2》159%的回報率面前,以及日后《泰囧》《分手大師》《致青春》動輒高達百分之三四百、乃至990%的回報率面前,無論嚴肅劇還是武俠片,中國的歷史片在投資人面前顏面無存。《智取威虎山》不到90%的回報率,已視作奇跡。
這就是今日中國電影市場的現實圖景。無論我們是否要痛批 “新喜劇片”沒有最低只有更低的底線,那些期望承載歷史民族思索以及導演“大我”夢想的歷史題材影片,正在被資本和觀眾趕出影院。
當然,還有一類“歷史片”可以生存:回報率超過380%的《武林外傳》。
不能說青春片沒有藝術價值。它有精致的畫面和鮮明的人物塑造,其敘事足以讓觀眾在走出影院后仍然久久回味自己的青蔥歲月。而對于青春片內涵膚淺的詰問,恐怕更多體現了不同觀影人群的口味差異。
還有那些都市劇,看一看流光四射的北上廣夜景、新潮奢華的“高大上”生活,怎么會不激起大都市觀眾的共鳴和對職場夢想的向往,更別說再加上這樣的情節——去美國生孩子。
喜劇片和青春片,以及都市片,是5年來國產片壓倒進口片、總票房從100億元上升至近300億元的核心力量。
它們甚至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電影觀眾:早在2013年,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協會的調查數據就顯示,觀眾平均年齡已從2009年的25.7歲下降為21.5歲。
恐怕也不能輕率批評大中學生的觀影取向——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當下主宰票房和回報率的這兩類國產電影,體現了對于觀眾的尊重和更加精準、科學的營銷方式。
正如70后作家、主持人樂嘉談及郭敬明:“我和他說,你的書我沒看過,推薦本看看吧。小四笑著說,你不是我的目標讀者,不用看,對你來講,不值得看。”
盡管可以批評“爛片”以及觀眾的庸俗、膚淺,但大導演們何時能拍一部讓中產階級重歸影院的“有內涵”電影,從而鼓勵資本重新歸隊,進而塑造并向世界介紹我們引以為豪的5000年歷史,展示我們有說服力的價值觀和世界觀?
有些問題需要厘清。第一,歷史片不全是戰爭片;第二,戰爭片不全是血腥片;第三,導演不能過分任性。
南京大屠殺為什么就拍不成《辛德勒的名單》?是不是只能拍成引發價值觀爭議的作品,而不能成為在大多數國民心中匯聚共鳴的國家大歷史?
按照當前全球影業的基本規律,當這類電影的精神內核成為全球觀眾的共識,才能廣泛盈利。
要尊重導演的創作自由,可當每個導演都拍“不是給所有人看”,甚至“不是給今天的人看”的電影時,當下中國電影的標簽,就只能是上世紀90年代的大學校園戀情、新世紀的辦公室戀情和看不出戀愛關系的搞笑戀情。
更令人喟嘆的是,作為一種特殊類型歷史片的武俠片,正在遭遇也許是近100年來最為慘痛的潰敗。
武俠片幾乎是唯一貫穿中國電影歷史的類型電影。中國武俠片長盛不衰,其秘密不僅在于極富沖擊力的動作,還在于包含著更為傳統和深厚的道德內涵。如所謂“俠之大者”。
“第五次武俠熱”之所以能夠沖進世界影業的中心地帶,也不是因為暴力美學,而是《英雄》中的“中國武舞”,是《臥虎藏龍》中“亂心的故事”,以及彌漫在中國古典風景之中的“道”。
無論是李慕白還是殘劍、無名,不僅有傳統武林的英雄本色,亦塑造了與周淮安乃至黃飛鴻、方世玉不同的世界觀。
與之相比,當下的武俠片既無法給人帶來上世紀90年代那樣的新鮮體驗,粗糙、據說還很貴的數字技術也不能與好萊塢的視覺盛宴相抗衡,至于對“俠義”的表達,則越來越簡單和無厘頭。
這樣的武俠片,在國內尚且無法被認可,何談在全球化語境下標識中國形象?倒是美國人的《功夫熊貓》,正在用有史以來最精簡、最“萌”的武打招式成功闡述kungfu的意涵。
作為極為重要、極具影響力的文化產業,電影當仁不讓地成為全球文化傳播的核心載體,也必然應該成為講述“中國故事”的核心載體。但我們能拿得出手的,只有“小妞” “小清新” “小溫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