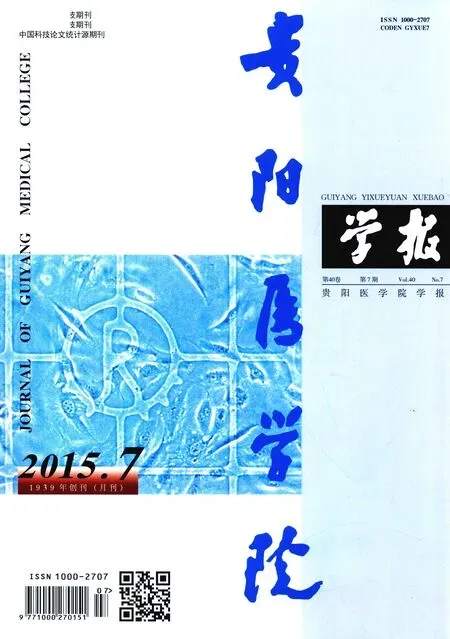簡化烏德勒支應對方式量表中文版在大學生中的試用*
潘 攀,鄒 濤*,湯穩權,王加好
(1.貴州醫科大學 醫學心理學教研室,貴州 貴陽 550004;2.云陽縣人民醫院,重慶 云陽 404500)
應對(Coping)又稱應付,是指個體處于應激環 境或遭受應激事件時,為了解應激事件或應激環境帶來的行為問題,或為了平衡因應激事件或環境帶來的情緒問題,而采取的種種對付辦法和策略的活動[1]。應對作為應激與健康的中介機制,對身心健康的保護起著重要作用。人們會采用許多不同的方式來應對在生產生活中遇到的壓力負擔,而在采取措施來解決困難時人們就有不同的偏好,這就是應對方式[1]。應對方式具有不同的分類和維度(如主動應對和被動應對、積極應對和消極應對、情緒關注應對和問題關注應對等),應對方式與許多心理狀態(如抑郁)呈相關關系[1]。持“特質——應對”觀點者認為應對是個體面對應激情境時其人格特質的體現,所以他們根據應對方式的適應效果,將其劃分為積極與消極兩種類型,即問題關注應對與情緒關注應對。1993 年Schreurs 等在1988 年提出的應對方式概念基礎上編制了Manual Utrecht Coping List(UCL),共47 個題目,已有文獻報告UCL 量表的信效度[2]。后來研究者在量表原有基礎上陸續簡化出不同版本,目前所知最簡化版量表為19 項條目,本研究試對烏德勒支19項應對方式量表(Utrecht Coping List-19,UCL-19)中文版進行信、效度分析,經試用和分析,發現在中國大學生人群中,根據因子探索分析進一步刪減后的14 項的Utrecht 應付方式問卷有更好的信、效度呈現,報告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采用方便取樣,對某大學一、二年級學生進行問卷試用,共發出問卷440 份,回收有效問卷411份,其中女學生占52.3%,男學生占47.7%。刪減條目后的UCL 在某大學一年級學生中進行采樣,發出問卷480 份,回收有效問卷464 份,女學生320人(69%),男學生144 人(31%)。兩組男女年齡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
1.2 工具
1.2.1 UCL 量表 自陳式量表問卷從原始的UCL-47 量表中簡化來,包含3 個分量表:問題關注應對、情緒關注應對和姑息應對。總共19 個條目:問題關注應對5 條,情緒關注應對5 條,姑息關注應對4 條;其余5 個條目不計算進任一維度,實際施測只用到14 個條目。采用4 點計分法,選項按“幾乎沒有,有些時候,經常有,大多數時間有”排列。計算每個分量表的總得分,在某個分量表上得分越高,被試越有可能在面臨壓力負擔時采用這個特定的應對方式。
1.2.2 流調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 評價當前的抑郁癥狀(1 周內),是適用于一般人群抑郁癥發病率普查的工具,常用于不同時間段面調查結果的比較。共20 個條目,需要反向計分的條目有4條。所有條目的計分總和即為量表總分,分數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高。本研究中總量表的a 系數0.88,重測信度0.84。
1.2.3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 采用劉賢臣編制的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共27 個條目,主要由可能引起青少年心理應激的負性生活事件構成。本研究中該量表的總a 系數0.92,重測信度0.72。
1.2.4 認知情緒調節問卷(CERQ-C)[3]此問卷共36 個條目,需要反向計分的條目20 條,分為責難自己、接受、沉思、積極重新關注、重新關注計劃、積極重新評價、理性分析、災難化和責難他人等9 個因子。本研究中該量表的總a 系數0.71,重測信度0.64。
1.2.5 社交性應激反應問卷(RSQ-SSV)[4]此問卷共57 個條目,需要反向計分的條目21 條,分為初級親近控制應對、次級親近控制應對、逃避反應、不隨意的親近反應和不隨意的逃避反應5 個因子,其中每個因子又包含了某幾個方面的內容,如初級親近控制應對有9 個條目,包含情緒表達、情緒調節、問題解決3 個方面的內容。本研究中該量表的總a 系數0.84,重測信度0.70。
1.3 研究方法
采用UCL-19 量表對440 名被試實施預測,回收預測數據后進行內部一致性分析與探索性因子分析,結合測試結果和量表施測過程中大學生對量表內容表述的反饋情況,對量表中含義不明確、不符合中文表達習慣的語句進行修改;因UCL-19 的總量表和分量表Cronbach a 系數較低,經過探索性因子分析后,最終刪除5 道題目,剩下的題目再次組成正式施測UCL-14 量表。采用修改過的UCL-14 對480 名被試進行正式施測,同時向他們發放CES-D,ASLEC、CERQ 和RSQ-SSV。初測1 月后,隨機抽取其中145 人重測UCL-14,實際回收有效問卷132 份。其中女71 人,男61 人;同時對所有被試再次測試CESD、ASLEC、CERQ 和RSQ-SSV。回收有效問卷464 份,對正式施測的量表進行信、效度分析與驗證性因素分析。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20.0,Amos17.0 對數據進行分析,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Pearson 相關分析、驗證性因素分析、回歸分析等。取a=0.05。
2 結果
2.1 預測分析
2.1.1 UCL-19 信度分析 UCL-19 總量表的Cronbach a 系數為0.63,3 分量表a 系數分別為0.46、0.45、0.42;總量表重測信度(r)0.75,3 分量表的重測信度為0.62 ~0.70,均P <0.01。
2.1.2 探索性因素分析 探索性因素分析顯示,KMO 的值為0.76 >0.70,表明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對量表的19 個條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取因素,進行方差最大旋轉,特征值>1 的因素共6 個,與Ziegler 的理論構想相對應,累積方差解釋率為51.41%,各維度選取分子負荷量>0.40 為一個因素,并以因子負荷<0.4 為標準進行條目刪減。此時發現該量表內容效度不嚴謹,需要二次方差旋轉,最后萃取出3 個因素,累積方差解釋率47.75%,因素1 解釋總方差變異量的23.24%,因素2 解釋總方差變異量的14.12%,因素3 解釋總方差變異量的10.39%。
根據因素分析結果比較原量表維度內容:情緒關注應對維度于原來條目分配基礎上刪去1 項條目,增加2 項原量表未歸入任意維度的條目;問題關注應對維度于原有條目分配基礎上刪去1 項條目;在國外被試中負荷大、差別明顯的條目,于本次研究中表現出不同結果,本應在姑息應對維度下,但在本探究中該條目在姑息應對維度的負荷是0.21 <0.4,表明該條目并不能很好的測量中國人的姑息應對傾向,而此項條目在問題關注應對維度下因子負荷>0.4,所以將其歸入到問題關注應對維度。修改后的量表中,問題關注應對包含5 題,情緒關注應對包含6 題,姑息應對包含3 題,總共14 題。
2.1.3 量表評分 見表1。

表1 量表評分情況Tab.1 The scores of UCL-14
2.2 信度
2.2.1 Cronbach's a 系數 刪減修正過的UCL-14總量表的Cronbach a 系數為0.78,各分量表a 系數分別為0.68、0.77、0.63。
2.2.2 重測信度 UCL-14 總量表重測信度(r)0.84,3 分量表的重測信度為0.71 ~0.82,均P <0.01。
2.2.3 條目間平均相關系數 量表總的條目間平均相關系數為0.47,各分量表的條目間平均相關系數為0.45 ~0.50。
2.3 效度
2.3.1 量表內部相關性分析 如表2 所示,3 個分量表與整個量表的相關系數為0.68(問題關注應對)和0.79(姑息應對);各個因子間的相關系數為0.17(問題關注應對~情緒關注應對)和0.49(問題關注應對~姑息應對)。以各因子為單位,條目與其對應的因子分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54 ~0.77。

表2 UCL-14 各分量表的Pearson 相關分析Tab.2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of the UCL-14 subscales
2.3.2 驗證性因素分析 以最大似然法對UCL-19 做驗證性因子分析檢驗擬合情況,這個模型與數據的擬合度并不好:RMSEA=0.09,TLI=0.84,GFI=0.86,AGFI=0.84,IFI=0.85;而對UCL-14模型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顯示:CFI=0.96,RMSEA=0.03,TLI=0.95,GFI=0.97,AGFI=0.95,IFI=0.96。將三因子模型及各條目對因子的負荷系數用標準化路徑用圖1 表示。

圖1 驗證性因子分析標準化路徑圖Fig.1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standardization path graph
2.3.3 應對方式量表效標關聯效度檢驗 分別以CERQ 和RSQ-SSV 作為效標,對3 種應對方式與CERQ 中的積極重新關注、積極重新評價、積極重新計劃、理性分析以及RSQ-SSV 中的問題解決、情緒調節、情緒表達、情緒喚醒和逃避等進行Pearson 相關分析,從表3、4 可見,問題關注應對與積極重新計劃、理性分析及問題解決顯著正相關,與情緒調節、情緒表達顯著負相關;情緒關注應對與問題解決顯著負相關,與情緒調節、情緒表達、情緒喚醒以及積極重新評價顯著正相關;姑息應對與問題解決、情緒調節、情緒表達、積極重新關注和積極重新計劃顯著負相關,與逃避顯著正相關。表明修訂后的UCL-14 具有較好的效標關聯效度。

表3 應對方式與RSQ-SSV 效標效度檢驗Tab.3 The criterion validity test of coping styles and RSQ-SSV
表4 應對方式與CERQ 效標效度檢驗

Tab.4 The criterion validity test of coping styles and CERQ regulation and social stress response mode
2.4 抑郁與應對方式、生活事件、認知情緒調節和社交性應激反應方式相關分析 由表5 可見,抑郁與情緒關注應對、姑息應對顯著正相關,與問題方式應對顯著負相關;與生活事件各因子顯著正相關;與沉思、重新關注計劃、重新評價、災難化及責難他人等顯著正相關,與積極關注、理性分析顯著負相關;與情緒調節、情緒表達、情緒喚醒、回避及逃避應對等正顯著相關,與問題解決顯著負相關。

表5 抑郁與應對方式、生活事件、認知情緒調節和社交性應激反應方式的相關性Tab.5 The correlation of depression and coping style,life events,cognitive emotion
3 討論
國內目前關于應對方式的量表使用較多的是肖計劃多維度量表,而缺乏從人格特質著手測量的量表,UCL 在國外臨床上研究使用時候,對認知情緒調節更有指向性以及針對性,于應對方式不良引起的行為障礙等矯正治療具有參考意義,另外,在參與臨床輔助治療同時能達到直接監控及時反饋患者的情緒調節情況這一目的。
原UCL-19 在施用時實際上只使用了14 個條目,有5 個條目閑置。本研究經過第1 次探索性因子分析結果萃取了6 個因素,但是發現有3 個因素包含條目數太少,共5 個條目,貢獻率均較低,不適宜單獨構成一個因素,說明其內容效度不夠嚴謹,且不易歸類,考慮將這5 個條目刪除。條目刪除后整個因素結構會改變,要進行第2 次因素分析[5]。再一次經方差最大旋轉后構成UCL-14 三因素模型。結果顯示刪減修正后的UCL 具有較高信度,總量表以及分量表的Cronback a 系數與在美國(a=0.56 ~0.76)使用時報告的結果相似[6-7],表明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較好。重測信度0.84 >0.6,說明量表具有良好的穩定性,內部一致性系數和重測信度良好表明量表是一個可靠的測量工具。驗證性因子擬合指數均達到測量學標準。大多數條目在其相應因子上的負荷>0.4,說明量表具有較好的結構效度,在中國UCL-14 的三因子結構是可行的。以CERQ 和RSQ-SSV 作為效標,結果表明UCL-14 具有較好的效標關聯效度。根據心理測量學理論,條目與總分之間的相關系數在0.3~0.8 之間,會產生良好的信度和效度[8]。UCL-14 的條目與其對應因子分之間均呈正相關,相關系數均>0.4,說明量表的條目具有較好的代表性和敏感性[9]。
應對應用于心理治療和咨詢當中,主要是研究如何矯正個體在某種應急條件下的不良應對方式,以增進人的心理健康為宗旨。有研究表明,應激與疾病有關,個體在高應激狀態下,如果缺乏社會支持和良好的應對方式,心理損害的危險度為普通人群的兩倍[10]。UCL-14 與抑郁之間的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個體在遭遇生活事件時,選擇使用情緒關注應對方式的頻率越高,報告的抑郁水平也就越高,若使用問題關注應對或者姑息應對的頻率越低,則報告的抑郁水平越高。不管是在追蹤研究還是跨情景研究都發現情緒關注應對的作用與較低的適應性有關[11]。抑郁情緒較高的個體更多采用情緒關注應對的策略,當遭遇壓力情景或應激事件時,個體首先傾向于調節控制應激引起的情緒反應,恢復情緒平穩,這與以往的研究結果一致[12]。關于生活事件、抑郁與應對方式之間的關系,已有研究結果顯示應對方式在抑郁與生活事件之間呈中介效應[13],生活事件會直接加重抑郁,應對方式可間接加重抑郁。同樣的生活事件,不同的應對方式可能會帶來不同的身心適應結果,應對方式作為生活事件與心理健康的一個重要中介變量,對心理健康的作用不可小視[14-16]。
[1]Berend T,Willem VR,Wilmar B.Schaufelis and Marten DE Haan.The Four-Dimensional Symptom Questionnaire(4DSQ):measuring distress and other mental health problems in a working population[J].WORK&STRESS,2004(3):187-207.
[2]Sanderman R,Ormel J.De Utrechtse Coping Lijst(UCL):validiteit en betrouwbaarheid[The Utrecht Coping List(UCL):validity and reliability][J].Gedrag Gezondh,1992(20):32–70.
[3]朱熊兆.認知情緒調節問卷中文版的信效度研究[J].中國臨床心理雜志,2007(2):121-124.
[4]肖晶.社交性應激反應問卷中文版在大學生中應用的信效度初步評價[J].中國心理衛生雜志,2008(10):775-780.
[5]吳明隆.SPSS 統計應用實務——問卷分析與應用統計[M].科學出版社,2003:75-76.
[6]Anja C.Huizink,Coping in Normal Pregnancy[J].Ann Behav Med,2002(2):132-140.
[7]J.Caroline D.Biopsychosocial Mediators and Moderators of Stress-Health Relationships in Patients With Recently Diagnosed Rheumatoid Arthritis[J].Arthritis care&Research,2001(45):307-316.
[8]賈茹,吳任剛.親密關系沖突應對方式量表的修訂及信效度檢驗[J].精神醫學雜志,2012(4):241-244.
[9]Marc,Van,Essen.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Corporate Governance:The Effects of Labor Institutions on Blockholder Effectiveness in 23 European Countries[J].Organization Science,2013(2):530-551.
[10]Willem VR.Coping and sickness absence[J].Int Arch Occup Environ Health,2008(81):461-472.
[11]姚娜.應對方式理論的研究發展綜述[J].西北大學學報.2011(9):9.
[12]Sesar,Kimi N,Bari M.Multi-type childhood abuse,strategies of coping,and psychological adaptions in young adults[J].Croation Medical Journal,2010(5):406-416.
[13]Floor,Aarts.Coping Style as a Mediator between Attachment and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in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Morbid Obesity[J].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i in Med,2014(1):75-91.
[14]王極盛、丁新華.中學生抑郁與其相關影響因素的綜合研究[J]中國學校衛生,2003(4):336-338.
[15]Mario M.Interpersonal psychotherapy for postpartum depression:a systematic review[J].Arch Womens Ment Health,2014(17):257-268.
[16]Hannah,Turner.A Psychometric Evaluation of an English Version of the Utrecht Coping List[J].European Eating Disorders Review,2012(4):339-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