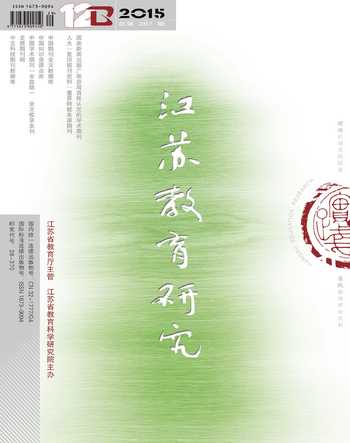教育的鄉(xiāng)愁:清代江蘇書院里的自主研讀

在知識大爆炸的時代,任何教育都不可能將所有知識傳授給學(xué)習(xí)者,教育的主要任務(wù)必然指向培養(yǎng)學(xué)生自主學(xué)習(xí)的能力。《基礎(chǔ)教育課程改革綱要》在談及新一輪課改目標(biāo)時指出:“改變過于注重知識傳授的傾向,強調(diào)形成積極主動的學(xué)習(xí)態(tài)度,使獲得基礎(chǔ)知識與基本技能的過程,同時成為學(xué)會學(xué)習(xí)和形成正確價值觀的過程。”教育實踐中,我們苦苦尋覓著涵養(yǎng)自主精神、提升自主能力的路徑,然而追求應(yīng)試效益的班級授課制、抱緊了不肯放手的教學(xué)習(xí)慣、喂久了不會覓食的學(xué)習(xí)方式,成了禁錮學(xué)子自主發(fā)展的“緊箍咒”。
“書院之真正的精神惟自修與研究”,胡適曾經(jīng)這樣提煉過書院教育的智慧。現(xiàn)代教育面臨的種種煩惱,在傳統(tǒng)教育那里也許早就得到化解,然而專注于變革與重建的我們,有多久忘了回顧“鄉(xiāng)土”教育智慧的默默啟示?
一、傳承與改良:清代江蘇書院中三個自主研讀范例
胡適指出:“書院之真正的精神惟自修與研究,書院里的學(xué)生,無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態(tài)度,雖舊有山長,不過學(xué)術(shù)上之顧問,至于研究發(fā)明,仍視平日自修的程度如何。”[1]歷代書院的“自修”,有以下共識——其一,以“學(xué)規(guī)”“會約”作為嚴(yán)格的監(jiān)督制度。例如朱熹擬定《白鹿洞書院揭示》,詳細規(guī)定了“為學(xué)之序”“修身之要”“處事之要”“接物之要”。其二,以“會講”“問難”的方式,張揚學(xué)術(shù)自由的思想,培養(yǎng)學(xué)子的批判精神。書院邀請持不同學(xué)術(shù)見解的大儒同時講課,互相辯駁,如朱熹張栻的岳麓會講,“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不能合”“學(xué)徒千余,輿馬之眾,至飲池水立竭”[2],可見學(xué)術(shù)爭鳴之激烈。其三,以“學(xué)友切磋”“以友輔仁”等學(xué)習(xí)活動支持自主研習(xí)走向持久深入,書院里生徒、師長長期聚居于僻靜山鄉(xiāng),便于相互砥礪志向、切磋學(xué)問,同歸于善。
江蘇書院因為能革故鼎新,弘揚時代精神而領(lǐng)風(fēng)氣之先。據(jù)《古代書院史資料》記載,清代江蘇書院興復(fù)、新建總計達253所,隨著贛籍、皖籍學(xué)儒大量入蘇主掌或執(zhí)教書院,江蘇再次成為全國學(xué)術(shù)與教育中心,“自修為主、指導(dǎo)為輔”的治學(xué)方式,也發(fā)生了衍變與創(chuàng)新,其中“日記學(xué)習(xí)”“月課促讀”“課藝點評”等關(guān)懷全體、尊重個性的教師指導(dǎo)下的自修方式各有所長,值得細細品味。
1.關(guān)注自主研讀的過程與心得:蘇州紫陽書院的日記學(xué)習(xí)法
紫陽書院始建于1713年,是晚清四大書院之一,沈德潛、錢大昕、段玉裁等飽學(xué)之士齊聚紫陽書院,紫陽書院一時成為乾嘉學(xué)派的大本營。
“日記學(xué)習(xí)法”是紫陽學(xué)子最重要的研讀方式。書院要求學(xué)生每天“記日行何事,接何人,存何念,讀何書,吐何論……”以便“查實錄,定賞罰,登記考核成績”。又要求分經(jīng)、史、古今文、雜著四類記讀書日記。例如“讀經(jīng)書類日記”,記“諸生每日看某經(jīng)某書,自某處起,至某處止,必潛思玩索,身體力行。凡有所得,即記于是日課程之內(nèi)。”每個學(xué)生每天要記兩種日記:行事日記和讀書日記。行事日記主要記錄每天的學(xué)業(yè)進程,強調(diào)學(xué)習(xí)的自律、自治;讀書日記主要記錄讀書的心得與疑惑,強調(diào)學(xué)習(xí)的自省、自悟。
“日記學(xué)習(xí)”意義有三:其一,學(xué)子通過查看日記,可以對自己的進步與不足、疑慮與收獲有過程性的認(rèn)識,并在相對寬松的環(huán)境中熟讀精思、切記體察。其二,教師通過批閱學(xué)習(xí)日記,深入了解學(xué)子每天學(xué)習(xí)的進程、功夫、收效及問題,并據(jù)此作出詳盡而有針對性的批注。其三,山長或講席每隔五天與學(xué)子作當(dāng)面交流,針對他們性情、學(xué)識的差異來傳授法門和路徑。龍門書院山長劉熙載每五日批閱、詢問,就學(xué)習(xí)日記“與學(xué)生辨析輒至夜分,雖大寒暑,衣冠沖整,無惰容,歷十余年如一日。”值得一提的是,師生當(dāng)面交流讀書日記時,均需穿戴嚴(yán)整,神態(tài)恭肅,充滿了儀式化的肅穆氣氛。書院還把讀書日記中的心得加以整理,匯編成冊,刊印成書,如蘇州圖書館藏《學(xué)古堂日記》兩冊,所刊內(nèi)容便是學(xué)生讀《爾雅》的心得日記。
在今天的校園里,教師苦心孤詣于研究教材、教法,少有精力體察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感受、學(xué)習(xí)心得;學(xué)生蒙昧靈性地默誦“秘訣”,苦練“真題”,極少反省困惑與收獲。“日記學(xué)習(xí)”提醒教與學(xué)都應(yīng)該越過課堂與課本的邊界,確保提供更充足的時間與空間,讓學(xué)生細細思悟,確證自己每天的學(xué)習(xí)成果、優(yōu)化自己的學(xué)習(xí)策略,比講授、訓(xùn)練也許更能幫助學(xué)生獲得學(xué)習(xí)效能感和自我成就感。
2.以考課引領(lǐng)與調(diào)控自主研讀:江陰南菁書院的月課制度
當(dāng)考試成了現(xiàn)代教育的常態(tài),應(yīng)試取向自然就成了教與學(xué)的常態(tài):教師教考,學(xué)生學(xué)考;凡考的必教必學(xué),不考的少教少學(xué)甚至不教不學(xué)。這是令整個社會頭疼的現(xiàn)代教育病。
古時的書院也有考試,但非常講究考課的頻率、方式與命題。“考課”是清代書院通用的方法,不過南菁書院的考課更關(guān)注如何為治學(xué)、修身服務(wù),對自主研讀起著引領(lǐng)與調(diào)控的積極作用。從考課頻率來看,南菁書院主要采用“月課制”,所謂“日有讀書行事之記,月有通經(jīng)博古之課”“每歲一甄別,而進退之”[3]。值得關(guān)注的是,遞交的考課文章先是每月兩篇,后變?yōu)槊?0天一篇,然而山長發(fā)現(xiàn),一個月要求學(xué)生準(zhǔn)備三篇文章,就減少了自主閱讀與記錄日記的時間,最后又減少到每月兩篇。再看考查形式,據(jù)學(xué)生錢崇威的回憶:“課卷(即作文)每月一次,由山長命題,三天內(nèi)完卷。每個作文題都有指導(dǎo),促使學(xué)生到藏書樓鉆研參考書籍,暢思路、助寫作。”為激勵學(xué)生潛心學(xué)問,書院還選取學(xué)生月課優(yōu)秀之作刊印成文集,如《南菁講舍文集》《南菁札記》《南菁文鈔》等等,以此宣揚勤奮自勵、持志居敬的自學(xué)功夫。
書院以月課試題引領(lǐng)學(xué)術(shù)方向,調(diào)控學(xué)習(xí)策略。例如錢大昕“課經(jīng)”之題強調(diào)讀經(jīng)應(yīng)當(dāng)博觀約取,讀有自悟:“太學(xué)石經(jīng),昉于漢代,五經(jīng)、六經(jīng)、七經(jīng),一字三字,說者各殊,能折其中歟?”“課史”之題引導(dǎo)讀史要深入探究,獨立批判:“史家之有述贊,昉于龍門,而班氏因之,小司馬譏述贊為未安,果何所見歟?”南菁書院的興盛期正是民族蒙受屈辱的時期,書院逐漸引導(dǎo)學(xué)子走出逼仄書齋,思考現(xiàn)實問題,尋求救國良方。因此月課大量出現(xiàn)“問抵制洋鹽進口之法若何”“各國產(chǎn)煤鐵考略”等切中時弊的論題。光緒27年編刊的《南菁文鈔》中的選文大多是《外國理財不主節(jié)流而主暢流論》《問五口通商以來時局凡幾變》一類指陳世務(wù)、辭氣激宕的文章。
3.強調(diào)尊重差異的個別交流:南京鐘山書院的課藝點評
學(xué)子對考課論題的書面解答,稱作課藝。課藝作品彰顯了優(yōu)秀學(xué)子自主研修的成果,成為書院學(xué)術(shù)水準(zhǔn)的重要參考。清代書院非常重視課藝集的出版,有《南菁講舍文集》《南菁文鈔》《詁經(jīng)精舍課藝》《格致書院課藝》等傳世。課藝作品由山長、講席精心批注點評,以此作為啟發(fā)教學(xué)、個別交流的重要方式。
南京鐘山書院的課藝點評堪稱典范。例如潘宗鼎《君子固窮》所得評點為:“寓牢騷于溫厚,托情抱于芳菲。短調(diào)長歌,低徊欲絕。然明珠必耀,幽蕙自馨,保此清寒,勿辜吾意。……”楊彥昌《君子固窮》所得點評為:“無一筆不曲,無一語不深,無一字不雅。氣味馚馥,深思幽微,直是散體文妙境。此文不特文字好,并見志趣亦好。真能固窮之士也,愿守此終身,不負厚望。切屬!切屬!”
兩則課藝的評點具有以下共性:一是以帶有濃重文學(xué)色彩、充滿深切關(guān)愛的筆觸,展開真誠的對話;二是重在褒揚課藝習(xí)作的文質(zhì)兼美,熱情地激勵應(yīng)堅持的方向;三是強烈體現(xiàn)了道德教化的滲透,反復(fù)叮嚀,砥礪氣節(jié)。同時,兩則點評又尊重差異,體現(xiàn)了因材施教的原則:潘生寫的是韻文,所以教師點評以四六文的駢偶筆法回應(yīng),措辭典雅;楊生寫的是散文,因此點評駢散結(jié)合,用語平易親切。通過點評文字,我們可以推測潘生有懷才不遇之悲惻,所以師長以“明珠必耀,幽蕙自馨”寬慰,擔(dān)憂其在逆境中難以堅守初心,所以叮嚀“保此清寒,勿辜吾意”;相比之下,楊君志趣高遠,意志堅定,因此師長點評重在告誡要“終身踐履”,并以“不負厚望”表達期許。
二、垂范與影響:書院導(dǎo)師在自主研讀中的積極影響
導(dǎo)師是書院的靈魂,課程的品質(zhì)、品位,教育的氣度、高度,都由他們的人格與學(xué)養(yǎng)決定。錢穆曾告誡新亞書院的學(xué)生:“課程學(xué)分是死的,分裂的,師長的人格是活的,完整的。你應(yīng)該轉(zhuǎn)移自己目光,不要僅注意一門門的課程,應(yīng)該先注意一個個的師長。”[4]可見師長的影響力之巨。
1.垂范是最經(jīng)典的教育
歷代山長往往終身在書院傳道授業(yè),以一輩子的身體力行來身教垂范。姚鼐一生從事書院教育40年,主掌鐘山書院26年,他的教育思想是與自身的治學(xué)經(jīng)歷是黏連在一起的,“義理、考據(jù)、辭章”的融合,既是他治學(xué)為文的原則,也是他的教育宗旨。錢大昕任紫陽書院山長達16年,最終卒于書院,以畢生的治學(xué)修為,既造就了乾嘉學(xué)派的繁盛,也為書院學(xué)子立一精神標(biāo)桿。
如果教師整天考慮的是職位升遷、待遇優(yōu)劣,焦慮于考核評價、人際關(guān)系,奔波于名人課堂、報告演講,他可能就沒有興趣、精力和學(xué)生“廝混”在一起,不可能贏得學(xué)生的仰慕與追隨,也就永遠不可能出現(xiàn)神圣莊嚴(yán)的教育“道場”。
2.在日常生活中影響感召學(xué)生
古代書院是師生共同的生活場所、精神家園,歷代名儒于鄉(xiāng)野創(chuàng)辦書院,薪火相傳,身死無憾;學(xué)生因仰慕大儒的人格、學(xué)識而終身追隨。“道在深山,學(xué)在民間”,山野間充滿著宗教氛圍與精神氣質(zhì)。書院里日常的生活,就是修身治學(xué),師生如父子,書院如家庭,他們朝夕相處,同學(xué)習(xí)、同游樂、同生活,可謂其樂融融。唐文治回憶南菁書院的生活:“春誦夏弦,讀書露坐,討論經(jīng)史疑義,滔滔辯論。得一新知,相與歡笑為樂。”吳稚暉在《寒崖詩集序》中回憶入南菁第一天謁見山長黃以周,見其座上銘刻“實事求是,莫作調(diào)人”八字,從此成了吳稚暉一生的“信仰”。導(dǎo)師于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中彰顯著學(xué)問道德。
治學(xué)精神的培養(yǎng)、學(xué)習(xí)方式的優(yōu)化,并不是通過課堂里的講授獲得的,只能是在受到教師的思維方式、治學(xué)精神的感染、影響,并在長期的模仿與踐履中習(xí)得、悟得。應(yīng)試重負下的學(xué)習(xí),其積極性容易挫傷,校園應(yīng)當(dāng)像書院一樣,讓學(xué)生在集體生活中充滿著展示與分享的快樂,燃燒著互相支持、相互砥礪的溫度。
江蘇書院對于自主研讀傳統(tǒng)的承襲與改良,是“鄉(xiāng)土”教育的豐厚遺產(chǎn)。傳統(tǒng)的力量,就在于她多姿多彩而不定于一尊,值得我們用心聆聽、體悟與回應(yīng)。今天,我們中的很多人言教育必稱美歐,在東西方教育文化的搏弈中充滿著自卑與拙劣,我們忘了鄉(xiāng)土教育的高貴血脈與高遠智慧,在求變與重建中找不到安頓身心的根基。不妨站在現(xiàn)代教育的高度,審視“鄉(xiāng)土”教育的智慧,正因為有了距離,有了新的視野,必然會有新的體悟與回應(yīng)。
參考文獻:
[1]胡適.胡適教育論著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215.
[2]陳谷嘉、鄧洪波.中國書院史資料[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2953.
[3]鄧洪波.中國書院史[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4.12.
[4]錢穆.新亞遺鐸[M].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4.2.
(陸鋒磊,江蘇省天一中學(xué),214101)
責(zé)任編輯:宣麗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