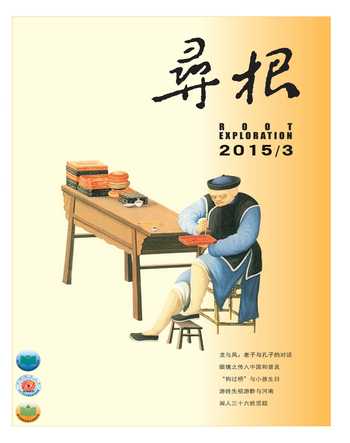燈曲罐的文化內涵及傳承流變
李福蔚
燈曲罐的掛件型制
筆者十多年前在民俗采風中對西府婚俗中的燈曲罐進行過采編,原文錄于2000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的《西府民俗》:燈曲罐是過去婚嫁時,娘家的陪嫁品。婚俗中,有一套六件新房掛飾品,“燈曲罐一對、信插、門簾帽、甩子(拂塵)、筆插各一件”,均是由女方必備之物。
燈曲罐的型制多為“前罐式”和“后罐式”(即罐體在后)兩種,材質多為布藝繡制品。我還見過木制的,只是未收藏得到。
“前罐式”一般通高21厘米,罐體在前,其型多為“缶”型或瓶型,頸小肚大。罐面多為刺繡,題材多為魚龍變化、石榴、蓮花等果木花卉。罐口上部飾牡丹,寓丹桂生枝等。
“后罐式”一對一般通高21厘米,其一為男童,頭戴秀才帽,雙手各舉一束海棠花,盤腿坐于金瓜之上,金瓜處有一半圓形罐體;其一為女童,頭扎雙髻,雙手亦高舉一束海棠花,坐于盛開的蓮花之上,蓮花處也是一個半圓形罐體,前者是“金瓜貴子”圖案,后者是“蓮生貴子”圖案,手中高舉海棠花,是取“滿堂富貴”之意。新婚掛在堂上,里面插著石榴花,寓“多福、多壽、多孫”之意。
我是親眼見過木制燈曲罐的,可惜未收藏。器物見方不足一尺,細木薄板構制,工藝精巧。如一個方斗提籃,罐體在前,全漆紅色,有金粉線畫,是插燈曲的。
燈曲罐的文化內涵
從社會存在角度看,民俗文化總是社會選擇的結果,社會歷史對民俗文化的選擇,是通過一定的物質形態的文化實現的。民俗事象以內涵的文化意識和外表的生活方式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傳承。民眾生活中的無數民俗事象,展示了生活無限豐富的風姿。但它不是單一的生活標記,而是具有明顯的文化意識和生活特征的二重性,即既有有形的生活方式,更有內在的文化意義,兩者不可偏廢。事實上內在的文化意義外延物化,就是生活方式。作為婚俗中洞房掛件燈曲罐這一民俗文化,亦有文化意識和生活特征的二重性。按此理論,我們研究燈曲罐為什么成為婚嫁必備物,姑娘為什么去精心制作它,從中看出燈曲罐的文化內涵。
一、它是祀火風習的圣物
生存意識避害趨利是民間文化的價值基礎,也是民俗文化的基因。祈祥求吉避害的民俗心理基因,長期虔誠地信奉著各種靈物,恪守著代代傳承的民俗禁忌,背后蘊含著人們的社會功利價值觀念。
在上古時代,受人崇拜之物或自然現象,往往被人格化,成為神靈。如傳說鉆木取火、燧石取火的發明者燧人氏,保存傳送管理火的炎帝、祝融、回祿等大神以及管理火種的閼伯。把灶神當作火神看待,源于當時人們居住處“火塘”這一最原始的灶的用火燒熟食物的自然崇拜。而保存火種最初是用陶罐,名曰“火種罐”。后來在傳承中流變為寓意“傳宗接代”的“子孫罐”和插引火物的“燈曲罐”,但其文化根基是“火種罐”。它象征的是火的發明者和管理者成為“圣物”而顯得神圣和崇高。這種火神崇拜信仰,在“頭頂三尺有神明”的原始思維定式下,人們對火十分崇尚而敬重,而產生敬畏感,唯恐恭敬不足而犯忌。處在“人在做,天在看,神在察”之中,會促使你的行為處在規范之中。西府是炎帝故里,對炎帝作為火神崇敬有加。因此,燈曲罐便成為人們“崇火”“敬火”“祀火”的“圣物”而代代傳承。
人類崇拜火之所以超過了崇拜其他自然物,不僅是因為在直觀直感中火的自然威力具有極大的神秘性,更重要的是火的利用關聯著人類原始文化的誕生和人間物質文明的劃時代進程。
二、它是婦女使命的證物
考究燈曲罐的來由,一說是老祖先“崇火”的痕跡。傳說在那原始先民剛剛懂得了用火的遠古年代,就已經有了這種陪嫁習俗,最初是陪送火種,而那時的“火種”的的確確是用罐盛放的。后來隨著社會進步,人們已經掌握了取火技術,并且能控制火的使用,便出現了“引火”的“燈曲”。人們制作了用薄薄的小木片子,上邊沾著引火的硫黃,此物名曰“燈曲”。燈曲罐是用來盛放“燈曲”的,陪此物寓意:閨女嫁到你家,香火(子孫)不斷,事事紅火吉祥。既然是盛火的,為什么不叫“火種罐”而稱“燈曲(取)罐”呢?可能是受佛教的影響,佛教稱佛法能破除黑暗,佛門常以燈為喻,還有破除黑暗和香火不斷之意,燈曲罐之名就順理成章了。另一說是根據民謠“抓髻撥味味(抖動之意),婆家不引來”。這是說我都梳上抓髻了,婆家還不來娶我。燈曲罐成了女人等待男人來娶的象征物。
在上古社會中,人類為了生存下去,除了想方設法維持自己的生命之外,繁衍后代是一件維系種族生命很重要的事。又由于對自身生育能力的神秘感,便產生了對生殖器官的崇拜,這同樣是萬物有靈的自然崇拜的一部分。在人們原始思維中,把“男根”和“女陰”比作“石柱”和“罐體”,認為懷孕是石與罐接觸碰撞的結果,所以生殖崇拜的形式一般是把火或石作為崇拜對象,希望生育的婦女有如火的生殖力一樣,增加懷孕機會,這是求子習俗最原始的形式。在原始社會中的生殖崇拜,很重視男女間的婚媾,把性關系的生育看作是十分神圣的。后來隨著婚姻制度的不斷科學和文明,產生了“禮始于謹夫婦”的認識,作為古代典章制度和行為規范的“禮”,談性總是運用“隱語、暗喻”,從而出現對男女關系問的事,持既神圣又神秘的態度。作為傳送火種的陪嫁物燈曲罐便有了“隱喻”之意,充當了造物的象征、生活的使者、達情的媒介。賦予了女性生兒育女、傳宗接代、種族繁衍的歷史使命而成為證物,成為婦女使命標志。
三、它是表達愛情的信物
“求善、求美、求真”構成了人們生活的三大樣式,民間求美的藝術創造活動是制作者的主體,完全依靠感受,不受他人意志和經濟的影響而創作的成果,是他所屬的群體的審美情趣和審美要求,所以他的作品是最純正、最質樸的。最美的燈曲罐往往是“觀象制器”,追求“言意互動”的效果。“言象”是直接用語言傳情,而“意象”則是“心心相印”不易覺察的復雜的綜合系統,是制作者的文化心態問題,是心靈作用的凝結。在造物制器中以最大限度地顯示自己的心靈手巧,在約定俗成的器物上,費盡心思追求美的設計,表達自己的意愿,而不斷地進行文化選擇,使其審美功能與工藝品的實用功能相輔相成,給人以“悅目”和“怡神”的審美滿足。美其目而悅其心,看了心里舒服,得到一種美的享受。這就是姑娘精心制作燈曲罐的原因所在。燈曲罐亦成為一種追求愛情,表達心愿的信物。
燈曲罐的傳承流變
燈曲罐是民間生活文化中的物質文化遺存和精神文化的物化遺存,它是反映民間風俗、習慣等民俗現象的遺物。它作為民俗文物是民眾幾千年來共同創造、享用和傳承的。但在傳承過程中,其文化主題和文化內涵在不斷流變,而在影響民俗文化流變的諸多因素中,起主導作用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我們在對燈曲罐的研究中,發現燈曲罐的傳承流變與社會生產發展水平的走向是一致的,或者說是同步的。實際上它直接受生產力水平的制約和影響。有什么樣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便有什么樣的民俗文化。
從“火種罐”到“子孫罐”的流變,反應的是由火崇拜到生殖崇拜的流變。燈曲罐是保存火種的、是女性承擔的。從鉆木取火到掌握燧石取火技術后,火種罐的這個罐體從保存火種的功能的火崇拜附會進“薪火相傳,香煙不斷,傳宗接代,生生不息的生殖崇拜,才成為女子出嫁配送物,寓意由‘火種罐變成‘子孫罐,材質從陶罐演變為布藝繡制品,插引火燈曲的燈曲罐”。由于燈曲罐含有“傳宗接代,生生不息”的婚育主題,在思維上便表現出“觀物取象,觀象制器,以器載物,透物見人”的心緒情結。滿足自身需求是人的本能,這種本能決定著造物的實用與審美。把生命維系和造物設計溝通,燈曲罐的制作者便千方百計、精心制作,要使燈曲罐成為生活的使者,達情傳意的媒介,生命的象征物以及制作者的勞動心理能透過此物傳達給使用者。通過這種心理交換,使用者感受到制作者的匠心、技巧、熱情、意向。從中看出燈曲罐的造物活動已超越了物的制作,升華為傳情達意的精神需求的一種象征活動。在這種心理驅使下,出嫁女做嫁妝中,對燈曲罐制作特別看重,材質的選擇、圖案的設計、色彩的喜好是費盡心機的,像罐型為童子坐蓮花,寓意“連生貴子”,布堆刺繡彩繪、金絲走邊等以顯其能。
大千世界永恒的只是運動著的物質。任何一個具體的事物,有興起就有衰亡。正如萬事萬物有生必有死,有存在必有毀滅的道理一樣。古老的婚俗用品燈曲罐的傳承發展必然也擺脫不了這一規律。事實上,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及科技的進步,民間的生活文化也處于急驟地變異之中。近代以來,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深入,“三從四德”封建意識的破除,婦女社會地位的確立,男女平等、婦女當家做主新風尚的推行,婦女不再是“生育機器”。同時,由于科學的發展,時代的進步,火柴、打火機的應用,使火鐮、火石、火腰、燈曲等取火工具漸漸退出人們的生活領域,插燈曲的燈曲罐這個陪嫁品的實用價值隨之減退,只有“保存火種,傳宗接代,傳續香火”的寓意留存于人們民俗心理之中。另外,人們在改善生存環境,提高生活質量的激烈競爭浪潮中,一是社會分工越來越細,人們生活節奏加快,成衣成品任你挑選,女孩子無須幼習女紅、扎花刺繡、自制信物,實際上時勢也使你無暇坐下來去精心制作燈曲罐。二是人們消費理念的寬泛,如洞房講究的六大件;手機普及,網絡媒體通信便捷取代書信往來,使信插退出;道路硬化、環境綠化,無須打土拂塵,甩子退出;打火機、電燈的普及,無須火柴燈曲引火,燈曲罐退出;現代書寫工具的使用,無須墨、硯,筆插退出。凡此種種,盡可說明燈曲罐這種文化現象在當代的流變趨勢。雖然如此,我認為在人類繁衍這個問題上,不論計劃生育也罷,還是傳宗接代也罷,這件事是亙古的、生生不息的。因此,象征生育的燈曲罐,作為洞房飾件,美化生活的觀賞品,仍作為婚俗必備物會再延續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