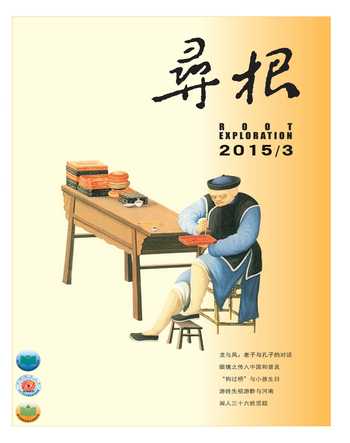從麻紙譜單到歷史圖籍的達(dá)斡爾族家譜(一)
王鶴鳴
達(dá)斡爾族的家譜文化,見諸文字記載的,盡管只有四百年歷史,卻經(jīng)歷了用滿文書寫麻紙譜單提升到以漢文編撰歷史圖籍的發(fā)展過程。
一
達(dá)斡爾族是我國(guó)北方歷史悠久、文明古老、勤勞勇敢的民族。
達(dá)斡爾族世居黑龍江中游北岸奧列斯莫日登廣大地區(qū)。這里依山傍水,山清水秀,土地肥沃,水草豐美,物產(chǎn)豐富。達(dá)斡爾族祖先具有體格強(qiáng)壯,性格忠勇,愛勞動(dòng),好團(tuán)結(jié),重禮貌,善于騎射,又好游藝運(yùn)動(dòng)等性情。達(dá)斡爾族以男性血緣團(tuán)體所居之山地河流之名稱而得姓氏,以氏族為群體,以打獵游牧耕種為業(yè),過著自給自足的定居生活。
關(guān)于達(dá)斡爾族的起源,目前存在著契丹起源說和蒙古起源說兩種不同的學(xué)術(shù)觀點(diǎn)。
達(dá)斡爾族以血緣氏族組織——“畢爾基”“哈拉”“莫昆”“莫音”“貝功”為基本社會(huì)結(jié)構(gòu)。
1 “畢爾基”是部落聯(lián)盟的統(tǒng)稱,在達(dá)斡爾族的歷史上確曾存在過,它是達(dá)斡爾族社會(huì)組織中最高一層的社會(huì)組織的名稱。
2 “哈拉”是部落的統(tǒng)稱,是由同一個(gè)父系祖先的后代組成的血緣集團(tuán),達(dá)斡爾族把古老的父系氏族稱為“哈拉”,是達(dá)斡爾族社會(huì)中重要的社會(huì)組織。
“哈拉”有其血緣集團(tuán)性職能:認(rèn)為土地是人類賴以生存的根本,重視和保持“哈拉”居住地域的聚居性和穩(wěn)定性,像珍惜生命一樣保護(hù)耕地、草場(chǎng)、山林、江河和周邊生態(tài)環(huán)境;恪守“哈拉”外婚制,不準(zhǔn)同一“哈拉”之間通婚;實(shí)行“哈拉”內(nèi)部民主制,凡事關(guān)“哈拉”整體利害的重大事宜,均在“哈拉”會(huì)議或“哈拉”首領(lǐng)、長(zhǎng)老會(huì)議上決策議定,一經(jīng)決定堅(jiān)決照辦:每隔若干年召開一次續(xù)修“哈拉”族譜會(huì)議,全“哈拉”各“莫音”都派代表參加;組織全“哈拉”大規(guī)模聯(lián)合圍山狩獵活動(dòng)。“哈拉”在清代還兼有基層行政和軍事機(jī)構(gòu)的職能,清廷在設(shè)置佐、旗的時(shí)候,沒有把“哈拉”等組織關(guān)系打亂,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達(dá)斡爾族原有的社會(huì)組織形式。
3 “莫昆”是氏族的統(tǒng)稱,是從“哈拉”分化出來的血緣關(guān)系更近的共同體,比“哈拉”具有更強(qiáng)的約束力,是達(dá)斡爾族社會(huì)組織中最基本的社會(huì)組織。
“莫昆”的職能主要是:嚴(yán)禁“莫昆”內(nèi)部通婚;管理“莫昆”公共財(cái)產(chǎn);具有不成文的“莫昆”習(xí)慣法;舉行“莫昆”祭祀和宗教活動(dòng);民主推舉德高望重、為人公正、有膽有識(shí)、能力強(qiáng)的人為氏族長(zhǎng)——“莫昆達(dá)”;有“莫昆”共同的墓地。
4 “莫音”是支族的統(tǒng)稱,是比“莫昆”血緣關(guān)系更為親近的共同體,它是隨著人口的增加由“莫昆”派生出來的組織。“莫音”沒有自己的族譜,其族譜包括在“莫昆”族譜之內(nèi)。“莫昆”有“莫昆達(dá)”(氏族長(zhǎng)),“莫音”沒有“莫音達(dá)”(支族長(zhǎng)),也無作為血緣團(tuán)體的職能范圍。
5 “貝功”是家族家庭的統(tǒng)稱,是達(dá)斡爾族社會(huì)組織的細(xì)胞和基石。清末以前,達(dá)斡爾族父系大家庭較為普遍,三世同堂和四世同堂的家庭比比皆是,有的大家庭多達(dá)四五十人。
“達(dá)斡爾”是達(dá)斡爾族的自我稱謂,早在6世紀(jì)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歷史上還曾有“達(dá)胡爾”“打虎兒”“達(dá)呼爾”“達(dá)古爾”“達(dá)糊里”等不同的稱呼,新中國(guó)成立后根據(jù)本民族的意愿統(tǒng)一定名為“達(dá)斡爾”。主要聚居在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莫力達(dá)瓦達(dá)斡爾族自治旗、鄂溫克族自治旗和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梅里斯達(dá)斡爾族區(qū),少數(shù)居住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塔城市。
達(dá)斡爾族人口較少。據(jù)史料記載:光緒三年(1877年)黑龍江將軍所轄地區(qū)達(dá)斡爾人共有2.9萬。1947年,全國(guó)達(dá)斡爾族人口約4萬人,1982年,全國(guó)達(dá)94014人,1990年為121357人。2000年全國(guó)人口普查,全國(guó)達(dá)斡爾族有132394人。
達(dá)斡爾語屬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有全民族通用的獨(dú)立語言,屬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的一個(gè)獨(dú)立語支。由于居住分散,形成了布特哈、齊齊哈爾和新疆三種土語,但語音、詞匯、語法的差別不大,可以互相通話。
達(dá)斡爾族曾經(jīng)有過自己的文字,由于歷史的原因失傳了。清代也曾有過滿文字母的達(dá)斡爾文。滿文字母的達(dá)斡爾文對(duì)達(dá)斡爾族文化的繁榮發(fā)展起了巨大的促進(jìn)作用。
達(dá)斡爾族過去信仰原始薩滿教。薩滿教產(chǎn)生于生產(chǎn)力和人類智能發(fā)展到一定程度的遠(yuǎn)古時(shí)代,是人類社會(huì)原始宗教的晚期形式,是漫長(zhǎng)歷史進(jìn)程中逐漸出現(xiàn)的原始拜物教。“萬物有靈”和“靈魂不死”的觀念是形成原始薩滿教的思想基礎(chǔ),認(rèn)為世上存在著一種超自然的力量,這種力量主宰或影響著人們的生活。薩滿教相信靈魂不滅,認(rèn)為人死靈魂不死,進(jìn)入靈魂世界,生前行善者的靈魂再次轉(zhuǎn)世為人,行惡者的靈魂轉(zhuǎn)為畜生。
薩滿教崇拜對(duì)象歸納起來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對(duì)自然和自然物的直接崇拜;另一類是對(duì)精靈、鬼魂和祖先的崇拜。
薩滿教作為人類社會(huì)原始宗教之一,沒有特定的創(chuàng)始人,沒有宗教社會(huì)團(tuán)體組織,沒有集中宗教活動(dòng)場(chǎng)所,沒有成文的經(jīng)卷大典,沒有統(tǒng)一規(guī)范的宗教禮儀。
薩滿教遍布全球,古代亞洲南起越南北至西伯利亞、北極海遼闊領(lǐng)域內(nèi)生存的各民族都曾信奉原始薩滿教。達(dá)斡爾族人信仰薩滿教,直到20世紀(jì)40年代還很盛行。
清太宗天聰八年(1634年)五月,達(dá)斡爾部長(zhǎng)巴爾達(dá)齊率眾歸附后金(清),進(jìn)貢貂皮。太宗崇德二年(1637年)閏四月,素倫、達(dá)斡爾部長(zhǎng)博木博果爾等進(jìn)朝貢皮,后于崇德四年(1639年)十一月間聚眾叛后金。后金遣諸將征之,博木博果爾等轉(zhuǎn)戰(zhàn)年余,終以寡不敵眾,被后金所獲,其部眾遂全體投降。
達(dá)斡爾族是勤勞勇敢的民族。在反掠奪、保家鄉(xiāng)的抗暴自衛(wèi)正義戰(zhàn)爭(zhēng)中,達(dá)斡爾族人表現(xiàn)了不畏強(qiáng)暴、勇往直前的英雄氣概;在沙俄入侵、國(guó)難當(dāng)頭的危急時(shí)刻,更是自發(fā)群起,全哈拉、全民族、全方位投入抗擊沙俄的人民戰(zhàn)爭(zhēng)之中,尤其是在舉世聞名的雅克薩反擊戰(zhàn)中,挫敗了沙俄覬覦黑龍江的圖謀,迫使沙皇俄國(guó)不得不回到談判桌上來,簽訂了中俄《尼布楚條約》,為捍衛(wèi)祖國(guó)北疆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在清代,達(dá)斡爾族涌現(xiàn)出一大批智勇雙全、戰(zhàn)功赫赫的戰(zhàn)將。在日本帝國(guó)主義侵占東北后,達(dá)斡爾族人積極支持和參加中國(guó)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抗日活動(dòng),在東北各族人民抗日斗爭(zhēng)中做出了重要貢獻(xiàn)。在敵強(qiáng)我弱、政局動(dòng)蕩、勝負(fù)未卜的關(guān)鍵時(shí)刻,主動(dòng)接受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導(dǎo),積極投身到火熱的解放戰(zhàn)爭(zhēng)之中,在東北乃至全國(guó)戰(zhàn)場(chǎng)都有他們鮮血染紅的足跡。在和平建設(shè)和改革開放的偉大實(shí)踐中,涌現(xiàn)出一批又一批忠于黨、忠于祖國(guó)、忠于人民、忠于社會(huì)主義事業(yè)的優(yōu)秀干部及帶頭人,他們率先垂范,團(tuán)結(jié)奮進(jìn),為振興家族、光大民族、昌盛中華再創(chuàng)輝煌業(yè)績(jī),譜寫了許許多多可歌可泣的光輝篇章。
二
達(dá)斡爾族于清太宗時(shí)歸附后金(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歸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管轄,編入滿洲旗內(nèi),受滿洲之文教感化,學(xué)習(xí)滿族文字。達(dá)斡爾族先輩不忘本源,受滿族編修家譜的影響,始立氏族家譜,以遺后世,各“哈拉”“莫昆”均用滿文或滿、漢文字進(jìn)行始修、續(xù)修家譜的活動(dòng),代代相襲。
達(dá)斡爾族主要以譜單形式編修本族的家譜。所謂譜單,就是從本家族始祖或始遷祖開始,將歷代家族成員按世系先后次序或按分支世系先后次序平列記載在一幅紙上,內(nèi)容包括姓名、任職等內(nèi)容,平時(shí)收藏起來,逢年過節(jié)掛在中堂進(jìn)行祭拜。
內(nèi)蒙古莫力達(dá)瓦旗民宗局收藏有數(shù)十種達(dá)斡爾族譜單,說明達(dá)斡爾族各家族以譜單形式編修家譜是比較普遍的。
《中國(guó)少數(shù)民族古籍總目提要》第3卷(達(dá)斡爾卷)介紹了達(dá)斡爾族7種家譜提要,即《郭布羅氏莽乃莫昆族譜》、《布特哈敖拉氏多新(多金)莫昆族譜》(“布特哈”為祖籍之意)、《布特哈鄂嫩氏總族譜》、《布特哈莫日登哈拉族譜》、《布特哈達(dá)斡爾德都勒氏家譜》、《布特哈郭布羅氏塔溫淺族譜》和《布特哈達(dá)斡爾蘇都爾氏家譜》,下面我們就以此7種家譜為例,對(duì)達(dá)斡爾族譜單家譜的形式、內(nèi)容等作一簡(jiǎn)介。
由上節(jié)簡(jiǎn)介達(dá)斡爾族社會(huì)組織結(jié)構(gòu)可知,以上7種家譜基本可分為兩類,一為“哈拉”部落類型家譜,如《布特哈莫日登哈拉族譜》《布特哈鄂嫩氏總族譜》等,是整個(gè)“哈拉”部落的家譜,包含部落內(nèi)諸多“莫昆”氏族譜系在內(nèi),是涵蓋面較廣的家譜。一為“莫昆”氏族類型家譜,如《郭布羅氏莽乃莫昆族譜》和《布特哈敖拉氏多新(多金)莫昆族譜》,就是兩部氏族家譜,記載的是本氏族世系、人物等事跡。
達(dá)斡爾族于清初即開始編修家譜。如《郭布羅氏莽乃莫昆族譜》和《布特哈鄂嫩氏總族譜》始修于清順治年間,《布特哈莫日登哈拉族譜》于康熙六年(1667年)立譜,《布特哈達(dá)斡爾蘇都爾氏家譜》修于雍正元年(1723年)。達(dá)斡爾族編修本族的家譜,與其原先存在的“靈魂不死”“崇敬祖先”的薩滿宗教觀念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
《中國(guó)少數(shù)民族古籍總目提要》第3卷介紹的達(dá)斡爾族家譜,基本上都是譜單。如《郭布羅氏莽乃莫昆族譜》,麻紙,楷書,頁面94厘米×2800厘米;《布特哈敖拉氏多新(多金)莫昆族譜》,麻紙,楷書,頁面94厘米×2310厘米;《布特哈鄂嫩氏總族譜》,麻紙,楷書,頁面94厘米×2310厘米;《布特哈達(dá)斡爾德都勒氏家譜》,麻紙,楷書,頁面98厘米×960厘米;《布特哈郭布羅氏塔溫淺族譜》,麻紙,楷書,94厘米×2600厘米;《布特哈達(dá)斡爾蘇都爾氏家譜》,麻紙,楷書,頁面490cm×90cm;等等。上述譜單皆為麻紙,用滿文或滿、漢文字書寫,由于歷代族人悉心收藏保管,盡管經(jīng)歷數(shù)百年,但以上7種譜單至今都保存完好。
上述族譜譜單,寬度一般90多厘米,而長(zhǎng)度很長(zhǎng),短的4.9米,最長(zhǎng)的達(dá)28米,平時(shí)卷起來收藏,到逢年過節(jié)掛起來或完全展開則一個(gè)房間都鋪不開,往往在室外用很多長(zhǎng)桌子連在一起,才能將譜單完全鋪開供族人查尋祭拜。
達(dá)斡爾族各部落、氏族每二三十年或稍長(zhǎng)時(shí)間必?fù)穸ㄟm中地點(diǎn),召集同姓各族之代表,舉行祭祖修譜會(huì),續(xù)修譜牒,將上屆修譜以來增加的男姓名單書寫到原來的譜單上,出生者名字在其父親之名下,以朱筆加填,死亡者名字,以墨筆寫之。如有異動(dòng)變更者,隨時(shí)訂正。續(xù)修族譜會(huì)前,各部落、氏族都要組建精干的籌備班子,保證續(xù)譜工作的接續(xù)性、準(zhǔn)確性、完整性,做到不錯(cuò)不漏不誤。
《中國(guó)少數(shù)民族古籍總目提要》第3卷介紹的達(dá)斡爾族7種家譜,就有各家譜規(guī)模較大的續(xù)修家譜時(shí)間的記載。如《布特哈敖拉氏多新(多金)莫昆族譜》,曾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道光三十年(1850年)、1927年三次續(xù)譜,后又于1988年第四次續(xù)譜;《布特哈鄂嫩氏總族譜》曾于1923年、1939年由5個(gè)莫昆兩次續(xù)譜;《布特哈達(dá)斡爾德都勒氏家譜》于1938年、1985年分別續(xù)修;《布特哈達(dá)斡爾蘇都爾氏家譜》,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光緒四年(1878年)、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和1938年4次續(xù)修。
作為主要記載家族世系成員姓名、任職的譜單,盡管屬于比較原始、形式比較簡(jiǎn)單的家譜,但也揭示了本家族的許多重要信息。
如《郭布羅氏莽乃莫昆族譜》,揭示了該氏族17世紀(jì)前世居精奇里江下游左岸郭布羅阿彥地方,順治六年(1649年)遷居嫩江支流訥莫爾河。一支是塔溫淺各屯,一支是莽乃、莫熱、莽乃伯爾科、倭都臺(tái)4屯,屬莽乃莫昆。該氏族始祖為薩吉達(dá)庫(kù),譜單共記載薩吉達(dá)庫(kù)以下19代世系人名,其中有百余名知名人物,如清朝末代皇后婉容、長(zhǎng)順、穆騰阿將軍等。
又如《布特哈達(dá)斡爾蘇都爾氏家譜》,揭示蘇都爾氏于順治八年(1651年)由精奇里江口東側(cè)遷至嫩江支流諾敏河后,建立了綽日哈、查哈陽、霍勒托輝、畢臺(tái)、烏爾科5屯。蘇都爾氏先人在清代任過佐領(lǐng)以上官員者28名。其中知名人物有參加過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及其前期中俄談判的外交官孟額德、齊齊哈爾建城總管瑪布岱、庫(kù)倫辦事大臣安住(又名安德)等。這些資料不僅對(duì)研究達(dá)斡爾族蘇都爾氏歷史,而且對(duì)研究整個(gè)達(dá)斡爾族歷史都有參考價(jià)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