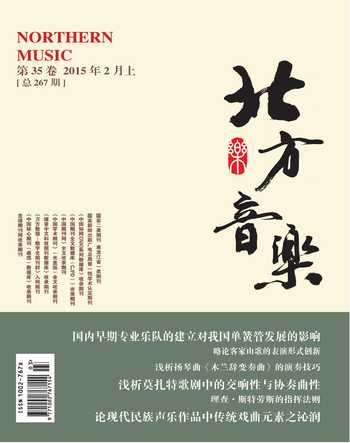論音樂審美移情的三個層次
陰慧慧
【摘要】移情是音樂審美活動中的常見現象,是音樂審美研究的重要領域。宏觀上,音樂審美移情是主客觀的辯證統一,微觀上,音樂審美移情有三個層次:原始移情、審美移情及道德移情,此三個層次具有時空意義上的遞進關系,同時也是音樂審美移情的三種存在形態,相互交織。
【關鍵詞】音樂審美;移情;層次
近現代西方美學中,移情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范疇, “移情從心理學的角度看,屬于外射作用的一類,所謂感情的外射作用,是指人們在藝術思維和審美活動巾,自覺或不自覺地把屬于人的知、情、意移入客觀的自然景物或其它審美對象之中,使本身沒有情感和知覺的審美對象,在審美主體的情感作用下,仿佛也具有r人的感覺、感情、意志、性格、行動等。這種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物我同一的現象,在美學中就稱之為移情”。移情研究的進展,形成r極具影響力的理論流派,里普斯(Theodor Lipps)的“移情”說、谷魯斯(Karl Groos)的“內模仿”說以及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的“異質同構”說是為典型。西方移情理論的興起,也帶動了中圍美學對這一理論的發掘、整理和探究。20世紀八、幾十年代我國掀起了一股移情研究熱,著名美學家朱光潛對西方重要移情理論成果進行了翻譯推介,他以巾國傳統文化思想和審美精神為基礎吸收消化西方移情理論,建立了白成一家的“物我同一”的移情理論。眾所周知,音樂是美學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而移情現象在音樂審美及教育活動中更是一個常涉話題,由此也成為音樂美學研究的一個命題,并顯示r其對于音樂審美研究的深入的重要意義。簡言之,音樂審美活動中的移情現象即稱為音樂審美移情,是指創作主體或審美主體在心理偏好和心理喚醒的作用下,把自己對生命、生存、生活以及大自然等因素的情感體驗,移入融化到音樂審美對象(音樂作品中出現的藝術形象或情思意念等)之中去,使其具有更加強烈而充分的“情感化”或“人性化”的美感價值,并且能在音樂審美的過程中充分感受到音樂之美的情緒情感體驗狀態。
音樂審美移情是主客觀的辯證統一。朱光潛先生曾指出,美必須以客觀事物作為條件,再加上主觀的意識形態或情趣的作用使物成為物的形象,即意象,然后才是美。他從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角度,肯定了審美主體與審美對象的辯證統一。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第五交響曲》(命運)的創作,其實就是得益于他本人的切身經歷。那一時期,貝多芬(Ludwig vanBeethoven)止經歷著他個人精神上的危機:疾病纏身、耳聾加劇、愛情破滅。而在絕望的當頭,康德(Immanuel Kant)“要忘掉自己的不幸,最好的方法就是埋頭苦干”一語驚醒這個失意之人。于是,他開始積極地面對人生,“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絕不允許它毀滅我”。種種磨難和不幸沒有使他屈服,最終使他重拾與命運抗爭的勇氣和精神,憧憬著美好的生活。這段客觀存在的人生經歷,是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得以創作《命運交響曲》的靈感來源,也是他創作的動力。他用諧謔曲特有的節奏突出、突發的強弱對比等表現手法,將他自身徹悟命運的過程展示在r這部無言的音樂作品當中。聽賞者能夠從音符的跳動巾,真切的感受到命運在“敲門”,在蹣跚,在歡呼。于是,一個鮮活的“命運”的審美意象就形成了。而命運意象的形成,恰恰是審美主體的情感與客體所描述的真實遭遇融為一體,產生了情感上的共鳴。
在“辯證統一”的整體性的宏觀認識基礎之上,還應該從層次性的微觀層面來進一步認識音樂審美移情的內涵。筆者以為,源于西方美學理論的移情概念在音樂域境中的應用,應當有二個層次。
一、自然移情
在人的社會化發展進程中,“盡管科學理性的思維方式代替了原始人簡單的移情的思維方式,但是,移情作用并沒有消失,而是以一種集體無意識的形式積淀在人類心理的深層結構巾,并在文學和藝術活動中得到保留和進一步的發展,由原始的低級的移情發展為審美的高級的移情”。“藝術情感和舞蹈情感并不是指生活中的真情實感,而是高于生活一定心理距離的審美情感,亦即移情以及在移情基礎上的表情、表現、體現和體驗”。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從康德(Immanuel Kant)的哲學和美學基本概念出發認為,無論個人或者整個民族,都不可避免地要經歷自然狀態、審美狀態和道德狀態這樣二個發展時期或者階段。人從自然王國進人道德的工圍,“除了首先使他成為審美的人以外,再沒有其他的途徑”。前人的這些論述,其實已經清楚的告訴我們,審美移情之“情”,只關乎審美,不是自然(原始思維或兒童思維)情感,亦不是道德情感。在音樂活動中,移情同樣也呈現出這樣的層次性。“原始禮儀是舞、樂、詩(咒語)、劇(舞有一定的情節)、飲食(很多儀式有祭品)的統一”,而在儀式的諸因素巾,特別強調音樂的作用,人心的和諧通過音樂的和諧達到宇宙的和諧。在原始人那里,思維方式呈現出主客不分的模糊狀態,他們認為“萬物有靈”,儀式上的音樂能夠使人的內心無限接近神靈,以達到人與天的和諧。這種原始的音樂活動中,聽者與聽者的情感本沒有必然的聯系,但聽者虔誠忘我的祭拜行為卻明顯表明聽者在音樂的過程中產生了移情,這種沒有主觀思維主動參與的無意識的移情現象,止是音樂活動巾的原始移情,或者說是生活移情。當然,在現代社會生活當中,音樂被用作背景的做法非常普遍。如今流行于大街小巷的瑜伽健身運動,練習時常常采用優美舒緩的音樂作為背景,以幫助練習者盡快進入專心致志的忘我境界。練習者聽的是音樂,但思維中并非是音樂,而是佛,其練習的最高境界就是梵我合一。對于瑜伽練習者來說,練習時所聽的音樂就是一種純粹的技術要素,是促使練習者能夠進入移情的輔助手段,也是音樂的生活移情的體現。
二、審美移情
隨著人類認識經驗的積累,原始移情“逐漸被排斥劍背景中去,但在藝術中得到保存并進一步發展,成為藝術思維的心理基礎。”在音樂的創作和欣賞過程中,首先需要主體具有音樂認知和經驗積累,因而谷魯斯(Karl Groos)的“內模仿說”,似乎并不能完全從審美意義上去解釋音樂移情現象,而是從某種程度上證明了音樂原始移情的存在及其心理機制。
比較而言,里普斯的移情論美學則首先強調移情的產生是建立在審美關系的確立之上的。而審美關系的確立,顯然又是建立在主體具有一定的音樂認知能力的基礎之上的。那些試圖將音樂審美追溯至遠古時代的看法值得懷疑。當人類還處于一種認識水平極其低下的蒙昧的集體無意識年代里,審美甚至尚未萌芽,音樂審美移情也就不可能產生。不過,音樂審美自我國先秦時期的《樂記》就已經開始萌芽一,后來的琴學專著《琴操》記載了一個至今廣為傳誦的例子:
“伯牙嘗從學琴,二年而成,于精神情志未能專一。成連云:‘吾師子春在海巾,能移人情。遂與俱至蓬萊山。曰:‘吾將迎吾師。刺船而去,旬日不返。牙但聞海水泊沒崩撕之聲,山林窗冥,群鳥悲號,槍然嘆曰:‘先生將移吾情。乃援琴而歌之。曲終,成連刺船返。伯牙遂為天下妙手。”
伯牙之師成連的手段,就是充分運用了音樂審美移情的心理機制,使伯牙學會了如何發現和把握音樂的意境之美,逐成一代宗師。
三、道德移情
“道德移情,是人們通過特定的審美活動從中汲取修身養德的一種道德接受方式。”我們知道,道德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人們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準則與規范。道德往往代表著社會的止面價值取向,起判斷行為止當與否的作用。這樣一來,音樂活動巾的道德移情就與審美主體的審美價值觀直接構成了聯系。例如社會上曾出現過的《那一夜》,歌詞就帶有明顯的色情意味。暴力恐怖的歌曲《妹妹背著娃娃》的歌詞是這樣的:
有天爸爸喝醉了
揀起了斧頭走向媽媽
爸爸啊爸爸
砍了很多下
紅色的血啊染紅了墻
媽媽的頭啊
滾到床底下
她的眼睛啊
還望著我呢
爸爸媽媽為什么呀為什么呀
然后啊爸爸
叫我幫幫他
我們把媽媽
埋在樹下
然后啊爸爸
舉起斧頭了
剝開我的皮做成了娃娃
充滿著血腥和暴力歌詞內容的歌曲,顯然是無法被社會普遍接受的。特定歷史年代的反動歌曲《織毛衣》則更是反黨反人民的反面教材。這些違背了正常的社會價值取向的音樂作品,顯然都不得人心。而萬山紅《公仆贊》、張明敏《我的中國心》、殷秀梅《黨啊,親愛的媽媽》等等一大批優秀歌曲,之所以能夠廣為傳唱且經久不衰,恰恰也是因為這些歌曲的內容和形式都與人們的社會道德取向相契合,并傳遞著中華民族人民真善美的品質和追求正義的止能量,很容易產生情感上的認同和共鳴,因而才成為經典。
最后需要指出,音樂審美移情的上述二個層次具有時空意義上的遞進關系,但并不意味著發展意義上的取舍,即審美移情的出現就意味著原始移情的消失,以及道德移情的出現就意味著審美移情和原始移情的消失。實際上,音樂審美移情的三個層次同時也是音樂審美移情的二種存在形態,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互交織的統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