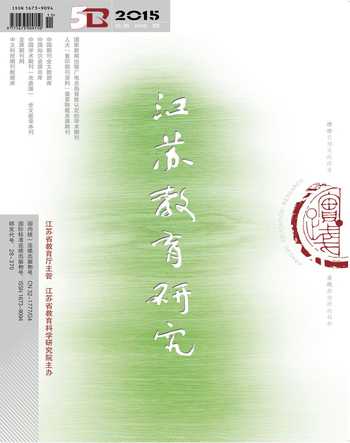講述·續編·創寫:讓寓言教學言意共生
寓言是一種特殊的文體,它往往通過一個短小精悍、生動有趣的故事,表達作者對某種人或社會現象的評價,或贊揚、或批判、或諷刺、或勸誡,篇幅雖短,卻蘊含著耐人尋味的哲理。小故事中有大道理,小故事能起大作用,正是這種文體獨有的魅力,也是區別于其他敘事文的最大特點。然而,不少教師因此在處理教材時,往往圍繞寓意大做文章,而忽略了語言本身,甚至因“理”廢“言”。寓言教學“理”太強,是教學中不容忽視的一個現象。
高效的語文課堂,言和意應該是和諧相生的,要讓學生理解寓意,感受文本所蘊含的思想情感,還是得立足于語言這個載體,讓學生在語言的積累與訓練中學會理解與運用。寓言教學,“理”是中心,“言”為根本,在教學中,我們不妨采用講述、續編、創寫的策略,讓寓言教學凸顯“故事”本色,回歸到語言的運用與實踐上,達到言意共生的境界。
一、講述故事,在積累內化中巧妙悟理
嚴文井曾說:“寓言是一個怪物,當它朝你走過來的時候,分明是一個故事,生動活潑,而當它轉身要離開的時候,卻突然變成了一個哲理,嚴肅認真。”這一特點決定了故事的生動性,同時也決定了寓言的教化功能。這種教化之所以能夠在人類的文學史、文化史上擁有持久的生命力,并非因為那些深刻的教訓,更多的得益于一個個生動的故事。試想,如果略去所有的故事,僅僅把《伊索寓言》中所有的寓意摘錄下來作為教育材料,這部作品還能流傳至今嗎?如果說寓意是寓言的骨架的話,那么,生動的故事就是寓言的血肉,使寓言豐滿而又充滿生機。因此,在教學中我們不妨抓住這一文體特點,還故事教學以本色——講述。以講故事為重要目標,又以講故事為策略,引導學生在講故事中閱讀理解課文,展開言語實踐,在言語實踐中悟得言語表達的形式,習得語言,讓寓言故事的語文教學價值得以完整體現,實現從“我教課文”到“學生學語文”的美麗轉身。
薛法根老師執教《揠苗助長》一課時,牢牢抓住了“故事”這一特點展開教學。故事是適宜講述的,學故事就得先學會講故事。課堂上,薛老師不惜時間,按照“故事新手”“故事能手”“故事高手”“故事大王”這樣的層次不斷提升要求,清清楚楚指導學生如何講好故事,扎扎實實讓學生練習講故事,學生興致盎然,講得繪聲繪色。事實上,要把故事講好,必須真正讀懂故事,在講故事的過程中,學生自然而然理解了農夫的急于求成,好心辦壞事,也懂得了違背事物發展規律必然導致事與愿違、適得其反的道理。講述和體悟如水乳交融,學生在對故事的積累內化中,巧妙悟理,言意皆得。
講故事,讓學生擁有了屬于自己的課堂,擁有了進行言語實踐的時間和空間,不僅讓學生在潛移默化中感受了中國古代寓言借事說理、寓意含蓄的特點,更懂得了中國傳統文化中講故事的智慧,因此,課堂上有了這樣精彩的對話——
師:真正像這樣傻的農夫,在現實的生活中有嗎?
生:沒有。
師:但是像農夫這樣揠苗助長的其他人、其它事有嗎?
生:我想讓豬籠草長快些,給它多灌了一點營養液,它死了。
生:媽媽為了讓我比其他同學成績好一些,給我報了好幾個輔導班。(其余略)
師:面對這樣的情況,聰明的小朋友會——
生:把“揠苗助長”的故事講給父母聽。
師:對,我們以后遇到這樣的人要講故事給他們聽,但是含義要說嗎?
生:不要說,讓他們自己去體會。
蘇格拉底說:“教育不是灌輸,而是點燃火焰。”其實,故事就是點燃智慧的火焰。寓言,產生于民間口耳相傳的故事,講述故事,讓學生在積累、內化、表達中巧妙悟理,他們的語文能力得到了有效的鍛煉,也讓寓言教學煥發出生命的活力,生動、扎實而又富有情趣。
二、續編故事,在想象思辨中發展思維
閱讀是一種意義建構,閱讀參與者全情投入,會身不由己地參與到互動中,在不知不覺中超越預期的目標,從而獲得意想不到的洞察力。寓言中他人的故事,對兒童來說已不僅僅是他人的故事,因為他們在自己的認知結構中建構了自己的意義。
如童話體的寓言故事《猴子種果樹》一文,教學臨近尾聲,總有教師愛這么問:猴子種果樹為什么沒有成功?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么道理?如此這般地叩問猴子失敗的原因,確實很難得到學生的共鳴,因為停留在紙上的故事終究是他人的故事,觸動不了兒童的心弦。
薛法根老師設計了這樣一個教學活動:教師做猴媽媽,所有小朋友做小猴子。猴媽媽在和小猴子的聊天中拋出許多問題:孩子啊,你辛苦了這么多年,怎么一棵果樹都沒有種成功啊?這些鳥兒朋友的話到底有沒有道理?既然鳥兒朋友的話都有道理,為什么你還是一事無成啊?如果以后你再種果樹,你會怎么種?如果再有鳥兒朋友來勸你,你怎么辦?一個又一個情景追問,促使學生以小猴子的視角進行反思,由此,小猴子的認知與學生的認知產生了勾連,使學生的思想受到了沖擊。對待他人的勸告應該抱著怎樣的態度?在學生設身處地的反思中,寶貴的人生哲理慢慢滋養著他們的心靈。尤其精彩的是,薛老師把這種步步深入、設身處地的叩問融入“續編故事”這個教學活動中,巧妙而又不露痕跡。
薛老師:“我們一起來續編故事。”
出示:正當猴子(傷心)的時候,一只( )對猴子說:“( )。”猴子一想:“( )。”于是( )。”
再給學生三分鐘時間,自己編一個故事。孩子們心中的故事猶如打開閘門的洪水,傾瀉而出。如:正當猴子傷心的時候,一只老虎對猴子說:“猴弟,猴弟,你怎么總是聽別人的話呢?你這樣是種不成任何樹的,你要堅持,要有耐心!”猴子一想:“對呀,我就種蘋果樹!”于是猴子就種蘋果樹了。過了一年又一年,猴子的蘋果樹豐收了,他把蘋果和伙伴們一起分享。
多棒的孩子啊,不僅有讀懂文章的智慧,言語中更閃爍著人性的光輝。
看大家說得差不多了,薛老師給孩子們講老師編的故事:“正當猴子傷心的時候,一只狐貍對猴子說:‘猴哥猴哥,俗話說‘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這些鳥的話都是害你的。猴子一想……”猴子會怎么想呢?薛老師再次開啟孩子的思維之門:鳥兒們是在害猴子嗎?狐貍這樣說有道理嗎?每一個故事的結局都是不同的,每一個人對故事都有自己的理解,通過思辨,薛老師在孩子們的心田播撒下了辯證思維的種子。
續編故事,開啟了無窮的想象;辯證思考,讓孩子的認知從一元走向多元。所有的這些訓練,都在有意識地延伸寓言的情感,拓展寓言的內涵,遷移寓言的表達方法,這是立足語言的理解,著力于語言的內化與運用,在實踐中學習語言的過程。續編故事,讓學生在學習中透視語言,發現不同,讀到自己,豐富自己,文本與孩子在原本語文實踐活動中積累的信息單位產生緊密的關聯,并且不斷地完善,讓孩子獲得了成長的感覺,使教學擁有了生長性。
三、創寫故事,在實踐表達中讀寫共生
寓言教學不是教會人相信,而是教會人思考:故事中的那些人或物為什么會那樣做呢?這樣的反躬自省,必然會促使學生將閱讀的視角從關注故事主角轉向關注自身,反思“我”或者“我們”是否會做同樣的事?這樣一思考,學生的心智就開竅了,就有了真正意義上的成長。這是寓言故事的教學價值之一,還有言語的價值。寓言故事就是借助故事說道理的,一般讀者不太關注故事本身的真假,而只會關注其中的道理。然而,語文教學是要教會學生“用故事講道理”的言語本領的,因而要細細琢磨的恰恰是故事本身,關注故事的敘述方式,而最為關鍵的是隱藏其中的言語“秘密”,會不會講故事,關鍵就全在這隱藏著的言語形式里面。
教材上常常會出現諸如“聯系生活經驗談談體會”的習題要求,如蘇教版第9冊第8課練習:“聯系自己的生活經驗,說說‘自相矛盾‘濫竽充數‘畫龍點睛的意思。”教者也常常會問諸如“在現實生活中你見到過這樣的情形嗎?你會怎么做呢?”一類的問題。對高年級學生來說,在發現、借鑒文本“隱藏著的言語形式”后,他們完全有能力“聯系自己的生活經驗”,通過創寫故事來表達自己對寓言故事的深刻理解。
我國古代經典寓言故事,不僅生動有趣,而且短小精悍,結構精巧,表達簡練。如《自相矛盾》一文,全文僅124字,按事情發展順序敘述,首先是概述故事的起因:“古時候,有個楚國人賣矛又賣盾。”一個人“賣矛又賣盾”,呈現了“自相矛盾”發生的可能性。接著描述楚人賣矛又賣盾的經過——他拿起自己的盾夸口說:“我的盾堅固得很,隨你用什么矛都戳不穿它。”又舉起自己的矛夸口說:“我的矛銳利得很,隨你什么盾它都能戳穿。”細讀文本便會發現這寥寥數語的表達之妙。“隨你用什么矛都戳不穿它”“隨你什么盾它都能戳穿”,言下之意,此人的矛“無堅不摧”,堪稱“天下第一矛”;此人的盾“堅不可摧”,可謂“天下第一盾”。顯然,這是言過其實的“夸口”。然后,把這兩句話聯系起來,細細揣摩,楚人“夸口”時的語言極為夸張地突現了他說話前后互相抵觸這一特點,像這樣,自己的言語行為前后相互抵觸,就叫“自相矛盾”。最后是故事的結果——有個圍觀的人問他:“用你的矛來戳你的盾,會怎么樣呢?”那個楚國人張口結舌,回答不出來了。為什么張口結舌?啞口無言之際,心里有著怎樣的想法?故事沒有寫出來,留給聽故事的人自己去體會。
教學中,我們不妨引導孩子學習課文的寫法,創作“新版《自相矛盾》”。以下是教學片斷:
師:這個故事選自《韓非子》,從2300多年前一直流傳到今天,使很多人受到了教育。生活中,你還見過哪些自相矛盾的現象?
生:我媽媽讓我多吃點,說胖胖的才可愛,她自己晚上不吃飯,說瘦了才好看。
師:媽媽一不小心自相矛盾了,其實無關胖瘦,營養均衡,身體健康最重要。
生:柯震東拍攝禁毒宣傳片,告訴大家吸毒不好,自己又偷偷吸毒。
師:對,這樣的藝人,失去了做人的底線,也就失去了公眾的信任。我們可以模仿《自相矛盾》的寫法,把生活中的這些現象寫下來。課文的寫法中最值得我們借鑒的是什么?
生:重點寫好人物自相矛盾的語言或動作。
十分鐘后,學生完成練筆,進行交流,賞評。
生讀習作:
“媽媽最近體形越來越豐滿,所以,她鄭重宣布:減肥!
為了幫助老媽實現減肥計劃,我自告奮勇:‘老媽,我們每天晚飯后出去散步30分鐘,ok?‘沒問題,飯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老媽興奮地做了幾下擺臂動作,貌似躍躍欲試。
吃過晚飯,我興致勃勃地邀請老媽:‘媽,散步嘍!老媽懶洋洋地窩在沙發里津津有味地看著電視。她揮揮手:‘不去了,飯后坐一坐,活到九十九。
咦,晚飯前老媽怎么說來著?”
師:哪里讓我們發現了媽媽的自相矛盾?
生:語言——“飯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和“飯后坐一坐,活到九十九。”
生:還有動作——“擺臂,躍躍欲試”和“窩在沙發里”。
師:前后一對比,矛盾的焦點就出來了。建議你今晚把這個故事讀給媽媽聽,明天告訴我們媽媽的反應。
孩子快樂地接受了這個建議,有意思的是,當晚,我接到了孩子媽媽的短信:潘老師,我今晚去黃山湖公園跑步了。當然,如果現實生活中沒有這樣的體會,那么,編寫一個童話類的寓言故事,也是很有意思的。
縱觀上述教學過程,由寓言故事的閱讀,語言文字的體會,到達文章的中心——寓意,這一過程猶如順流而下,自然天成,既是語言文字工具性的體現,也符合學生心理的認知規律。然后,由“理”出發,逆流而上,回溯故事,體會作者如何得出這個“結論”,或聯系生活實際反思自己或身邊人的言行,或表達自己對這個“理”的看法和理解,如此由“理”溯“言”,讓道理和寓意都回歸到生活實踐和語言實踐中。創寫故事,是學生把閱讀產生的“意”,結合自己的理解產生新的“意”,并通過自己的言語表達而出的過程,以“言”寓“理”,使理解和表達同生共長。孩子創寫的故事,源于生活,又服務于生活,給人啟迪,發人深思,這是寓言學習價值的真正體現。在這一過程中,閱讀、理解、表達相輔相成,讀寫共生,語文學習的價值更得到了真正的體現。
楊九俊先生在《理解兒童》一文中提出:“理解兒童是教育的根本問題。教育是人學,教育是兒童學。基于兒童立場的教育,要以理解兒童為前提。”兒童學習寓言故事,絕不是僅僅為了接受某種人生哲理。單單理解一下寓意,懂得它的意義,絕對不是寓言學習的終點。由言到意是理解,是言語輸入;由意到言是表達,是言語輸出。講述、續編、創寫,使寓言教學凸顯了“故事”本色,達到了“言意共生”的境界。它是由“意”到“言”,由“言”到“意”雙向通途中的風景,不光關顧落點于言和意的獲得,更著眼于獲得的過程。在或講述、或續編、或創寫的過程中,故事讀透,寓意彰顯,言意共生,水到渠成,不失為寓言教學的上策。
(潘雅頻,江陰市實驗小學,214400)
責任編輯:宣麗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