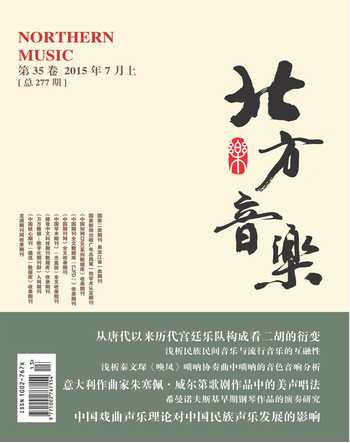論劉勰的音樂美學思想
【摘要】魏晉南北朝是戰亂紛飛、國家分裂的時期,這種王朝的更迭與割據促使出了其思想活躍、精神解放的文化環境。尤其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音樂藝術的發展,在歷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產生于這一時期的偉大文藝理論批評家劉勰,其專著《文心雕龍》中有不少關于音樂美學思想的闡述。本文擬從《文心雕龍》中關于音樂的論述入手,來分析其所體現出的劉勰的音樂美學思想觀念,從而為理清南朝復雜的音樂環境和研究魏晉南北朝的音樂文化思想奠定基礎。
【關鍵詞】劉勰;文心雕龍;音樂美學思想
前言
劉勰,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朝梁代的文學批評家,字彥和,東莞人,早年篤志好學,24歲投靠高僧僧祐,居住于定林寺,并且幫助僧人僧祐校訂佛經十余載,在博通佛教經論的同時,也深入研究儒家經典。中年時開始為官,并為梁昭明太子蕭統所重用。晚年后遁入空門,改名慧地,不久辭世。歷史上記載:“劉勰擅長佛學禮教,京城里的寺廟佛塔以及名人高僧的碑林墓志都由其來編撰書寫成文。由此可知,他是當時遠近聞名的作家,只是由于種種原因,他的作品除《文心雕龍》以外,都失傳已久。所以《文心雕龍》不僅是他的代表作,也是其最重要的論著。實際上,對劉勰音樂美學思想的論述就是從其著作《文心雕龍》中所體現的。
《文心雕龍》集史、論、評為一體,其成書于南齊朝末年。為重要的古典文學理論著作,也是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典籍。其書于文學理論批評頗多建樹,然而,對于集中論述音樂的部分,則為《樂府》篇,它敘述了先秦至魏晉樂歌的演變,是一篇簡明的音樂史。另有《聲律》、《時序》兩篇也論及音樂。因其書主要是從文學著眼,故其中有關音樂的論述,亦注重與詩歌的關系。而且,由于我國自原始社會時期起,音樂就以歌、舞、樂三位一體的表現形式體現,所以詩歌與音樂、舞蹈是分不開的,那么,其音樂美學思想也必然體現在其中。
一、劉勰“詩為樂心”的音樂美學思想
劉勰生活在詩歌樂舞互動頻繁的時代,“由于魏晉南北朝時期自東晉以來,王朝統治者提倡宴享之樂,在帝王的帶領下,社會之風逐漸被夜夜笙歌的享樂風氣所取代,在一段特定的歷史時期里,甚至出現了諸侯等貴族在禮樂制度上對帝王的僭越,從而促使出了詩詞歌賦、歌舞升平藝術繁榮發展的景象。”《文心雕龍》一書是劉勰在前人創作經驗與自身創作體驗相結合的基礎上,撰寫而成。 其內容不僅展示了劉勰的文學觀,而且,也有不少關于音樂的論述。由此,在對他的音樂美學思想觀點進行整理闡述時,由于中國古代文學藝術中,詩歌與音樂相互依存,那么,就不能只談音樂而不論文學。所以,在“樂心在詩”觀點的基礎上,對“詩”與“樂”的發展沿革以及關聯進行疏通理解,然后,再闡述他“中和雅正”的音樂美學觀念,從而也可知,劉勰對儒家樂與政通的思想傾向。
在《文心雕龍》的《樂府》篇中,劉勰主要以詩樂作為該篇的論述目標,并對其“聲律”與“詩歌”的關系進行了論述。然而,這里的“聲律”不僅是指聲調、韻律,而是要與詩歌的內容和情感相聯系,由此可知,樂府的核心是詩句,其形式本體是聲律,那么這就勢必需要好的樂器輔以樂曲,再配上和諧動人的歌辭。而從《樂府》里先秦“葛天氏之樂”到魏晉南北朝“清商曲”的敘述,則是為梳理樂歌的發展與演變,由此,也為進一步追溯音樂產生的根源,即“詩為樂心”奠定基礎。
那么,再看“凡樂辭曰詩,詩聲曰歌”,凡出自樂府的文辭叫做詩,詩句所配音律叫做歌,然對《樂府》中“詩為樂心,聲為樂體”里“詩”與“樂”的論述并沒有輕重之分,而是為了便于內容和形式的區分。正如修海林先生所說:“詩樂的存在,即觀念的存在,也就是樂心與樂體的存在;因此,《文心雕龍》即便是文學論著,卻并不妨礙作者思想中的樂心觀,他把文學與音樂互為融合,卻又可以使樂論具有獨立性,那么,這對領會劉勰及其作品《文心雕龍》的音樂思想起到了促進作用。況且,《文心雕龍》中包含借“文心”寫“樂心”的內容不在少數。我們只有在“詩樂一體”同源性的基礎上有所體會,并與時俱進,才能整理出接近作者想法的音樂美學思想觀念
二、劉勰“豈惟觀樂,于焉識禮”的音樂美學思想
《文心雕龍》中的《時序》主要是講文學藝術作品發展變遷與實際生活的關系。劉勰認為古代民間風土民謠的演變與其所處時代的社會政治環境有極為密切的聯系,有如“風吹草動”一般。 作者認為堯、舜至文王時的歌謠使人心情歡快, 恭敬有節制,而幽王、歷王、平王時的音樂卻呈現出悲愁哀傷與憤懣不滿,由于他們生活在不同的時代,時局環境和政治背景都各不相同,那么,作者的這種音樂反映政治的觀點與儒家“樂與政通”的思想是一致的。《樂記》有言:“治世之音安以樂, 其政和; 亂世之音怨以怒, 其政乖。聲音之道與政通矣”。由于魏晉南北朝是處于戰亂頻繁、社會動蕩不安的時期,人民飽受戰爭的摧殘,也正是與此,這一時期的人們才需要精神寄托,渴望幸福、自由、和諧的美,因此,亂世之音以哀為主,那么該時期的音樂也就以哀樂為主,并且以悲為美是那一時期的音樂審美觀念。作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南朝文人作家,劉勰的這種音樂思想不僅體現在《時序》篇中,還在《樂府》篇中有所表示,他稱:“周朝吳國的延陵季子季札可以在《詩經》的音樂里體悟周朝與各個諸侯國之間的興衰沉浮,還可以透過觀賞音樂來洞察一個國家禮儀風俗的轉變。即 “豈惟觀樂, 于焉識禮”。
(一)樂與政通的教化功能
一個國家的盛衰興廢可以從其音樂中反映出來, 這種說法自古就有。由于人的創作之情是與當時的社會風貌息息相關的, 上至帝王的政治統治得失, 下至民風民情都有一定的聯系。魏晉南北朝是一個戰亂紛飛、動蕩不安的時期,連年的戰爭導致百姓流離失所、民不聊生,各種勢力的割據爭奪造成了禮樂制度的破壞,儒家思想在這一時期開始走向衰落,而作為區分等級地位的“雅樂”也必然被人們所遺棄,從而,也就造成了魏晉時期“禮崩樂壞”局面的產生。可是,縱觀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社會狀況來看,頻繁的戰爭并沒有影響歌舞百戲音樂的發展,由此,也可說明當時社會的經濟發展沒有受到戰爭的阻礙。據史料記載,南北朝時期南朝的齊國武帝在位時,曾出現“十許年中,百姓無犬吠之驚,都城之盛,女士昌逸,歌聲舞節,袨服化妝。桃花綠水之間,秋風春月之下,無往非盛。”社會生產力的進步與商業經濟的繁榮使得百姓對歌舞藝術充滿興趣,這勢必促成了俗樂的興盛,上至王侯將相,下至文人百姓都陷入了縱情享樂的社會風氣之中,我想,這除了依靠富足的經濟外,也有人們面對戰亂時渴望自由、崇尚美好,因逃避死亡相隨時絕望的心聲。然而,對于統治者棄雅崇俗,追求享樂之風的作為,劉勰在其《樂府》篇中也進行了駁斥,因為禮樂喪失了教化作用,被俗樂所替代,這與他提倡的儒家“樂與政通”的思想觀點相悖。
孔子說:“人的修養開始于學習《詩經》,獨立于學習禮教,完成于學習音樂。這是對人的教育過程,也是儒家樂教思想的體現。然而,孔子作為儒家學派音樂思想的代表人物,他認為音樂不僅可以抒發人們的感情,使其修身養性,還可以對人進行潛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成為統治者治理社會時管理人民、教化百姓的工具。孔子把“樂”與“禮”作為共存的實行制度,一切政治準則、道德規范、規章制度以及等級區分都要嚴格按照禮樂制度劃分。同時,劉勰也相信音樂具有改變社會風氣的社會功能,認為,要想轉變社會風氣和民風習俗,沒有比音樂再好的了。所以,劉勰及其作品《文心雕龍》的音樂思想是對儒家樂教思想繼承和發揚。而且,儒家思想無疑為文藝具有教化功能的觀點起到了支撐作用。
(二)崇雅斥鄭,追求中和之樂
在儒家的音樂思想中,孔子對如何欣賞音樂與如何看待藝術的問題上提出了中正平和的觀點,他認為“鄭聲”為“淫樂”,帶有“邪惡”的顏色,并且有違他推崇的“仁”、“善”、“美”的音樂評判標準,也就是符合仁愛道德即為善良,表現的平和中立就是美好。而正統音樂即雅樂,才可以凈化人的心靈,才合乎禮儀的規范。而孔子理想音樂的形式美與內容善,也只有“雅樂”能夠體現。由此,中和的音樂思想一直以來就影響著中國音樂的審美, 那么,自然也對劉勰的思想觀念產生了影響。
首先, 劉勰崇尚雅樂、排斥鄭聲。他提倡藝術風格的多樣性,將“典雅”放在第一, 視“鄭聲”為“淫樂”,覺得藝術作品的美是通過正道之樂的雅聲體現的,認為對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文學藝術作品不能一視同仁。由于漢代至南朝的統治者開始對民間俗樂產生興趣,所以從這一時期的詩文音樂便問題不斷,這正是因為俗樂不能理智自律,不能節制全面,由此也說明,音樂反映了社會與民情。
其次, 劉勰追尋中正平和之樂。他對《文心雕龍》的《樂府》篇中所提到魏晉時期的樂府在發展音樂時,沒有尊崇中正平和的原則予以批評。他說漢朝的樂府作品豐富多樣,審美以美麗繁復為主,到了魏晉時期就多以凄美哀婉的靡靡之音為主要審美方式,且漢魏音樂的歷史走向也是雅樂衰落與俗樂盛行中和之聲的發展。劉勰感慨雅樂正聲不易流傳,鄭衛之音卻容易被人們所接受。他對音樂審美的主張則是在保持傳統音樂純潔的基礎上,加入民間新異音樂元素,因為宮廷雅樂來源于民間風土人情與自然結合后的再加工再創造,而且,對藝術的欣賞是通過復雜感情活動折射的感官反應,所以劉勰對崇雅斥鄭有追求中和之樂的標準。
劉勰認為雅正之樂逐漸衰微,鄭聲淫樂肆意發展是有違常理的,隨著時間的推移,現在的我們會認為他的觀點缺乏全面性,但是,設身處地的在劉勰所處的時代背景中思考,在儒家思想地位逐漸被玄學及佛教取代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劉勰無疑是有著深重社會文化責任感的代表,然而,這種缺陷并無法約束其思想高度。而從劉勰所推崇堅持的中和之樂中可以體現出,儒家“中正平和”思想在劉勰音樂美學思想中的地位。
三、重情的音樂美學思想
劉勰在《文心雕龍》的《情采》篇提出了在文學創作中“為情而造文”的思想,即不要一味注重文辭的華美漪麗,因為只有感情真摯才能創作出真實有價值的作品,作品失去了文學藝術的情感也就是失去了根,那就是無意義的。 然而,他不僅對文學論如此看待,對音樂藝術他也同樣重視情感的表現。
在劉勰的《知音》篇中可知,音樂能表達感情,而文學作品同樣也可以傳遞感情。作者有言:“夫志在山水, 琴表其情,,況行之筆端,理將焉匿?”他認為人們可以通過音樂來體會情感的存在。如果說演奏音樂的人心有所感,那其樂器就會表現出來,同理,他覺得如果作家具備真摯的情感和理性的思維,那么透過他的作品也會把這種真情實意體現出來。而好的作品也會被懂得欣賞的人所珍視,是因為它能賦予人積極向上的力量和輕松喜悅的感覺。
《文心雕龍》中的《序志》篇是研究其與劉勰音樂美學觀念的重要部分。劉勰認為:“夫文心者, 言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 王孫巧心, 心哉美矣, 故用之焉。”作者通過把文心、琴心與巧心的結合,來推測文學與藝術的創作都應該著眼于美,也就是音樂的創作演奏能體現文學的才情,而文學家的也能塑造出具有藝術的美感,由此可見,劉勰的文藝思想里還體現了追崇美的重要內容。而這種觀點更是對孔子音樂評價標準“真”、“善”、“美”的繼承。即所謂凡是合乎“仁”、“德”的就是“善”,凡是表現“平和”、“中庸”者即為“美”。況且從《文心雕龍》里對情感論的闡述中,我們也可以知道,劉勰重視表達情感,但是這卻與他崇尚的儒家理性論所相悖,我認為在這里,他把將理性與感性有機結合也是可以的。
綜上所述,在論述《文心雕龍》的文學性時,離不開它所包含的藝術性。就像朱謙之先生所說,文學的發展離不開音樂。其實,中國自古就把音樂與文學相提并論,這也為《文心雕龍》成為后人研究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音樂美學思想提供了重要依據。對于劉勰主張中正平和的觀點在其著作《文心雕龍》有所體現。由于魏晉南北朝時期雅俗共賞,當時自由寬松的社會風氣使音樂得以蓬勃發展,所以,劉勰一方面主張音樂的和諧與統一;另一方面,由于戰亂不斷,政權更迭頻繁,從而造成這一時期禮樂制度的破壞,而伴隨享樂之風的盛行,新異的俗樂逐漸取代了高貴的雅樂,面對南朝禮崩樂壞的社會現狀,崇儒的劉勰提出用“中正平和”之聲配以“內容敦厚”之辭,期望重振“豈惟觀樂、于焉識禮”的具有樂教功能的音樂美學思想。而劉勰在重視音樂表現理性與感性的同時,針對魏晉南北朝時的復雜矛盾背景,既要能使音樂抒發情感,又要讓它兼具禮樂的教化作用,也就是對音樂中正平和諧和感的審美實現。
因此,《文心雕龍》不僅是一部文學批評論著,其中也包含著音樂美學思想的觀念,由于它既涉及了根本性的音樂審美理論,也同時將其提升到了哲學的高度。于是,在探究劉勰及其著作《文心雕龍》的音樂美學思想時,不僅可以為理解魏晉南北朝的政治社會對音樂美學與思想的影響有所幫助,而且,也能從中體會儒家音樂思想對中國社會政治文化藝術發展的深刻影響。
參考文獻
[1]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1.
[2]朱謙之.中國音樂文學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3]蔡仲德.中國音樂美學史資料注譯[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0.
[4] ]蔡仲德.中國音樂美學史[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5.
[5] 宗白華.美學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6]李澤厚等.中國美學史?魏晉南北朝編(上)[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
[7]張前等.音樂美學基礎[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2.
[8][蘇]莫·卡岡著,金亞娜譯.藝術形態學[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
[9]羅宗強.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M].北京:中華書局,1996.
[10]修海林.中國古代音樂美學[M]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
[11]李延壽.南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5.
[12]陳四海.中國古代音樂史[M]西安:陜西旅游出版社,2000.
[13]王軍.如何看《文心雕龍》中的音樂審美.《交響.西安音樂學院學報》[J].2006(03).
[14]倪亞青,周小露.論《樂府》等篇中體現的劉勰的音樂美學思想.雞西大學學報[J].2014(09).
[15]鄧婷.從《文心雕龍》看劉勰的音樂思想.《樂府新聲?沈陽音樂學院學報》[J].2013(02).
作者簡介:賀琳(1989—),女,籍貫:河南省舞鋼市,現就讀于陜西師范大學音樂學院2014級藝術學理論專業,主要研究方向:中國古代音樂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