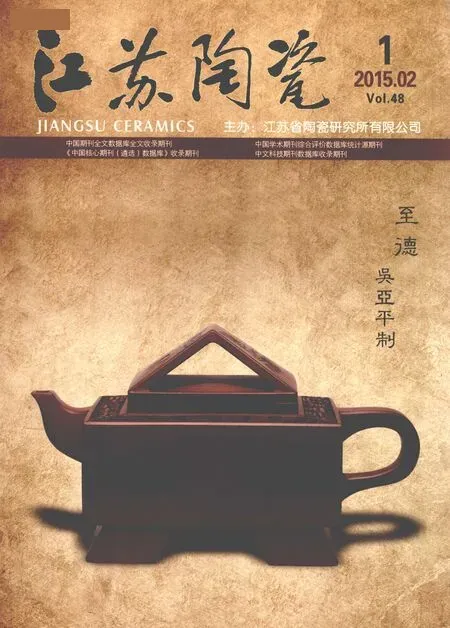淺談肌理語言在紫砂藝術中的運用
向峰

宜興紫砂壺藝歷經數百年的發展和沉淀,至今已成為中國傳統手工藝中的一朵奇葩,它集實用、把玩、欣賞與收藏等諸多價值于一體,獨具藝術之美和文化魅力。依托于得天獨厚的紫砂泥料,得益于歷代壺藝人的優化改進,紫砂壺始終流露著一種泥性的本質之美。傳統紫砂壺不施釉,手工捏制成型,因而散發著獨特的古樸典雅、脫俗嫻靜的氣韻,將泥性特征與肌理語言淋漓盡致地呈現于世人面前。隨著時間的推移,紫砂壺雖在經歷著不斷的創新和變化,但對于肌理語言的運用卻一直在延續。因此,對于壺藝創作者而言,泥性肌理猶如一門精深的學問,而熟知并能夠恰到好處地表現泥性肌理則顯得十分重要。現以設計制作的紫砂壺“遠古”(見圖1)為例,談一談肌理語言在紫砂藝術中的運用。
肌理是指物體表面的組織紋理結構,即各種縱橫交錯、高低不平、粗糙平滑的紋理變化,作為一種客觀的自然形態,肌理往往給人以不同的視覺美感,呈現出素面朝天的氣質。人們將物體的肌理語言與各種藝術形式結合,并通過先進的工藝手法、巧妙的創新創造,在不同的材質上生成不同的肌理效果,創造出豐富的外在藝術形式。諸如繪畫、雕刻等藝術形式,都是比較常見的肌理語言運用對象,而在紫砂藝術創作中,肌理語言的運用空間同樣寬泛。
在任何一種藝術創作中,肌理語言的本質即是體現材料的美感。泥是紫砂藝術創作的語言介質,在這一過程中,體現泥性之美便是紫砂藝術的肌理語言。回歸到創作本身,對泥性的駕馭則是表現肌理語言的第一步,揉、拉、拍、摔、印、壓、推、刻等都是表現的類型,通過人與泥的接觸磨合達成默契感,進而在泥的物理屬性之上呈現出多樣的視覺效果,使人們感受到不同的審美意蘊,同時更延伸出深層的人文意境,升華作品的藝術和文化價值。
設計制作的紫砂壺“遠古”便是一件運用藝術表現手法,充分體現泥性肌理語言,進而詮釋內在人文內容的壺藝作品,該壺完美地繼承了紫砂泥的天然本性,同時更因工具與泥巴的相遇而幻化出別樣的藝術美感和高曠原始的時空氣息,令人神往不已。紫砂壺的造型豐富、變化多樣,圓器、方器、花器和筋紋器各呈其態,彼此相輔,“方匪一式,圓不一相”充分說明了紫砂壺的基本形態概念。“遠古壺”的壺體形態飽滿,各部比例協調、渾然天成,壺身圓潤大方、氣場十足;圓蓋內嵌于壺口,嚴絲合縫,使得整個壺身呈一扁圓球狀,流露出一種韻律自然的線條感,骨肉亭勻、雋永耐看;一彎短壺流與圈把前后呼應,形制小巧卻不可或失,使整把壺在造型形態上更為完整,壺蓋中央置一顆小巧的扁圓珠壺鈕,其形態猶如壺身的微縮版本,妙不可言。整把“遠古壺”充分延續了傳統圓器的造型規則,其圓穩勻正、素雅簡約,給人以高遠空靈的視覺美感。與此同時,壺身和壺鈕上隨性自然的肌理紋絡裝飾,則將整把壺的意境提升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其肌理語言充分體現出泥性本質,成為整把壺的技術核心和形象中心,完美詮釋藝術風格之美。在壺身下部和壺鈕上部均以竹尖刀工具將與壺體性質一致的泥料在其表面拉出層次不一的肌理圖案,其深淺均勻、走勢隨性,猶如繪在其上的一幅混沌而絕美的圖畫,展現出一種原始的、粗糙的、曠遠的泥料之美,呈現出遠古開天辟地之時的場景,營造出獨特的懷古情結,巧妙地對應整把壺的內在精神主旨,使人文內蘊通過肌理語言得以升華。
在這把紫砂壺“遠古”中,泥性肌理通過形狀和厚薄的配置關系,增強了造型的立體感和層次感,豐富了立體形態的風格特征,使肌理語言的運用構成了一定的視覺美感和觸覺質感。但是,對于一把紫砂壺而言,其整體價值含量既體現在外在形象上,更體現在內在人文蘊意中,因此,“遠古壺”恰以肌理語言將開天辟地的混沌之感巧妙地融入壺藝形象中,達到無聲勝有聲的效果,賦予人豐富的想象空間。“遠古壺”是對肌理語言在紫砂藝術中進行運用的完美演繹,它將嚴謹的設計和巧妙的構思融入壺器,綜合紫砂泥料特質,注重表現手法和表達力度,營造出高雅的藝術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