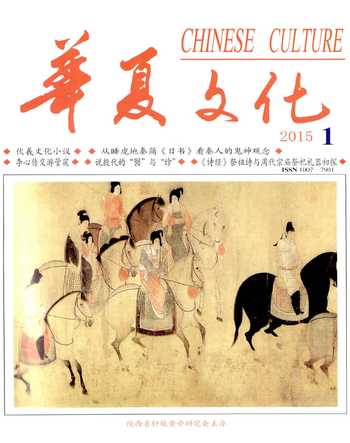德性與行善
鄭相峯
一、孔子言仁
現(xiàn)今已踏進(jìn)了21世紀(jì),東亞各國走向數(shù)碼科技極為發(fā)達(dá)的社會(huì),同時(shí)為了提升其經(jīng)濟(jì)水準(zhǔn)施行各種措施,然而整個(gè)社會(huì)的道德意識(shí)變得非常薄弱 人際關(guān)系圍繞著個(gè)人利益而旋轉(zhuǎn),從而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也不如以前。不過,應(yīng)該如何做人處事、建設(shè)什么樣的社會(huì)等問題還是令人自問不已 在此我們通過探討傳統(tǒng)儒學(xué)的價(jià)值取向和其倫理思想,及其現(xiàn)代意義,或許有助于人們懷著真誠的道德情感相互對(duì)待,并且依賴稱情合理的禮儀和睦相處,以此建設(shè)大家和諧相處的先進(jìn)社會(huì):
春秋時(shí)代末期的孔子開創(chuàng)儒家哲學(xué)并企圖以此挽救亂世、自從周公以宗法制與封建制奠定禮樂文化以來,統(tǒng)治階層之間的血緣關(guān)系逐漸疏遠(yuǎn) 當(dāng)時(shí)整合社會(huì)秩序的禮樂文化敗壞,各地的諸侯先后起兵以謀天下,天下陷入混亂。在這社會(huì)動(dòng)蕩不已的情況之中,人們都迷失了其人生的價(jià)值取向。孔子則挺身而起提倡“仁”,同時(shí)要恢復(fù)名實(shí)相副的禮樂文化。假如孔子僅要追求恢復(fù)禮樂制度,則不可能稱之為儒家哲學(xué)的創(chuàng)始人。孔子進(jìn)一步指出禮樂文化必須依靠“仁”,以此使每個(gè)人樹立其人生方向,并且使得整個(gè)社會(huì)充滿相愛和諧的風(fēng)氣。
二、“仁”與為仁之方
在西周滅亡之后,中國歷史進(jìn)入春秋時(shí)代,整個(gè)社會(huì)的文化體系崩壞。處于春秋時(shí)代末期的孔子目睹了天下無道的情況。“名不正”“言不順” “事不成”“禮樂不興”的現(xiàn)實(shí)狀況,讓孔子深思反問何以能夠天下有道,然后進(jìn)一步追問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zhì),于是孔子提出了“仁”。
孔子一向重視上古以來的眾多德目,例如仁、禮、義、智、信、忠、孝等等。其中“仁”字最早出現(xiàn)在《尚書·金滕》,有日“予仁若考”;《詩經(jīng)》中《鄭風(fēng)·叔于田》則有日“洵美且仁”。其原義代表仁厚、仁愛,就是貴族之美好的風(fēng)范和昂揚(yáng)的氣度。但是經(jīng)過孔子的解釋,“仁”的涵義得以深化,成為其哲學(xué)思想的樞要概念。我們可以說孔子的哲學(xué)思想是仁學(xué)。這個(gè)“仁”是道德實(shí)踐的最終理論根據(jù),也是統(tǒng)攝諸德的第一義性品德。所以人們要在自身修養(yǎng)或與人相處之際,無頃刻離開它,孔子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論語·里仁》)孔子雖然沒有直接給“仁”下定義,但在回答樊遲問仁的時(shí)候,他說:“愛人”。“仁”字是合“人”與“二”兩個(gè)字而組成的。它表明人與人之間的人際關(guān)系的重要,孔子的學(xué)生有子(有若)說過:“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xué)而》)子女懷有孝順之情以奉養(yǎng)父母,弟弟懷有敬順之情以對(duì)待兄長。孝順之情和敬順之情是出白于“仁”。就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而言,父子兄弟的關(guān)系是最基本的人際關(guān)系,人們應(yīng)該起碼通過這種血緣關(guān)系實(shí)現(xiàn)“仁”。同時(shí)須是要使對(duì)父母兄長的親愛恭敬之道德情感擴(kuò)而充之,推廣到其他的人際關(guān)系之巾、如此就能夠達(dá)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所謂“安人”以及“安百姓”也不外乎實(shí)踐“仁”之后可達(dá)到的功效。
不僅如此,孔子提出了為仁的道德自律性與道德主體性,如其所言:“為仁由己,由人乎哉?”意即:實(shí)踐仁德,是全憑自己,而不是靠別人。他又說:“仁遠(yuǎn)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這表示仁離我不遠(yuǎn),我要實(shí)踐仁德,仁德立即實(shí)現(xiàn)出來。在此孔子強(qiáng)調(diào)“求仁而得仁”(《論語·述而》),意指求諸自己本有的“仁”通過實(shí)踐,“仁”德性就實(shí)現(xiàn)出來。
這個(gè)“求仁而得仁”,需要眾多為仁之方。其為仁的實(shí)踐門徑之中,孔子經(jīng)常提到“恕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衛(wèi)靈公》)所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說是消極的“恕”。再者,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dá)而達(dá)人”是積極的“恕”。在《論語·雍也》篇載有子貢與孔子的問答:“子貢日: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jì)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日: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dá)而達(dá)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巳。”消極的“恕”,是自己所不想要的,就不加給他人。積極的“恕”,是想要立自己,也得立他人;想要達(dá)自己,也得達(dá)他人。 “恕”,足推度他人之心如同自己之心的,就是說涵蓋南自己內(nèi)心的“仁”而發(fā),為他人關(guān)懷、著想、體貼孔子所自述的“吾道一以貫之”(《論語·里仁》),表述了他的一生就以“仁”來貫穿之,而其具體實(shí)踐方法則是“恕”。“安人”或“安百姓”是推廣“恕”到他人與老百姓而使之平安。
三、仁禮彬彬
其實(shí)孔子當(dāng)時(shí)的禮樂制度已經(jīng)喪失了原來的意義,然而在生活禮節(jié)和儀禮形式上仍然使用西周以來的禮樂制度。“禮”(或“禮樂”)就包括:1.經(jīng)營國家的典章制度和與之相關(guān)的社群規(guī)則;2.在人際關(guān)系上的倫理規(guī)范;3.各種儀式典禮如五禮(吉禮、兇禮、軍禮、賓禮、嘉禮);4.日常生活中的禮節(jié)細(xì)目。“禮”本身有兩個(gè)層次的特色,即有其普遍性的一面和時(shí)宜性的一面。 孔子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這里的“因”,是繼承的意思。殷朝的禮基本上繼承夏朝的禮,周朝的禮則繼承殷朝的禮。即使朝代改變,但超時(shí)空的禮則應(yīng)當(dāng)繼續(xù)沿襲而使用之。這表示禮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不過如果有不適合于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環(huán)境的禮,則要廢除;如果有適合于新的社會(huì)環(huán)境的禮,則要加以約定。這種“損益”即加減的卅施要隨著社會(huì)環(huán)境而實(shí)行。這就是禮有其時(shí)時(shí)宜性的一面。不管普遍性的常禮或時(shí)宜性的變禮,稱情立文的“禮”之最終目標(biāo)是“和”,所謂:“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 ”“和”指和睦、和合、和諧。人與人之間的和睦和整個(gè)社會(huì)的和諧離不開“禮”。“禮”需要以“仁”作為其根底。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如其所說,無論禮或樂,如果沒有仁的基礎(chǔ),都是無所用的。換句話說,以禮樂為中心的外在性文化體系,不以仁為其本質(zhì)內(nèi)容,就毫無意義。
不過“仁”與“禮”(或“禮樂”)的關(guān)系,是相互呼應(yīng),適當(dāng)配合的。真能如此就稱之為君子。所以孑L子說:“質(zhì)勝文則野,文勝質(zhì)則史。文質(zhì)彬彬然后君子。”(《論語·雍也》)“文”代表外在的文彩,是指“禮”(或“禮樂”);“質(zhì)”涵蓋內(nèi)在的本質(zhì),就指“仁”“文”是屬于形式的,而“質(zhì)”是屬于內(nèi)容的實(shí)質(zhì)內(nèi)容超過外表形式,則是粗略;外表形式超過實(shí)質(zhì)內(nèi)容,則是虛浮。所以實(shí)質(zhì)內(nèi)窬與外表形式相互配合,是最理想的。然而如果要論兩者之間的先后本末,則應(yīng)該“質(zhì)”先于“義”,并且以“質(zhì)”為本,以“文”為末。雖然孔子如此重視“質(zhì)”的一面,但他以為“禮”也是很蕊要的,是不可缺少的。子貢紹述孔子之意以發(fā)叫這一點(diǎn),如《論語·顏淵》:“棘子成日:君子質(zhì)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日: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zhì)也,質(zhì)猶文也。”總而言之,內(nèi)在本質(zhì)的德性(仁)和外在文飾的形式(禮),兩者之間可有先后本末之序,然在人倫日用之際需要兩者兼攝,以達(dá)致仁禮彬彬的人格境界,同時(shí)也會(huì)引致人人和合的社會(huì)風(fēng)氣。
四、孔子仁說的現(xiàn)代意義
就儒家哲學(xué)而言,德性是行善的內(nèi)在根據(jù)。孔子以為“仁”是人先天具有的道德本性。所以人們應(yīng)該要自律地主動(dòng)地實(shí)踐“仁”,求仁就能夠得仁 為仁之方非常多,其中“恕”乃是最為代表性的門徑。 “恕”是由內(nèi)而外,推己及人的一推廣“恕”到他人以及老百姓,這才是君子的行善模式。不過在人倫日用的生活世界中,古來多有言行舉止上的禮節(jié)細(xì)目與儀式典禮上的形式,即所謂“禮”。“禮”是屬于外表文飾的形式一 “禮”需要與人之所以為人的內(nèi)在本質(zhì)即“仁”互相搭配,君子是兼?zhèn)鋵W(xué)識(shí)與品德的人,是追求知行合一的知識(shí)分子,可以說是為人處事的榜樣二
在個(gè)人層次上或社會(huì)層次上,道德意識(shí)頗為淡薄的當(dāng)今社會(huì),就非常需要仁禮彬彬的君子。人們先要修己,然后與人相愛。修己則包含涵養(yǎng)內(nèi)在具有的德性,推己之心以忖度別人之心,培養(yǎng)道德心性的實(shí)踐意志。行善的道德實(shí)踐也由修己的工夫出發(fā),對(duì)他人關(guān)懷、著想、體貼,之后能以物質(zhì)上與精神上的支持來表現(xiàn)道德情感。再者從社會(huì)層次看,各級(jí)學(xué)校必需普及行善的教育課程,政府機(jī)構(gòu)則一定要施行具體的福利政策。
我們離孔子所處的時(shí)代已過兩千五百多年。現(xiàn)代社會(huì)的政治制度與經(jīng)濟(jì)體系改變了很多,同時(shí)倫理規(guī)范隨之而變。不過人們的道德價(jià)值的向往以及社會(huì)建設(shè)的目標(biāo)還是以相敬相愛、和諧和合為坐標(biāo)二所以孑L子所講的君子依然受人注目,也許會(huì)為當(dāng)今所面臨的現(xiàn)實(shí)問題提供一些啟迪。